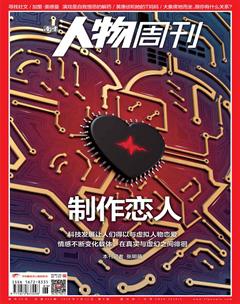记者眼
何处是终南
实习记者 王双兴
在终南山游荡的最后一天,我在紫阁峰遇到一对年轻情侣。从农民手里租下的破旧泥屋随时漏风漏雨漏尘土,于是他们在房子里支起了帐篷。砍柴煮饭,是每天最主要的活动。
闲聊的几个小时里,他们有一半时间在争吵,全然不顾我这个局外人。争吵的主题有两个:煮茶叶蛋前是否应该清洗鸡蛋,以及鸡蛋煮熟后是否应该敲碎入味。
男生是80后,女生是90后,因为遭遇家庭和事业变故而进山静心,偶遇后走到一起。在山上,摆脱了各自的社会属性后,两个人近乎24小时四目相对,细枝末节常常被无限放大,最终变成矛盾和争执。

当然,住山的麻烦不止于此。
冬季气温低,和衣而眠,盖两床被子,依然有被冻醒的可能;昆虫、老鼠、蛇轮番造访,“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野猪;农家厕的粪便要定期清理,然后和草木灰搅拌到一起倒进菜地……原始,让人拥有对生活的安全感和把控感,但远离忙碌,享受闲云野鹤的生活,就要承受经济上入不敷出的困窘;远离雾霾,享受山居秋暝的风景,就要承受饮食、交通等诸多不便。
柴米油盐之外,还要对抗大把的空闲时间。顾城说,中国人只创造了两个理想,一个是山中的桃花源,一个是墙里的大观园。当人们被大潮裹挟进大观园之后,便开始不自觉地寻找或打造另一个理想:桃花源。但终于身处其中后会发觉,习惯了效率和充实,很难消受隐居的悠闲和无目的;厌倦了追名逐利,却并未真正摆脱心里的欲求;到山中逃离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但新的烦闷继续萌生……山居生活的新鲜感退却,而精神层面则无所归依,于是有人选择宗教,有人继续困顿。
以上种种“残酷现实”,赶走了许多“隐居客”。终南山迎来送往,成了某种时代坐标。
山上的一个采访对象说,他常常想起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讲一只鼹鼠决定搬家去一个永远不会做噩梦的地方。于是它不停地搬家,地球被它挖得坑坑洼洼的,但一个能不做噩梦的地方也没找到。
和大理、拉萨一样,终南山也被定义成一个标签、一种表达,受惠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给予,它满足所有田园牧歌的想象和诗意栖居的奢望,在都市的幻想里,它意味着自由、野性、与世无争、与众不同,可以制造足够虚妄的优越感,修图发到社交媒体上,很快就会让身体被掏空的人们心驰神往:“看呐,这才是生活!”
世人热衷从众,商业嗅觉灵敏,都让终南山在特殊的时代里失去了最初的宁静。修行人原本是这片山峰最早的主人,他们按自己的节奏长久生活在山中,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漫不经心又无比虔诚,但如今常常被后来者搅扰,驴友、商人、访道者、开发商,层出不穷,而“天下修道,终南为冠”越来越少被提及。
我清楚自己是个不尽成熟的年轻人,去终南山伊始,采访更像是自我求解。无意探索古今隐士的精神蜕变,但总试图考量人生何处是终南。不过,对我来说,这个题目依然太严肃也太大了。
有修行人说,佛教里讲“不破本参不住山”,我逢人便问何谓破本参,回应相仿:心下清静。这听起来像极了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问佛故事,但事实上,究竟如何寻得清静,从来没有一个可以让人醍醐灌顶的明确答案。
去大峪的那天恰逢信号塔坏了,我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上采访,野鸟就在耳边叽喳,风过起松涛,难免让人想起古画。但不得不承认,因为手机没信号,我整個人都有些心不在焉。次日下山,收到许多微信消息和新闻弹窗,矫情地想起一句古诗: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但仔细想想,互联网上被我错过的风谲云诡,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那几天,我在终南山也遇到一些同龄人,穿黑T恤的小杨说起过一个比喻:人来到世界上,就像一个人住进旅馆,只住一个晚上,有的人把房间当成自己的,重新装潢、摆弄家具,折腾一个晚上都没有好好休息;但他选择不折腾、好好睡觉,好好享受这个晚上。于是,他在“终南山旅馆”住了四年。
那是个天真的男孩子,有点幼稚,爱纸上谈兵,但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