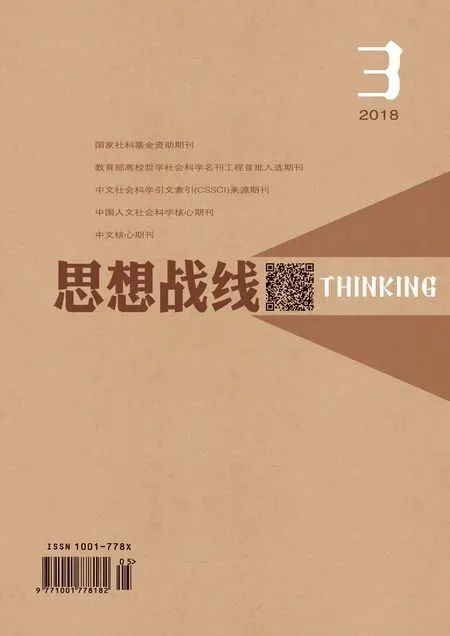浪漫主义的反讽概念:实质、类型和限度
李金辉
一
浪漫主义的反讽是一种对有限的否定,这种否定并不导致对无限和绝对的概念性把握和认识。“反讽的否定作用展示了无限性”,但“不涉入绝对的空间,只处于绝对的渴念之中。”*[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聂 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反讽作为否定性的力量使世界浪漫化,使对象成为无限和绝对精神的象征和暗示,从而使有限的经验“某物”具有无限的美学意义。反讽打开了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意义无限生成的空间,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美学空间。通过反讽,有限的存在者具有了无限的意义,有限的存在者通过毁灭自身使无限得到“展示”和显现。但是这种反讽是有限度的,它永远不能获得无限,无限永远不对有限完全展露自身。因此,有限只能通过“此在”的无穷筹划,保持对无限的永恒渴念。简言之,反讽是一个有限否定自身,进而趋于无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被浪漫化,人自身作为特殊的存在者也被浪漫化。世界和人仿佛都具有了无限的意义和价值。不过,反讽获得这种意义和价值是以人和世界的自我毁灭为代价的。无限价值和意义的获得,是以有限自身存在的否定为代价的。有限对无限的渴望是一个过程,这个否定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决定了有限会激发浪漫的时间和空间。反讽的存在是一个运动的、过程的、历史的和时间的存在,是一种永恒的矛盾、分裂和生成。由于有限的经验存在物既作为有限的存在又作为无限的暗示和象征,因此,它一直处于时间性的不断流动之中。它的存在总是向外“绽出”并开启时间性视域,但总是填不满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被浪漫化的某物和存在者是“活的”和“有意向的”,它总是指向存在和无限,总是具有否定自身的意向性,因而使自身处于无限的流动之中。因此,被浪漫化的世界和人是处于流动之中的存在,它们永远在运动,不停息地自我否定和超越。它们总是具有自我否定的意志和力量,趋向无限和绝对,但无限和绝对永远不会降临。浪漫主义的反讽永远通过对自己的否定而保持着对无限和绝对的渴念。通过这种对无限和绝对的“念兹”,仿佛无限和绝对就“在兹”了一样。不过,这仅仅是浪漫主义者的自欺欺人而已,无限和绝对作为存在本身和“物自体”是不能被存在者捕获的,它始终是暗的和黑的。它不能通过主体性的否定、牺牲甚至献祭而被照亮。浪漫主义的主体的力量是通过牺牲和奉献自己的存在而获得的,它的力量并不是自己存在的力量,而是靠自己的虚无化而获得的由无限和存在施舍的“神力”。在这种自我的虚无化和对无限力量的沉醉中,浪漫主义的主体感到与无限融合在一起,仿佛自己瞬间成为了上帝。但这只是“仿佛”而已,主体只是“借来”了无限的力量和意志,它自己没有任何存在和意志力量。浪漫主义的主体只具有想象和象征的力量,它自己没有任何存在的现实力量。它是无力的、自否定的、没有存在感的“虚无的存在”或“存在的虚无”。他对自己的存在始终保持“不知”的反讽态度,而且恰恰这种“不知”才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知”。浪漫主义的反讽,就是要保持这种自否定的、虚无化的“不知”过程,在这种“不知”过程中,上帝和绝对才能赐予反讽主体力量和自我存在的意识。总之,浪漫主义的主体只是一个没有存在的“空无”,它需要无限和绝对赐予其存在和意义。对无限和绝对能否降临,他能否被赐予意义,以何种方式被赐予力量,浪漫主义的主体并无信心。他只能保持对无限和绝对的永恒谦逊和卑躬屈膝的姿态,以期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认知。浪漫主义的逻辑是只有先消灭自己才能成全自己,只有保持无知才可能有真知,只有对自己无情才能获得自己的真情,只有自己无力才能获得神力。显然,人必须对自己无知、无情和无意,才能获得对自己存在的真知、真情和真意。这明显是一种反讽的和悖谬的存在逻辑。
二
表面看来,浪漫主义的逻辑似乎是一种巫术的和神话的逻辑,是一种“灵知”的逻辑,是有限通过毁灭自身、奉献自身、牺牲自身,借助无限和绝对的力量重新占有自身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浪漫主义者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里的重点不在于“仁”和“义”而在于“杀”和“舍”,在于对自身有限性的无穷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对无限的肯定。“杀身”本身就意味着或象征着“成仁”,因而就有了崇高的意义和道德美学的意味。而“舍生”同样意味着或象征着“取义”,意味着对自己的“救赎”。由此,“此身”和“此生”都不重要,因为它们都是有限的、要被否定的,而“仁”和“义”则是无限的、要被肯定的。这里预设了一种应然的价值判断和道义逻辑,即无限高于有限,来世高于现世,神高于人。浪漫主义似乎蕴含着一种神圣的目的论逻辑。不过,这不是浪漫主义的本意,浪漫主义不强调目的,也不认为无限和绝对一定会达到。它只是强调趋向无限的过程并保持这种过程。相比于结果和目的,过程和手段更重要。因为,过程就蕴含着结果,手段就包含着目的。浪漫主义就是要保持无限的自我否定过程,这本身就是人的自我完善。一旦有限在精神上达到无限和绝对,浪漫主义也就自身毁灭了。因此,浪漫主义的要义就是要保持反讽,让反讽作为反讽而存在。反讽不是为了什么外在于反讽的目的,反讽就是反讽本身。这也是早期浪漫主义反讽和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有所区别的地方。在后者看来,反讽只是一个历史阶段或思维阶段,它是无限和绝对实现自身的手段和途径。反讽总有一个结局,这等于取消了反讽的独立性。反讽这种无限的否定性过程被同一性收编了,历史的悲剧结束了,神正论的历史开始了。从此,再也没有历史、没有冲突、没有时间性、没有生成,神圣的天国永恒如斯,一成不变。一切差异、矛盾和冲突都完成了,历史剧情结束了,人类历史完成了。自然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和神的历史凝结为“一”。这种“一”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共产主义的王国,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普鲁士王国。在这种王国里,“一切是一,一是一切”。这就是人类自由的理性王国,理性之光照亮了一切领域,通体透明,一览无余。人类精神和理性终于完成了圆梦之旅,达到了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和意识自身的透明性。这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托马斯·莫尔所说的“太阳城”。理性的阳光普照,万物和谐。人类重回“伊甸园”。
总之,浪漫主义的反讽是一个悖谬性的、矛盾性的概念。它在自我消解中自我确认,而这种自我确认是蕴含在自我消解的形式中的,是以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肯定。反之亦然。在反讽中,有限和无限作为存在都被虚无化、时间化和存在化了,都从属于反讽,都处在反讽自身所包含的矛盾性引起的无穷运动之中。但这里的存在,无论是有限的存在还是无限的存在,都是“反思的存在”和认识的存在,而不是“超反思的存在”和绝对的、本体的存在。“由于存在只能在时间之中和借助于时间来表现,所以,索尔格可以说,永恒本身也陷入了暂时性之中,因为永恒毕竟处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综合之中。然而,恰恰由于这种暂时性,永恒从反面成为否定自身的暂时的东西,这种否定借助了暂时性在时间长河中的否定作用。人们有这样的体验,即有限事物的无限消逝可以清楚地代表有限事物内部主宰着的永恒,反讽的观点就是从这种体验中产生的。”*[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聂 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1页。这段弗兰克对索尔格的解读,极其精彩地说明了反讽的观点。反讽来源于绝对、超反思存在的不可表现性,一旦人试图用有限来表现无限和绝对,就会使无限的存在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永恒的存在就成为暂时性的、时间中的存在。而有限的存在由于处在无限的运动之中,却成了永恒的存在。这种试图表达绝对存在但失败的体验造成了反讽的观念。绝对存在的“说不可说”“表达不可表达”就是反讽的内在辩证结构。为什么会有反讽,就因为人们试图用“现象”去把握“物自体”,用“暂时性”去把握“永恒性”,用“相对”去把握“绝对”,用“有限”去把握“无限”。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就是反讽的自身的无穷否定性,这种否定性恰恰是对反讽自身合法性的肯定。在康德的三大理性批判中,《判断力批判》发挥的正是这种反讽功能,康德美学的批判表现了浪漫主义的反讽功能和本质。在康德的体系中,知性和理性都有合法性的领地,唯独情感和感性没有,因此康德《判断力批判》为此做出了努力。美学就是要为感性和情感确定自己的领域,判断力批判就是要通过在知性和感性、现象和“物自体”、自由和必然以及有限和无限之间进行调节,从而确定自己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浪漫主义美学和反讽的领域。这个领域中,知性和理性、现象和“物自体”、自由和必然的矛盾促成了反讽。在反讽中,矛盾双方都以否定的方式悖谬地显示自身。因此,不能以肯定的方式给反讽下个定义,反讽本身是个运动、是个过程。它不断地在否定,包括对自身的否定,必须以反讽的态度来对待反讽。反讽是时间化、存在化同时也是虚无化,必须用变化的观点来看待反讽,让反讽“反讽化”。
反讽不仅仅对艺术和美学有用,更对哲学和伦理学有用。这反映在对自我存在的理解上,自我的存在可以分为绝对的、超反思的存在和相对的、依赖于反思的存在。自我的绝对存在不能由笛卡尔的“我思”来认识,它不同于“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在”。自我的绝对存在只能信仰不能论证。自我的绝对存在是反思的本体论基础,反思不能认识它。“反思只有经过自己的失败经验,才能对存在和统一赋予它本身的东西获得一种间接的体验。这里指的是由反思在自己身上所获得的一种自我消亡的经验。”*[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聂 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2页。这是一种反讽的经验。即当“我思”不思之时,作为绝对的本体的“存在的我在”开始登场了。当我思进行时,作为意识,我就被剥夺了存在的肉身。认识论的“我思”是存在论的“我在”的毁灭。帕斯卡尔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存在对我思的嘲笑和讽刺。它反映了人自我存在的分裂,我思的我在与我的绝对存在的矛盾,这揭示了人自身存在的反讽结构。由此,艺术的反讽“也会使哲学的反思及其代理者自我意识那种自恋的全能幻相受到屈辱”。*[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聂 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4页。笛卡尔的反思自恋受到浪漫主义反讽的侮辱。启蒙主义的意识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思维和存在的内部矛盾,存在论的自我始终是“我思之光”无法照亮的“黑”,意识遇到了无意识存在的界限。意识不仅表现为对对象的胜利,还表现为对自身存在认识的失败,表现为对自身存在的无意识和失败体验。意识向外攻城略地,无往不胜、无坚不摧;意识向内则无能为力,保持对自身的永恒渴望。“我是谁?”,始终是自我意识无法驱除的自身阴影。它时刻提醒人类“认识你自己”,始终告诫人类“不知道自己”的绝对存在这一“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
三
通过浪漫主义反讽,人和世界都被浪漫化了。处于有限和无限无穷的矛盾中,人和世界都被抛在无尽的运动和时间的长河中。这是一个非存在和异化的世界,但人始终保持着对存在的渴念和“回家”的热情。不过,显然这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和西西弗斯式的热情。因为,存在也处在被抛的状态中。因此,这种浪漫主义的渴念和热情也是一种反讽的渴念和热情,家在哪?存在在哪?没有人告诉我。我们能回到哪里呢?所以,对浪漫主义的反讽不要太认真,要持一种轻松和戏谑的态度。
之所以对反讽不要太认真,是因为“反讽不是语义内容方面的东西,而是一种语言处理方式;它是一种文学风格和写作方式,似说非说,似是而非”。*[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聂 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3页。反讽着重表达的是“言外之意”和“话外之音”,它用字面的意义表达引申之意。反讽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又毁灭了表达对象,从而指出一切语义之外真正所指的东西‘无限’”。*[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聂 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4页。无限作为“物自体”是不能用概念确定和表达出来的,哲学反思遭遇到了界限。因此,需要艺术和审美的表达方式即反讽,作为哲学的补充。
浪漫主义的艺术和文学的反讽,关注的是“奇异”的幻觉而不是哲学的知识论“惊诧”,这种“奇异”的幻觉是由文学语言的反讽风格表现的。由于反讽具有由有限和无限的张力构成的双重意向结构,并且在二者之间不断变换,这就使理智疲于奔命地陷入迷茫之中,因而产生奇异的幻觉。这种奇异的“全部效果都产生于反差(并始终是矛盾的)快速变换,致使镇定的理智也仓促起来,最终虚弱无力地屈从于幻想,但又不能把握这种幻想的规律。”*[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聂 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6页。文学的反讽使哲学的理智主体产生了迷幻的感觉,从历史的旁观者变成了历史的剧中人。使观众入戏了,成了剧中的人物的化身。这就是反讽自身的力量,它使人身不由己地沉醉在反讽造成的美学情境中,身临其境,欲罢不能。他抛弃了自己的理智和反思力量,进入到反讽的无限运动中去,随波逐流。浪漫主义者进入反讽造成的浪漫化世界,对自己的存在浑然不觉。反讽借助无限的神力使人束手就擒,俯首称臣。文学家和戏剧创作者用这种反讽的表达风格,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浪漫化的美学世界,它们仿佛具有了无限的力量,召唤我们进入诗歌、文学和戏剧世界,使我们浪漫化、梦幻化。因此,早期浪漫主义者仿佛是巫师一样呼风唤雨和使用迷幻的法术,使人沉迷其中。弗兰克认为,很容易从奇异效果的说明中,看出反讽概念的基本特征:“两种完全相反的感受很快联系于同一个对象,致使判断力陷入迷茫,最终自愿听从反差影像的支配。这是对表义自我消除法的出色描述。使信息内容更赋予表现力,则是由一个新的信息取而代之并使之成为相对的东西。”*[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聂 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5页。浪漫派的反讽,强调的是对无限的审美表现力,而不是有限之物的确定认识论含义。同一个对象具有两种对立的感受,即感性和理性、审美愉悦和道德崇高,这造成了关于同一对象的反差影像,这种反差的流动造成了认识论自我的消解和自我分裂。显然,浪漫主义反讽是反对认识论的。这种倾向遭到了美国哲学家安·兰德的批判。
四
早期浪漫主义的反讽和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情感和意志,属于主观主义美学的领域。艺术和反讽仅仅是主观情感和意志的表达,与客观世界无关。这在兰德看来是一种致命的缺陷,她主张一种客观主义美学,强调艺术和美学的精神认识论功能。在她看来,艺术和美学不是与人的生活无关的、神秘的与绝对合一的宗教迷狂,也不是存在主义的个人对自己意志能力的迷狂崇拜,它们是由理性和意识支配的,具有形而上学和价值论的基础。“艺术是现实根据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价值判断的选择性重塑。”*[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 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7页。如果说,早期浪漫主义是主观的、感伤的、抒情的和豪放的、唯意志论的,那么,兰德的浪漫主义则是客观的、理性和科学的。前者导致放弃人的理想和意识,沉入潜意识的迷醉之中,是非理性的神秘情感和神秘意志。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浪漫主义。豪放的、唯意志论的浪漫主义夸大了人的意志能力,忽视了人的知性能力,是一种主观神秘主义。而兰德的浪漫主义反对自然主义,主张浪漫主义是人的意志的反映。“浪漫主义是基于人具有意志力的这条原则的艺术类别。”*[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 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07页。这种意志能力是一种理性能力,而不是非理性的能力。19世纪的豪放的浪漫主义恰恰将意志力等同于非理性能力,从而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潭。“理性能力等同于意志力,在19世纪的时候尚未被提出,各种关于自由意志的理论都是非理性的,于是又增加了意志和神秘主义的关联。”*[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 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所以,兰德的浪漫主义是意志主义的,更是理性主义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在兰德看来,19世纪的浪漫主义或者是情感主义的或者是神秘的、非理性的意志主义,都是与现实生活无关的“逃避的”浪漫主义,是一种反讽的、个人的、美学的、后现代的浪漫主义。由于他们都跟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和个人意志力无关,无法对现实进行选择性重塑,因而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是一种对现实和历史无力的逃避。正如兰德批评所说:
如今的浪漫主义一直都在逃避,不是在历史中逃避,而是在超自然中逃避——公然抛弃了现实和我们的生活世界。他们所描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戏剧性的、不同寻常的一切——根据他们的创作理念——都不是存在的;不要太认真,我们只是写点白日梦而已。*[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 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
这种浪漫主义对于人的现实生活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缺乏足够的意志力、行动力和改变现实的勇气。这种浪漫主义于人的生存无益。兰德主张的浪漫主义是积极的,在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基础上,人的意志力量对现实进行重新塑造的理性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认为人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价值观,达到自己的目标,把握自己的存在”。*[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 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38页。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以人为本的浪漫主义,它强调人对自己生活的价值选择和理性重塑。它体现了人的自由和本质,体现了人的意志和力量,展现了人自身的价值。这种浪漫主义的敌人是各种形式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现代哲学和利他主义的副产品。“作为现代哲学的副产品,最基本的假设就是反人类、反思维、反生活;作为利他主义的副产品,自然主义是对道德判断的疯狂逃避——一种有关怜悯、忍耐和旷日持久的哭号。”*[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 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这种自然主义不管是以神学的形式还是以实证主义的形式,抑或以集体主义的方式,在兰德看来,都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削弱人的意志和自由存在,使人不负责任,把自己和世界的命运交给各种异己的力量。自然主义者,“通过拒绝理性,毫不掩饰地听命于自己脱缰的情感(或者不如说是幻觉),那些存在主义者、禅宗的佛门弟子、非客观的艺术家,均没有达到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幸福的人生观,而恰恰陷入了天旋地转、天昏地暗恐怖人生观”。*[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 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44页。
兰德反对早期浪漫主义美学的反讽,认为它们是纯粹情感主义的、不受意志控制的、神秘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它们都反对理性,否认人的意志对现实的理性重塑和价值选择,从而陷入道德虚无主义,是一种自我消解和毁灭的人生观。这种浪漫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一种虚伪,是一种“不可告人的浪漫主义”。在兰德看来,早期浪漫主义者不敢公开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是“道德上的懦夫”。*[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 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62页。他们“逃避选择、逃避价值观,逃避道德责任”。*[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 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61页。他们通过反讽“说服人们放弃价值观,放弃自尊”。*[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 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58页。这种浪漫主义是自然主义的、道德虚无的和价值真空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的结局是拒斥一切价值观,“不要卷入道德问题,这里的潜意识含义是:不要对任何东西做价值判断”。*[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 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75页。道德虚无主义导致审美情感的泛滥,导致审美反讽的盛行。人人都没有严肃的人生观和道德意识,都学会了嘲笑一切也嘲笑自己。人人开始过一种犬儒主义的、轻松的、随波逐流的生活。崇高和平庸、伟大和渺小都被浪漫主义的反讽磨平了,生活失去了意义,一切都无足轻重。形而上学的价值被消解了,只剩下了“后形而上学的希望”和后现代主义的反讽。而在兰德看来,这种浪漫主义的反讽,这种“嘲笑着的欢愉”*[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 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76页。是不可能实现的。任何反讽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以一定的形而上学的选择为基础。反讽一定包含着意志和自由的选择。浪漫主义反讽的轻松感中,总是潜藏着道德和形而上学的重量,毕竟,浪漫主义的人生没有了形而上学的重量,人就会落入“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后现代漂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