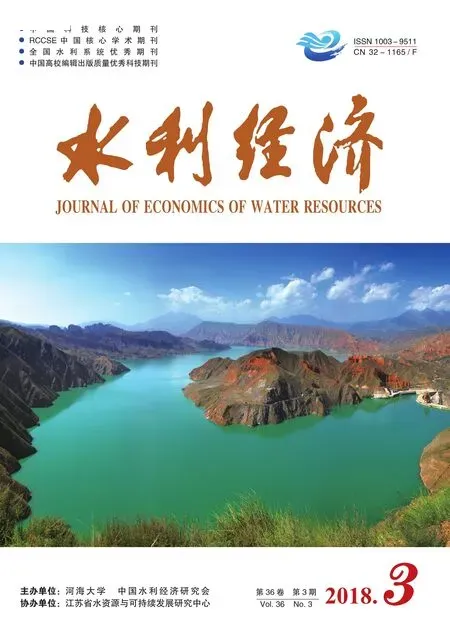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及其标准研究综述
刘 洋,毕 军
(1.济南大学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2.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流域是自然过程和人文活动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与人类生产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流域是以自然水系分界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系统,河流作为其中的连续体,承接上下游之间的物质流动、能量交换,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同时,流域又被不同的行政区分割,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技术和历史背景等方面的不同,流域内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增加了流域系统的复杂性。流域上中下游是利益共同体,上游过度开垦土地、破坏植被、过量取水、排放废物等,不仅影响当地生态环境,还会使中下游的河道淤积抬高、水量水质下降,造成下游用水危机;如果上游为保护流域水环境,实行更严的环保措施和标准,虽然能保障下游用水,但却使本地丧失了发展机会,影响区域经济收入和当地居民生活质量。流域上下游之间水资源供给和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水环境纠纷不断出现。
生态补偿作为典型的经济激励手段可有效地促进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协调发展。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相比,生态补偿更具灵活性和成本有效性;通过政府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手段向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付费,从而激励供给者主动保护环境,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供给及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生态补偿研究涉及内涵、主体、标准、方式及效应评价等多方面[1-5],而补偿标准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影响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及效果[3]。国内外学者针对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尤其是测算方法,诸如市场定价法[6-8]、成本费用法[9-11]、支付意法[12-14]等。然而,目前生态补偿标准尚未形成完备、成熟的研究体系,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待完善。笔者在流域生态补偿理论探讨的基础上,重点针对补偿标准的确定方法进行归类总结,并提出存在的问题和研究展望,以期为流域生态补偿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
1 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概述
1.1 流域生态补偿的基本概念
尽管生态补偿已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点,但目前国内外对生态补偿的界定并不统一。在国外,生态补偿一般被称为“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或“为环境服务付费”(Pay for Ecosystem/Environment Service,PES),是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给予的付费补偿。Wunder[15]认为生态补偿是指至少一个买者付费给至少一个卖者之间的自愿、有条件的交易,从而维持可持续的环境管理实践,促进生态系统服务或环境服务的增加。目前比较有影响的概念分别是RUPES项目和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对生态补偿的界定,两者均认为生态补偿不同于传统的命令控制手段,是在一定条件下,双方自愿的用地行为或交易,并对界定范围内生态环境服务进行付费[16]。
国内一般将生态补偿理解为一种资源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17],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补偿包括对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奖励和向生态环境破坏受害者的赔偿,也包括对造成环境污染者的收费;狭义概念则为生态保护补偿,是对人类活动产生的生态环境正外部性所给予的补偿。由于概念的不确定,20世纪90年代前期,流域生态补偿普遍被认为是流域水污染赔偿,随着源头控制的水环境管理需求,流域生态补偿逐步转向对上游水环境保护行为所产生的生态效益的补贴。
1.2 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
1.2.1 公共物品
萨缪尔森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定义为公共物品[18]。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得物品在使用过程中难以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从而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发生,造成供给不足;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使得物品的消费不会引起个体成本的增加,从而导致“公地悲剧”,造成过度使用。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为避免“搭便车”现象和“公地悲剧”,需要从公共服务的角度,通过付费补偿或政府管制的方式进行管理,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的合理利用。流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和改善流域生态环境的行为,其产生的良好水环境可视为一种公共物品,需要下游受益者对上游保护者进行经济补偿,从而促进上游保护者生态建设的积极性,达到优质水环境的持续供给。
1.2.2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是指一方的行为活动对活动之外的第三方产生的非市场化影响,从而造成外加效益或成本产生。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分别是使他人受益而无需付费,或使他人受损而不付代价。如果外部性问题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将会降低环保行为积极性或加剧环境破坏行为,造成环境质量持续恶化。庇古税和科斯定理被认为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庇古税主张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如税收与补贴等)进行干预,消除外部不经济性[19]。科斯定理则认为在产权明晰和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外部性可以通过市场解决[20]。流域环境资源利用中的外部性表现为开发利用造成的外部成本和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外部效益。对于水量问题,在中小流域尺度上可以通过明晰产权的方式进行市场交易来解决外部性;对于水质问题,在企业层面上可以通过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等方式解决,但在区域层面上则难以明确权属,需要通过付费补偿来调整上下游的边际成本或边际效益,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提高流域整体社会效益,进而促进流域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1.2.3 生态资本论
生态资本论认为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环境是有限、稀缺的,具有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其中食物、生产资料、生活用水等直接消耗的资源具有使用价值;而生态环境自净能力、水土保护等是生态系统功能的内在价值,对人类来说是非使用的间接价值。Costanza等[21-22]对全球生态系统进行的价值评价、联合国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3]、美国研究机构发起的自然资本项目[24]以及欧洲环境署主导的“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计划等项目均表明环境和资源的价值论意义。生态资本论为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社会需求、效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等,流域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服务具有价值属性,是重要的生态资本。通过实施流域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下游发达地区通过支付补偿费用以获取上游地区提供的生态服务,从而体现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1.2.4 可持续发展论
可持续发展是指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应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不能超越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永续利用,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间的协调性发展。流域上下游是利益共同体,上游的经济活动会对下游的水环境造成显著影响;如果为了保护流域整体环境,上游被迫放弃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这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原则。因此,通过流域间的生态补偿政策,下游受益方付费给上游保护者,促进区域发展的公平性。此外,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流域资源环境开发过程中,应维持生态系统的长久效益,避免短期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完善流域资源环境的长期发展战略,从而保障流域生态系统安全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方法
从我国目前的环境经济政策实施来看,排污收费、环境处罚等流域水污染赔偿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较多,并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法规,但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研究与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在补偿标准、补偿主客体等方面尤为不足。2016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中指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的标准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项措施的成效。在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时,其理论计算方法起到关键作用。为此,笔者重点围绕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综述。
2.1 基于市场交易理论的补偿标准研究方法
基于市场交易理论的补偿标准研究方法是指根据供求关系的市场原理,将流域上游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商品化,下游通过支付货币购买该商品,达成一定的交易价格,即补偿标准。该方法多用于流域水资源定价和水权交易研究中。理论上讲,该补偿标准应按市场交易的均衡价格,即供求曲线的交点;但现实中,与传统的市场不同,生态系统服务难以按照商品价值定价,一般通过谈判协商或拍卖的方式确定补偿标准。例如,Guabas河流域下游用水者与上游土地利用者通过协商确定将额外的水费作为补偿标准,从而在旱季获得了相应的供水量[6]。法国Vittel公司与周围农户签订协议,给其提供资金来促使他们改变用地方式或放弃生产,从而达到维持水质的目的[7]。印度尼西亚的研究者通过模拟拍卖的方式,计算不同拍卖试点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曲线来确定补偿标准,以其达到解决咖啡豆种植园的水土流失问题[8]。周大杰等[25]应用影子工程法、市场价值法等方法确定官厅水库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江中文在比较了机会成本法、费用分析法和水资源价值法之后,认为水资源价值法可以用作计算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26]。刘玉龙等[27]建立了改进的总成本计算模型,并引入水量分摊系数、水质修正系数和效益修正系数以计算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量。
通过市场理论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可以满足双方的利益条件,其结果适用程度较高,因此很多研究都进行了相关探索,包括水资源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但是由于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复杂性,该方法仅可用于产权清晰的服务类型,适用范围较小。同时,由于政府或相关组织机构的干预,限制了市场的公平、自由交易。此外,由于生态、社会、经济在内的不确定因素较多,补偿标准计算的准确性有待验证。
2.2 基于微观经济学模型的补偿标准研究方法
国外一些学者以微观经济学原理为基础,根据理论上的供给曲线模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供者或享受者的微观决策过程与生态服务的变化关系,以此确定生态补偿标准。该方法具有严谨的逻辑推理过程,可以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生态补偿研究。例如,Antle和Valdivia 开发了最小数据方法(Minimum-data Approach, MD),利用概率密度函数和其分布函数将个体决策者的经济生产模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通过生态服务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来模拟新增生态服务的供给,将支付水平与新增生态服务量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耦合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人文决策过程和自然变化过程。Antle等[28]将最小数据法应用在美国蒙大拿州的粮食生产区,以此计算农户通过改变用地、提高碳封存而获得的补偿费。同时,研究者也指出该方法虽然为政策者提供了充分且精确的分析结果,但是需要机会成本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且假设个体决策者不考虑风险规避。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的状态难以实现。为此,Smart[29]尝试将风险规避等因素加到MD模型中,并应用到肯尼亚土壤碳封存合约中。结果表明,由于生产存在一定的风险,影响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机制的意愿,进而影响了补偿标准的确定。同样,最小数据法也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中有所应用。刘玉卿等[30]用最小数据法和SWAT水文模型分析了黑河流域上游机会成本的空间异质性以及补偿价格对上游禁牧比例及水源涵养服务的影响。赵雪雁等[31]采用最小数据方法模拟了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草地水源涵养服务供给曲线,根据不同的生态恢复目标,确定补偿标准,估算新增水源涵养量。
通过微观经济学模型方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其所需数据相对少,模拟也足够精确,可以作为生态补偿标准方法研究的理论依据,为决策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但由于该方法理论体系尚未完善,且一些假设条件也未被充分认可,因此应用于生态补偿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2.3 基于意愿调查的补偿标准研究方法
该方法通过询问下游补偿者或上游受偿者对保护环境的支付或受偿意愿,以确定补偿标准。调查者需要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包括对调查问卷的设计、被调查人群及影响区域范围的确定等,同时也需要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结果进行拟合、回归计算。Bienabe等[12]对哥斯达黎加流域居民和旅游者进行了意愿调查,并建立了计算补偿标准的多项式逻辑斯谛回归模型。Moran等[32]对苏格兰地区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采用AHP和CE法进行了统计分析。Loomis等[13]对美国Platte河流域5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总经济价值进行了讨论,并结合支付意愿法研究了支付费用与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Van等[33]在局地尺度上采用定性的访谈调查,结合定量的情景条件价值(Contingent valuation scenarios)分析,得出下游城市地区对上游水质改善的支付意愿,为当地环境管理政策提供参考。张翼飞等[34]系统梳理了生态服务及其价值评估、支付意愿与补偿标准之间的理论联系,指出充分考虑利益主体的意愿是科学制定补偿标准的必要环节,意愿价值评估法的应用将增强我国生态补偿标准的科学性。张志强等[35]以支付卡的方式对黑河流域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进行了调查,从而得到生态补偿的经济效益。
通过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的意愿调查,能够更直接地明确成本和期望等因素,理论上应该最接近边际外部成本的数值,故应用范围很广。但是该方法却存在很大风险,调查问卷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被调查者的认知情况等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结果的真实性,甚至会产生重大偏差。
2.4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定量模拟的补偿标准研究方法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有2种方式,一是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主观感知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量化;二是结合生物物理过程的定量研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物质量进行精确计算,再借助经济价值化方法将服务量进行货币化,为决策者提供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值。很多学者提出应该整合多学科方法用于评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便为决策者确定生态补偿资金提供参考。例如,Fisher等[5]认为在坦桑尼亚的生态补偿中应该模拟生态服务产品、过程变化,并懂得不同尺度上生态系统功能与人类福利之间的关系;Kumar[36]认为在诸如印度一样的发展中国家,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需明确并评价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状况和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驱动因素,并借助水文水质模型、社会经济评价模型等多种方法来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然而,如何评价生态系统服务变化过程,并将评价值与生态补偿标准进行衔接是现今面临的重要挑战。Daily等[37]指出需要创新或更新方法,用科学的手段明确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产生及变化机制,并在生物多样性和社会背景下,设计适当的经济、政策和管制体系,利用激励或制度法规等方式促进人们更好地认知生态系统,并加以保护。国际上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自然资本项目也带动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的不断发展,为生态系统服务精确量化及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我国的相关研究大多以用地类型和面积为度量单元,借助Costanza等[21]或谢高地等[38]的研究成果,调整不同用地类型的服务价值单价,从而得出研究区总体生态服务价值,并借助社会经济系数予以修正,得到生态补偿标准。例如,牛叔文等[39]对黄河上游玛曲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估算,结合牧民生活水平,确定了区域生态补偿标准。史晓燕等利用Costanza对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原理,界定了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补偿范围,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评价了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以此计算其补偿标准[40]。
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针对基于投入费用计算补偿标准的研究较多,应用生态系统服务定量评价的研究较少,而且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多是建立在现状评估的基础上的。国外研究者关注生态补偿与改善环境、消除贫困等之间的关系,并从生态效益和社会福利供给等角度确定用地管理者的生态补偿标准。国内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尚未深入,较少应用生态系统服务定量模拟方法,多是根据生态环境变化的成本费用法进行量化,而该方法没考虑环境变化对区域生态效益的影响,造成补偿标准计算不准确,不利于管理决策的实际应用。
3 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
3.1 流域不同类型的生态补偿标准测度
流域生态补偿一般是针对流域内特定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例如洪水消减、水量供给、水体净化、水土流失等。其中,对于水资源量这一有形的服务类型可以通过商品交易定价等方式获得其公允价值,以作为其补偿标准值;而对于水质保护这类无形的生态服务类型则较为复杂,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计量和定价。此外,不同类型生态补偿的作用效果具有显著差异的周期性。因此,对于水体净化、洪峰消减等无形的生态服务,需要通过评估方法获取其公允价值,并从时间和空间多维度分析服务的变化量,以评估促进补偿标准的核算。
3.2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多情景分析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可归结为2种方式:①从环境资源的角度,量化上游环保行为所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按取得的生态效益计算补偿标准;②从经济学成本的角度,量化上游环保行为所承担的经济损失,包括投入成本、机会成本等,并按损失的成本计算补偿标准。前一种方式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价方法不完善,使得补偿标准计算结果偏大,不能应用于实际管理;后一种方式则难以全面量化成本,使得计算结果偏小,影响补偿实施的持续性。因此,在分析流域水污染控制政策的基础上,建立不同情景的补偿方案,充分考虑各自的社会成本和效益,以得到基于特定管理目标的补偿标准,为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提供参考。
3.3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动态优化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行为产生影响,而行为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果又进一步对管理者的决策产生反馈作用,进而促进补偿标准的改变。然而,目前的补偿标准确定多是针对当前状况,没有充分考虑微观主体行为变化以及不同行为所带来的环境效益的改变,使生态补偿标准缺乏动态优化机制,进而影响补偿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因此,未来研究应结合个体行为分析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估,建立动态优化的补偿标准,以促进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永续性。
3.4 基于多学科理论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未来主要研究趋势之一。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化需要充分考虑地区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建立合理的评价指标及有效的量化方法。因此,在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交互作用下,研究符合区域实际情况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化方法,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准确制定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CAPLAN A J, SILVA E D. An efficient mechanism to control correlated externalities: redistributive transfer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regional and global pollution permit marke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5, 49(1): 68-82.
[2] KINZIG A P, PERRINGS C, CHAPIN F, et al. Paying for ecosystem services-promise and peril[J]. Science, 2011, 334(6056): 603-604.
[3] 赖力, 黄贤金, 刘伟良. 生态补偿理论、方法研究进展[J]. 生态学报, 2008, 28(6): 2870-2877.
[4] ENGEL S, PAGIOLA S, WUNDER S. Designing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 663-674.
[5] FISHER B, TURNER K, ZYLSTRA M. Ecosystem services and economic theory: integration for policy-relevant research[J].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08, 18(8): 2050-2067.
[6] 王燕,高吉喜,王金生,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述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337-339.
[7] PERROT M D. The vittel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 “perfect” PES case[J].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06, 9: 24.
[8] JACK B K, LEIMONA B, FERRARO P J. A revealed preference approach to estimating supply curv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use of auctions to set payments for soil erosion control in Indonesia[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9, 23(2): 359-367.
[9] WUNDER S, ALLBAN M. Decentralized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the cases of pimampiro and PROFAFOR in ecuador[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 685-698.
[10] KALACSKA M, SANCHEZ G A, RIVARD B, et al. Baseline assess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ayments from satellite imagery: a case study from Costa Rica and Mexico[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8, 88(2): 348-359.
[11] GIACOMO B, LESLIE L, BERNARDETE N, et al. Payments for watershed services support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nzani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2011, 20(3): 278-302.
[12] BIENABE E, HEARNE R. Public preferenc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scenic beauty within a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ayments[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06, 9(4): 335-348.
[13] LOOMIS J, KENT P, STRANGE L, et al. Measuring the total economic value of restor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 an impaired river basin: results from a contingent valuation survey[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0, 33(1): 103-117.
[14] 李晓光, 苗鸿, 郑华, 等. 生态补偿标准确定的主要方法及其应用[J]. 生态学报, 2009, 29(8): 4431-4440.
[15] WUNDER S.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the poor: concepts and preliminary evidence[J].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13(3): 279-297.
[16] PESKETT L, KATE S, JESSICA B.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for carbon financing in the forest sector: learning lessons for REDD+ from forest carbon projects in Ugand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1, 14(2): 216-229.
[17] 刘传玉, 张婕. 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的国内外比较[J]. 水利经济, 2014, 32(2): 61-64.
[18] 张真,戴星翼. 环境经济学教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9] 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 西方经济学[M].3版.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0] 沈小波. 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政策工具及前景[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6): 19-25.
[21] COSTANZA R, DARGE R, DEGROOT R,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 Nature, 1997, 387(6630): 253-260.
[22] COSTANZA R, DARGE R, SUTTON P, et 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 2014, 26(2): 152-158.
[23]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our human planet: summary for decision makers[M].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005.
[24] KAREIVA P, TALLIS H, RICKETTS T H, et al. Natural capit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pping ecosystem servic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5] 周大杰, 刘莉, 马军, 等. 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官厅水库流域为例[C]∥第六届环境与发展中国(国际)论坛, 北京:中国环境保护部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0.
[26]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生态补偿原理与应用[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7] 刘玉龙, 许凤冉, 张春玲, 等.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模型研究[J]. 中国水利, 2006(22): 35-38.
[28] ANTLE J M, VALDIVIA R O. Modelling the supply of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agriculture: a minimum-data approach[J].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6, 50(1): 1-15.
[29] SMART F C. Minimum-data analysis of ecosystem service supply with risk averse decision makers[D]. Bozeman: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2009.
[30] 刘玉卿, 徐中民, 南卓铜. 基于SWAT模型和最小数据法的黑河流域上游生态补偿研究[J]. 农业工程学报, 2012, 28(10): 124-130.
[31] 赵雪雁, 董霞. 最小数据方法在生态补偿中的应用: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10, 16(5): 748-754.
[32] MORAN D, MCVITTIE A, ALLCROFT D J, et al. Quantifying public preferences for agri-environmental policy in Scotland: a comparison of method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3(1): 42-53.
[33] VAN H G, JOHAN B, WILLIAM F V. The viability of local payments for watershed servi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atiguás, Nicaragua[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2, 74: 169-176.
[34] 张翼飞, 陈红敏, 李瑾. 应用意愿价值评估法科学制订生态补偿标准[J]. 生态经济, 2007(9): 28-31.
[35] 张志强, 徐中民, 程国栋, 等. 黑河流域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条件价值评估[J]. 生态学报, 2002, 22(6): 885-893.
[36] KUMAR P. Capacity constraints in operationalisation of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n India: evidence from land degradation[J]. 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 2011, 22(4): 432-443.
[37] DAILY G C, MATSON P A.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theory to implement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 105(28): 9455-9456.
[38] 谢高地, 甄霖, 鲁春霞, 等. 一个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J]. 自然资源学报, 2008, 23(5): 911-919.
[39] 牛叔文, 曾明明, 刘正广, 等. 黄河上游玛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和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设计[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6): 79-84.
[40] 刘青, 胡振鹏. 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7, 16(4): 532-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