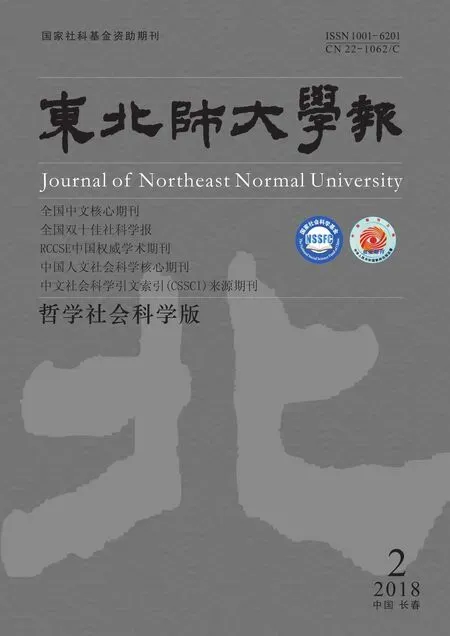社会责任与女性道德完善
——乔治·爱略特后期创作中的伦理思考
夏文静,吕美嘉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家乔治·爱略特以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深刻的哲学思辨能力等特点被评论家们所称道,但其文学创作的最本质特征当数在作品中对伦理道德问题的严肃探讨。事实上,爱略特作品中的哲学分析和科学理念也更多地服务于严肃的道德主题,她也因此被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大师和精神导师。文学评论家亨利·詹姆斯就曾表示,小说对爱略特而言,“是一个道德化的寓言,是一种努力示范喻人的哲学的最新发明。”[1]52
一、前后期创作中的伦理差异
文学评论界一般将爱略特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两个时期的创作不仅在内容上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其伦理意蕴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在凭借早期三部关于乡村生活的小说《亚当·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织工马南传》确立了自己在维多利亚文坛上的地位之后,爱略特的创作轨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将逝去的乡村文明不再是她创作的唯一着眼点。在日益步入工业时代的维多利亚社会中,人们的信仰动摇、道德沦丧,人们为了追逐物质利益而在精神方面付出的巨大代价成为爱略特关注的主要问题,她希望用手中的笔唤起人们心中一息尚存的良知。在促进人们从奉行利己主义到利他主义的转变中,爱略特也尤为强调了女性的作用。在爱略特后期的创作中,在时间的纵轴上,她将目光回溯到了15世纪90年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从而以古喻今;在横向的共时截面上,她也将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工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方面纳入其作品之中。在爱略特创作于后期的四部长篇小说中,《罗摩拉》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记录了处在新旧交替转折时期意大利社会中的动荡局面;《激进分子费利克斯·霍尔特》则是一部政治小说,关注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中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于政治权力的争夺;《米德尔马契》的内容涉及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被称为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史诗,也被看作是爱略特的扛鼎之作;《丹尼尔·德龙达》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对作者所处时代的英国社会的表现中包括了对英国社会中的犹太人生活的关注。
爱略特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不仅反映在作品的主题方面,也反映在作品的思想内涵中。麦克斯威尼在《乔治·爱略特的文学生活》(GeorgeEliot(MarianEvans):aliterarylife,1991)中曾指出,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爱略特也经历了创作生涯的中年危机。这种中年危机仿佛是她创作生涯中的一道分水岭,她感觉到创作早期的一些东西已经不复存在,那些充满了清新创作力的作品也无法再现。对于这种感觉,华兹华斯曾在诗中将其形容成:“一种力量已经逝去,无法恢复”;“一种深刻的痛苦”使早年的信仰和力量仿佛愚蠢的幻觉[2]106。而在分水岭的另一侧,用华兹华斯的话来说,哲学思想成为其主要的特征。詹姆斯也曾指出,在爱略特创作初期,“感知”(perception)和“思辨”(reflection)在她的天赋中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逐渐取代了前者。詹姆斯将其解释为刘易斯对科学和宇宙问题日益增长的兴趣影响了爱略特的思想发展。而我们无法否认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爱略特和刘易斯共同生活之后,她便与整个社会越来越彻底地隔绝,因此她对社会生活详尽而具体的了解宣告结束,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方面,她所能利用的始终只有她在生命的前30年所占有的资料,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她对于思辨日益增强的依赖。而这种转变在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相应地表现为,对抽象道德意识现象的思考取代了对具体道德活动现象的关注。因此,本文将在文学伦理学视域下聚焦爱略特后期创作中强调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女性的道德完善。
二、斯宾诺莎《伦理学》影响下的社会责任论
爱略特进行文学创作的后期也恰逢维多利亚社会从中期向后期转变的转型期。在这一时期,社会的繁荣富足在到达巅峰之后开始走向下坡路,社会与政治矛盾则呈上升趋势。并且,在保守的爱略特眼中,大部分的劳动群众是“自私的激进主义者和无理性地沉溺于感官享受中的人”[3]254。因此,在这一时期将注视的目光逐步转向社会生活领域的爱略特试图以笔下的道德训诫唤醒人们日益沉沦的道德意识。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在总体上仍值得被称作一个重视道德的时代,道德意识居于维多利亚主义的核心。但维多利亚时代崇尚成功,因此,当时社会中崇尚的道德标准多教导人自制、自律、自强、自助,凭借自我奋斗获得为人瞩目的成功。“维多利亚社会,各方面都从它强迫性的道德中获得了好处……这种道德意识着重个人的思想训练,也就产生这个时代的一种坚强的个人主义。”[4]277也就是说,当时社会中奉行的道德标准仍多以个人利益为着眼点,这与当时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所推崇的功利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
从外部原因分析,正是针对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为驳斥这种以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爱略特格外强调了自己以责任为核心的利他主义伦理道德观。在探讨促使人向善的三种力量时,爱略特曾这样说:“上帝,灵魂不休,及责任,……第一项令人无法想象,第二项令人难以置信,第三项的召唤是绝对的、不可违抗的。”[5]36爱略特在这里所强调的责任正是以对他人或社会应尽的义务为表现形式。
强调责任是爱略特小说中的伦理主线之一,在她前期的小说中,由于爱略特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传统的乡村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因此着重阐释了人在家庭中对亲人的责任;在后期的作品中,爱略特对责任的理解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她将人置于社会关系网中,既分析了公众生活对于个人生活的决定程度,也指出了人对他人和置身其中的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
为实现以文喻世的目的,爱略特后期的四部小说都将故事的背景设置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纷繁动荡期,其中《罗摩拉》的背景设置在15世纪90年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以处在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交接时期混乱中的意大利喻指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处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型期动荡中的英国;之后的《激进分子费利克斯·霍尔特》和《米德尔马契》以英国中部小镇为背景,以第一改良法颁布前后发生的政治动荡类比19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中要求改革国会选举法时即第二改良法颁布前夕不同阶级之间爆发的矛盾与冲突;爱略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丹尼尔·德龙达》则是他唯一一部以本人创作时的时代为背景的小说,爱略特针对英国社会中存在已久且已深入人心的反犹倾向,表达了自己具有前瞻性的对多民族多元化社会的认同。
在论及各种先进思潮对爱略特产生的影响时,我们便不能不提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当时科学的进步。斯宾诺莎认为,庞大的宇宙由无数组成部分共同构成,各组成部分既各自独立,遵循各自的轨迹存在于整体中,又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协调,在共同遵守的次序和规律下构成一个和谐整体。对作为宇宙间极其微小组成成分的人类来说,“只能去认识和理解这一永恒不变的次序,并且遵循这一永恒不变的规律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6]53在科学领域,19世纪的生物学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生物学中对生命有机体结构的研究也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有机社会说提供了基础。生物学中的有机论的核心内容包括:生物体是由相互协调的组成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发生变化,都会对整个生物体产生影响。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有机社会说则认为:“人类社会跟植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一个不断运动着的,不断生长、裂变、内部关系根据外部关系不断进行调整的生命体。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就像人体的不同器官一样,互相依赖,相互作用。”[7]60
作为斯宾诺莎《伦理学》的英译者和有机社会说的追随者,这些观念都在爱略特的伦理道德观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爱略特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这样的有机关系,即个人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与爱好,但不能摆脱社会的限制;社会提供给个人发展的空间和自由,个人也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爱略特在创作于后期的四部小说中,都设置了为了履行社会责任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和为了个人的享乐千方百计逃避社会责任的典型对比。如《罗摩拉》中坚持“一个佛罗伦萨的妇女,应该为佛罗伦萨而生活”[8]409的女主人公罗摩拉和为了金钱地位在各派政治纷争中不惜成为多方间谍的蒂托;《激进分子费利克斯·霍尔特》中,为了发扬英国政治自由的传统和为了最大限度谋得个人私利而分别卷入政治选举中的费利克斯和哈罗德等等。倘若比较爱略特笔下三个对社会责任持截然不同态度的典型形象,便可诠释爱略特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见解。
在《罗摩拉》《米德尔马契》和《丹尼尔·德龙达》三部小说中,爱略特分别塑造了蒂托、利德盖特和丹尼尔这样三个典型形象,这三者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头脑聪颖的年轻男子。蒂托曾从身为卓有成就学者的养父那里接受了教育,并与养父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探寻古代文化的碑刻和其他遗迹。他承诺作巴尔多的助手,将自己的见闻与他的经验相结合,形成一本伟大著作。利德盖特曾留学法国,希望能凭借他的留学所得,改善米德尔马契的医疗条件,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赏识。丹尼尔则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上层社会一个有身份、有教养的绅士,相较于前两者的踌躇满志,他曾因对自己身世的疑惑而对未来感到茫然。
爱略特笔下的三名年轻男子,尽管具有相似的良好开端,对于责任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在蒂托看来,生活的目的是取得最大限度的快乐。最初的理想对于他来说渐行渐远,社会利益不过成为他手中换取个人利益的砝码。利德盖特的理想抱负与现实情况的冲突在于,他没有意识到个人与他置身其中的社会的关系,也就更谈不上思考个人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主宰着他对未来生活所做决定的,仍然是他“无意识的利己心理”[8]330。丹尼尔的责任感,则无论巨细地覆盖了身边所有的人和事,更在得知了自己的犹太血统之后义不容辞地放弃了自己原有的高贵身份,立志为复兴犹太民族而奋斗终生,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更好地植根于民族的土壤中。”[9]3
如同相同的种子在不同的外界条件下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生长态势一样,同样的青春与才华在不同道德观的影响下为三者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对于背弃了责任的蒂托,妻子因为对他彻底的失望离他而去,为获取最大利益而成为多方间谍的蒂托最终在逃亡途中被前来复仇的养父杀死。人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宛如一张巨大的网,任何凭借自身微薄之力企图挣脱社会责任之网甚至破坏社会责任之网者必然在网中跌得头破血流。爱略特用这种命运惩罚的方式表现了她对背弃责任卑劣行径的鄙弃。对于怀有抱负但对责任认识不清的利德盖特而言,没有责任约束的抱负难免流于松懈,“‘无意识的利己主义’使得他纵然具有完美的智慧与专业品质,也不过是道德上的庸庸碌碌之辈。”[2]128他在米德尔马契一事无成,最终反而因为需要借钱偿还家庭债务而被卷入富商布尔斯特罗德的丑闻中,几乎身败名裂。忽视社会责任之网的人,社会责任之网会成为他的羁绊,使他成为陷落在网中的鸟儿无法展翅高飞。对于利德盖特,爱略特表现出来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遗憾。唯有丹尼尔,对责任的坚守使得他对未来不再迷茫,而是信心百倍地投入到神圣的民族复兴任务中去,开始他的复兴犹太民族之旅。唯有正视社会责任之人,责任方能成为他信念的支柱和力量的来源,使他将自身与社会融为一体,成为社会之网的一个结点、一股细绳,将自身的微薄之力投入到社会进步的洪流中。爱略特正是在这样一个正视社会责任的人物身上,真正寄托了对未来的期望。
三、孔德实证主义关照下女性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爱略特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孔德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对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孔德的实证主义反映在道德领域主要是对人本宗教的信仰。孔德认为,人本宗教逐步取代了基督教,是历史前进以及科学和哲学进步的必然结果。在信仰人本宗教的实证主义阶段到来前,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神学阶段(theological stage)和抽象阶段(metaphysical stage)。在前一阶段,人们需要在超自然的存在中寻求现象的解释;而在后一阶段,抽象的概念和虚构的实体被用来解释现象。在最终的实证主义阶段,人们才认识到,上帝不过是人类具有高尚品质愿望的投射,没有什么地位比人类更高,也没有什么知识是不能从实践中获得的。
对于孔德来说,在实证主义阶段,人类的善是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最终标准,道德的主要信条应该是将社会和他人利益放在首位的利他主义,所有教育和道德规定的目的都是使人性中的利他主义战胜利己主义。人类的最原始的本能,如性的本能和自我保护的本能,都是利己主义的。但是在人性中也有利他主义的因素,正是在人性中利他主义因素的引导下,人才能爱和尊重他人;而且,如果人性中利己主义的因素得到充分控制,利他主义因素将会引导人们爱社会,甚至爱整个人类。依据孔德的见解,人类的性的本能是最为利己的,因此婚姻中对配偶的爱是将利己主义转变为利他主义的最根本途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两性中代表着人性中感性因素的女性,在孔德的实证主义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孔德的思想对爱略特晚期的作品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爱略特的晚期作品,尤其是《米德尔马契》和《罗摩拉》,都强调了女性的重要作用,即通过家庭将自己的影响带给社会。两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多萝西娅和罗摩拉都在生活的实践中经历了迷惘、错误、幻灭直到通过自省达到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使人性中的利他主义战胜利己主义,从涉世未深的懵懂女孩转变成了为他人无私奉献的圣母般的人物,并在此过程中将自身的影响从家庭延伸到社会,从而帮助人类实现由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的转变。
在爱略特笔下女主人公通往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中,道德自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自省意味着人对自己的审视和检查,而道德自省则指人对自己品德和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自我审视和检查,是人类特有的现象。通过道德的自省,人能认清自己犯下过错的原因,并在日后的行为中尽力避免;通过道德的自省,人也可以鼓励自己对善行的坚持。“道德事实上取决于我们的一种内省,它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彼此相待和相互满足。”[10]110说到底,道德自省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动机与行为效果及其所表现的个人道德认识、个人道德感情和个人道德意志的道德价值自我检查。”[11]37正是通过这种对人生旅途中道德印记的修正,人才能逐步走向道德的完善。
《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被称为“降生在人间”的圣德蕾莎,“她的内心自有一种动力,在它的驱使下,她向往着永无止境的完美,探求着永远没有理由厌弃的目标,让自身的不幸融化在自身以外的永生的幸福中。”[12]1但在一个将女性视为附属品的世界中,她的满腔热情除了引起众人非议外,从来得不到重视。因此,在涉世未深的女孩眼中具有渊博学识和崇高信仰的老书蠹卡苏朋,能够提供给她理想中的婚姻,帮助她走上庄严、崇高的道路。于是,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卡苏朋,却在婚后逐渐认清了卡苏朋冷漠、保守、顽固、自私的本质。
多萝西娅的早年憧憬幻灭之时,也同样是她的道德自省开始之日。经过对个人道德认识的检查,多萝西娅意识到自己早年认识的偏颇,不该将对未来的期许寄托在卡苏朋身上。在那之后,多萝西娅摒弃了个人利益对自己的束缚,从而将自己最高尚的道德理想付诸实施,并在其指引下使自己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效果获得了统一,多萝西娅也由此获得了道德上的完善。她最终放弃地位和财产,嫁给了威尔,并尽力承担生活中的责任,从不退缩。在她的支持下,威尔进入了议会,为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全力以赴。很多读者和评论家将多萝西娅与威尔的婚姻看作小说中的败笔,但事实上,这构成了多萝西娅一生都不曾停止的对于道德至善追求的一部分,因为正是以这种方式,“她对她周围人的影响,依然不绝如缕,未可等闲视之,因为世上善的增长,一部分也有赖于那些微不足道的行为。”[12]783
对于小说《罗摩拉》,亨利·詹姆斯曾不无批评地说道:“乔治·艾略特的小说里,就数这一本是从她的道德意识——一种为车载斗量的文学研究所环绕的道德意识——演变而来的。”[1]81詹姆斯的话表达了他对于爱略特在小说创作中“由抽象走向具体”倾向的不以为然,但我们却得以从中窥见道德主题在小说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而罗摩拉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正是小说最为重要的道德主题。
小说中的罗摩拉立志像个男孩子那样勤奋学习、努力拼搏,弥补由于兄长的离家出走带给父亲的失落感和遗憾。但无论她如何努力,父亲始终固执地认为,女性无法具有跋涉在学问道路上的人所必须具有的“坚持不懈的热诚和不屈不挠的耐心。”[8]59同样是在无法找到前进的方向时,罗摩拉遇到了蒂托。蒂托年轻、富有朝气、学识渊博且聪敏机智,而蒂托同样对罗摩拉一见钟情,两人便水到渠成结为夫妻。婚后由于蒂托对金钱和地位的欲望日益膨胀,他逐渐背弃了最初的理想,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进行了双重背叛。对罗摩拉最致命的打击来自于她对一度视为精神导师的季罗拉莫修士本质的认识:他口口声声宣扬的上帝的事业,不过是加强自己党派的力量而已。情感与信仰的双重打击使罗摩拉希望幻灭,并先后两次离家出走。在第二次离家出走时,罗摩拉坐上随波逐流的小船,准备放逐她的责任、过去,甚至生命。在这里,滔滔江水象征着大地母亲的羊水,提供给她精神与道德的新生。当她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到了一个瘟疫肆虐的小村庄,在与死亡较量救助村民的过程中,她经历了一次个人道德感情的审查和洗礼,对他人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舍己为人的信念成为她心中新的信仰,罗摩拉由此获得了道德的完善。她意识到,只要自己拥有道德上的完善,“站得更高”“就不会那么容易丧失所有的信心”[8]633。
不仅在这两部堪称女性史诗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经历了从懵懂、迷茫走向道德完善的过程,在爱略特后期的其他作品中,女性的道德完善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一个话题,《激进分子费利克斯·霍尔特》中的埃丝特从起初的一心向往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转变为心甘情愿与一无所有的费利克斯共度人生低谷,《丹尼尔·德龙达》中以婚姻作为人生赌注,试图以此摆脱物质生活困境的格温德林在小说结尾写给丹尼尔的信中说:“我会成为一个最好的女人,一个会让别人觉得自己一生很值得的女人。”[9]675尽管爱略特一再声明自己并非女权主义者,但在小说中,爱略特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男性并非女性的救世主,女性如果将对于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注定只能得到幻灭。爱略特并不赞同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为女性争取诸如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她认为女性应凭借自己独特的个性才能以另一种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即在家庭中成为男性的有力支柱,将爱与关怀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才能在获得自身道德完善的同时惠及他人,使自己的影响从家庭延伸到社会。在罗摩拉的身上,爱略特再次强调了自己人本宗教的信仰,即宗教信仰的精华并不在于抽象的上帝,而在于人本身,上帝不过是人崇高情感的外化。因此,当危机到来时,抽象的上帝无法起到对人的信仰的约束作用,只有人做到能够约束自己的情感,信仰之塔才不会轰然倒塌。
如果将爱略特前后期作品进行对比,人们就不难发现她在表达相同伦理主题时侧重点的变化。在探讨社会伦理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爱略特前期作品中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相对较强的凝聚力,作为个人归属感的来源存在,而个人在对社会依赖的同时,在主观上也自愿维护着社会的传统与秩序,人与社会之间呈现出和谐的关系。但由于现代文明进程对农业社会的入侵,田园时代的传统正在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爱略特在小说中对这种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赞美的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眷恋。爱略特后期的作品则聚焦了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新兴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中的个体更多地关注自身的成功,社会的凝聚力逐渐丧失。在这种情况下,爱略特更多地强调了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她将现代工业社会看作一个巨大的有机体,社会中的个体则是这个有机体中的细胞,有机体功能的执行依赖于构成细胞的正常运作,而构成细胞也同样依赖于整个有机体而生存。因此,只有将个人投入社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才能获得个体与社会的双赢。而在探讨家庭伦理时,尽管爱略特从未以女权主义者自居,但她身为女性的视角也使得她不可避免地在小说中关注了女性的处境。在前期的小说中,爱略特更多地赞扬女性具有的勤劳、善良、坚忍、无私等传统美德,认为尽管男性居于一家之主的地位,但通常是女性以母性的力量将家庭成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维系着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虽然爱略特对男性惯有的刚愎自用、缺乏宽容等特征进行了批判,但她笔下的女性对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往往毫无怨言地接受,即便曾经尝试,终因并不清楚自己的真正需要而归于沉寂。而在后期的小说中,爱略特着重歌颂的是女性从自发上升至自觉的道德完善。在经历困惑彷徨后,爱略特笔下的多萝西娅和罗摩拉们明确了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改变了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使自己的影响从家庭延伸到社会,以女性特有的方式投入到为社会和他人的奉献中去,从而转变成为圣母般的人物。相对而言,这一时期小说中男性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但削弱他们主导地位的,并非女性的抗争,而是男性自身的弱点,如威尔的软弱犹豫,蒂托的道德缺失。爱略特认为,“社会必然会变化,会发展,人类一定会进化,会进步,但一切必须因势利导,循序渐进。”[7]59因此,她并不赞同激进地为女性争取如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的做法,她笔下的男性与女性也从不是两个敌对的阵营。她认为女性应该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在女性特有的领域中发挥力量和影响,与男性携手并肩,共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1] 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M].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 McSweeney,K.GeorgeEliot(MarianEvans):aliterarylife[M].New York: St.Martin’s Press,Inc,1991.
[3] Eliot,G.Letters.Gordon S.Haight[M].New Haven: Yale UP,1954
[4] [美]罗伯兹·戴维.英国史:1688年至今[M].鲁光桓,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5] Carroll,D.GeorgeEliot,theCriticalHeritag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1971.
[6] 洪汉鼎.斯宾诺莎《伦理学》导读[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7] 马建军.乔治·艾略特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8] [英]乔治·爱略特.仇与情[M].王央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9] Eliot,G.DanielDeronda[M].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1996.
[10] 罗秉祥,万俊人.宗教与道德之关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11] 王海明.论自省[J].伦理学研究,2008(1).
[12] [英]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M].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