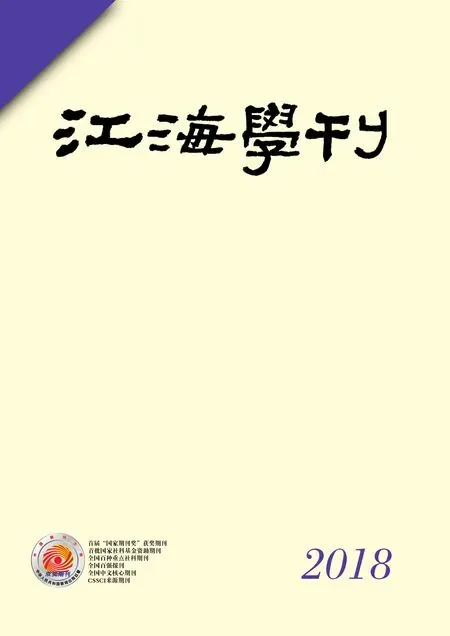学术宗旨与史学批评*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考察
刘开军
学术宗旨是在学术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核心学术理念和研究取向,它一旦形成便会对学术研究产生长久且深刻的影响,成为学术的方向与灵魂,并鲜明地投射到学术思想、学术评价和学术关怀等方面。古代大思想家黄宗羲已明确提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①黄宗羲强调学术要有宗旨;宗旨是为学的根本,是以简驭繁之道;学人无宗旨则无“得力”处;后人不知前人宗旨,则无法得其要领。这番话是有根据的。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②,到司马光的“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③,再到章学诚的“吾言史意”④、龚自珍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⑤,中国古代史学家始终重视学术宗旨的提炼、表达与贯彻。而这些宗旨也的确是前代史家治史的法宝和后人揣摩前史的门径。
学术宗旨、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三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这表现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上那些精粹的表述往往与学术宗旨的批评有关,比如会通与断代、史法与史意、撰述与记注、良史与信史等。而且“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是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⑥。围绕批评家的学术宗旨来讨论史学批评问题,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或可有新的认识。
宗旨对立引发史家争议
史学批评何以发生?史学理论何以提出?关于史学的理论认识又何以被继承、覆盖和超越?这自然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时代的变化、思潮的涌动、政治的介入,甚至门户的偏见等。而由学术宗旨对立所引发的批评,也是其中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因为它能够显现出争论的思想底色,并推动史学理论的创新。
魏晋至隋唐间,史注之风盛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是这一时期享有盛名的史注。如所周知,陈寿作史“微而显”⑦,《三国志》也素以“简净”⑧著称。但在裴松之看来,《三国志》却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故于《三国志》“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⑨。裴松之对于《三国志》“补阙”“备异闻”“惩妄”和“论辩”的批评固然是奉了宋文帝的旨意,但裴氏注史自有其宗旨,即“务在周悉”,这才是他发表上述批评的学理依据。一百多年后,另一位史注大家颜师古却与裴松之的宗旨大相径庭,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说:“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呵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⑩有意思的是,争论到此并未结束。又过了一千多年,在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关于裴注的评价又发生了转向,认为裴注“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陈寿与裴松之的学术宗旨不同,故而裴松之批评《三国志》疏漏。颜师古与裴松之在史注旨趣上迥异,所以人们看到了颜师古的反驳。而史学发展到清代,在推崇征实考信的四库馆臣眼中,裴注又成了文献渊薮,自然功不可没了。
唐宋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会通”与“断代”的优劣之争。这一争论具体表现为刘知幾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评论以及郑樵对于刘知幾、班固的批判,也是一桩因学术宗旨不同而引发的经典批评案例。
刘知幾在史学上推崇断代为史,这在《史通·六家》篇关于“《史记》家”和“《汉书》家”的评论中有非常清楚的表达。他说:
《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在这百余字中,刘知幾指责了通史三个方面的缺憾,即“为体之失”“撰录之烦”和“劳而无功”,依次指向通史的体制之失、叙事繁冗和事倍功半。尽管刘知幾在《史通》中也肯定过《史记》,但其“基本格调是纠谬规过,锋芒所向直指司马迁”。相比之下,《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这恰与前述对《史记》的三重批驳一一对应。
刘知幾重视断代、轻视会通的倾向引来了与其学术宗旨不同的郑樵的激烈反驳。郑樵为学的宗旨可以概括为:“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在《通志·总序》中,郑樵再三高扬“会通之义”的旗帜,认为《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马”。虽唐宋相隔,但郑樵把断代为史说得一无是处,显然是要与刘知幾一较高下。郑樵还意犹未尽地说道:
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昩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
郑樵认为会通之可贵,在于它呈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礼乐文明的损益之迹。而断代修史既重复繁琐,又割断了历史的内在联系。在今天看来,刘知幾对于断代和会通的上述看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二者的优劣并非全如刘知幾所言。同样,断代为史也不像郑樵所说的毫无意义。
这类由于宗旨对立而发生的争议,虽不无偏颇,但既要批评他人,便需摆事实、讲道理,势必对旧有的理论作纠谬与商榷的工作,力求有所突破,这样便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
宗旨歧路,批评殊途
史学批评是一项主体性鲜明、思想性突出的学术活动。学术宗旨不同,对于事物的评价自然有所区别。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名著,但班固父子却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刘勰继而论司马迁有“爱奇反经之尤”。到了明代,评论界则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为旨趣的李贽反戈一击,讥讽班固父子关于司马迁的批评“适足以彰迁之不朽而已。使迁而不残陋,不疏略,不轻信,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则兹史固不待作也。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可见,他们所发表的评论或褒或贬,不过是基于不同宗旨的一种学术表达。这从史学批评的纵向维度上证明了学术宗旨对于批评的决定性影响。
若从史学批评的横向维度来看,宗旨对于批评的制约亦极大,甚至会出现同一时期不同学派对相同问题的看法尖锐对立的情况。
清乾嘉时期史家辈出,若以学术宗旨划分,则有比较明显的两大学派:以钱大昕、王鸣盛为领军的考据派和以章学诚为中坚的浙东学派。两派在宗旨上的分歧可以用章学诚的一句话来概括:“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何谓“高明”和“沉潜”呢?“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浙东学派服膺“独断之学”,推崇的是思想;考据派醉心于“考索之功”,则偏向于功力。再读章学诚与汪辉祖的信,有“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之说,这也折射出浙东学派与考据派的学术分野。而考据派和浙东学派关于《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的评论,就生动地体现了宗旨歧路而导致的批评殊途。
王鸣盛晚年的重要著作《蛾术编》中有一篇《通典通志通考》,专门评论“三通”,认为《通典》虽有可议之处,但它“条贯古今,端如贯珠”,“诚有不可及者”。《文献通考》继《通典》而作,“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会要及百家传记;凡论事则取当时臣僚奏疏及名流燕谈、稗官记录,其史传可疑,论辨未当者,则以己意附其后,庶几可辅翼《通典》者欤!”相比之下,尽管郑樵自视甚高,却属自我吹捧,《通志》着实乏善可陈,“于‘三通’为最下”。这是王鸣盛给“三通”排出的名次。
那么,四库馆臣又怎样评价“三通”呢?他们批驳《通志》的纪传部分“删录诸史,稍有移掇,大抵因仍旧目,为例不纯”,至于郑樵“平生之精力,全帙之菁华”所在的《二十略》,也是错讹百出。“《六书》《七音》乃小学之支流,非史家之本义。矜奇炫博,泛滥及之,此于例为无所取矣。”同样,“《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亦但删录《通典》,无所辨证”。总之,“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这条提要绕了一大圈,重点还是说《通志》考订粗疏,而矛头所指则是“宋人以义理相高”,现出了宗旨之争的端倪。四库馆臣评价《通典》时又是另一种口吻了。《通典》“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评论的落脚点是可以藉此考订“唐以前之掌故”,恰与上述有关《通志》的评价相互映衬。至于《文献通考》,虽有小疵,然全书“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肯定《文献通考》史料翔实,可供考史之用。显然,《四库全书总目》关于“三通”的品评都是围绕是否有益于考证而发的,这与其重“考索之功”的宗旨是一致的。对王鸣盛、四库馆臣关于“三通”的评论作必要的梳理和分析之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考据派的评价体系中,《通典》与《文献通考》远胜《通志》。
再来看看浙东史家章学诚对“三通”的看法。
章学诚关于《通典》的评论,较重要者有三处:一是《通典》“谈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则著书之独断,编次之通裁”。二是杜佑“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裁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入于正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余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三是《通典》“博采异同,归于实用。故其文虽简直,而指实开通。体虽旁摭旧闻,而义则裁以独见”。尽管浙东学派和考据派都推重《通典》,但理由却不同。章学诚称赞的是《通典》在编纂上的匠心和史意上的通达,与前述考据派强调的为考证之渊薮的意思已呈对峙之势。在郑樵被乾嘉学术主流大批判的背景下,章学诚却对郑樵及其《通志》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维护、提升郑樵的学术地位。乾隆三十八年(1773),当章学诚在杭州听到戴震痛诋郑樵后,讥讽“其言绝可怪笑”。《文史通义》中的《答客问》《申郑》和《释通》等篇皆极力表彰郑樵。《文史通义·申郑》写道: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絜长较短;亦未尝欲后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
在章学诚看来,郑樵是别出心裁的史学大家,非一般辞章家和考据家所能比肩。郑樵继承了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发凡起例,自成一家。那些批判郑樵的人虽勤于考据,却无见识,他们不懂得《通志》本不是要与小学家的著作争一时的短长。郑樵瞩目于史学之大要,批评者却吹毛求疵。章学诚又说:
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于古人,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猵狙见冠服,不与龁决毁裂,至于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
章学诚还特意回应了考据派对郑樵的批判,说:“今人大抵全尚名数……夹漈体大而材疏,今人于其材疏则诟詈之,其体大之处,全不解也。”言语之间,对考据派的批判不以为然,且有愤恨不平之意,又盛赞郑樵将一家之言寓于史裁之中,乃是千古不朽之业。
那么,《文献通考》在章学诚的史学批评中又居于怎样的位置呢?“《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于对策敷陈之用。”在章学诚看来,《文献通考》不过是备科举之需:“进士之科,多问礼、乐、兵、农、政令、制度,故马氏贵与广辑历史书志成迹,附以前人评论,汇为《文献通考》,以为有备之无患焉。”章学诚还为此设计了一个问答题:“马氏《通考》之详备,郑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独取其义旨,而不责其实用,遂欲申郑而屈马,其说不近于偏耶?”章学诚答道:“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谓其智既无所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门类,取便翻检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论议,易于折衷耳。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至于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闻也。”章学诚反复批评马端临不明史意,认为《文献通考》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综括上述诸论,章学诚对郑樵的褒扬主要集中在其“发凡起例”和“独具心裁”上。他欣赏郑樵不拘于程式,不泥于成规,批评考据派只盯着《通志》中的疏漏,却全然不去理会郑樵的“独断之学”。与此相对应,章学诚对考据派所欣赏的《文献通考》则嗤之以鼻,显露出几分不屑与傲慢。
浙东学派与考据派关于“三通”针锋相对的判词,归根结底是因为两派的学术宗旨不同,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视角差异。在“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这两种宗旨引领下的批评话语中,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三通”的学术地位自然也就有了天壤之别。不过,若跳出对“三通”的评价窠臼,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正是有了考据派和浙东学派等宗旨各异的史学家们的相互商榷与辩难,才告别了理论的单调与单薄,构建出一幅古代史学理论的多元图景。
关于宗旨与批评之关联的反思
世间本无尽善尽美之史家与史书,长于论断者或乏史学,善于考索者或短于史识。更何况宗旨相异,批评之分歧自然无法避免。回顾史学批评史,结合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流变,梳理学术宗旨与史学批评之间的学术关联,更需检讨宗旨对批评的影响,思考其中的得失与启示。
第一,就批评的对象而言,史学批评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关于史料来源,记载真实性、准确性的批评是第一层次;关于史书编纂、修史制度、叙事艺术的批评是第二层次;关于史家素养、史学思想、学术宗旨的批评是第三层次。这三个层次呈现出从具体到抽象、由微观而宏观的批评次第,构成了古代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但三者却不宜等量齐观,一般来说,关于学术宗旨的批评高于其他层次的批评,尤能体现史学理论的新动向。
以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例。关于《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纪传体例、文风、史论等方面的批评固然重要,且有理论意义,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新五代史》的书法问题。这就不能不提到欧阳修的作史宗旨了。欧阳修在史学上崇拜《春秋》,《新五代史》效仿《春秋》笔法,制作义例,书与不书皆有所指,正所谓:“自即位以后,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然而,到了清代,史学理论的方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折,义理史学不再被主流学术界看重,欧阳修的修史理念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钱大昕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欧阳公《五代史》自谓‘窃取《春秋》之义’,然其病正在乎学《春秋》。”欧阳修认为史家叙事的笔法能够惩恶劝善。钱大昕却主张“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各若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无怪乎以严谨著称的钱大昕会这样毫不掩饰他对《新五代史》书法的不满。事实上,在这些对立的评论表象之下,涌动着的是史学理论的暗流。
第二,对学术宗旨的理解越深刻,则批评越有效,理论价值也就越高。反之,不明白或不从学术宗旨出发而作出的批评,则可能沦为无效批评。顾炎武与好友李因笃之间关于《资治通鉴》的对话,为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
李因笃长于文,故有“《通鉴》不载文人”之论,这看似击中了司马光的要害,实际上却是强人所难。顾炎武深知《资治通鉴》之宗旨“本以资治”,也就不以它缺载文人而为憾事了。一部史书无论卷帙多么庞大,也无法囊括全部的历史,若一味追求面面俱到而不突出修史宗旨,则难逃史料拼凑和毫无章法的误区。作为一部帝王政治教科书,《资治通鉴》在北宋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以“资治”为要义,于人物和史事上自然有所选择。李因笃的批评没有考虑到《资治通鉴》的撰述宗旨,所谓“《通鉴》不载文人”也就成为一条无效批评了。
相反,王夫之对《资治通鉴》作出了大量的有效批评,理论色彩十分突出,这不能不归因于他对《资治通鉴》的宗旨具有的深刻领悟:
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这大概是古往今来对“资治通鉴”四个字最透辟的理解和评论了,反映了王夫之对史学的独到见解。倘若王夫之不深谙司马光之宗旨,仅仅是对《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作具体评论,则《读通鉴论》的史学理论价值将大打折扣。可见,史学批评的有效性与对评论对象学术宗旨理解的深浅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学术宗旨鲜明,批评往往犀利,但也易于走向偏颇、武断,即便是一流的史学家也不能例外。上面提到的郑樵批驳班固和章学诚批评考据派即属此类情况。郑樵关于“会通”的理论不可谓不高明,但在他的笔下,纪传体断代史的开创者班固成了窃书之贼、浮华之士。他一味指责陈寿、范晔以下的史家沿用班固的断代史体例,但却没能深刻分析后世史家为何如此。倘若班固真的一无是处,何以东汉以降的史家竞相效法呢?郑樵大概也感到费解,只能说一句“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在这个问题上,郑樵的论述就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是错误的。更有甚者,郑樵把司马迁比作龙,而将班固斥为猪,言辞几乎不堪入耳目。同样,在上引章学诚为郑樵所作的辩护中,辩词十分精彩,但他把驳郑者比作“猵狙”和“群怪聚骂”,称考据派因少见故而多怪,就不能不说是有失分寸、流于表面了。与章学诚同时期的疑古史家崔述,对诸史的批评也是得失兼有、是非杂糅:
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卮言,真伪相淆。……虽以宋儒之精纯,而沿其说而不易者盖亦不少矣。至《外纪》《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前编》(原注:六字共一书名,与温公《通鉴》、朱子《纲目》无涉)等书出,益广搜杂家小说之说以见其博,而圣贤之诬遂万古不白矣!……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
崔述的疑古辨伪成绩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他以“六艺”为考信的准则,在他眼中,不仅先秦诸子“诬圣贤”,《史记》等书也“旁采卮言,真伪相淆”,而且《通鉴外纪》更使“圣贤之诬遂万古不白”,这就有些夸大了。倘若圣贤之诬真的已万古不白,那么崔述又何以能够“维护儒家经典的纯洁性”,崔述甚至认为与其“不知所择”,还不如孤陋寡闻,这也是比较片面的看法。如果仅将此归咎于批评家的学养浅陋或知识偏见,是缺乏说服力的,或者说把问题简单化了,这其中起根本作用的还是批评家的学术宗旨。
学术宗旨是史学批评的理论出发点和立场所在,对于批评的价值取向和感情倾向具有直接影响。鲜明的学术宗旨是一柄双刃剑,它让批评者形成了明确的评论标准,但也会构成难以逾越的理论障碍——凡与其宗旨不合者,多在被弹射之列,而被批评者的合理性却被遮蔽了。对于这类极高明而又有破绽的史学批评,研究者当作何处理呢?首先应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可随其批评坠入偏执。其次,既提炼其批评中蕴含的理论,又指出存在的问题,不因其高明而无视缺失,也不因其疏漏而一概摒弃。而面对相互矛盾、对立的批评时,研究者又须探究批评背后的宗旨,才能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并有所鉴别和判断。
消弭宗旨的批评既无可能,亦无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旨总是随着时代变迁和学术革新而变,其间有渐变,有剧变,有回归,有突破。研究者能否总结、洞悉、阐释这些变化,并对产生于特定时代和学术氛围中的史学批评作出准确和深刻的评论,这关乎能否对古代史学理论的演进作细致的考察,并指引当代的史学批评与学术发展。
①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
③司马光:《进书表》,《资治通鉴》卷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7页。
④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⑤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页。
⑥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后记》,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70页。
⑦魏收:《魏书》卷四三《毛脩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60页。
⑧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事得实处”条,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5页。
⑨以上引文皆见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附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71页。
⑩颜师古:《汉书叙例》,《汉书》卷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页。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