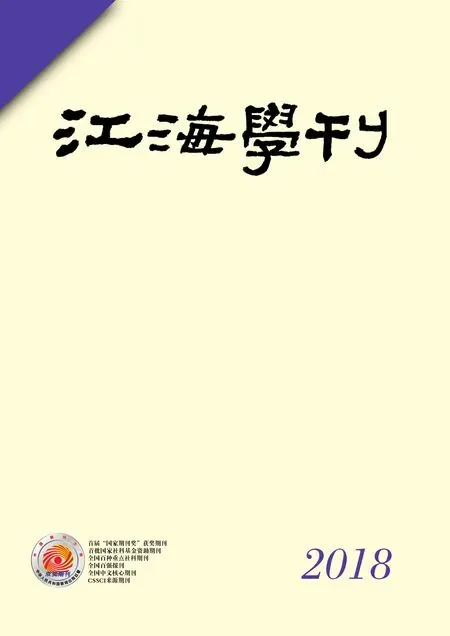数字人文:概念、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郭英剑
“数字人文”的英文为Digital Humanities,也有译为“数位人文”或者“数位人文学”,简写为“DH”。学术界也有用“数字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简写为“DS”)来指称“数字人文”的,但实际上,这两者有区别。从事这一领域的学者、研究者,就是数字人文学者(Digital Humanist)。
如果google一下“Digital Humanities”,人们可以发现有140万条相关信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数字人文日渐成为一门显学,同时也处在不断演化中,其概念还在不断变化、延伸与发展。从目前看,数字人文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①,大多数学者和研究者都认为,要为这一概念下个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②,而且,从研究著述中以及各种网络资源上也可以看到,数字人文的相关定义达到数十种。
但我以为,数字人文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见,其核心概念已经形成,基本内涵也已相对固定,研究内容既有已经成型和完全成熟的学术型、技术型和应用型成果,也呈现出越来越广阔的开放性趋势,其应用与发展前景相当广阔。因此,到了可以为之做出一定总结的时候。
为此,本文试图在厘清“数字人文”的核心概念、基本特征、相关内容与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梳理当下全球数字人文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建设与发展现状,注重探讨数字人文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与前景,特别是带给文学研究怎样的变化,进而对中国数字人文在文学研究中的未来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核心概念与四大基本特征
虽然“数字人文”的概念与定义较难确定,但在网络上与各种学术著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概念、定义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人们很容易查找到的,学术界也比较流行的,或者被人们较为广泛接受的有关“数字人文”的定义与概念,然后对此做一番梳理。
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③,Digital Humanities,既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但现在人们更多使用的还是复数。简言之,数字人文是指将计算工具(computational tools)与方法运用于诸如文学、历史与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的学科领域(an academic field)。这一定义简明扼要,说出了数字人文的基本特征,但它却是不全面的。
维基百科综合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的相关定义,提出数字人文是计算或数字技术(computing or digital technologies)与人文学科(the disciplines of the humanities)相交叉的学术研究范畴(an area),且包括了人文学科中数字资源的系统运用,同时也反思这种运用④。这种概念补充了前述定义之不足,强调了学科交叉性,也提到了对这种数字资源运用的反思,但作为概念,其表述不太清晰,特别是对“反思这种运用”语焉不详,令人困惑。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定义较为清晰,认为数字人文是位于人文学科与计算技术交叉地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其目的在于考察数字技术是如何用以提高与转化艺术与社会科学的。同时,它也运用传统的人文技巧,去分析当代的数字化人工制品(digital artefacts),考察当代数字文化⑤。这一定义应该说较为全面,提到了数字人文的两个方面,但除了不够简洁外,其中它提到了“社会科学”,而这一点则是大多数数字人文的定义中所没有的,也是一些数字人文学者所反对的⑥。
在学术界,有“数字人文之父”之称的布萨(Roberto A.Busa)的观点自然备受学术界重视。数字人文起源于“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布萨认为,数字计算简言之就是对人类的表达(human expression)进行各种可能性分析的自动化(automation)体现。他所以用人类的表达这一说法,是因为这就是一种很精致的人文主义(humanistic,也是人道主义)的行为。他选取了这个词汇的最广泛的意义,涵盖了从音乐到戏剧,从设计与绘画到语音学等人文学科的相关领域,但其核心依旧是书面文本(written texts)的话语⑦。布萨的观点是从数字人文的源头谈起,但从广义上明确了数字人文的人文特征,并且特意强调了文学艺术在其中的重要性。
《数字人文指南》主编史雷布曼(Susan Schreibman)等所做出的解释认为,数字人文从一开始就是运用信息技术以照亮人类的历史记录(human record),而且,理解人类的历史记录也能对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产生影响⑧。这个解释看上去富有诗性,也囊括了所有的人类文献,但突出了信息技术之于人类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字人文指南》(2004)的出版,使得“数字人文”一词迅速取代了“人文计算”,成为了一个在世界上开始迅速传播的新兴跨学科研究的代名词。
史雷布曼等人的观点与博迪克(Anne Burdick)等人在所著《数字人文》一书中的观点相一致。博迪克开宗明义提出,数字人文诞生于传统的人文学科与计算方法(computational methods)的偶然相遇⑨。由此,他们强调了所谓数字人文的最基本内涵,就在于“数字”与“人文”这两者相结合。
到这里,数字人文的核心概念已经呼之欲出。就此,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总结来定义数字人文,或者给出一个核心概念。
所谓数字人文,是一种将新的技术工具与方法运用到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教学、科研、服务以及其他创造性工作之中的新型学科。反过来,数字人文学者也运用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的思维与方法去反思数字人文的运用与价值。“数字”与“人文”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联动关系,新技术的生成与应用,改造了传统的人文学科,诞生了数字人文,拓展了新型的人文学科;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依据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观察、研究、质疑乃至批判数字人文之于文化传统与数字文化的深刻影响。
通过上述对于概念的基本梳理,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数字人文所具有的四大基本特征。
首先,数字人文是文理结合的产物。由人文学科与计算或信息技术相结合,推翻了文理之间、人文与技术之间过去极为森严的壁垒,走到了一个全新的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阶段。其次,数字人文具有跨学科与学科交叉的特点。由于人文学科包括了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各种领域,与计算或者信息技术相结合,往往超越了单一的学科范畴,从而走向了跨学科的研究。再次,改变了传统人文学科知识的生产、保存与传播媒介。在过去人文学科单纯或者主要依靠印刷文本来完成并获得人们认可的基础上,引入了数字工具与方法,从而使人文学科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最后,数字人文令传统的人文学科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学科盛行的时代,在物质主义横行的年代,在人们不断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人文学科日趋为人所怀疑其价值与意义。而数字人文的不断发展,使传统的人文学科在一片技术世界的大漠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拓展了新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也使传统的人文学科在信息化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个发展阶段
数字人文是时代的产物,更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反映。虽然是新兴学科,但数字人文源于人文计算,其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70年前,也就是电子计算机诞生(1946年)不久之后的1949年。
70年来,数字人文经历了五个历史时期,也是五个发展阶段。前四个发展阶段,由数字人文学者霍基(Susan Hockey)所命名。她在写于2003年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中,将数字计算与数字人文的发展历史归纳为四个历史时期。⑩
第一个时期为初始阶段(1949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这一时期,先驱者布萨和他所领导的团队与IBM合作,成功地为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1000多万字的拉丁文作品做了编制索引,名为“托马斯著作索引”(Index Thomisticus)。这项富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将文本与计算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计算机在语言学领域中的运用,此后,这类研究开始逐步扩展到文学、历史学等领域。
第二个阶段为巩固时期(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是计算机逐渐在西方世界普及的时期,欧美各国召开了不少学术研讨会,人文学者与计算学者逐渐开展联合,重点在语言学语料库建设上,在对文本的创建、保存与维护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开发和推广。
第三个阶段为新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个人计算机开始出现,从而促使众多的西方个体学者通过电子便捷有效和创新的方式,进入到了数字人文的研究领域。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西方开始出现人文(Humanist)邮件群,从而逐步建立了数字人文的学术共同体。
第四个阶段为互联网时代(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2003年)。这个阶段,已经是西方“互联网”逐步广泛使用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图形界面计算机与超文本可以为所有人使用,从而使得任何一位人文学者都可以介入这些资源,从而在网络空间中出现了大量“档案”类的学术课题与研究成果,学者、编辑、图书管理员、程序员等或合作或各自为战,但却形成了一大批致力于数字人文研究的学者。
从霍基撰写上述文章到现在,15年过去了,数字人文也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我看来,从2000年代早期到现在,是数字人文极为活跃的阶段,我们不妨称之为数字人文的成熟时期。
在这第五个时期,数字人文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为成熟和高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2009年在费城举办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数字人文”成为热点话题,数字人文学者极为活跃。为此,人们普遍认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如果有大的学术热点,那么数字人文将会首当其冲。此次会议彻底改变了数字人文在美国的历史地位,从此,数字人文成为了一门显学。
也是在这一时期,国际性的和东西方各国的全国性的数字人文组织相继诞生,学术会议不断,议题日新月异。特别是,欧美等西方高校相继出现了数字人文的本科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乃至博士研究生专业。各种研究课题以及艺术领域的相关项目层出不穷,数字人文的边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数字人文专业在全球高校中的学科建制
现在,数字人文的机构组织在全球遍地开花。据国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ADHO)的统计,目前全球有超过183个冠以“数字人文”的机构或项目正在运行。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高校中的机构组织同样众多,像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MIT、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包括我国的北京大学、我国台湾地区的台湾大学等高校中,都设立了数字人文研究机构。同时,新型的数字人文学术刊物也涌现出来,既向全球传播数字人文的理念与方法,也传播相关的研究成果。
但在这股数字人文蓬勃发展的时代洪流中,更值得关注的则是在众多大学中所设置的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再到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建设。下面,我将以英美两国几所名校为例,来加以说明。
英国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简称KCL)的“数字人文”专业建于1970年代初,时间早,专业全,水平高,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KCL的数字人文系(The Depart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的数字人文专业在全英排名第一,属于世界一流的专业。该系的相关研究项目众多,仅大项目就超过30个,其中包括与英国皇家歌剧院合作的一个项目,制作移动应用程序,为艺术与文化部门服务。这些项目讲究与其他部门的通力配合,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还与国内以及国际上的组织或高校开展国际合作。
目前,KCL是全英仅有的提供“数字人文硕士专业”的三家高校之一,也是全英唯一提供“数字人文博士专业”的高校。最近,它又启动了授予本科学位的工作。其硕士专业包括数字人文硕士学位(MA in Digital Humanities),数字文化与社会硕士学位(MA programme in Digital Culture and Society),还与e-Research研究中心合作开设数字资产与媒体管理硕士学位(MA in Digital Asset and Media Management)。其博士专业为数字人文博士学位(PhD in Digital Humanities)。其正在建设的本科生的数字人文专业设置,拟包括社交媒体、游戏、数字记忆、经济、政治等。
那么,像在本科阶段的数字人文专业,他们都学习些什么课程呢?我想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简称PENN)的“数字人文”辅修专业(Digital Humanities Minor)为例来加以说明。
PENN的这一辅修专业名称全称为“本科生数字人文辅修专业”(the Undergraduate Minor in Digital Humanities),由文理学院(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所推出。该专业欢迎人文学科与非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选修。该专业由不同文理学院的不同系别的教师来授课,鼓励学生选修自己所选专业之外的课程。这一专业的相关话题包括数字文本分析、数码绘图、3D图像以及运用数字工具去搜集、组织和研究物质文化。同时,除了上课、参加研讨外,还要求同学们参与到相关话题的讨论与争辩中。
为此,学院设置三级课程,由宽泛到深入,逐步过渡。前两个阶段的课程以技能为主,第三阶段则教会学生以技能去从事自己的研究项目。其核心课程包括数字人文概论(ENGL 009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计算数据研究(CIS 105 Computational Data Exploration)、计算编程概述(CIS 110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Programming)。这三门课程,至少选一门,但不能超过两门。
二类课程众多,包括:数字人文漫谈(ENGL 209 Topics in Digital Humanities)、数字世界中物质的过去(CLST 127 The Material Past in a Digital World)、视频I(FNAR 061 Video I)、社会统计学(SOCI 120 Social Statistics)、传播中的定量研究方法(COMM 210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Communication)、大数据与社会研究(COMM 321 Big Data and Social Research)、数据学概况(PSCI 107 Introduction to Data Science)、数字人文与环境(ANTH 581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等等。这类课程至少选两门。
三类课程包括:东亚数字人文(EALC 111/511 East Asian Digital Humanities)、图书的数字化生活(ENGL 208 Digital Lives of Books)、草原游牧制度古今谈(NELC 106/606 Pastoral Nomadism in the Past and Present)、数字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地理信息系统(NELC 346/646GIS for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与全球变暖时代的灵性(RELS 246 Spirituality in the Age of Global Warming)等。此类课程至少选一门。
由上述课程我们不难看到,该专业是为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而开设,致力于教给他们一些可以有效地用于当代相关学科以及跨学科学术中的技能,而像这样的技能,对于未来学生走入社会,无论是否要从事学术研究,都将使他们受益终身。
“数字文学研究”的概念、意义、经典案例与困境
数字技术可以分为两类:数字人文与数字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前者涉及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人文学科,后者则在更大的范围内涉及数字科学。在科学界,学者早已开始了数字学术研究。数字人文虽然涵盖了人文学科的诸多方面,但就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而言,两者依旧是极为密切。曾经参与编写了《数字人文指南》的西蒙斯(Ray Siemens)和史雷布曼两位学者,于2008年又共同主编了《数字文学研究指南》(A Companion to Digital Literary Studies)。对数字文学研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在这里,我们需要简单探讨一下何为数字文学研究、数字文学研究的意义、有哪些经典案例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首先,“数字文学研究”的概念。根据上述数字人文的核心概念与基本特征,我们可以这样来对“数字文学研究”做一概括性定义。所谓“数字文学研究”,就是利用计算工具对文学进行电子化或数字化分析,即运用计算的方式进行文学分析或文学批评,同时,也利用批评方法或者理论方法对网络文学(electronic literature)、数字媒体与文本资源进行分析和批评。
就历史而言,虽然数字人文早在1949年就诞生了,但数字文学研究则晚了大概10到20年。隆美尔(Thomas Rommel)在2004年发表的文章中写到,首次基于计算机的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种时间上的延后,原因应该是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其与计算、计算机等性质、内容、表现手段以及运作模式完全不同,一般很难将这两者放在一起讨论。
因此,当两者最早开始相遇时,其目的和方法也都相当简单。主要是为了识别电子文本中的字符串和模式,而作家用词列表与作家用语索引则有助于学者更加仔细地去观察文本特征。然而,后来人们发现,文学计算(Literary Computing)还是为研究文学风格与文学理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洞见。
其次,“数字文学研究”实践的意义。第一,自从文学研究引入了文学计算,就已经改变了当代文学的研究版图。从20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以来,人们就不难发现:可以几乎毫无限制地访问高质量的电子文本;精致的软件,可以让人们去定义分析的词汇;强大的计算设备提供了无限的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第二,数字文学研究同样可以向语言学那样,不仅为文学文本也为批评家本人建立起相应的语料库。在隆美尔看来,文学研究中的计算机不过是没有分析能力的纯粹的工具,但却能够增强批评家的记忆力,也就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符合所有预定义模式或者搜索标准的结果数据库。第三,现在,计算机辅助研究中的计算机,不单单是用来当作使用的新型工具,而是可以顶替一些批评家的工作,保留一些信息。速度、精确、无限制的记忆力以及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文本,是其显著的特征,也让人们看到了这种新型工具的强大力量。而且,通过利用不断增长的知识库和通过链接文本的方式,使它们可以被用作文本材料的巨大存储库,如此一来,传统文学批评也可以从搜索中积累的知识和专业知识中获益,从而对基于计算机的研究中实践的文献进行更严格的分析。第四,“数字文学研究”可以彰显人文学科的价值。隆美尔认为,文学计算最能体现数字人文的价值,将文学与自然科学的技术和程序连在一起,相当于引入了两种文化。正如波特所说,技术与文学批评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模式,这种新的模式与科学方法完全相通,但也绝对弥漫着人文学科的价值。
再次,数字文学研究的经典案例。在这里,主要以中国近年来所完成的几个较大规模的数字文学研究项目与课题为例。案例1:北京大学中文系分别完成了《全唐诗分析系统》和《全宋诗分析系统》,不仅对5.7万首唐诗和25.4万首宋诗文本进行了文本化入库,而且在此基础上,结合人文研究、创作的需要建立了一系列的数据模型或数据集(如28种诗歌模型、音韵库、诗人信息库等),并通过数据模型对诗歌的全文文本进行标注和分析,方便人文学者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经典案例2:在1981年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陈炳藻发表了《从词汇上的统计论〈红楼梦〉作者的问题》一文,首次借助计算机进行了《红楼梦》研究,主要从字、词出现频率入手,通过计算机进行统计、处理、分析,对《红楼梦》后40回系高鹗所作这一流行看法提出异议,认为一百二十回均系曹雪芹所作。由此研究让人们看到了字词统计分析,已经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在鉴别文学风格和文学流派分析上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经典案例3:最近,《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读本》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数字人文方法进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个读本。该读本是清华大学中文系、芝加哥大学Text lab、清华大学图书馆共同发起的“清华大学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国际工作坊”的论文集。该国际工作坊,也是数字人文研究兴起以来,我国国内首次举办的以“文学研究”为主题的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国际会议。其中,霍伊特·朗(Hoyt Long)教授的团队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去识别和研究英文俳句,通过机器学习俳句特有的词频、音节数、常用意象等特征,对语料库中的材料进行分析和区分。其研究中表现出的对文学和普通文献材料辨别的思考和对机器学习误判情况的解读,对于数字人文学者重审“细读”式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文本的“文学性”提供了值得反思的案例。同时,霍伊特·朗教授还以中日近代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展示了数字人文方法在文体研究中的应用,无论在微观的词汇、意向检索统计还是宏观的体裁、类型和写作风格分析方面,数字人文方法都为研究者展示了不同于以往的角度,使得定性、描述和批评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转化为量化的、可视的和非主观的数字成果,展示了文学研究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最后,“数字文学研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第一,认识上存在有偏见。文学文本,一般都被认为是一种美学构造,因为字词句与意象的搭配与编排而达到某种效果,可以在各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因此,不少人认为像这样的文学之美、语言之妙乃至主题之深刻,计算机是无法通过计算来加以体会和发现的。但在隆美尔看来,如果一个文本带有某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是可以通过细读的方式而获得的,那么,基于计算机的研究就应该能够被看做是这种文本理论——假定这里有“a”的含义是被困在某些文字和图像之中的,只有等待着有知识的读者把它找寻出来,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于文学之中——的一种实际的延伸。第二,现实中的困境。尽管无论在硬件和软件开发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当下的电子文本也已经在网上提供了,但文学计算依旧是处于边缘地带。原因在于在人文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们所接受的人文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没有很好地认真对待数字技术,这要等到向他们展示了工具可以改进我们探索和解释美学作品的方式时,才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第三,对数字人文冲击传统文学研究存在担忧。在学术界,也有些学者对数字人文与数字文学研究保持警惕,甚至认为会给文学研究带来负面的影响。《新共和》的高级编辑科奇(Adam Kirsch)在2014年的《新共和》上发表《技术接管英语系:数字人文的虚假承诺》一文,对高校管理技术化和职场化倾向提出质疑,尤其对流行的数字人文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思维体验和文字表达是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的精髓,而数字人文的出现很有可能使这样的目标落空。也有学者会认为,数字人文有可能使得人文学科脱离了自身存在的理由,会给人文学科带来伤害。有学者对数字文学研究有可能成为数据库、语料库的附庸而表示担忧。
中国数字人文与数字文学研究的建设与发展
近年来,中国开始高度重视数字人文。像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都在国内召开过多次相关会议,其中有不少都涉及了文学研究的问题。2016年5月,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和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建设与发展研究课题组”,共同举办了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该论坛对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概念、实践和反思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其论题涉及数字人文语言文学的应用问题。2017年7月1~2日,“数字人文:大数据时代学术前沿与探索”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近200位专家学者对数字人文的前沿思想与话题展开了广泛研讨。
然而,与国外的研究现状与规模及相应的成果相比,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未来几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高校亟待建立数字人文专业。从目前看,尚未发现有高校建设有明确的以“数字人文”为名称的本科学位点、硕士专业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也未发现有与其他学科相关联的数字人文的学位点与专业建设。建立数字人文专业,培养专业人才,既是高校的职责所在,也是为当代社会的新事物提供智力与人才支持。
其次,高校与研究机构亟待建立数字人文的学术组织与研究机构。从目前看,除了少数名校外,中国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或者研究院还较少,也没有国家层面上的数字人文学术组织,与国外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近几年来,中国对人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重视,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受到国外高校的高度赞誉。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多次在演讲中赞扬中国对人文学科的高度重视。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发展时期,大力发展数字人文研究,成立相应的学术组织与研究机构,无疑将有助于尽快推动数字人文在中国的大力发展。
最后,在国家与省部级层面上,加大对数字人文研究的资助力度与科研投入。对2014~2017年这四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课题做一简单检索会发现,只有2017年有两项(其中一项为青年基金项目)以数字人文为名的研究项目。这一点,也与国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2006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简称NEH)专门设立了“数字人文计划”(the Digital Humanities Initiative),两年之后即2008年,转为专门的“数字人文办公室”,负责数字人文方面的学术研究立项。目前,我们尚缺乏这样的机构措施,更主要是还未意识到数字人文带给人文学科的巨大变化与深刻的挑战。
数字人文与数字文学研究的未来
今天是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时代,文本的数字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科学技术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时代,改变了我们身处的世界,也在改变着我们的学术图景。人文学科也不能例外。数字人文的盛行,数字文学研究的诞生就是人文学科正在发生巨变的明证。
首先,数字人文不仅为传统的人文学科带来了便利和高效,更带来了科学研究的思维与方法,使得人文学科拉近了与科学研究的距离。未来,在技术层面上推动人文学科的发展,研究范围会更广,学者个人参与度也会更高。在实践中,学者们既可以自行开发也可以定制各种工具包,以解决人文学科中的相关问题。图像识别与数据可视化已成为近年来的热点。
其次,当今是网络文学的时代,根据中国作家创研部报告,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生产的主流。数字化文学生产与传播、发行,呼唤新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出现。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新型的方式,数字文学研究在未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数字人文是一门学科,是运用技术手段,针对计算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进行教学、研究以及创新的新型学科;其中,传统的人文学科也可以发挥其主体性与能动性,用于观察、反思与评判科学技术及其手段。数字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它可以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与新的学术视角。数字人文具有显著的跨学科性,其目的是要创建超越文本源的学术,包括多媒体、元数据与动态的环境等的集成。数字人文在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数字文学研究也将改写现有的文学研究的历史。
①Gavin, M. & Smith, K. M, “An Interview with Brett Bobley”,DebatesintheDigitalHumanities, eds. Gold, Matthew K &Lauren F. Klein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 pp.61~66.
③“Digital Humanities,”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ies online (English). 参见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digital_humanities
④Drucker, Johanna, “Intro to Digital Humanities: Concepts, Methods, and Tutorials for Students and Instructors”, UCLA Center for Digital Humanities online, part 1.1A Introduction.
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数字人文项目课程(Digital Humanities Major)主页中有相关定义,详见https://programsandcourses.anu.edu.au/major/DIHU-MAJ。
⑦Busa, Roberto A., “Foreword: Perspectives on the Digital Humanities”,ACompaniontoDigitalHumanities, ed., 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John Unsworth (Oxford: Blackwell, 2004), pp.xvi~xxi.
⑧Schreibman, Susan, Ray Siemens, and John Unsworth,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Humanities Computing: An Introduction”,ACompaniontoDigitalHumanities, ed., 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John Unsworth (Oxford: Blackwell, 2004), pp.xxiii~xxvii.
⑨Burdick, Anne; Drucker, Johanna; Lunenfeld, Peter; Presner, Todd; Schnapp, Jeffrey,DigitalHumanities,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