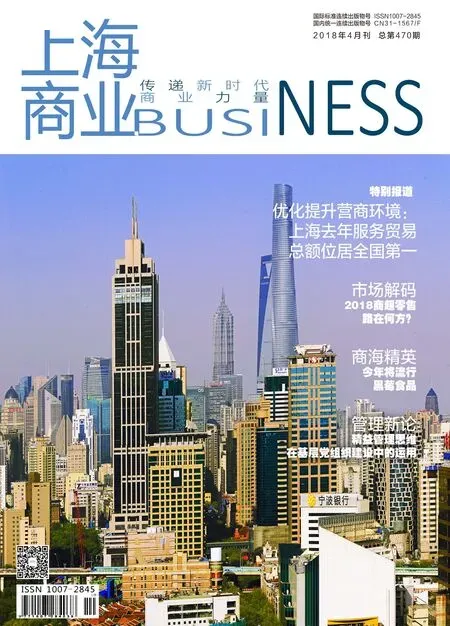香糟最知名,糟肉胜鱼蟹
—— 访老大同调味品有限公司掌门人王浩秋
文 /史 斜


认识王浩秋,是从糟肉开始。作为上海老大同调味品有限公司的掌门人,他浸淫调味品行业40多年,深得糟货之精髓,不仅熟谙糟料制作技艺, 而且精于糟货料理。
比如, 一块很普通的糟肉, 他可以制作出:肉溜黄魚卷,嫩滑的肉片津润着醇厚糟香、鲜嫩的黄鱼片里伴着淡淡的糟香。先食鱼,后食肉,整个品味过程精致典雅。值得称道的是,这个菜吃在嘴里没有油腻,是一款宴请宾客的美味佳肴。
再比如:小炒香糟肉,将香糟风肉切片、洋葱切块、青椒、红椒切块、冬笋焯水后切蒲片;热锅放油少许,将香糟风肉放入锅,快速煸炒至熟取出备用;锅内留油少许,放入洋葱、青红椒、冬笋煸炒,然后加少许酱油,放入肉片,翻炒片刻。出锅前放入少许鸡精,装盘上桌,味道好极了。
当然,好的菜肴需要有好的食材、好的工艺制作。老大同香糟肉,以该公司生产的三年陈香糟和双汇品牌肉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产品生产过程需经过鲜肉盐渍、糟制、凉干、风干四大工序,整个加工过程需20天时间。
用王浩秋的话来说,上海老大同调味品有限公司希望能为传承上海地方特色尽一份责任。
一
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黄酒。至少远在秦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把酒糟加工成为一种调味品了。
据考证:汉朝时有了“糟醉腐乳”,晋朝时有了“糟腌蟹”,到了北魏时,贾思勰已经可以在他那本著名的《齐民要术》里淋漓尽致地描写“糟肉”的做法了。
制糟之风,起于战国,盛于南宋,为江南寻常人家所用,最初应与食品储藏有关。非虚构类文字记载,见《随园食单》,如“糟鲞”、“糟肉”和“糟鸡”;虚构类的,就更多了:《红楼梦》提及“糟鹌鹑”、“糟鹅掌”的食风:那一股若有若无、有酒香无酒味的特殊的糟香,令人闻香而至,胃口大开;《金瓶梅》有“糟鹅胗掌”、“糟鲥鱼”之说:里外青花白地磁盐,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据说周代八珍中的“渍”,就是用酒糟浸渍的牛羊肉。
“糟”与“醉”相似,调料都源于酒,做法也相似,故有“糟醉一家”之称。江南自古为稻米产地,也是黄酒的故乡。除了众多的酒厂作坊造酒以外,民间农户都有酿米酒的习惯。米酒俗称“老白酒”,加点红曲就成了黄酒。秋收过后,谷粒进仓,家家户户就陆续酿起米酒。酒多了,酒糟也自然多。
但这种“远古的美味”真正得以不断升华并得以发扬光大,上海人功不可没,而其中最大的功臣,是 “老大同”酱园。
清咸丰四年,也就是1854年,在如今的广东路327号,一家酒店开张了,店名“大同酒店”。当家的徐老板有点文化,取了《易经》中“大有”、“同人”这两卦的意思来讨个吉利。
徐老板是苏州人,他来上海开店时,那会儿的上海才刚开埠11年。彼时,全中国把“糟”这种味型做得最好的就是苏州太仓。早在清乾隆时期,太仓人李梧江就做出了糟油。此后嘉庆年间的大美食家袁枚断言:“糟油出太仓,愈陈愈佳。”当时的《太仓州志》也说:“色味佳胜,他邑所无”。所以自然而然地,徐老板就把“糟”字特色当作一张品牌来打。
起初,这家大同酒家主要供应大众酒菜,兼供糟味卤菜外卖。想不到,本来是兼营的这种清醇爽口的外卖糟香卤菜,在当时还是个小县城的上海引起了轰动。此后开张的各家餐馆或多或少地在他们的菜单上也加上了一部分糟香味型的菜式,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跟了大同酒店的风。
为了稳定这种秘密调味品的货源质量,大同酒店的老板娘会定期回到苏州,按照大同酒家的标准,向做糟的酱坊“定工艺、定配方、定加工”下订单,再把这种香糟用船运到上海来。
1930年,徐增德把酒家转让给元和酱园的经理龚志祥等五人。新老板们接盘后,决定,只做调味品,具体来说,只做最受市场欢迎的那个“糟”。因为只要上海人还喜欢这一口,那么他们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按照当时上海餐饮市场约定俗成的规矩,他们也在招牌前加了个“老”字,以彰显自己的血统身份。这样,最早的“老大同酱园”就形成了。
1936年,浙江人王肈瑞出任老大同酱园经理,聘请技师范康年对香糟进行专题研发:对原料反复筛选,对配方不断调整。针对江南气候条件下何时制作为最佳质量的课题,他们进行了反复认证比较,费时数年,最终形成了香糟生产的原料、配方和工艺的《制糟要术》。使生产出来的香糟,味更浓更醇。由于味醇质佳,广受酒家饭店的喜爱,产品时常脱销。后来,商店扩大了生产规模,派员工到苏州、昆山、嘉善等酒厂监督生产,由原单一酒厂生产转为多家酒厂生产,保证了市场供应。
也许今天的人们只记得当年杜月笙是如何怀念“糟钵头”风味的那则故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没有“老大同”工艺定型在前,“糟钵头”很难做到让杜月笙如此念念不忘,此中,王肈瑞功不可没。
公私合营后,老大同酱园迁到了广东路233号,并更名为上海老大同油酱店。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此时的老大同香糟已在业内成为本帮菜烹饪的一种秘密武器。而它捧红的最著名的一家餐馆,就是本帮菜四大名店之一的“同泰祥酒楼”(另三家是荣顺馆、德兴馆、老正兴)
二
岁月荏苒,时光变迁。1976年,王浩秋高中毕业到老大同学徒。彼时,他是单位里最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但他也是一个有心人。他秉承了老一代上海技术工人的优良传统——踏实认真、刻苦钻研,随着老一代师傅们的退休,王浩秋成为厂里为数不多掌握香糟生产全部技术核心机密的人士。

香糟的生产工艺看起来很简单,将酒厂的黄糟运来,拌上老曲引子,再加上磨碎的香辛料,一起搅拌均匀后,封进小口的陶坛子里,陈放两年就可以了。但细细推敲下来,这里每一步都暗藏玄机。比如酒糟是味道的底坯,原料酒糟不好,香糟根本出不来,而原料糟是与黄酒厂的生产工艺分不开的,所以要做糟,先得懂做酒。其中奥妙,非局外人知晓
王浩秋介绍,香糟的制作工艺非常严谨,比如作为发酵种子的老糟曲种与原料糟的份量配比是多少,一定要把握“轻酵慢涨”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能放得太多,要在确保全部香糟发酵的前提下,尽量少地用老糟曲。再比如香糟味型的点睛之笔是中药香料配方,香料可以多一味,也可以少一味,比例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王浩秋说,就像炒菜时放的盐和糖一样,有一个宽容的范围,但一定有一个最佳的比例。这个比例,老师傅一般是不外传的。能够传给你的比例也能用,但往往少了一种味道上的神韵。王浩秋靠着自己的勤学苦练,加上参悟,掌握了其中的要义。
三
王浩秋是老大同香糟制作技艺第四代传人。有他参与制作的老大同香糟,在本帮菜糟味系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京、鲁、闽菜的菜谱中也常见其踪影,苏、杭菜则使用频率更高。
每到做糟的季节,他便一个人开着车,从上海赶到苏州吴江七都镇的香糟制作工厂。
走进工厂,只见一排排黄酒坛,酒坛中间一座高压电塔显得格外高大,这里看似有些不规整,却保留着传统的味道。
“我们全是传统的。有些人现在用塑料封口,那是不对的。你看我们的荷叶,还有当地特有的这种泥巴,它们都是透气的,发酵过程也需要呼吸。”王浩秋说,“这里边将近20味的药材都是我亲自配的,茴香要用哪儿的,花椒要用哪儿的,打碎的时候哪些要细一些,哪些可以粗一点,都有讲究,一点也错不得。”酒糟坛被涂成了黑色储存起来,等待它们的是至少两年的时光。
如今,用香糟调味的食材,可烹饪出许多脍炙人口的美食名肴:既有清凉爽口、增进食欲、回味隽厚的夏令糟味卤菜,又有沁人心脾、芳香四溢、回味悠长的冬令糟味汤锅;既有饭店厨师的精品糟菜,又有平民百姓家庭制作的一般糟味。糟味菜肴既是知己酒友的下酒良菜,又是青年白领电视机前的休闲美食。
长期以来,凡上海滩有名的饭店、酒家、熟食店(如和平饭店、锦江饭店、老饭店、杜六房、马咏斋等),均是老大同忠实客户。
王浩秋说:“上海不应该失去这个东西,它是上海的一张名片。最早苏州传过来,后来苏州没有了,上海传承下来了。苏州、无锡以前的都叫酒糟,上海人聪明,叫香糟,因为里边加了香料,现在大家都只认这个品牌。”
在王浩秋心中,香糟是风味调味品,它的滋味难以形容。似酒非酒、若有若无的陈年糟味,代表着上海的老味道,是根植在许多人脑海中的味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