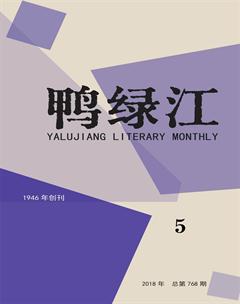无雨之城
武歆
1
躺在急诊科病床上的马青山用手指敲击床栏杆,他的意思孙青懂,那是指责孙青,见不到女儿马敏,你孙青是有责任的。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的孙青,还没来得及解释,就感觉有一张惨白的脸在眼前晃动了一下,定睛再看,已经不见了。
惊吓不已的孙青,看着马青山现在躺的病床,猛然想起来,这是母亲两年前躺过的病床。母亲就是在这张病床上心脏停止跳动的。孙青心慌意乱,对着马青山摆手说去厕所,赶快退出了病房。在关上病房门的瞬间,他听见马青山又开始敲击床栏杆。那是马青山气愤的特征,也是骂人的意思。晚年的马青山不爱讲话,似乎把嘴巴嫁接到了手指上,用敲击桌子、屋门、墙壁、暖气片、饭碗、碟子、地面甚至自己脑壳的方式来代替嘴巴讲话。他敲击得颇有耐心、极富特点,不同的情绪会用不同的节奏表达出来,听上去像是战争年代的电报声。
身心疲惫的孙青斜倚在走道的墙壁上,依旧能够听见病房内马青山发出的电报声,声音若隐若现,在马青山电报声的呼唤下,孙青怎么能够忘记母亲去世前与马青山蹊跷的关系?
那是马敏拿来的马青山年轻时的照片。马青山穿着一件黑呢子大衣,戴着黑色礼帽,站在一棵没有树叶的白杨树下面。照片的时间应该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冬季。当时母亲偶然看见,看着看着,脸上竟然掠过一派红晕,接着又是奇怪的惨白。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变得一言不发,总是出神地眺望窗外。孙青觉得奇怪,以后只要来看望母亲,几句话过后就会旁敲侧击、巧妙说起马青山。母亲听到“马青山”三个字,不接话茬也不说话,也不看孙青,依旧姿势僵硬地望向窗外。后来母亲患上了可怕的老年性痴呆。去世前的半年多,脑子更糊涂了,也可能不懂得躲避关于马青山的话题,偶然就会说起一些有关马青山的支离破碎的往事。
母亲说,那个戴礼帽的姓马的,年轻时是当官的勤务兵,后来那个当官的做了更大的官,他也跟着做官了,做得可不舒心。孙青问母亲,戴礼帽的是马青山吗?姓马的是马青山吗?戴礼帽的和姓马的,他们是一个人吗?你说的是马敏的父亲吗?母亲面对儿子孙青的盘问不置可否,继续自己的思路,开始讲起马青山的故事。当然那些故事都像碎片一样,前言不搭后语,是后来母亲去世后孙青一点一点整理并且连接起来的。
关于马青山的故事,孙青在整理母亲的“胡言乱语”之后,了解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1946年12月16日,刚刚过完15岁生日的马青山不顾爹娘的阻拦,偷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穿上军装、打上绑腿,做了团长何大炮的通信员(并非孙青母亲说的勤务兵)。马青山那时候不叫“马青山”,叫“刘宝福”。参加革命队伍之后,确切地说是在一场惊心动魄的雨夜之后,刘宝福才为自己改了姓名的,改姓马克思的“马”。
在还不叫“马青山”时候,刘宝福的最大特点就是腿脚快,团长何大炮一声令下,眨眼之间人已经蹿出了门外,只留下刘宝福跺脚跑走带起的尘埃。何大炮对通信员刘宝福非常满意,对他这个小娃子也很照顾,缴获敌人的罐头,他自己舍不得吃,也要给刘宝福吃。还把缴获的棉鞋、棉衣让刘宝福穿。何大炮这么好,刘宝福却是惧怕,他恨不得何大炮命令不断,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跑走传令,可以短暂离开何大炮。
刘宝福惧怕何大炮,源于1947年10月16日一场惨烈战役刚刚过后的雨夜。那天晚上,何大炮当着刘宝福的面突然开枪打死了叛徒,也是他颇为得意的侦察排长熊四狗。何大炮枪法极好,可以百步穿杨,面对站在眼前、不到五步距离的熊四狗,他就是闭着眼睛都能打死。何大炮骂了一句,突然转身,枪向背后一撩,一枪打在熊四狗的左胸上,熊四狗身子向前剧烈地倾了一下,竟然没有摔倒,接着努力站稳,大约几秒钟之后,身子又后仰了一下,眼睁睁看着始终背着身子的何大炮,身子笔直地向前冲去,何大炮也不躲,白杨树一样挺立,熊四狗的身子从他侧面冲过去,扑地一声摔在地上,这时候外面站岗的士兵提着枪、哗啦啦地拉着枪栓跑进来。
何大炮这才转过身,先是对着熊四狗尸体,然后对面前的战士,突然怒吼道,这家伙叛变了!那么多弟兄们牺牲了……我们被他出卖了!他提供了假情报,高粱村一战,死了那么多弟兄呀……
现场所有人都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何团长还有何团长拍在木桌子上那把依旧冒着袅袅白烟的盒子枪,随后几个人又一起看向嘴唇抖索、脸色惨白的刘宝福。显然,何大炮何团长怒吼熊四狗的叛变,需要刘宝福做证。
刘宝福吓得目瞪口呆,眼珠和手脚都是一个姿势,一动不动。
几个战士垂下脑袋,默默地把还带着体温的尸体抬了出去。他们掀开破旧帐篷的帘子时,外面的雨丝豪放地飘进帐篷里来,舌头像四肢一样僵硬的刘宝福看见外面泥泞的洼地上闪跳着无数的亮点。那是一个奇怪的有着月亮的雨夜。从乡村参军的刘宝福,记忆中即使下雨时出现月亮那也都是短暂的雨,可何大炮枪毙熊四狗的那个夜晚,之前却是下了好几天的连绵之雨。从那以后几十年,刘宝福——马青山——再也没有遇见过连绵雨天时还会出现月亮的夜晚。
那时因为战事吃紧,回后方的路已经被敌人切断,被停职的何大炮暂时没有回到后方接受调查,师部派来联合调查组,同时还要了解高粱村战斗失败的真正原因。
就在听说调查组马上来到团部的前一天,刘宝福失踪了。用何大炮的话说,刘宝福“开小差”了。
2
孙青不再拨打马敏的手机,马敏的手机反而通了,还是她主动打来电话,语调平静地告诉孙青,不用为她担心,她在秘鲁。
孙青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真的……我是在利马。马敏的声音倒是平静,似乎就住在孙青的隔壁,下一刻就会立刻推门进来。
孙青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问道,你出那么远的门,应该告诉我一声吧?我们是还没有结婚,可我是把你当作……
马敏接过孙青说了半截的話,道,走前没有跟你讲,是怕你不让我走。
你为什么去……利马?孙青完全糊涂了,大声质问,你知道吗,你父亲犯病了,前天住院了。我现在病房里。我在守护你精神错乱的父亲。
前天下雨了吗?马敏突然问,然后自答道,一定是下雨了。
孙青迟疑了一下,想起前天马青山犯病时……确是下了雨,进入冬季的华北不下雪竟然下了雨,让很多人惊诧不已。气象台解释说这是“冻雨”,历史上这座城市曾经有过很多次冻雨。下雨不下雨又能怎样,与你不辞而别跑去秘鲁又有何相干?
孙青气得啪地合上手机。他觉得马敏有事瞒着他。两人三年的“亲昵生活”好像他们从来没有走近过,尤其是最近半年来,孙青感觉马敏心不在焉。他认真检讨自己,似乎自己做得也没有什么不好。
可不管怎样,现在孙青也不能把马青山扔在医院不管,一切都要等到马敏回来再说。孙青越发感到不可思议,马敏为什么跑到秘鲁去了,难道仅是为了公司下达的通知——干休假再不休息年底就会作废?肯定不会是这样的原因。他觉得马敏是在寻找什么。
孙青一夜没睡,转天一早,昏昏沉沉的,他不敢闭眼,只要闭上眼,就有可能睡去。可是不能不管马青山,他最后还是去了医院。
孙青刚走进病房,个子娇小的护士就凑过来,似乎有话要讲。孙青见她犹疑,问她有事吗?
护士看了看安静睡觉的马青山,小声讲,马爷爷身体状况还不错,可就是……
怎么了……孙青问。
小护士说着,用手敲了一下自己脑袋,不眨地看着孙青。
孙青伸展一下双臂,让自己清醒一点,他倒是明白了小护士的意思,她是在用动作和表情询问孙青,马爷爷是不是脑子受过什么刺激?
你就说吧,孙青道,什么事?
老爷爷晚上自己说话,说得津津有味的。小护士看了一眼依旧熟睡的马青山,然后小声说,孙大哥,您晚上没来病房吧?
昨晚上我来病房……没有呀?孙青感觉头皮发奓。
我以为您不放心,来看看。
你们急诊病房不是不让家属晚上陪伴吗?
是。小护士说,有的家属不放心,晚上过来看,这种事经常有,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我没来。孙青说,莫非他女儿来了?
小护士可能听过主治医生介绍病人马青山家属的特殊情况,见孙青这样讲,想了想,坚决地摇摇头。
昨晚我值班。小护士指了指病房对面的值班台,说,我就坐在那儿,夜里安静,听见屋里马爷爷说话声,我抬头看见门不知怎么自己开了,我就进来看了看,看见马爷爷翻过身子,趴在床上,摇头晃脑地说话。
孙青走到门口,试了试病房门,感觉门很重,关上的话,绝对不会自己打开。
是不是有谁进来……忘记关门了?孙青猜测道。
小护士还是摇头,说,你们家属要是没来,别人不会进来。
走错门了呢?孙青看着楼道里来来往往的人,继续猜测道。
小护士似乎没听见孙青的话,紧接着说,好像是雨、下雨,对,马爷爷说下雨了,还说已经下了一百年的雨,什么时候能停?
孙青哼了一声,道,哪有雨呀,下了一百年……说胡话哩,不是胡话也是梦话哩。
小护士似乎不想争论是“胡话”还是“梦话”,看了看手表,说她该下班了,又对孙青叮嘱说,孙大哥,一会儿主任查房,您别跟主任讲这些。
不会讲的,孙青说。
小护士面容憔悴地去了护士站。
孙青看着还在熟睡的马青山,觉得他肯定晚上没睡觉,否则楼道里那么乱,他不会睡得那么香甜。孙青使劲儿呼出一口大气,又用双手使劲儿揉搓着脸,他忽然做了一个决定,决定晚上来陪伴马青山,看看马青山晚上梦话说的什么。又担心不是小护士值班,会有一些想不到的麻烦,就又到对面护士站,问小护士今晚还值班吗。小护士正在换衣服,把门打开一条缝,脑袋探出来笑道本来不该值班,另一个护士家里有急事,她只好替班了。孙青高兴了,说他晚上过来看看。小护士伸出食指,放在嘴边上,意思让他小声点儿,然后朝他点点头。
孙青刚回病房,急诊科主任查房来了,身后跟着一大帮人,有主治医生、护士长,还有医学院的实习学生。马青山终于醒了,面对一屋子“白大褂”,脸上毫无表情。主任跟他说话,他倒是也很配合,只是问一句、答一句,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似乎倒也清醒。主任又看了看病历,没说什么,带着人又去其他病房了。
3
当天晚上,孙青十一点钟来到急诊病区,果然看见小护士端坐在护士站里,在大本子上写着什么。孙青说够辛苦呀。小护士虽然看上去有些疲惫,但双颊上显出的一对小酒窝,消退了些许倦意。
孙青幽灵一样潜进病房,担心有电话打来,他猫下腰,把手机调到静音状态。
马青山果然没睡,大睁着双眼,歪着脖子,正在看窗外。白色的纱帘被窗户缝隙处吹进来的风鼓荡起来,好似一个曼妙女子在轻舞。
清冷的夜,清冷的月光,寂静的病房。
孙青搬過凳子,坐在病床边上,问马青山心口还疼吗?
马青山用手敲了一下栏杆,大概意思是说,你走。
我陪你,你是病人。孙青说。
马青山继续敲击,大意是说,我没病。你走。
孙青想了想,站起来,出了病房。
小护士问孙青怎么出来了?马青山说他不睡,我过一会儿进去。
孙青站在走廊里,左右看着。
走廊的西端很少有人去。那里是运送货物和垃圾的电梯,也是病人去世后“上路”的电梯。死人和活人是不能走同一电梯的,这个阴阳必须相隔的规矩,就像这座城市清末民初时期的四个城门,只有西门可以走棺材,其他城门是不可以走的。走廊西端那里有一架带轱辘的担架车停放在门口,那个担架车是为去世的人留用的,平时孤零零地停放在那儿,仿佛一具死去多年的干尸,从没有人去碰它,家属偶尔走到那儿,好像都有感应一样,看都不看它一眼,斜着身子赶紧过去。
走廊的东端,是病人和病人家属出入的地方。出了楼道的门,是片很大的空地,即使有六部电梯,白天还是排了长队;还有一处有长椅的阳光区,冬季时常有人在那里一边晒太阳,一边隔着落地玻璃窗眺望外面璀璨的夜景。
孙青迷蒙地去了走廊东端。
孙青站在落地玻璃窗前望着外面的夜景,等一会儿马青山睡着后,再悄悄潜入病房。大楼前方是一条河,河不宽,源头不知来自哪里,也不知流向哪里。在医院和小河之间有一条坑洼不平的小路,原本是医院大楼建好后废弃的路,却不想硬是被抄近道的车辆轧出了一条路。虽然路不好走,却比大道近了很多,白天车辆时常拥堵。孙青想起母亲去世后殡仪馆来的车就是走的这条路。当时孙青和两个姐姐没有想到这所医院没有太平间,病人去世只能联系殡仪馆的车马上接走。那天晚上也是这个时段,孙青从殡仪馆车窗向外望去,发现路边上隔几步远就是一堆燃烧的纸钱,烧纸钱的人们站成一圈,用木棒不断去撩拨没有烧尽的纸钱。孙青和姐姐纳闷,烧纸钱的人怎么偏偏集中在这条僻静的小路上呢?开车的司机告诉他们,医院大楼所在地过去是周边几个村庄的坟地。在周边村民的眼里,无论这里改造成什么,这里永远都是坟地。孙青多了嘴,问司机后来这片坟地的坟墓迁到哪里?司机好像全都了解,用下巴向小河对岸一撇,那里就是公墓。孫青和姐姐朝着河对岸黑漆漆的地方看去,模糊中看见一个没有灯光的壮观的门楼,心中猜测大概就是墓园的大门吧。那天晚上,不知是路不好走,还是司机忙着回答孙青的提问,车子好像轧到了一块石头上,剧烈地蹦跳了一下,紧接着孙青就感觉车上掉下了什么东西。司机说还能有什么东西,门都关着呢。于是车子也没停,继续向前开。两个姐姐暗地里用手拉了一下孙青,让他歇会儿别说话了。果不其然,到了殡仪馆,孙青发现母亲住院时穿的一件灰色毛衣外罩没有了。当时那件灰色毛衣外罩搭在一个白色脸盆上,脸盆里面放着漱口的水杯、牙刷、牙膏,还有洗脸的白毛巾、洗脚的灰毛巾。脸盆还有脸盆里面的东西都在,唯独那件肥大的灰色毛衣外罩没了。不是掉在车外了,还能掉哪儿了?孙青清晰记得是他把灰色毛衣外罩搭在脸盆上,又拿到车上的。
孙青看着小河对岸的墓地。那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看见鬼魅般的墓园门楼。已经夜深人静了,孙青回到病房外,悄悄把病房门打开,弯腰挪了进去。整个过程无声无息。他坐在床铺尾部的沙发上,正好看见马青山被子里面鼓起来的脚,头靠墙壁的马青山根本看不见他。他真的听见了八十五岁的马青山在独自说话,也像是跟人对话。孙青仔细听,只是始终无法把前后意思连接起来。每句话都像是正常的话,但每句话又都具有独立的意思,只要把两句话连接上,马上就会是另外一个不知所措的意思。
黑暗中的孙青闭着眼睛,耐心地仔细听着,后来他终于听到了一个跟他有关的名字——于丽娇。
4
马青山住的是急诊病房,住院费用每天都要结清。这一天,孙青交完费用,在自动打印机上打印住院明细单。
这是一台自动柜员机,在住院部的进口处。对面是挂号处和交费处。柜员机的显示屏上有各种触摸式按键,诸如门诊挂号、自助缴费、自助预约、取号、凭证补打,最后一项是患者信息。
孙青打印完毕马青山的住院明细单,好奇心驱使,他想看看“患者信息”里面是否还存有母亲的信息,犹疑了一下,像是触碰火热的铁块一样,快速用食指点击了一下屏幕,提示出现——请输入患者姓名。
孙青有些慌乱,感觉心脏跳得极快,输入了母亲的名字——于丽娇。提示再次出现:请输入患者身份证号。孙青手有些抖,紧张地屏住呼吸,一下、一下按出了如下数字——“××××××19440416××××”。
孙青完成上述操作后,屏幕上赫然出现了“于丽娇”的信息,什么时候住院、病情、死亡原因……孙青感到特别奇怪,人已经去世了,怎么里面还留有信息,莫非机器出现失误没有删除?留存一个死人的信息还有什么作用?
孙青看了看四周,都是匆忙的人,问谁?没有一个人肯停下脚步,眼睛都是盯着各个窗口,办理各种手续。
孙青走向门口的导诊台,柜台里面坐着一位身穿护士服的中年女人。孙青讲了情况,中年女护士脸上有些茫然,似乎这个问题她从来没有遇见过,没有人问过她。
人已经……去世了?中年女护士双眼像是刀子,不解地说,那你还查什么资料呢?想跟医院打官司?医疗事故?
孙青觉得无法对话,气鼓鼓地离开了导诊台。
身边都是走来走去、急匆匆的人。没有人去关注已经很多天没有安稳睡觉、精神恍惚的孙青。直达电梯前挤满了人,孙青一点儿耐心都没有,掉头就朝前方走,去走相对来讲人较少的电动扶梯。
远远地,迎着光亮,他看见前方一个坐在轮椅车上的身穿灰色毛衣外套的老年妇女,虽然老年妇女的背影被推轮椅车的女人阻挡,但那背影像极了去世的母亲,尤其是那件灰色毛衣外套,他甚至怀疑就是母亲的那件,就是从殡仪馆车子上掉下来的那件。孙青紧跑几步到前面,转过身子去看,当然不是母亲,怎么可能是母亲呢,母亲已经死了,已经变成了一捧白色的骨灰。
脑袋昏沉的孙青,记得在母亲于丽娇老年痴呆之前,曾经跟女儿——孙青的姐姐——概括性地说过“自己的情史”,却始终没有说起“那个人”的名字,孙青把听母亲说过的那些“糊涂事”与姐姐讲的有关母亲往事片段相互联系在一起,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母亲说的“那个人”就是“马青山”,因为“那个人的故事”与“马青山的故事”相互吻合。
母亲于丽娇与马青山认识。
何大炮打死了熊四狗,之后上级把何大炮停职了,让他交代问题。最初是让他回到后方接受调查,可当时战局吃紧,把何大炮调离,一时没有适合的人顶上去。上级派来一个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调查组组长是师政治部副主任老窦。老窦的调查重点是,何大炮是怎么知道熊四狗叛变的?熊四狗叛变是否影响到了高粱村一战的失败?只要把这两点调查清楚、能够互相对应,问题就会解开。熊四狗真是叛变,那是罪有应得,何大炮最多接受处分。反之,情况就复杂了,就要调查何大炮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打死熊四狗?是否想要通过熊四狗“叛变”之事来推卸他指挥高粱村一战失败的责任?
当时何大炮跟调查组老窦的解释是这样的:熊四狗是叛徒,证据确凿。因为熊四狗从上到下都是疑点。短枪没有了,剩下一把匕首,短枪一定被敌人缴了;脸上、手上一点伤痕都没有,假如没有叛变的话,真是被敌人抓住,应该有搏斗痕迹的,起码脸上、手上都应该有伤才对;熊四狗带领一名士兵一起进村子外围侦察,那名战士死了,熊四狗却活着;应该当夜返回,熊四狗却是转天晚上回来的,一天的时间去了哪儿,高粱村虽说是个大村子,但也不该滞留一天,还能躲到哪儿去?只能是被敌人抓住审讯,然后又被放回来并且提供了假情报,说高粱村只有敌人一个连,可实际上周边还有埋伏,而且是配备了美式装备的一个营,兵力差距如此大,所以导致转天过后的高粱村一战的彻底失败。
老窦反问何大炮的话也很有力。除了你,还有谁能做证熊四狗叛变?只靠短枪丢失、脸上没伤这点情况,不能证明熊四狗叛变。那名战士的牺牲也不能代表熊四狗叛变。最关键的是,在何大炮打死熊四狗之前,没有经过审讯,没有证人。侦察不清与故意隐瞒提供假情报,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问题。
何大炮面对上级老窦的质问,永远都是硬邦邦的一句话:当时由于气愤过度而失手打死熊四狗的,现场有人,通信员刘宝福就在现场,他是可以做证的。同时何大炮有理有据地还原现场情况,说他刚一拔枪,熊四狗就跪地求饶,说他做了错事。窦主任你说,他不是叛徒怎么会求饶呢?老窦双眼鹰隼一样看着何大炮,一字一句地追问道,熊四狗是承认自己没有侦察清楚,还是承认自己当了叛徒?犯错误和叛变投敌是不同性质的问题。何大炮怔了怔,说当时下雨天,他又在气头上,没有听清。老窦没言语,但目光始终没离何大炮脸上。
于是现场证人刘宝福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可是……可是通信员刘宝福“开小差”跑走了。后来又多次询问当时进来抬走熊四狗的几个站岗的士兵,几个人都说当时刘宝福吓傻了,像个木头橛子一样戳在那儿,什么都没讲。
何大炮的事只能暂时放下。当时对何大炮的处理是暂时降级,降为副营长。这件事师部没有给出明确结论,老窦始终觉得这件事没有确凿的证据,尤其是通信员刘宝福的“开小差”,没有这个重要的现场证人,更不能直接定罪熊四狗了。刘宝福的“开小差”是不是与熊四狗之事有联系?于是,这件事变得更加疑窦丛生。所以对何大炮的处理并不代表最后结论,也就是说,是把何大炮的问题给“挂”了起来。
这一“挂”,就是一年多,直到这座城市迎来解放,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5
孙青始终认为,母亲与父亲的婚姻并不幸福。
在孙青以及两个姐姐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跟父亲友善地说过话,说不了几句话就会吵起来,就会给父亲甩白眼。母亲家里有钱,她上过私塾,认字,能看报纸。父亲从乡下来,解放后上过“扫盲班”,但也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能囫囵吞枣地看报纸上的图和照片。
母亲嫁给工人阶级的父亲,在外人面前意气风发,恩恩爱爱。但是到了晚上,从她床下甩白眼、床上背对背来看,她还是看不起老实巴交的父亲,她实际的婚姻理想是找一位革命干部或是戴眼镜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布鞋厂的工人。用母亲的话讲,“凑合过呗”。但是后来……后来她认识了马青山,情况急转直下。
于丽娇认识马青山,充满了戏剧性。
解放后,师政治部副主任老窦还有团长何大炮没有继续转战,而是同时转业到了地方,有意思的是,他们竟然一同转业到了纺织系统。老窦被任命为纺织局的书记,何大炮当了一家纺织厂的书记,两个人依旧是上下级的关系。于丽娇是何大炮任职的那家纺织厂的女工。
那家纺织厂有数千人,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企业。能进那家纺织厂当工人是莫大的荣耀。在那家纺织厂当上领导干部,那就更是大荣耀了。
“进城”后的何厂长看不上自己的黄脸婆了,娶了纺织厂一個年轻漂亮的女工。原配老婆不依不饶,从农村哭着上告到了市里,而且直接告状到了市长那里,上级准备处理何大炮,当作典型来处理。就在这时,关于熊四狗的事又被牵扯出来。原来解放后熊四狗的家人一直找上级领导,要给熊四狗一个公正的说法,说熊四狗是烈士,绝对不是叛徒。上级正在处理何大炮“换老婆”的事,加上熊四狗的爹娘上访,于是干脆就把两件事一起处理。
于家与熊家有点亲戚关系。于家住在城里,熊家住在城外;于家家境好,熊家穷,解放前熊家曾经找亲戚于家借过钱,借十块,也就给两块。按辈分算,于丽娇应该是熊四狗的表妹。
熊四狗的家里没有识字的,熊四狗的娘就找到了于丽娇。一来于丽娇识文断字,二来又和何大炮一个厂子,解决问题容易一些。熊四狗的娘倒不是要把何厂长怎么样,就是想给儿子一个烈士名分。
解放后,于家和熊家的地位不一样了。熊家来求办事,于家也想办,想要拉近关系,于是于丽娇家立刻答应下来。但是熊四狗的娘不知其中关联,要给熊四狗正名,就必须把何大炮打倒;不打倒何厂长,就无法给熊四狗正名。这件事不容易。但是于家也答应了,必须办。于丽娇想到要找当年那个“开小差”的通信员刘宝福。
刘宝福去了哪里?那时候,谁都不知道刘宝福就在邻近一座县城里,只不过已经不叫刘宝福,有了新名字——马青山。
窦书记决定通过军管会通报协查,无论是死是活,一定要找到刘宝福。于是军管会向华北地区已经解放的城市发出了协查令。其中一张协查通知正好到了马青山手里。
这时候的马青山是河北沧县的公安科科长。
6
马青山已经住院四天,孙青也忙碌了四天,再加上马敏蹊跷的利马之行,孙青更感身心疲惫。可是母亲与马青山之间逐渐清晰起来的关系,又让孙青有些亢奋。他发现直接跟马青山对话,老人的表现常常是混乱的,反倒是他的自言自语偶尔清晰,而且信息量极大,当然需要剔除夹杂其间不知所云的一些梦呓——“你还记得吗,我们从北京上船,四个小时就到了维也纳”抑或“我们见面,是呀,在地中海见的面”——从某些只言片语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再重新组装,就会发现数十年前的画面。
孙青夜晚走进病房前,发现走廊西端那个带轱辘的担架车停在病房门前。这是谁把车放在这里了?孙青左右看看,走廊一个人都没有。护士站也没有人,可能这会儿值班护士去了厕所或是去了其他病房。孙青把手搭在担架车上,要把它推到走廊西端。把手异常冰凉,仅仅通过手掌,一下子就把全身的热气都给吸走了。可是一只手却无法推好,担架车左右摇摆,只好两只手都用上,身体感觉更凉了。
静静的楼道,只有担架车艰涩前行的声音。孙青终于把车停稳在电梯旁,转身就走,却被什么东西拽住了,瞬间感到头皮发奓,转过身,原来大衣下摆恰好夹在车子缝隙处。
孙青头也不回地赶紧走进病房。
马青山没有睡,也没声音。孙青坚强地坐在病房的黑暗处。
时间慢慢过去,困意慢慢袭来。他抑制住困意,努力睁开眼睛,脑海竟浮现出了母亲与马青山数十年前的会面。
穿着黑呢大衣、头戴黑色礼帽的马青山,站在了于丽娇的面前。
我叫刘宝福,现在叫马青山。
于丽娇怔住了。寻找多年的证人,自己出现了。她看了看墙上的皇历——1955年11月16日。
车间副主任于丽娇换好衣服,带着马青山走出车间,走在厂区大道上。
于丽娇穿着双排扣的“列宁服”,扎着两条辫子,额头留着刘海儿。虽然她只比马青山大两岁,却显得非常成熟。
马同志。于丽娇似乎也不知该从哪里说起,你怎么找到的我?
马青山说,我现在在沧州公安局,找到你不是很难。
当年……你为什么开小差?
我无法面对,只好逃跑。马青山伤心地说,何大炮团长不是坏人,他是无法面对那些牺牲的战士,他心里无比悲伤。熊四狗也不是叛徒,他是英雄。
那你呢?于丽娇看着黑色礼帽下英俊的脸。
马青山低下头,久久不肯抬起来。
厂区大道人来车往。于丽娇与认识的人打招呼。但是许多人不看她,而是看身边的马青山,然后脸上露出会意的笑容。
我今天来办案,顺便把我的案子也办了吧。
怎么办?
我们一起去见何厂长吧。
于丽娇这时才发现,马青山已经把她领到了厂长办公的那排平房前。更让于丽娇惊讶的是,何大炮正好站在办公室门前,静静地看着他们,似乎也是在等着他们。
马青山走到近前,向何大炮敬礼。何大炮感慨地拍了拍马青山肩膀,把他让进屋。
屋里冰凉,炉子已经灭了,地上堆着劈柴、煤块。显然何大炮正想把炉火点上。于丽娇蹲下身,想帮助点火,被何厂长止住了。
屋里死一样静寂。
何大炮没有一点惊讶,像是昨天刚跟马青山见完面一样。他沉吟片刻,叹了口气,说,这些年我总在想,当初不该……不该答应你那个愚蠢的办法……也把你害了呀……现在想想,我就是觉悟太低了。
团长你别说了,我是心甘情愿的,我从来没埋怨你,开小差是我想的办法,马青山连珠炮一样说,你是气火攻心。高粱村一战失败,你是气糊涂了。你认为熊排长侦察不力,你是失手打死熊排长的。
何大炮道,我每年都给四狗上坟。我对不住他,他这条命早晚我要还给他。
于丽娇这才明白什么,急问,何厂长,每个月熊四狗的娘都能收到汇款……也是你吧?
那点钱算什么,四狗的命都沒了。何大炮叹口气,让他背了这么多年不好的名声,我对不住他。
我们完成任务了。马青山激动起来,你让我给你五年时间,说是把厂子建好,你就投案自首。我刚才看了,多么漂亮的工厂,想不到盖起了那么多厂房……那么多工人宿舍……
何大炮站起来,望着窗外宽阔的大道。
一会儿,我陪你一起去自首。我要接受处罚。
责任在我!何大炮把马青山推到一边。
于丽娇吃惊地看着眼前两个泪眼模糊的男子。她明白了,在这五年时间里,何大炮跟马青山始终有联系。
革命江山打下来了,我怎么也得添上几块砖、加上几块瓦,然后再去陪我四狗兄弟呀!何大炮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转。
马青山上前一步,抱住何大炮,两个人紧紧地拥抱。
于丽娇眼泪流了下来。
7
2017年12月16日。马敏从利马打来电话,孙青刚一接,马敏就哭泣起来,她喊道,利马下雨了,真的下雨了。
下雨又怎样?孙青疑问。
利马一百年没有下雨了,这是一座无雨之城。马敏说,为什么要下雨?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孙青茫然无措。
马敏哭道,你不知道,当年我爸爸陪着何叔叔去自首,何叔叔……就是何大炮,他要求上级枪毙他,后来熊四狗的娘也出面了,央求法院不要判刑何厂长。
最后呢?孙青急问。
马敏说,何叔叔最后被判刑二十五年,后来病死在狱中。
你父亲……马叔叔呢?
马敏说,我爸爸要求上级处理自己,后来他被开除公职,退回原籍,在街道清洁队做卫生。后来历次运动……你知道那是怎样的结局……最后留下了后遗症,一到雨天,就会看见熊四狗被打死的场面,他的心脏就会犯病……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忍受着,我想帮助爸爸解脱困境……
孙青似乎明白了马敏秘鲁之行的想法。
我想要为我爸爸寻找一座无雨的城市,马敏声音颤抖地说,可是一百年不下雨的利马……却在今天下雨了。
孙青站在医院走廊东端的落地玻璃窗前,他举着手机,无法回答马敏。这时候他看见外面的天空飘起了亮晶晶的东西,那是雨……这座城市又下冻雨了……最近几年连续冻雨。
对面的墓地掩映在雨中。
你怎么不说话了?远在利马的马敏说。
孙青恍惚起来,那一刻,他看见马敏的身体在利马的夜雨中抖颤。
【责任编辑】 邹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