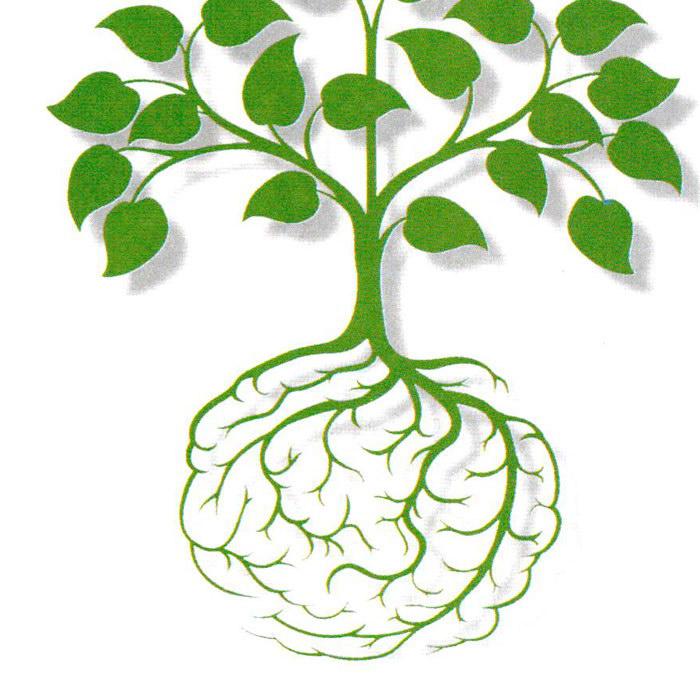聪明的植物
莫妮卡·加利亚诺是西澳大学的一名进化生态学家,最近她一直在为自己的实验结果而焦心。加利亚诺的课题组在做一个关于植物联想学习的实验:能否像巴普洛夫训练自己的狗那样训练一株豌豆。两个星期过去了,实验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大家都以为这一实验已宣告失败。
一天,当加利亚诺进入实验室准备拆掉所有的器材时,突然间,她明白过来——那些植物的行为不正如她之前所设想的那样吗!只是那些植物做得太好了,远远超出了研究人员之前的预料,以至于一开始他们都没能察觉到。
就这样,加利亚诺和她的研究小组证实:你完全可以像训练狗那样训练你的植物。巴普洛夫的狗一听到铃声,就知道食物快到了,而加利亚诺的豌豆们要学习的是风扇与光线的关系。
研究小组将这些豌豆的种苗种植在一个由管道组成的迷宫内,豆苗在生长过程中会不断碰到分岔口,它们得决定接下来自己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最初的三天是训练的关键期。加利亚诺将豌豆分为三组,并在迷宫的一边设置风扇朝这些豌豆们吹风,同时又架设了一些发光设备,以便输送出豌豆们最爱的蓝光:第一组,风扇的风吹来的方向与蓝光出现的方向一致;第二组,风扇的风与蓝光所在的方向正好相反;第三组为对照组,其风扇所在位置与蓝光所在位置没有关联。
进化生态学家莫妮卡·加利亚诺正在研究不同种类植物的认知能力。
研究人员以豌豆苗作为研究对象。
实验中,豌豆幼苗被放置在塑料管道构筑的迷宫内,它们需要去学习找到自己生长所喜爱的蓝光。A组要学会将风扇与同方向的蓝光联系起来,并循着风扇所在方向生长;8组需要学会将风扇与反方向的蓝光联系起来,并循着风扇所在方向的反方向生长;C组为对照组,风扇与蓝光之间没有联系。
实验显示,这些小小的豌豆的学习能力太强了!短短三天,它们似乎就完全明白了那架吹风的风扇与获取自己喜爱的光线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三天后,一旦管道内送风开启,第一组的豌豆便会明确无误地往风吹来的方向生长,第二组的豌豆却坚定不移地朝着风来的反方向蔓延,而第三组豌豆的生长方向则呈现出随机的特点。
这样的迷宫实验最初是由动物研究发展而来的,于是,加利亚诺的团队也以为豌豆一开始会和大多数动物一样随意地生长,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些向光而生的小小植物,其自身系统中的适应性与学习能力是如此的強大。
对此,加利亚诺感叹道:“当我看到豌豆们的生长行为时,其结果完全打破了我的设想。之前,在我所接受的学科训练中,或者说大多数的学者都相信,向左还是向右,这样五五开的选择是随机的。但豌豆们教会了我一点,那就是有时你得超越自身的思维限制去想问题。”
加利亚诺团队的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植物拥有联想学习的能力。这一结果不但令人惊叹,也同时反映了一个事实,那便是一直以来,我们都过于低估植物的能力了。
有思想的根
早在1880年时,查理·达尔文便提出了一个理论猜想:植物拥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能够像人类的大脑那样处理信息并决定根系的生长。直到1990年,德国波恩大学的一名植物细胞生物学家弗兰蒂泽克·巴鲁斯卡才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并试图证明达尔文的相关理论。
巴鲁斯卡承认自己以前对于植物也存在轻视态度。在其职业生涯早期,他只是怀疑在植物的根系中,有一组细胞至关重要。许多年后,他才和同事发现,这些细胞不但重要,而且是植物的指挥中心。巴鲁斯卡认为:这些细胞是高度专业化的,负责采样并处理信息,输出信号,决定根的生长。这与我们人类的神经细胞十分类似。
如此一来,植物拥有一个根植在土壤里的“大脑”也就说得通了。巴鲁斯卡认为:在土壤里存活并不容易,对于根来说,要想成功地从土壤中吸收营养物质,取决于至少20种物理参数,如温度、湿度或者重金属含量等。不仅如此,这些参数还时时处于变化的状态,需要植物不断地采集数据并分析。所有这些信息都会被植物一一处理,并最终作出正确的决定,决定它们该朝哪里生长。我们可以把植物想象成有着与人类相颠倒的发育体制的生物——它们把头深深地埋在土里,后背与生殖器官却留在地面上。虽然这一图景很难形容,但要知道,达尔文对于植物的形象也有着类似的想象呢。
植物的根不仅重要,还是指挥中心。我们可以把植物想象成有着与人类相颠倒的发育体制的生物——它们把头深深地理在土里,后背与生殖器官却留存地面上。
植物的记性
不管这些植物的“大脑”到底长在哪里,也不管对于“植物大脑”一说学界还有多少争议,许许多多的植物行为研究都已表明:植物远比我们所以为的要有头脑得多。例如,植物的记性可是极好的。如果你忘了给自己家里的绿植浇水,它们也许不会生气埋怨你,但它们会记住你的这一疏忽。
为了研究植物的记忆,科学家们采取了一种名为“干旱胁迫”的效应作为辅助。在2015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把三周大的拟南芥苗从土里拔了出来,用滤纸轻轻拍打它们的根将水分吸走,再将它们放置在干燥的环境中暴露两个小时。喝不到水对于植物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情,这会让它们压力倍增。两小时之后,当这些年幼的植株被放回水里时,面对新环境它们显得十分迟疑,仍旧表现出时刻准备忍耐干旱的样子一叶片上的气孔半闭着:一方面限制水分的摄取,一方面也保证自身水分不会过多地流失。
研究人员用3星期大的拟南芥苗进行试验,暴晒两小时后再放回水里,幼苗仍旧表现出时刻准备忍耐干旱的样子——叶片上的气孔半闭着。
其实,在2014年,加利亚诺便已针对植物的记忆开展了自己的研究,不过她选择的是另一种植物——碰一碰就会缩紧自己叶片的含羞草。熟悉含羞草的人都知道,哪怕只是用手指轻轻拂过表面,这种敏感的植物也几乎瞬间就会将自己的叶片闭合。不过,加利亚诺与她的同事这次采用了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来对待含羞草。研究人员把含羞草从6英寸(约15厘米)高的地方扔下去,以保证其能够做出反应。是的,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被扔下去时,含羞草都赶紧闭上了自己的叶片。不过从第四次开始,这一反应开始变得有些迟缓。在第60次被摔下之后,含羞草对于这样的遭遇彻底免疫了,可能知道摔下去不会有什么事。即便过了一个月,它们似乎仍然记得这一点。因此,当一个月后再次将它们从这个高度扔下去时,这些害羞草根本不会理睬。有意思的是,如果此时研究者改用摇晃的方式而非将其扔下去,含羞草便又会赶紧闭合上自己的叶片以防止被伤害。这一实验表明,并非是疲惫让它们在被摔下去的时候丧失了做出反应的能力,而是记忆为之。
植物竟然可以做到这样?!它们确实能做到。因此,我们应该换一种角度来提问题,我们应该问: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对于这个问题,现阶段植物学界还未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有几种猜想被提了出来。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记忆是基于植物细胞中钙含量的波动而留下的压力痕迹,与动物的长期记忆形成机制相类似。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植物的记忆可能属于自然界中的表观遗传效应。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基因组DNA决定着生物体的全部表型,但后来逐渐发现有些现象无法用“经典遗传学”理论来解释。比如,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生双胞胎在同样的环境中长大后,他们在性格、健康等方面会有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在DNA序列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生物体的一些表型却发生了改变。因此,科学家们又提出了“表观遗传学”的概念,它是在研究与经典遗传学不相符的许多生命现象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前沿学科,它是与经典遗传学相对应的概念。现在人们认为,基因组含有两类遗传信息: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遗传信息,即基因组DNA序列所提供的遗传信息;另一类则是表观遗传学信息,即基因组DNA的修饰,它提供了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去应用DNA遗传信息的指令。例如,老鼠可以通过改变基因的表达方式,从父辈身上继承可怕的记忆,而不需要对DNA本身进行任何改变。
在第60次被摔下之后,含羞草对于这样的遭遇彻底免疫了。
这一点在植物身上同样适用。2015年,加拿大科学家发表了他们对于印度油菜——一种与大头菜有着亲缘关系的油料作物的研究结果。研究人员将两个星期大的油菜幼苗反复暴露在高温下(大约41.7℃),之后,再让这些植物在一个十分舒适的温湿度条件下成长繁衍。当采集这些植株的后代组织做检测时,研究人员发现:即便这些新一代的油菜从来没有遭受过高温袭击,但它们仍然拥有着耐高温的表达基因,而这正是表观遗传记忆的明显标志。
黄岚植物间的窃窃私语
和人类一样,植物也会运用许多办法来探测周围的生存环境。即使不能依靠自己的记忆来对环境进行比对,它们也始终能够通过菌根网络来彼此交谈,以知晓身边都在发生着什么。这个隐藏在地下的菌根网络系统连接着植物的根系,利用相互交织的真菌进行信号传导。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森林生态学家苏珊·斯马尔德是菌根网络研究的著名学者,在她眼里,菌根网络就像电话线一般,将植物与植物直接用管线连接在了一起。
人类首次证实植物会通过地下网络进行“交谈”的研究始于2013年。来自英国的科学家们将蚕豆分为三组:第一组名为“警报员”——这组倒霉的蚕豆将被饥饿的蚜虫包围,这些蚜虫将会津津有味地咀嚼蚕豆植株直到完全吃掉它们;第二组蚕豆通过地下的菌根网络与第一组蚕豆相连,但它们不会遭到蚜虫的袭击;第三组蚕豆为对照组,既不会遭受害虫威胁,也不会与其他两组蚕豆有任何联系。研究人员发现,第一组“警报员”通过菌根网络释放出的化学物质,成功地通知了第二组蚕豆有昆虫袭来的危险。收到警报的第二组蚕豆则立即开始释放驱逐蚜虫的化学物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不在菌根网络之内的第三组蚕豆则对此毫无察觉,完全不知危险已经逼近,也没有释放出任何驱逐蚜虫的物质。
为了证实这些蚕豆可以完全通过根系相互交流,研究人员还将三组蚕豆分别用塑料袋封了起来,以防止它们利用空气传播化学物质来传递信息——要知道这可是植物們常用的另一种“交谈”方式呢!当你走进森林里时,深深地吸一口气,感受一下森林中的空气,你所闻到的便是树木的“话语”。许多植物交流时所产生的挥发性化合物都含有气味,正因为这样,我们有时才可以感知到它们之间的“对话”。一项1983年的经典研究显示,当某些树木的叶片因虫蛀受了伤,其身边健康的邻居们也会释放出酚类和鞣酸类物质等天然的驱虫剂,仿佛自己也遭到了伤害一般。
植物之间会交流,被蚜虫包围的蚕豆会告诉它们的同类:有危险。
当植株被置于缺水的环境中,它们就会拉响警报,通知“邻居”。
当然,可能你会问,这些植物真的是在“交谈”吗?有没有可能这只是其中的一些个体在“窃听”自己的邻居呢?例如,当某一植株正被昆虫吞食的时候,另一棵植株恰巧监测到了其释放出的驱虫物质,而这并不能说明前者是有意识地在向大家发出警报。还好,这点疑问已经被以色列科学家对豌豆进行的干旱警报研究所排除了。
以色列科学家将其中一株豌豆置于缺水的环境中,以使得它们拉响干旱警报。当这株豌豆监测到水分缺乏时,就会释放出化学物质,其邻居接收到信号之后,便会将自己叶片上的气孔闭合,减少水分的流失。不过,这样的警报传递并未到此停止。
研究人员发现:那些接收到警报的植株,哪怕自身并未遭受缺水的威胁,也会开始释放信号物质,将干旱的警报传递给更远的植株,告诫它们做好准备,迎接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困难时期。植物们做这些并非因为什么无私的精神。拿豌豆来说吧,抵御干旱就如同抵御昆虫袭击,虚弱的植株更易遭到伤害。如果自己周围的邻居都健健康康的,那么它们就更不容易吸引那些喜欢啃食叶片的昆虫到访,这才是皆大欢喜的局面。
信息会从一棵植株直接传递到另一棵植株,这改变了它们的行为。我们人类会通过声带推动空气发出声音,而植物却是通过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到空气中。植物释放的这些化学物质也是一种“语言”,是属于植物的“语言”。而且,如人類一样,植物之间也有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个体间会释放不同的挥发性物质到空气中,这些挥发物质就好比词汇一般,有的是在表达某种意思,有的则仿佛是植物的“签名”。因此,亲缘关系越近的植物,它们的语言也更相近,它们之间的交流也就更加容易与顺畅。
在2014年进行的一项蒿属植物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有的蒿属植物偏向利用樟脑进行对话,有的则喜欢通过侧柏酮(与苦艾酒中的致幻物质恰好是同一种)来交谈,但不论哪种,只要构成语言的物质类似,植株间相互通报昆虫来袭的消息时便更为顺利。另外,植物还能将父辈的语言继承下来,用同样的语言来“说话”。共同的语言还能帮助植物辨别自己的亲属呢。
弄清楚自己的家谱
如果你是自然界中的一株植物,那么在你的有生之年里,不管是好是坏,你基本上都将生活在被整个家族所包围的环境之中。对于自然界中的植物来说,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促使它们去识别自己的亲属:一是避免与亲属展开竞争,另外就是可以从亲属关系中得到好处。竞争是相当耗费能量的行为,那么,你会在生存竞争中相信谁呢?你的亲属分享着你的基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的成功也是你的成功,这便是基本的裙带关系的由来。加拿大科学家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拟南芥会对它们兄弟姐妹传递过来的物质进行采样,一旦识别出自己亲属的“签名”,它们便会约束自己根系的生长,以便给亲属留下更多的资源。但如果它们识别出分泌物来自于陌生植株,这样的约束行为就不会发生。
植物不仅通过语言,它们还能够根据彼此的身形来辨认出自己的“亲属”。当然,亲属的身形往往和自己的长得差不多。在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来自阿根廷的生物学家们将拟南芥分开种在成排的盆中,并进行了不同的设置。例如,有的拟南芥与自己的亲属植株被陌生的植株间隔开来,而有的拟南芥植株间被放置了塑料滤光器,还有的则启用了光受体缺失的转基因植株作为实验对象。在分析了所有的数据之后,研究者们断定:植物可以通过辨认身形来识别自己的亲属,这是因为植株的光受体能够感知到环境中各种红光及蓝光组合,并进一步通过周边植株反射的红蓝光来对彼此的轮廓进行建档。试想一下,这就如同在拥挤的人群中,你的朋友朝你走了过来,即使光线混乱,她的面部特征也并不清晰,但你依然能够辨认出她来。对于植物来说,一旦识别出与自己身形相似的“亲属”植株,之前所说的裙带机制便会启动,植物会将自己叶片的生长方向远离亲属植株,以防挡住了对方的光源。
植物可以通过辨认身形来识别自己的亲属。一旦识别出自己的亲属植株,植物便会将自已叶片的生长方向远离亲属植株,以防挡住了对方的光源。
捕蝇草通过计算猎物触碰其感觉毛的次数,就可以判读出这只倒霉的昆虫的大小,以及何时该关上叶片捕捉猎物,甚至能借此知道该分泌多少消化液。
除了能够彼此交谈,能够识别亲属并记住压力事件之外,植物甚至能够计数。就拿捕蝇草为例吧。这是一种原产自美国卡罗莱纳州湿地上的食肉植物,当一只苍蝇飞进它的陷阱里时,捕蝇草便会关闭叶片,并开始消化它的猎物。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植物会计算猎物触及陷阱外部感觉毛的次数,并以此确认捕捉到的是活着的且可食的猎物。一下、两下,叶片闭上了,三下、四下、五下,消化液此时开始分泌。其实,这其中的机制十分简单,但却使人不禁联想起动物大脑中所发生的事情:触碰感觉毛就会触发电信号传递,或者说“动作电位”的传递(“动作电位”是指可兴奋细胞受到刺激时在静息电位的基础上产生的可扩布的电位变化过程。神经纤维的动作电位一般历时约0.5~2.0毫秒,可沿膜传播,又称“神经冲动”),这与动物的神经冲动十分相似。
对此,有科学家解释:植物会通过陷阱所传播的动作电位次数来判断,到底是没用的枯枝落叶掉了上来,还是捕到了可口的猎物。计数同样需要记忆,起码植物得记住之前已经有几次动作电位传递过了。
如果植物既能够学习,能计数,还能识别自己的亲属,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植物会思考么?或者说它们聪明吗?有意识吗?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大部分取决于你会怎样去定义智力与认知。不过,我们对于植物的看法总算是改变了。几年前,只要提及植物行为,可能没有谁会相信你的研究。但现在,关于植物行为这一概念已经不存在争议了。
我们过去之所以认为植物不具备智力,完全是因为习惯使然,因为大多数人依然对植物报以轻视的态度。心中所想会影响眼中所见,如果你坚持把植物看成一种不具目的性的生物,那么你对它的认识也不大可能进步。现在是我们转变对植物认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