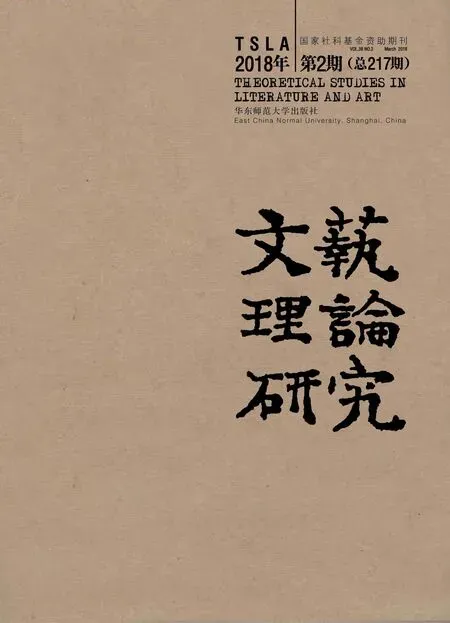从动物视角看“物化”中的道家情感论
胡素情
一、“物化”中的物种间情感现象
“物化”是庄子哲学的重要概念,它既是“道”的本体论和宇宙论表象,也是通往道家功夫论和境界论的必经之路。“物化”一般指万物间的相互转化,也可引申为纷繁世相的变化。但如《说文》所释,“物”也有“动物”之意:“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庄子》最初的“物化”语境也与动物相关: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谓之物化。(《齐物论》)
无可否认,“物化”的典型范例是一只昆虫。更重要的是,醒后的庄周“蘧蘧然”,暗示失去自我身份的瞬间恐慌。然而“物化”的目的正在于此:“化”的反差越大,“物化”的体悟更深刻,“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在这个意义上,“物化”既是人向昆虫转化,更是人向自己的对立面——动物的转化,它的隐含逻辑是对人类-动物差异的二元消解。事实上,动物在“物化”中频频出现,如鲲鹏之化、子舆死后“化予之左臂以为鸡”(《大宗师》),又如《天运》中的“程生马,马生人”,无不是令人惊奇的动物之化。也只有推衍到人类-动物关系时,“物化”才能彰显更重大的颠覆和转化意义。可见,动物是“物化”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物化”潜藏着人类-动物关系的哲学张力。以此,本文认为庄周化蝶的动物案例并非偶然,很大程度上,“物化”就是人与动物之化。
“物化”中的人类-动物关系在“濠梁之辩”中进一步彰显: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
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这个故事有两种动物观:惠施主张绝对的物种差异,庄子主张人类-动物的同一性。它与“庄周化蝶”一道反映了中国古代思维在战国末期的两大重要分支:一是以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的逻辑和思辨的认识论进路,如《庄子》提及的“坚白离”“白马非马”之论;另一是庄子强调的主客合一、物我亲密的诗性情感进路,“化蝶”和“知鱼”正是这一进路的物种间情感案例。无独有偶,庄子对“物化”中“化作动物”的快乐之情多有向往,他羡慕鲲化鹏徙的逍遥(《逍遥游》),愿变成乌龟自在地“曳尾于涂中”(《秋水》),或“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大宗师》),动物自由、优美、适意的自然之态深深感染了庄子。对动物世界的向往暗含对人类身份的厌倦离欲,对它者的惊奇和艳羡,情感意欲是“物化”的重要驱动。正如有西方学者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庄周梦蝶的心理机制,认为梦蝶是人深层欲望的表达(Skogemann 77),化蝶、知鱼或想象鲲鹏之化时,都不乏与动物相关的情绪驱动。可见,“物化”不仅有着动物的身影,更潜藏着人类-动物间的情感现象。
物种间情感论反映了庄子对他所在时代弊病的反拨。诚如孔子认为诗可“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自然的对象化,人的主体化和符号化始于春秋;至战国晚期,以名家为代表的分类和逻辑思维渐臻成熟而自成一派,而庄子恰恰处于这一转折时期。他深刻意识到自然客体化的分类和求同异等逻辑思维带给人的弊端:“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分化会导致种种情感困顿:“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齐物论》),因而庄子以“混沌凿七窍而亡”的寓言主张回到混沌如一的大同世界。也如葛瑞汉(A.C.Graham)所言,庄子对扭转以惠施为滥觞的古代中国逻辑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体现了一种原始主义进路(198)。这既表现为以自然(动物)对抗人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又表现为以感性对抗理性,如化蝶、知鱼。概言之,向着动物的“物化”能弥合人与自然的分裂并疗愈这一疏离带来的情感创伤,“物化”背后有庄子对人类情感状态的关注及解决之道。
人类-动物间情感如何可能?德勒兹和瓜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的“生成-动物”及其情状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后现代的理论启示。他们将人向动物的转化归于一种“广大的移情”(a vast empathy),即在与动物他者接触过程主体受其感染导致情感或感知上的变化,这一人与外物在身心交接下的移情状态被称为“情状”(affect),而动物恰恰能“给人一种未知的,不可思议的感觉——一种情状”(A Thousand 258),如一个人面对中毒濒死的群鼠感受其苦痛的“神魂颠倒”之状(268)。
庄子进入蝴蝶和鱼的“物化”之境与德勒兹等人的“生成-动物”及其“情状”十分类似。“物化”也大多是在某种感觉或情绪中的身心动态中发生的,如“梦蝶”就是一种半清醒,半混沌的“梦”的身心情状,人被蝴蝶的自由翩跹激起对自然的向往和脱离伦常自我的强烈欲望。知鱼之乐、羡鹏高飞,都有人对动物的情状勾连。可以说,庄子向动物昆虫的“物化”也是“生成—动物”,它们并非人幻化成动物,而是逼真情境下脱离自我想象其他身份的创造性异质体验。庄周梦醒时分有失去自我的瞬间茫然和恐慌,但在移情性体验中自我的短暂缺席却换来了扩展身心、通往他者之境的独特感受。庄子对于这点应是了然于心的:《齐物论》中,子齐要听天籁,必须“形容枯槁”,清空自我虚位以待,在天籁中达到“吾丧我”的境界。爱莲心(R.E.Allinson)指出,庄子不仅意图突破庸常思维,还刻意解构自我,重构自我,其“忘我”“丧我”是自我解构,而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则是自我重构(491)。庄子的“忘我”并非完全消弭自我,而是将主体意识缩至最小,在移情中体会天地万物,进入“道”的境界。借用柏格森的话,面对自然万物,庄子要“进入”而非“绕行”,如吕梁丈夫蹈水,“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达生》)。就动物而言,最典型的例子是庖丁解牛时消弭了感官自我与对象客体之间的二元关系,将自我消融于牛所蕴含的自然天理的肌理之中;佝偻承蜩时“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因凝神于蝉将自身化为“株拘”和“槁木”(《达生》)。 鱼之乐、鹏之逍遥、化蝶的适志之情表明,《庄子》主张在动物昆虫的影响和感染下以主体的消弭和低伏姿态重返动物的天然本真,达致“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同一”(《齐物论》)的移情之境。以德勒兹和瓜塔里概言之,“纯粹的情状包含一种去主体化的运动”(A Thousand 270),反言之,“物化”是部分让渡主体性去成为他者的过程,潜藏着情状的生发。
二、“物化”中的情感本体论
如果说“情状”概念从后现代哲学视角启发我们对“物化”中物种间情感的理解,下文将回到中国语境探究“物化”中“情”的确切生发。庄子的“物化”之“情”既是对主客分化理性思维的反拨,也有着战国末期流行的气化宇宙论基础。《庄子》持有气的发生论:“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万物互相转化,“通天下一气”,都是气的“委形”(陈鼓应35)。生命的本质在于流动之气,物化就是气化,气化也是物化(赖锡三,“气化流行”50)。其次,气与其高级形式如精、神、魂、魄的密切关联还预示着气的心性论和情感论。有学者指出,气一方面通向躯体,一方面通向心灵(杨儒宾 444)。气与情的关联早现于《左传昭公25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庄子·在宥》称尧舜“矜其血气以规法度”,“血气”就是人的情感冲动,《论语》《礼记》《荀子》中也可见血气与情感之关联。成于庄子与后学之间的《性自命出》曰:“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其实是以气指情。稍晚的《管子·禁藏》已有气情之说:“故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穀,衣食足。”很显然,在《庄子》的成书年代,气与情已存在或隐或显的关系。
《庄子》虽未直言情发于气,但常以气论情志变化。《庄子》中,我们能发现两种情绪类型。一是气、物交接中的前情绪兴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亲不和”(《渔父》)。 气凝成“精”,可以“动人”,表现了人与万物在生命网络中交接时的前认知状态和情绪变动。《大宗师》道:“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四时乃时气、物气,它们对人的情绪感染在《庄子》中多有表现,如“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知北游》)。即便是“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他们也无法逃避宇宙气化带来的身心变化:“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大宗师》)。庄子以气的融通为理论依据,将人和万物关联在一个拟人化的“有情”世界中,气化流行中的万物难免于各种情态:“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
《庄子》中情的另一形态是复杂的人情纠葛:充溢于身体和万物的气无时不在变化和运行中,人、事、物的交接中必然充满了气的多寡、凝滞、冲突,从而“物有结之”(《大宗师》),致情志失调,如“阴阳并毗,四时不至[……]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在宥》)。如赖锡三所言,庄子深刻洞察礼教、伦理、关系、价值等文明规范对身体的符号制约和割裂;“混沌凿七窍而死”的寓言表明,身体不仅在符号化和主体化的过程中丧失其天然本真之气,更意味着与天地生命之气阻隔疏,带来各种身心情感困顿(“《庄子》身体观”10)。“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齐物论》),从这个角度看,庄子主张“无情”:“[……]庄子曰:‘所谓无情者,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言”(《德充符》)。
在庄子看来,气通于物是自然之情,气滞于物则多为人为之情。前者是外界激惹下的本能情态反应;而后者更多是社会产物,是人加诸自身的情感纠葛。两种情的区分反映了战国末期“言志”传统下个人之“情”仍未正式确立,带有非个人化和中性化特征。同时,“物化”既为气化,“气”“情”不离,那么气、物交接而成的个体必然是情状中的自我,潜藏着“情绪”或“前情绪”的生发,这在理论上将情上升到宇宙论或本体论的高度,有助于情的“合法化”。但“物化”之情的自然旨趣凸显了情的物质交互性和原始唯物论色彩,“受而喜之,忘而复之”(《大宗师》),某种程度上带有被动和消极色彩,回避了情应有的社会维度及自我构成的丰赡情态,使之成为类似风雨阳晦的自然现象,有将情简单化、客体化的倾向。
不难理解,“物化”以气的交感打开封闭自我,使被名、知、德、欲遮蔽的异化自我重返气通于物的流畅性,对保持情志舒畅有重要作用。动物作为“物”的代表和自然的典型表征,它对人类-自然之间的“复情”有特殊作用和意义。首先,动物是物化循环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庄子·秋水》形象地描绘了气的作用下生物链条的形成:“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在战国晚期气化生成论的背景下,其中的“机”即为气。可见,动物是气化生物链条及其完整循环的重要环节。而在庄子诟病的对象化思维发轫之际,“道在蝼蚁,何其下也”,人类-动物之分可谓“天下为道术裂”的典型表征。向着动物生成与气化,气的融合便越有意义,越能弥合人与自然分离的巨大鸿沟,摆脱与自然之气割裂导致的情志困顿。
其次,相对于其他万物,动物与人类之间“物化”的情感关联更可能、有效。如前文所述,《左传》用“血气”指情绪冲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以“气”“血”“血气”来区分生物与非生物,且动物与人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气之精粗。《礼记》《荀子》《列子》《语丛》等皆提及,“血气”为生物所特有,是性情和情绪的直接来源。汉代王冲则直接指出,因“血气”之故,鸟兽在情绪和欲望上与人类并无二异(《论衡·道虚》)。以上观之,在《庄子》成书年代,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相似和相通性有着丰富的背景支撑,动物作为有血有情之物,特殊地享有“万物”中能与人“物化”的物质和情感基础,同时也规定了“物化”中情感的自然向度。
三、“物化”中的情与动物具身化
如前文所述,身体的“物化”即气化,气引发情,情物并生意味着身体的生成与感知和情感同时发生,是一个具身化(embodied)的过程。在分析思维不占优势地位的古代中国,具身化是人的常态。《庄子》不仅重视身体,更开启了以形入神的先河,这一点毕来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吴光明(Kuang-Ming Wu)、赖锡三等学者多有论述。但他们并未体察到动物与道家身体的关系。《庄子》中体现了大量对动物身体的模仿、企羡和操练,尤其在对理想人格和人生状态的功夫论塑造中,动物是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如: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主寿考者之所好也(《刻意》)。
夫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天地》)。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
真人、圣人、神人们自如而不自觉的动物身体切换体现了人的动物本真和人作为自然之物的理想状态。如果说身体往往是社会规约及符号的傀儡和绑架对象,向着动物生成,无疑是对社会规范机制的反抗,体现了庄子反智、反权力的身体政治实践。这既是不断追寻生命直觉和自发性的回归之路,也将人从种种世俗考量和情感困顿中解脱出来,达至身心愉悦的情绪状态。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逍遥游》)
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狼之野。(《应帝王》)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就空间而言,“物化”的“气”媒介不仅意味着不同身体的融合,更意味着身体空间的主体间性及其中间状态。身体随物化之气延展空间,气情不离,人与物、物与物的交接间会形成类似于情的空间氛围(aura)。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 Ponty)从现象学角度有着相似的描述:我们的身体与环境之间有着类似于情感(sensibility)的感知,它是非理性、前语言的(qtd.in Burkitt 75)。因而,就动物而言,“物化”意味着在化身为动物的代入感中达成自我与动物所在空间的情感融合,进而融入近“天”的自然情境。如庖丁解牛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毕来德在《庄子九札》中认为,“神”并非庖丁身上或身外的某种力量,而是一种类似于“境界”的身体“机制”(régimes)(22)。 本文认为,若以“气”释“神”,更能体现人与牛之间气化融合交接之态,也为具有空间色彩的“境界”概念提供了一种物质解释。化作动物的“物化”意味着人以动物为媒介对环境的想象性情境进入,是以身体交感感知动物及其所在的自然山水,并在空间上发生情感联接和渗透。
四、“物化”关于动物的抒情性书写
我们知道,道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反语言”的,道家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对语言挟带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暴力等幽暗本质最敏感且炮火猛烈者(赖锡三,“神话·变形”7)。这在《庄子》对杨朱“坚白离”的关注以及数次庄惠之辩中可见一斑:庄子对抽象概念语言与隐喻性语言的分野高度自觉,也对命名与分类带来的淆乱了然于胸。“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人间世》)。他受困于语言的悖论陷阱,既主张无言,又要“强言之”“尝言之”,即便已言说,又反复质疑言说的真实性:“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齐物论》),表现了对语言的深度质疑以及在“语言的分裂处”的流连反复。因而在语言有效性的矛盾中折衷地运用流动的,富于弹性的语言或是庄子寻求的语言策略。
《庄子》中大量动物形象暗示我们,作为叙事主角之一的动物或是庄子突破语言逻辑,回归诗性言说的策略之一。而动物与语言的隐秘关系在于,动物曾参与了语言的构成,是“语言分裂处”的一个特殊存在。“语言的分裂”指语言在指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言语和语言、符号和语义之间的分裂,而最初与人类共享语言符号的动物则被摒弃于人类“话语”之外(Agamben 59)。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有类似的响应:动物是出入前语言(pre-linguistic)与再现性语言的动态力量,是突破再现性象征语言系统的活力因子(10—12)。
庄子虽未直言“语言分裂”和“前语言”,但无不渗透对相关问题的洞见。动物为庄子打破言说的悖论僵局提供了另一种可行性。如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即便狮子能说话,人类也无法理解,这意味着在承认动物主体性的前提下,动物有不经人类语言媒介的难以言喻或辞不达意的经验和存在。又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动物的论述:动物在人类语言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动物所缺乏的,正是像人那样“通过能指并受制于能指而成为主体”的东西(130)。这些“缺乏”既是语言指涉链条的断裂处,又是语言指涉的逻辑真空。如果说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因而可算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那么庄子的动物言说也屡屡挑战人类的有限理解。如《逍遥游》中“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或雕陵中庄子见到异鹊发出的疑惑:“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山木》);或极端性:道“在蝼蚁”“何其下也”《知北游》;或不容于世的非实用性,如“大而不能执鼠”《逍遥游》的斄牛。这些无法理喻的动物意象不仅表明经由语言的人类思维之狭隘,更以其模糊性和不可言说直指语言的有限及其内在漏洞,故庄子“以马之喻白马非马,不若以非马之喻非马”(《齐物论》),他秉持的正是以难言之物(如动物)言难言之物(道)的语言策略。这与庄子“正言若反”的否定性思维特征是相通的。动物这一不可知、不可言之物使得语言本身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它们来去无踪,变动不居,直指言说的虚无和逻辑的空洞。动物书写不仅提供了理解“道”所需的非人类视角,而且提供了一种来回于语言和前语言中间地带的非逻辑指涉言说方式。
不难理解,庄子主张重返以动物为代表的前语言之境,因而“物化”的语言哲学意义在于,当人回归以动物为典型表征的“物”的状态时,将必然脱离以语言建构的自我,就像卡夫卡《变形记》中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那样,动物式的失语成为割裂他与人类世界关联的最大鸿沟和标志,将他引向了德勒兹式的,对艰辛恶俗生活机器的逃逸和超脱。庄子对动物“无知”“无言”境界的孜孜以求,无疑也是对“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引发“是非之谓”,使人“苶然疲役”的人世生活的逃离。濠梁之辩中,庄子打破人、鱼之分,以看似狡辩的方式指出语言固有的逻辑漏洞,其实质是摒弃语言对物的指涉功能,以身心的情状感知恢复万物间相即相入的状态,是在直观中追寻物之诗性,从概念回归情感的动态过程。
关联动物的前语言使得言说成为将发又似未发、情感与理性混杂交缠的话语方式。这在《在宥》的鸿蒙中有充分体现:
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鸿蒙方将拊脾雀跃而游。云将见之,倘然止,贽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为此?”鸿蒙拊脾雀跃不辍,对云将曰:“游!”云将曰:“朕愿有问也。”鸿蒙仰而视云将曰:“吁!”云将曰:“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鸿蒙拊脾雀跃掉头曰:“吾弗知!吾弗知!”云将不得问。
在这个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中,智者鸿蒙总处于“拊脾雀跃”的半人半动物状态,面对“云”从语言中获得普适之道的渴望和希冀,他以“游!”“吁!”等叹词对之,并以“弗知”草草离场。这暗示语言初期的半透明状态:既是感性抒发,又有命题取向。而且,这一辅以身体语言的言说为我们提供了述行和转化的动力,如鲲“化”鹏“徙”,“雀跃”而“游”。进而本文认为,庄子的动物书写本身就有功夫论或操演论的修为(perform)之意,它是经由写作“生成-动物”,在审美情绪中实现自我转化的有效途径。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指出,卡夫卡的《变形记》书写就是经由“生成—动物”实现对宏大叙事的逃逸和解域,是反意义的,有强度的语言操作(Kafka 22)。庄子屡屡通过动物重温与物为春的逍遥喜悦,它们在语言中是更直观、纯粹、身体化的感性真实。先秦哲学典籍中,也唯有《庄子》出现大量的动物形象并常充当主角,体现了从人类向动物世界的频频回顾、从文明到“蒙昧”,从理性到诗性的逆向运动。庄子的写作本身就是以书写为身体实践,在“物化”中“生成—动物”,成就诗性自我回归的过程。
结 语
如陈世骧所言,中国文学的光荣,在抒情的传统里(32),情物关系当属这一抒情传统的关键性内容。从动物视角考察“物化”,可以细致而微地观察“情”如何在初发阶段战胜语言逻辑进路的叙事冲动,挣脱先秦“言志”的政治怀抱,并在“物”中回归自然向度。一般认为,情从“志”中脱出逐渐独立要到荀子的年代,写于战国晚期的楚简《性自命出》对情的大规模论述则标志着“尚情”思想的确立。而从“物化”中的“气情”关系看,《庄子》不仅最早尝试将情从志中剥离出来,确立了理想化个人情感的自然维度、空间化和具身化,还蕴藏着物感、感物、物色乃至意境等一系列中国抒情概念的哲学基础,可谓是中国抒情传统核心内容的最初滥觞。当然,《庄子》的“物化”并非凭空而来,它有着古代中国原始文化的深厚背景,也广泛存在于庄子及同时代人的思维当中。细察之下,“物化”又并非原始思维的活物论,而是有意为之的感性对理性的反拨,是向着以动物为代表的自然之物与人类的亲密情感的回归;而《庄子》也以书写为媒介践行了这一道家情感论。
注释[Notes]
①本文的《庄子》引文皆出自[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篇目随文括注。
②吴光明认为《庄子》体现了中国式具体的“身体思维”,即思维离不开身体,身体也是思维着的身体,见Wu Kuang-Ming.On Chinese Body Thinking(Leiden: Brill, 1997) p.291;毕来德对《庄子》中身体的技艺性操练有深入的探讨,认为“出神入化”的身体技艺性操练是体“道”入“神”的必经之路。简言之,体道是在娴熟进而自发的身体式“无限亲近”与“几乎当下”中实现的(“庄子四讲”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gamben, Giorgio.Infancy and History.Trans.Liz Heron.London: Verso, 2007.
Allinson, Robert E..“On Chuang Tzu as a Deconstructionist with a Differenc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0.3&4 (2003):487-500.
毕来德:《庄子四讲》,宋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Billeter, Jean Francois.Four Readings about Zhuangzi.Trans.Song Gang.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9.]
——:“庄子九札”,《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2卷第3期“毕来德与跨文化事业中的庄子研究专辑”(上),(2012): 1-36。
[---.“Nine Chapters of Zhuangzi.” Chines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Communication 22.3(2012): 1-36.]
Burkitt, Ian.Bodies of Thought: Embodiment, Identity and Modernity.London: SAGE, 1999.
陈鼓应:“论道与物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台大文史哲学报》8(2005): 33-37。
[Chen, Guying.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 and Things.”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Journal of Taipei University 8(2005): 33-37.]
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陈世骧文存》。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
[Chen, Shih-hsiang.“Lyrical Tradition of China.” Works of Chen Shih-hsiang.Taipei: Zhiwen Press, 1972.]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
Derrida, Jacques.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Graham, A.C..Chuang Tzu: The Inner Chapters.London:Unwin Paperbacks, 1986.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Guo, Qingfan.Chuang-tzu and Its Comments.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Kristeva, Julia.Powers of Horror.Trans.Leon S.Roudiez.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赖锡三:“神话·变形·冥契·隐喻——老庄的肉身之道与隐喻之道”,《台大中文学报》33(2010): 1-44。
[ Lai, Xisan. “ Myth, Transformation, Mysticism and Metaphor: Body and Metaphor of Laozi and Zhuangzi.”Chinese Journal of Taipei University 33 (2010):1-44.]
——:“《庄子》身体观的三维辩证”,《清华学报》42.1(2013): 1-43。
[---.“Three Dimensional Dialectical View of the Body.”Journal of Tsing Hua University 42.1(2013): 1-43.]
——:“气化流行与人文化成”,《文与哲》22(2013):39-96。
[---.“Flowing of Qiand Forming of Humanity.”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2(2013): 39-96.]
Skogemann, P..“Chuang Tzu and the Butterfly Dream.”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31(1986): 75-90.
Sterckx, Roel.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Albany: SUNY Press, 2002.
Tuan, Yi-fu.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王冲:《论衡校释》,黄晖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
[Wang, Chong.The Book of Lunheng with Comments and Annotations.Ed.Huang Hui.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Wu, Kuang-Ming. On Chinese Body Thinking.Leiden:Brill, 1997.
杨儒宾:“支离与践行——论先秦思想里的两种身体观”,《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杨儒宾主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415-50。
[Yang, Rubin.“Broken and Performing: Two Views of Body in Pre-Qin Thoughts.” Qi and Body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s. Ed. Yang Rubin. Taipei: Juliu Book Company, 1993.41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