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世界历史”
——赫尔德的“狂飙突进”剧论与激进启蒙
冯 庆
一、 “狂飙突进”中的“莎士比亚”
正如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伴随着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大量译介一样,德意志“狂飙突进”也具有鲜明的“比较文学”色彩,其基本的理论主张大多通过对其他民族与文化系统的经典进行批评而得以生成。尤其是,英语与德语据说是日耳曼语同宗,德意志知识人在英国作家,尤其是莎士比亚这样的伟人那里找寻自己的“民族气质”,当然也没什么问题。可以看到,除了盖尔斯滕伯格(H.W. Gerstenberg)的《试论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天才》之外,莱辛在《现代德意志文学通讯》和《汉堡剧评》中的评论与赫尔德的著名论文《莎士比亚》(Shakespear
)算是德语知识界最有理论建树的莎士比亚评论。莱辛与赫尔德不像盖尔斯滕伯格那样依据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戏剧理论来厘定莎士比亚是否“高雅”,而是试图给予莎士比亚的创作方式一种新的哲学解释和艺术评价。显然,他们不仅是在对作为英国民族作家的莎士比亚进行评论,还旨在为德意志未来的文学创作寻找新的法则和尺度。作为“狂飙突进”的理论宣言,赫尔德的《莎士比亚》具有显著的思想史地位。文学史一般认为,通过聆听赫尔德关于莎士比亚的教诲,歌德明确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奠定了十九世纪欧洲的基本文学主流及其历史主义基调(勃兰兑斯19—27;梅尼克407—38)。那么,赫尔德对歌德进行的教诲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莎士比亚》结尾处他对歌德所说的这段话:
我的朋友啊!你在读这篇文章时,会认识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我曾不止一次在他的神圣形象(heiligen Bilde)前面拥抱过你,在这个时代,你还能怀有这样一个甜蜜的、配得上你的才干的梦想: 从我们的骑士时代(Ritterzeiten)取材,用我们的语言,为我们的变质如此之甚的祖国建造起他的纪念碑!我羡慕你有这样一个梦想,希望你不放松你高贵的德意志事功(edels deutsches Würken),一直到花环高高挂起!(Grimm520-21)
“神圣形象”指莎士比亚。而这里的“纪念碑”会让我们想起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夫子自道的著名诗句:
我完成了这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恒久,比皇家的金字塔更巍峨[……]我为寒微的出身赢得了尊严,率先引入了艾奥里亚的诗歌,调节了拉丁语的韵律。(贺拉斯51)
在这一互文关系中,赫尔德似乎是在暗示歌德像贺拉斯那样,通过引入新的作诗方式来重新建立起德意志诗歌的典范。显然,这指的就是莎士比亚的作诗方式。赫尔德相信,德意志的文化精神在拉丁语和法语文化的侵蚀之下,已经“变质”;唯有重新回到“骑士时代”,才能将其找回。敏锐的歌德对此呼吁给出的回应,则是在从莎士比亚历史剧中获得大量营养的《铁手骑士葛兹》(G
ötz
von
Berlichingen
mit
der
eisernen
Hand
)一剧里塑造了“只听命于上帝、皇上和自己的自由骑士”葛兹这一形象(歌德24)。1771年10月,歌德在法兰克福的莎士比亚命名纪念日上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其中提到:
莎士比亚的舞台是一个美丽的百像镜,在镜箱里世界的历史挂在一根看不见的时间的线索上从我们眼前掠过。[……]他的剧本全部围绕着秘密的一个点旋转(这个点还没有哲学家看见和确定过),我们自我的特殊性,僭拟的自由意志,与整体的必然的进程在这一个点上发生冲突。可是我们败坏了的趣味使我们眼睛周围升起了一阵这样的迷雾,以致若要使我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几乎需要把世界重新创造。(“汇编”290—91)
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狂飙突进”运动选择崇拜莎士比亚的几个根本见解: 首先,莎士比亚的剧作里面包含着对“世界历史”之线索的洞察;然后,莎士比亚的剧作呈现了个体自由意志与整体必然进程之间的冲突,之前的哲学家们对此困难的表述都不如莎士比亚清楚;最后,莎士比亚的创作能够启发德意志的诗人们,让他们从败坏的趣味中解放出来,尝试通过革新文学趣味,开创新的世界。
——其实,这都是赫尔德直接传授给歌德的教诲,并在《莎士比亚》一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历史告诉我们,在“狂飙突进”之后,歌德的这些见解得到了大多数德意志文化精英的认可,歌德本人则最终成为了不亚于贺拉斯和莎士比亚的文学大师,的的确确为德意志文学树立了“纪念碑”,让后来人不断瞻仰。那么,赫尔德的教诲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调动起歌德走向不朽的志向呢?
歌德的三个见解其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让我们从第二个显得最为“哲学”的见解说起。在《莎士比亚》一文开篇,赫尔德就描述了一个能在暴风骤雨中安享阳光的莎士比亚形象,他远远高于文学圈那些攻击挖苦他的人,能够“寓一于多和寓多于一”(vielfach einfältiger und Einfach vielfältiger)——这等于是在说莎士比亚是一个符合“形而上学定义”(metaphysischen Definition)的诗人,能够调停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和文学创作中的特殊性(Grimm507-508)。具体说来,人们在观看莎士比亚的戏剧时:
就像面对着一片汹涌澎湃的事件之海(Meere von Begebenheit)一样。自然的场面不断前进,不断后退,它们虽然各不相同,却相互产生深刻的影响;它们不断产生,不断消灭,为了使作者的意图得以实现,这位创造者似乎在他的貌似充满醉意和混乱的构思中把这一切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了——这一切都是模糊的、微小的象征,为神之神义论(Theodizee Gottes)作出概括说明。(Grimm 509-510)
赫尔德认为,莎士比亚在处理历史事件时具有一种诗人的“天才”,能够通过构思来整合自然发生的事件,使之构成能够彰显基于神之意志的“神义论”。一旦将这样的莎士比亚与其他同时代墨守“三一律”的剧作家相比,不难发现,赫尔德的理解本质上在于凸显戏剧超出客观形式规定的主观的“历史化”维度,并给这种天才披上神义论的外衣。
赫尔德认为,通过高明的手法,莎士比亚的每部剧作在观众眼中都是广义上的历史剧,是“为了造成对中古时代的幻觉而上演的历史、英雄行动和国家大事!或者一件世界大事里的、一个人的命运里的一个完整的、有长度的事件。”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
空间和时间本身根本算不了什么,它们是最相对的东西,为此在(Dasein)、行动、激情、思想过程以及主观上和客观上的灵魂的注意程度所制约,这一点难道还用得着对世界上任何人加以证明吗?[……]现在你设想你一霎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进入了一个诗人的世界,或者只是进入了一个梦境[……]你没有感觉到,随意给自己创造空间、世界和时间标准的,只是这个心灵么?[……]诗人的空间和时间就存在于他所写的事件的进程中,存在于他的世界的ordine successivorum[先后的秩序]和ordine simultaneorum[同时的秩序]中。(Grimm 517-18)
在康德那里,时间和空间是先验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它们是感官认识现象的前提条件(康德37—39)。在赫尔德这里,诗人的天才正在于能通过营造空间和时间的内在主观感知秩序来左右人的心灵。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客观的历史时空被悬置,得到艺术性凸显的是剧作家悉心安排的剧中人物的自我存在状态以及由此引出的行动、激情和思想。剧作家能够任意凭借他自己对应然的时空规律的把握而让笔下人物“亲在”遭遇的事件变得比真实的历史更加有秩序。这样一来,我们能在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那里看到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所表达的全新的人类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营构的事件发生逻辑并非旨在呈现业已发生过的历史,而是“表现”应然的、可能性的历史。这种历史直接对观众的“心灵”产生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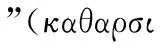
二、 莱辛与赫尔德戏剧观的异同
文学史的常识是,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之所以能够得到德意志文艺评论界的重视,是因为莱辛的大力倡导。《诗术》的最早德译本出版于1753年,译者库尔提乌斯(Konrad Curtius)算得上是莱辛与赫尔德的同时代人。莱辛在德译本出版后不久与书商尼柯莱(Friedrich Nicolai)和学者门德尔松就如何理解《诗术》曾经有过著名的“关于悲剧的通信”,在其中,莱辛主要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赫尔德同样感兴趣的那个问题——“悲剧怎样引起情感”。对此,莱辛给出的答案曾经是 :“最好的悲剧是最有力的激起情感者,而不是适于净化情感者”(《关于悲剧的通信》84)。在这个阶段,受到来自哈奇森、沙夫茨伯里和卢梭的同情论学说的影响,莱辛一开始先是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畏惧”与“赞赏”都与人和人之间的社会性“同情”关联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悲剧具有的强烈的世俗道德功效并非直接宣扬道德观,而是激发人的自然同情 :“同情却直接教人向善,无须我们自己参与其事;它既教化有头脑的人,也教化傻瓜”。然后,莱辛特别强调,“对于模仿之作为模仿本身所产生的愉悦感本来就是对于艺术家的娴熟技巧所产生的愉悦感”(《关于悲剧的通信》84)。这些观点共同指向的就是莱辛本人长期的市民悲剧实践,在其中,他试图通过艺术技巧来激起民众的一般的同情,由此缔造一种共同的市民文化。显然,赫尔德之前关于诗人激发情感、改变观众时空观的看法,与莱辛这个时候的判断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不妨先了解莱辛在何种意义上通过他对亚里士多德诗学观的发挥和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刺激了赫尔德写作《莎士比亚》。
莱辛与温克尔曼论战的《拉奥孔》的副标题用Poesie(源自古希腊的“创作”“作诗”)一词、而非后来在歌德《诗与真》的标题中对应着强调虚构、幻想意涵的Dichtung一词来称谓一般意义上的“诗”,这是在提醒读者《拉奥孔》一书与古希腊文化,尤其是与亚里士多德《诗术》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拉奥孔》中,通过与温克尔曼的争论,莱辛区分了两种“希腊”: 温克尔曼凭借现代新古典主义的伦理趣味观总结出来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其实只点出了希腊文化中偏重永恒形式与沉思的一面;然而,就具体的作品而论,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行动的”“活生生的”希腊。后者必须借助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人德性内容的伦理学才能得到符合“中道”的理解(张辉156—66)。在反对新古典主义教条化倾向的《汉堡剧评》中,莱辛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就体现出对“行动”或者说“情节”的重视:
演员的艺术,在这里是一种处于造型艺术和诗歌之间的艺术。作为被观赏的绘画,美必须是它的最高法则;但作为迅速变幻的绘画,它不需要总是让自己的姿势保持静穆[……](《汉堡剧评》29—30)
“情节”的出场,意味着更加自然也更加生动有感染力的呈现方式。就戏剧而言,在“情节”之上不应当有带有形而上意味的造型艺术“规则”把关。所以,莱辛会进一步认为,在处理客观人物的情节时,对于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诗人来说,“制作”本身具备的主观特征能够因其高超的认识与阅历而编织出更加系统、有条理的历史效果:
作家利用这少许情节,编成一个浑圆的整体,在这个整体里,一个情节完全可以得到另一个情节的说明,在这个整体里,我们不会因遇到某种困难而无法在它的布局里得到快感,而是必须在它之外,到事物通常的布局里去找寻快感;这个尘世的创造者的整体应该是永恒的创造者的整体的一幅投影;若要使我们相信在永恒的创造者的整体里,一切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那么在尘世的创造者的整体里是否也能做到呢?(《汉堡剧评》400)
莱辛发现,从事诗性创造的天才作家与世界的创造者——上帝——之间有着显著的可类比性。上帝在世间对历史的安排和诗人对戏剧的情节安排都体现出一种创造时间规律并使之完全组织起来的整体性。同时,观看戏剧的某些观众也具备一种能力,在看戏的时候,会同时将戏剧中的整体性与“在它之外”的现实事物的整体性进行对比,将剧中的情节规律投射到对现实历史规律的理解当中。在戏剧天才所营造的那个世界里,“动机和效果引出另外的结局,当然同样是以善良的普遍效果为目的[……]至高无上的天才,把现实世界的各部分加以改变,替换,缩小,扩大,由此造成一个自己的整体,以表达他自己的意图”(《汉堡剧评》176)。换句话说,天才能够用制作戏剧的方式传达他对于现实世界某种规律与可能性的独特的见解,并且,至少在戏剧中,这种见解具有唯一的普遍性。观众看戏的目的,则是为了借助天才的重构规律的能力来重新看待现实。
这样看来,莱辛与赫尔德对莎士比亚的“天才”的理解十分相似。这两种看法在“狂飙突进”时期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细究一番,就会发现其中有极大的差异。
莱辛相信,通过观赏莎士比亚和其他优秀剧作家的作品,观众重新“发现”生活可能性的潜能也将得到激发,因此,可以在这种戏剧文化基础上缔造揭示历史内在可能性的启蒙教育 :“我们不应该在剧院里学习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做了些什么,而是应该学习具有某种性格的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做些什么。悲剧的目的远比历史的目的更具有哲学性[……]”(《汉堡剧评》100)。戏剧中能够表达出关于现实政治的更加深刻的哲学反思机制——这等同于说,优秀的剧作能够启发出关于政治的哲学,乃至于政治任务。
这正是赫尔德同样渴望在戏剧创作机制中证成的带有启蒙性质的教育立法力量。但与莱辛首先瞄准现实社会生活的出发点不同,赫尔德的理论依据显得更为理论化或者说“自然哲学”化。他认为,单纯的现实行动仅是历史、文化或宗教整体当中的产物,而诗人的任务就是“从这个单纯的伟大整体中去发现部分”,所以,“希腊戏剧的规则的艺术性不是艺术!是自然!”(Grimm501)。这里的“自然”,指的就是人的具体历史生存处境。天才只能在历史处境的限定之下表现当时当地的“亲在”,进而,他所整合的情节最终体现的只会是当时当地的可能性。
赫尔德会认为,亚里士多德对索福克勒斯的理解也凸显着这样一种认识方式 :“这位伟人也是本着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精神进行哲学的探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除了观众的眼光、心灵、幻觉以外,不知道、也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规则。”赫尔德其实是想借亚里士多德和希腊悲剧的权威性来说明,诗人天才能够有效地利用现实中的各种情节素材,基于让观众致幻的目的,让现实时空发生扭曲变化。这一变化当然并非随意,而是基于“精神、生命、自然、真实性”——而这些因素全都来自诗人在具体时空中具备的“民族精神”,来自他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生存处境的全面把握。所以,只要天才能够对“民族精神”进行模仿,那么就能够创造出“有最高深、最重大的教养意义的民族戏剧”。言下之意,赫尔德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本身也只在解释古希腊戏剧时有意义。但是,从他的学说的建构方法和思路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尊重“民族精神”的态度,从而推导出一种“根据自己的历史、时代精神、习俗、见解、语言、民族偏见、传统和爱好来创造自己的戏剧”的天才观(Grimm 503-06)。
赫尔德的这种理解当然是为了延续莱辛的思路,抨击当时人对所谓“三一律”的抽象理解,进而抨击由法国绵延到德意志地区的新古典主义风气。问题在于,在莱辛那里,亚里士多德的天才学说与赫尔德式的历史化、处境化的“自然”没有关系。莱辛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是超越时代界限的普遍原则的提出者,这种普遍性才是保证戏剧启蒙的根本要素。
三、 公民道德与自由激情: 两种戏剧启蒙
莱辛相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戏剧以感染民众为目的。但是,“一切悲剧作家中之佼佼者,绝不想如此轻视自己的艺术。他知道艺术能够达到更完美的境界,而迎合一种幼稚的好奇心理,是最低劣的手法”(《汉堡剧评》250)。所以,对于真正的戏剧天才来说:
他的主要人物的气质和素养,包含着远大的目的,即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允许做什么的目的;教导我们认识善与恶,文明与可笑的特殊标志的目的;向我们指出前者在其联系和结局中是美的,是厄运中之幸运;后者则相反,是丑的,是幸运中之厄运的目的[……](《汉堡剧评》178)
这就是莱辛所理解的戏剧的公民教育之普遍性。莱辛一贯强调,亚里士多德《诗术》的核心意旨是对普遍的善恶高低秩序的持守和相应而来的针对不同人的德性教育。他会认为,唯有根据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修辞术》中表达出来的德性秩序学说,才能理解《诗术》中的这层教育意涵。比如说,莱辛会强调,当时的古典学家将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畏惧”翻译成“恐怖”,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畏惧”并非针对剧中人物境遇所感到的单纯不快和拒斥,而是观众看到人物遭受不幸而唯恐自己也会遭受同样不幸的同情、担忧与恐慌;因此,悲剧营造“畏惧”的情感并非为了引发观众的恐怖情绪,而是引发他们的同情,进而引发对自己可能遭受命运惩罚的自我警戒与反省(《汉堡剧评》378)。唯有这样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才能正确理解古希腊悲剧在何种意义上具有针对观众提醒命运必然性及其背后崇高神意的教化功能。依据《修辞术》,这样的教化具有面对不同的人的特殊功能,能让缺少虔敬心态的人重新唤起畏惧的情感,也能让过于杞人忧天的人不被命运彻底压倒。莱辛特地援引《尼各马可伦理学》强调:
每一种道德,按照我们的哲学家的意思,都有两个极端,道德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所以,如果悲剧要把我们的同情转化为道德,就得从同情的两个极端来净化我们。[……]就同情而言,悲剧性的同情不只是净化过多地感觉到同情的人的心灵,也要净化极少感觉到同情的人的心灵。就畏惧而言,悲剧性的畏惧不只是净化根本不惧怕任何厄运的人的心灵,而且也要净化对任何厄运,即使是遥远的厄运,甚至连最不可能发生的厄运都感到恐惧的人的心灵。(《汉堡剧评》396)
换句话说,悲剧能够让灵魂品质有具体差异的市民共同走向“中道”的道德状态——既让畏惧者获得自信,也让无所畏惧者感到畏惧——这就是莱辛试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的戏剧启蒙。的确,莱辛明白,悲剧的效果要通过对具体的人物及其具体处境的表现而得到呈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悲剧诗人将具体时空处境上升为根本的创作尺度。相反,莱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看到的是,悲剧诗人,尤其是天才诗人,有义务让各种在具体处境当中已经养成其性情的民众能够通过悲剧获得通向性情之中道的“净化”。对“中道”的诉求也就体现为对情节的“典型”(Ideal)的塑造 :“古人几乎不得不把地点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场所,把时间限制在固定的一天之内[……]他们承受这种限制是有原因的,是为了简化行动,慎重地从行动当中剔除一切多余的东西,使其保留最主要的成分[……]”(《汉堡剧评》237)这也就意味着,悲剧天才的创作并非直接反映具体历史与习俗,并非直接表达“民族精神”,而是必然要让这些东西经历哲学化、典型化的过程,以戏剧的方式启发真实的“反省”(戴维斯103—105);因为,唯其如此,才能够真正克服多数民众或是过度或是不足的自然性情,对他们进行通向中道的教育。
相比起其他同时代同情学说的提出者,莱辛相信戏剧具有基于同情机制而凸显的启蒙功效,首先在于他秉持对人性参差不齐之实质、也就是人之德性高低善恶的信念。不同的戏剧之所以同样具备启蒙意义,能够让民众在戏剧中潜移默化从事自我反省,通向中道,原因在于民众本身有善恶高低、过度与不足的本质差异。但是,赫尔德却会将这种民众的差异用其自然生活起源或者说“亲在”的语境差异来解释,使得这一切差异都具备自然维度的合理性,进而也就取消了如何批判人类德性高低与如何从事德性教育等问题的考虑,取消了戏剧天才应当承担的在政治共同体中维持德性基本认同的公民教育任务。
但这并不意味着赫尔德不相信戏剧应当承担启蒙的任务,只是他心中的启蒙目标并非针对多数人的道德净化,而是对“民族精神”和“个人自由”的灌输。赫尔德与“狂飙突进”参与者们的许多观点来自于莱辛的戏剧理论启蒙,但是,他们却以自己独特的理解暗中偷换了莱辛的意思。比如说,在莱辛《汉堡剧评》里曾经有这样的段落:
莎士比亚作品之于我们,当犹如暗箱之于风景画家: 多往里瞧瞧,可以学习自然在各种情况下是怎样投射到一个平面上的[……]莎士比亚作品的各部分,甚至连最细微的地方,都是按照历史剧的宏大篇幅剪裁的,这跟具有法国趣味的悲剧相比,犹如一幅广阔的壁画和一幅绘在戒指上的小品画。(《汉堡剧评》370)
可以发现,这与歌德关于“百像镜”的譬喻是几乎一致的。不同的是,歌德认为莎士比亚揭示的是秘密的世界历史的线索。但莱辛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莎士比亚所反映的政治生活与人性好坏善恶的自然;莎士比亚能够将细微的情节整饬为历史剧整体中的部分,其作为“广阔的壁画”,试图让观众去看到的不是客观事物的杂多,而是人性自然的无限丰富如何在有限的“投射”中变成一种观念性的尺度。
但是,赫尔德却将莎士比亚这种对人性自然的观念性投射反过来理解为对实际的一切质料性、历史性事物的全面呈现。这是因为,赫尔德所理解的自然整体是泛神论意义上的自然整体,而非莱辛的理念化、典型化的整体。泛神论的自然整体对于一切世界中的“亲在”是以一种无差别的态度进行囊括的。这些内容生成于具体的时空处境,彼此之间无分好坏高低,地位平等。因此,赫尔德会在《莎士比亚》中扮演“热情的演说人和颂歌手”,将莎士比亚称为“自然中一切语言的译者”: 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一样,都是对其所处时代的各种“自然”的敏感的传声筒,是“世界和天命”在“时代狂飙”(Strum der Zeiten)中的记录者。也就是说,所谓的作为世界历史之见证的莎士比亚是一个能够效仿泛神论之上帝对英雄传奇和国家大事进行完全囊括式的安排的天才,他通过“写作一切次要的情况、动机、性格和场面,让这一切在戏里发展为整体[……]处处都有事件的灵魂在喘息”(Grimm512)。通过把活力灌注在每一个“次要”之处,莎士比亚“不是吸引人们去注意,而是自始至终抓住人心,抓住一切激情和整个灵魂”(Grimm509-11)。进而,莎士比亚简直就是上帝的天使,他的任务是:
把人的各种激情(Leidenschaften)加以衡量,把各种心灵和性格分类加以组合,提供给它们种种机会,使它们都让自己在这种机会当中本着自由的幻想(Wahn des Freien)行动,而他却通过它们这种幻觉,像通过命运的锁链似的,把它们都引导到他的观念(Idee)上去——原来,这位天使便是在这里设计(entwarf)、构思(sann)、绘制(zeichnete)、操纵(lenkte)人的精神。(Grimm512)
这当然是将莎士比亚理解成了一个具有启蒙观念的幻觉营造者。不管现实中的莎士比亚究竟是怎么样从事戏剧创作的,在赫尔德的理论构想中,莎士比亚的意义显然不在于提供凝练的政治生活教诲,而在于展现一切个体实存的行动、性情、欲求如何能够巧妙地在一种自然的历史秩序中达成虚拟的统一。这种“历史秩序”显然并非对观众的劝诫、规训和引导,而是向他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生存可能性,尤其是鼓动起他们对未来之自由的幻觉与激情,对既有的生存尺度进行想象乃至于现实的修正。显然,在莱辛那里构成重要目标的通过陶冶同情心而展开的公民道德教育,被赫尔德修改成了对即将来临的自由幻觉的宣传营造。赫尔德在莎士比亚身上试图找到的启蒙并非道德启蒙,而是激情启蒙,是对公民的自由意志的启蒙。在“狂飙突进”参与者的眼里,莎士比亚不仅仅是制作诗的天才,还是制作历史线索的天才。诗人是未来可能历史在观众心灵深处的启示者,通过戏剧对“精神”的启蒙,这种历史也将成为现实。
四、 “世界历史”与激进启蒙
在赫尔德的理论中,任何质料性的实存与思想都将以一种平等的、有活力的方式参与到诗人笔下的世界历史事件当中,并且构成一条不间断的必然发展线索。通过将“世界历史”的启蒙任务安置在莎士比亚身上,赫尔德并非认可既有的世界历史进程,毋宁说,他要求后来的民族天才能够学会莎士比亚的戏剧手法,重新调动某些特定观众群体的激情,使他们懂得追求“自由”,从而积极参与塑造未来的世界历史:
如果说莎士比亚找到了神妙的手法,把形形色色极不相同的场面抓住,揉成一个事件(Begebenheit),那么,他每次还把地点和时间理想化,使它们也帮助造成幻觉,这自然就是他的事件的真实性的必要条件。[……]在青年时代,在激情的场面,在一切生命的行动中!在这里不正是由场所和时间以及丰富的外在情况来让历史获得趋势(Haltung)、持续性(Dauer)和实存(Existenz)么?[……]莎士比亚在这个问题上是最伟大的主人(der größte Meister),正因为他只是、而且总是自然的奴仆(Diener der Natur)。[……]这里奇异的、最大胆的场面最能加强真实的幻觉(den Trug der Wahrheit),这里诗人掌握时间和地点的变更,以最大的声音喊道 :“我并不是诗人!而是造物主!是世界历史(Geschichte der Welt)!”(Grimm512)
这里的“世界历史”是基于诗人对已有历史处境的规律把握而形成的: 如果没有对外间自然历史的敏感认知,诗人无法在剧作中加强“幻觉”的真实性,从而造就“事件”。这也就是戏剧天才要成为“自然的奴仆”的原因: 诗人和作家要积极学习关于自然的规律性探索,在成为诗性的启蒙者之前,他们首先要在与自然的打交道过程中自我启蒙。这就是泛神论的世界观和生活观对于诗人的重要意义。诗人要懂得历史规律,他首先得去体验和自我教育,“自然”是他们最好的老师。在这个意义上,赫尔德的泛神论的历史主义是他对莎士比亚作品表现一种应然性的“世界历史”的判断的来源。他将莎士比亚的作品视为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小宇宙”,视为神一般伟大天才的匠心独运,“整个世界只是这一伟大精神的肉体”,这其实是说,莎士比亚的剧作是神性的世界历史在艺术上的投射。这样一来,戏剧天才也只是对神性权威的客观反映。启蒙诗人就此可以在自然历史进程与诗化的未来历史之间充当中介者,并由此享有一种超出宗教、但又带有宗教性的世俗权威。
为了让诗人的这种中介角色得以实现,赫尔德一贯强调,要将戏剧中的情节视为“青年行动”,视为对不可抑止的激情之自然流露。这种激情实际上来自于对地点、时间和个体处境的敏感反应。戏剧天才作为“作者、诗人、戏剧之神”,需要制造相对的、内在的时空标准,“使一切观众都进入这个世界”,通过以加速度的方式推动事件进行和场面变换,最后让观众“完全进入幻觉中,陷入他的世界和激情的深渊里去了”。从泛神论自然观到诗化的“世界历史”的基本逻辑就是如此,在这一整套戏剧理论里,最终得到揭示的只是被天才所唤起的青年的自然激情,也就是他们真正“自由”的最终依托(Grimm516-18)。所以,所谓的“自然的奴仆”只不过是“最伟大的主人”用来引导和驱使其他人的激情的一种幻觉身份。
最后,我们发现,赫尔德这种对“狂飙突进”的诗人天才进行“神圣化”的设计,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赫尔德笔下,即便莎士比亚这样可以与索福克勒斯比肩的天才,也只是其所处的文艺复兴英国的具体语境的产物。眼下,在法国戏剧的新古典主义趣味开始逐渐败坏德意志人民自然品性的时代,需要呼唤与德意志民族有血缘关系的新一代天才,来表达属于德意志的激情与自由。这就是“狂飙突进”的现实目标。于是,在歌德的讲演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莎士比亚剧作中调解自然和自由的思路的向往,这实则是对赫尔德所表述的泛神论的诗人形象的向往。歌德尝试通过戏剧——从《铁手骑士葛兹》到《浮士德》——表达“世界历史”乃至于与之呼应的“世界文学”观,也是基于他对赫尔德式诗性立法计划的理解与执行。
可以说,《莎士比亚》是歌德思想的出发点之一,也是德意志现代文学风格的出发点之一,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与莱辛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戏剧观明显有异的历史主义的天才戏剧观,这种戏剧观并不旨在引入对必然命运的警醒进而引出德性教育,而是旨在通过艺术手法对民众激情进行频繁不断的介入、触发和方向指引。歌德则整合了赫尔德超出古典自然观和诗术观的激情启蒙思想,在其生命后期创造了浮士德式的现代目标。用洛维特(Karl Löwith)的话说就是,“不可避免的应当”在歌德的理解中被“对立的意欲”所加强,这种以激情为基础的“意欲”就是“现代的上帝”;唯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懂得“我们的艺术和气质为什么与古代的艺术和气质永恒分离的原因”,而歌德就是重新揭示这种分离并尝试联合的统一者,也就是德意志最伟大的民族与世界文学代言人(洛维特268)。赫尔德与歌德式的“狂飙突进”诗人基于现实的民族忧患,渴望最大程度地整合当下时代与习俗的所有内容,使之变成对未来历史的规律探索,并通过在这种探索的结论之上孕育抒情机制,造就虚幻的时空观和哲学观,向观众、进而向整个民族启示通向未来世界普遍历史的方向。这种诗化后呈现出来的“世界历史”不同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模式,其根基完全来自于对“自然事件”的泛神论式权威化,来自于诗人对激情和生活的敏感再造。“歌德在大自然自身中看到了理性和理念,并由它出发找到了理解人和历史的一个入口”(洛维特304—05)。
从莱辛到赫尔德再到后来的浪漫派,对莎士比亚的理解愈加偏离古典的趣味,让“莎士比亚”愈加抒情化、“意欲”化。在日益理论化的批评实践当中,莎士比亚旨在提供政治德性教诲的“自然”渐渐成了教育民众争取自由、进而客观促成现代自由民主革命进程的艺术铺垫。布鲁姆(Allan Bloom)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值得引用:
莎士比亚有如自然之镜,呈现人本来的样子。他的诗让我们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what is there)。他与浪漫派的不同在于他绝不说教。[……]莎士比亚没有任何要改善或拯救人类的大计。这并不是说,莎士比亚就不相信真理于人有益,而是说他认为艺术家不是应该担此重任的人。他的戏剧让我们想到沉思的古典式目标,而不是志于改良的现代野心。[……]他深深沉浸在自然的奇观之中,顾不得把自己当成其中最重要的存在。他不像浪漫派那样试图创造,而是尽力记录自然。(布鲁姆5)
在发现政治而非重新创造政治的意义上,莎士比亚的戏剧并非指向未来变革的“世界历史”,而是对真实历史与其背后自然规律的沉思与客观呈现,其中一以贯之的与其说是浪漫派的民族精神,毋宁说是古典的哲学精神。只是,这种哲学戏剧同样具备面向不同层次的人进行道德教育的功能。这在莱辛对莎士比亚的理解中早已得到揭示。相比起莱辛,赫尔德的启蒙的戏剧天才事实上并不追求提升民众对于真善美的崇高趣味,毋宁说是要用在审美活动中的激情与行动效果取代崇高趣味。这种激情与行动的“自然”其实只是一种基于个人情感的自我解放冲动。这反而会引起剧烈的思想动荡,让部分人——正如19世纪欧洲思想史实际上呈现的那样——在试图打破旧有的善恶观和高低界限的过程中激起新的革命。
注释[Notes]
① 可对比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385b12—33的表述 :“那些彻底绝望之人不会有怜悯之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饱受创伤,再也没有什么灾祸可遭受的了;那些自认为极度幸福的人也不会有怜悯之情,他们有的毋宁是暴虐之心[……]那些认为自己有可能遭遇不测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曾经遭受过灾祸而又幸免于难,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是孱弱之人,特别是较为懦弱之人,或者是受过教育的人,因为他们会凡事三思[……]只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人才会有怜悯之情”(苗力田43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