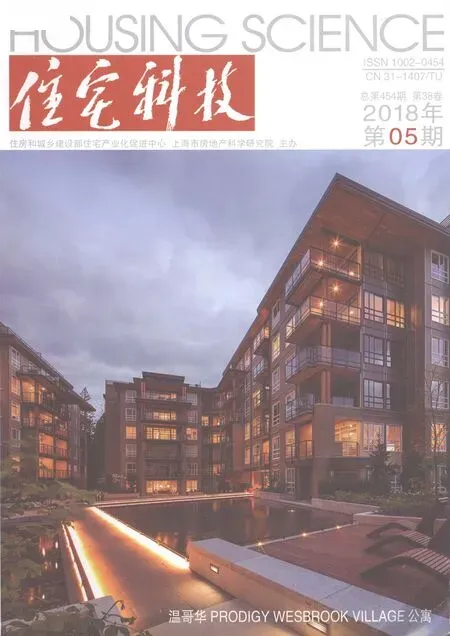连接自然的儿童友好城市空间网络构建
■ 陈长虹 Chen Changhong 刘 颂 Liu Song
0 引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人居中心(UN-Habitat)在20世纪90年代以“儿童福祉和生活质量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管理的终极指标”为理念,倡导建设“儿童友好城市”(Child Friendly Cities,CFC),并提出行动框架,认为对儿童友好的城市环境是儿童身心健康和人格精神发展的先决条件 。理想的城市环境不仅是为儿童提供庇护的场所,而且要为儿童接触自然空间提供机会和场所。2008年世界性环保大会提出“孩子回归大自然”的决议,“重建人们,尤其是少年儿童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我国在《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以“改善儿童生存的自然环境,增加森林和绿地面积”为目标,提升城市品质和宜居性。
但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在带来儿童居住环境很大改善的同时,自然环境在儿童生活中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游乐环境。在高密度的人工城市环境下,城市与自然对立或隔离的规划建设方式,切断了孩子与自然的联系,违背了儿童亲近自然的天性。自然缺失会造成儿童感官逐渐退化,容易产生肥胖、抑郁和注意力紊乱等身心问题,间接地影响儿童智力、审美能力和人格道德的完善[1]。
在我国城镇化加速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儿童生活在城市环境中。我国0~14岁的儿童有22 132.3万人,其中有4 938.5万儿童生活在城市环境中,占城市总人口的12.23%(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因此,如何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避免城市与自然割裂,更好地发挥城市的优势,关心儿童的身心健康和保护儿童的成长权益,创造出适宜的友好城市空间环境,值得深入探讨。
1 自然环境是儿童成长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儿童与其生活环境之间是一种主动关系,儿童各个阶段身体和智力的发育过程本质上是在学习和处理自己与外部环境的关系[2]。日常活动环境对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起着重要作用[3],其中,自然环境对于儿童的影响更为深远。
1.1 自然环境给儿童无限探索的可能性
儿童天然的好奇心在自然环境中更容易得到满足和激发,通过观察和探索自然,激发了孩子的求知欲,培养了观察力以及环境适应力;孩子的玩耍和游戏活动相对自由,少受限制,进行跳跃追逐、爬上爬下等多种活动,可以促进孩子们大脑与肢体之间的平衡能力和运动能力的发育,树立自信心,增强抗挫折的能力。如在日本幼儿园中开展森林教育活动(图1),对比普通幼儿园的孩子,经过“森之幼儿园”教育的儿童不仅有较强的运动能力,而且有更好的学习专注力[4]。
1.2 自然环境能促进儿童社交活动和人格健全
自然环境不仅能缓解精神压力[5],而且能促进儿童的社交活动能力[6]。在无固定游戏模式的自然环境中,孩子会自发设计游戏形式,并与不同年龄、个性的孩子一起玩耍,有利于孩子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有利于降低传统的性别差异,让女孩有机会同男孩一起尝试和探索自己的能力;有利于缓解儿童抑郁及注意力紊乱的症状,并减少儿童心理攻击性[7]。

图1 日本森之幼儿园(八王子市摇篮幼稚园)
2 造成城市中儿童与自然环境割裂的原因
2.1 学习压力和新娱乐方式割裂了儿童与自然环境的心理连接
由于时间、地点的局限,儿童的户外活动普遍受到限制。一方面,是学龄儿童的学习活动占据了大量时间。《中国儿童参与状况报告(2017)》以全国7个城市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发现54.6%的小学生、61.4%的初中生、66%的高中生,离开学校以后几乎没有玩耍的时间;即使有机会玩耍,时间也在1h以内[8]。由于学习任务重和距离等原因,儿童娱乐休闲活动只能在家里或者小区进行。
另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初期,一般以成人为主要服务对象考虑,对于儿童的友好程度较低,存在数量少、规模小、安全性差、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等问题,导致儿童更愿意呆在室内或与电子产品设施玩耍。而商业化的儿童游乐场、大型主题公园等,根本目标是消费和盈利,机械的光电游乐设施,刺激着儿童的感官,成为户外自然环境的替代品。
2.2 “不友好”的城市设计割裂了儿童与自然环境的物理连接
现代交通发展和城市功能分区极大加剧了空间隔离,使得儿童生活、学习、娱乐不得不分散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对汽车、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的严重依赖,导致步行环境变得十分糟糕。不安全的街道和城市公共空间,加剧了父母对于儿童出行安全的担忧,增加了儿童对于父母的依赖性,削弱了儿童获得独立行动能力的机会。
许多公园、广场及公共绿地的同质化,对于儿童逐渐丧失了吸引力。根据对上海中心城区3~15岁近2 000名儿童的问卷和访谈,发现仅有4%的儿童认为公园是常规户外活动场地;活动需求最多的8~10岁儿童,反而认为公园是一个无趣场所。儿童活动时间局限在周末或节假日,活动对象限制在成人与儿童之间,难以看见儿童之间群体性游乐活动[9]。

表1 基于10~15岁儿童调研GUIC对城市环境质量评价指标[10]

图2 社区花园(上海创智农场)
3 面向“儿童友好”的城市自然空间网络构建
3.1 基于儿童行为特征的城市空间需求
按照儿童身体发育过程和行为心理特征,可以分为婴幼儿期(0~3岁)、学龄前儿童(3~6岁)、学龄儿童(7~12岁)、青少年(12~18岁)4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儿童活动范围从以家园为中心,逐渐向住区游园、公园、校园、城市公共空间拓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在城市中成长(GUIC)计划”,根据儿童对于城市感受的调研,提出了积极或消极儿童活动空间的评价指标(表1)。
可见,家园、校园、公园是城市为儿童提供的基本积极空间环境,代表着儿童在家、学校/幼儿园和社会的活动范围。营造积极的儿童空间及其相互串联的安全自然网络空间,将是面向儿童友好的城市更新的重点。
3.2 家园、校园和公园三大积极空间的自然化
3.2.1 友好家园的自然化和社会化
家园是儿童生活最为密切的场所,是儿童认识外部世界的第一站,是可以自由玩耍、感知自然、认知自然的地方[11]。儿童友好家园的社区环境要以儿童尺度为基础,满足儿童的生理健康需求,同时考虑儿童社会化的心理需求。
在自然设计方面,充分利用阳光、通风、降水等特征和地形、植物等资源,开阔的草地、变化的地形、流动的水体、沙子对儿童具有天然的吸引力,阳光草地配合缓坡地形能吸引儿童在上面奔跑、打滚、躲藏;溪流中的小鱼小虾激发儿童的好奇心,沙子可以为儿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近似自然的环境能发挥儿童玩乐的天性,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
与传统观赏的方式不同,儿童友好家园的景观营造不仅在于美化,更重要的是让儿童接触、参与到其中。在一定区域内允许儿童触碰、采摘甚至攀爬植物。通过“社区花园”“菜园”的种植和营造(图2),为少年儿童提供自然教育机会,为家庭提供亲子活动的场所,促进社区邻里的公共交往,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和活力[12]。
3.2.2 生态化的校园景观和自然教育引导
学校是学龄儿童平常白天活动的主要场所,学校教育肩负起对儿童的性格塑造和人格培养的重大作用。相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在儿童自然教育方面处于薄弱环节。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国学校组织儿童到自然山林中体验越来越少。而通过校园景观环境的生态化设计,可以将自然教育融于教学活动中。生态化的校园景观能为儿童提供自然健康的物质空间,而且是儿童学习自然、接受生态教育的重要场所。通过小型生态群落、雨水花园等设计,让儿童能够直观感受到生态环境的作用;利用校园里的空地或者边角地,开展学校花园及菜园体验,以班级为单位,开展种植蔬菜、花卉的活动,可以让孩子体会种植、收获的感觉。
课程上适当开展自然教育的课程或活动,进行自然通识教育。引导孩子们走进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野营活动,让孩子从静坐的教室和繁重的课程中解放出来,走进自然,通过观察自然、记录自然、创作自然,在潜移默化中建立儿童与自然之间良性关系。
3.2.3 友好公园的趣味自然
城市公园绿地是城市与自然融合的关键场所,也是人们日常休闲、儿童活动的主要场所。城市内部由于空间有限,大型公园多建于郊外,而儿童到大型公园游玩的时间和频率受到成人的时间和经济能力的限制。因此,儿童友好公园应以家庭附近的小型口袋公园、街心公园为主,大型公园为有益补充。根据儿童的阶段性活动范围和我国公园设置规范,儿童友好公园的适宜距离应为300~400m,以可达性为原则,保障儿童能最简便快捷地到达活动场地。
小型公园不必设施齐全,以简单、杂乱、游戏性为主,注重儿童活动的自主性,调动儿童参与的积极性,增强自然趣味性(图3)。空间设计上不必复杂,以儿童使用便捷性为原则,适当划分出一定的不受限制区域,儿童可以自由活动[13]。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允许适当的杂乱,枯枝落叶比精心保持的公园更有野趣。注重儿童与自然的活动性,留有空间让家长带领儿童或儿童之间开展建小屋、搭城堡、做树屋、挖坑洞等活动,引导和鼓励儿童自主创造,对场地进行重新规划。
大型公园具有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应该充分发展大型公园的优势,通过举办特色观赏活动、生物生境学习会、夜游活动等,以生态科普教育为先导,提供自然通识教育,重塑儿童与自然的联系。

图3 小型儿童游乐场(西班牙马德里)
3.3 变消极道路为友好街道空间
并非在正式的公园或游乐园才能玩耍,孩子具有一种在街上也能发展自己嬉戏场所的好奇心和观察力。城市公共空间中,道路街区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偶然相会和接触、移动中的变化等未知的情景,给儿童提供了发生自发性游戏的空间和丰富的可供度。儿童游戏行为发生和发展都与道路、沿街商业和开放空地等路径空间关系密切[14],孩童在嬉戏玩耍中就能学习和熟悉城市复杂的空间布局。
儿童独立出行的可能性和意愿性是衡量儿童友好环境的重要准则[15]。因此,如何在以汽车为主体的城市道路系统中营造儿童友好街道空间,应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安全性,二是吸引力。
街道作为少年儿童与城市最重要的接触面,安全是根本。儿童需要安全、畅通的街道网络,以便于他们能独立穿梭于城市中的自然空间,可选择连接家园、校园、公园的城市支路、小路作为“儿童出行路径”,限制车辆通行,梳理道路交通系统,营造便于儿童独立出行的线性公共空间。如荷兰代尔夫特的kindlet路径,通过对儿童出行路线的选择,建造安全的交叉口、人行道和自行车道,提供良好的交通可视性以及儿童可明显辨识性等措施,显著提高儿童出行的安全性[16]。英国的“家庭地带”街道设计,提倡改变街道的使用方式,鼓励增加街道等非正式儿童空间活动,提升街道的生活品质。
儿童友好街道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以熟悉加意外的形式,通过艺术化的景观设计和小品布置,增强街道的吸引力。我国对于道路绿化带有明确要求,但一般以纯粹的植物种植为主,可以在此基础上减少灌木,增加草地的可进入性,配合简单的个性游戏设施,将道路变成可以停留的空间。在道路管控方面,改变传统红线管控方式,变成街区空间管控,结合周边商业设置和公共空间功能,提升街道活力。
3.4 网络链接
通过儿童友好街道,连接着家园、校园、公园三大积极空间,形成少年儿童安全出行的安全网络。美国丹佛市“见学地景(Learning Landscape)”,通过一些被忽视或废弃的校园空地的景观改造,形成了安全、充满活力、多功能的城市开放空间;并且把学校的活动场地、街心公园、城市绿地有机地联合起来,点状的小空间彼此连接,最终形成不同规模层次、儿童步行可达的城市空间网络系统[17]。
4 结语
儿童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自然的关系和连接;二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儿童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尊重儿童是儿童友好城市的先决条件,将儿童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让成长中的孩子们按照自己意愿选择活动的场所,从家庭庇护走向自立过程,最终完成走向城市和更广阔的空间。
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儿童的行为特征和心理需求,在“建筑森林”为主的城市环境中,以自然化设计提升家园、校园、公园积极空间的吸引力,以友好街道线性空间串联起一个城市与自然相融的空间网络系统,不仅为儿童也为城市其他居民提供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
[1][美]查理德·洛夫著,自然之友,王西敏译.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
[2][日]高桥鹰志,EBS组著,陶新中译.环境行为与空间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58.
[3]任泳东,吴晓莉.儿童友好视角下建设健康城市的策略性建议[J].上海城市规划,2017(03): 24-29.
[4]高杰.日本儿童室外游戏空间研究及实践[J].风景园林 ,2012(5):99-104.
[5]Beyer K M M, Kaltenbach A, Szabo A, et al. Exposure to Neighborhood Green Space and Mental Health: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the Health of Wisconsi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 Public Health,2014,11(3):3453.
[6]Laaksoharju T, Rappe E, Kaivola T. Garden affordances for social learning, play, and for building nature-child relationship.[J].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12, 11(2):195-203.
[7]Corraliza-Rodr'Guez J, Collado-Salas S, Ferrer-Ispizua P. The nearby natural environment as a buffer of children's life stress. Differences between a rural and an urban environment[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2008,70(4):603-613.
[8]苑立新等主编,中国儿童参与状况报告(20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9][德]谭玛丽.适合儿童的公园与花园——儿童友好型公园的设计与研究[J].中国园林,2008.20:43-48.
[10][澳大利亚]布伦丹·格利森,尼尔·西普主编,丁宇译.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11]林瑛.儿童友好型住区活动场地设计——对一岁以内婴幼儿的关注[J].住宅科技,2012(3):11-14.
[12]刘悦来,尹科娈,魏闽,等.高密度城市社区花园实施机制探索——以上海创智农园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17(2):29-33.
[13]M·欧伯雷瑟·芬柯,吴玮琼.活动场地:城市——设计少年儿童友好型城市开放空间[J].中国园林 ,2008,24(9):49-55.
[14]沈瑶,张丁雪花,李思,等.城市更新视角下儿童放学路径空间研究[J].建筑学报,2015(09):94-99.
[15]Sharmin S, Kamruzzaman M.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 A meta-analytic review[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2017(61):104-117.
[16]李志鹏.儿童友好城市空间研究[J].住区,2013(5):18-23.[17]Kingston B, Wridt P, Chawla L, et al. Creating child friendly cities: the case of Denver, USA[J]. Municipal Engineer,2007, 160(2):9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