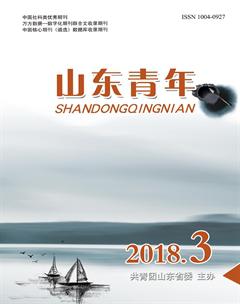春秋决狱:法律儒家化的汉代表现
王杉
摘 要:法律儒家化是指儒家的道德观念向立法、司法领域的渗入过程。汉代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对研究整个法律儒家化的脉络有重要的意义。汉代春秋决狱是以儒家经义来断案的司法审判制度,以儒家思想弥补汉律的漏洞与僵化,开启了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先河。本文重点是从春秋决狱的历史必然性分析,结合春秋决狱的主要表现、核心宗旨来窥视儒家经义如何与汉代成文法律相融合。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春秋决狱;主要表现;原心定罪
儒家乃春秋末期没落贵族代表孔子所创,在西汉汉武帝时期经董仲舒开创新儒学,后使儒家经义逐渐渗入汉代成文法中,从司法领域的引经决狱到在立法领域进行引经注律,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已经进入了一个蓬勃鼎盛时期,引礼入律的程度也不断渗入,直接将儒家思想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如“十恶”“八议”“官当”“准五服以制罪”制度等,都在立法领域直接体现了儒家的封建伦理观念。法律儒家化在历史前进中不断的演化和变迁,正如瞿同祖所言:“前一朝的法律因素多为后一朝所吸收,并在吸收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新的儒学因素,因此内容越来越多,体系越来越精密”[1]由于儒家思想向司法领域、立法领域的不断深入,至隋唐时期在立法领域最终实现了“依礼制刑,礼法合一”,“纳礼入律”的进程才基本结束。西汉开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先河,具有历史必然性,然而西汉时的法律儒家化表现颇多,春秋决狱为何能成为西汉法律儒家化的主要表现,笔者在下文分析。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必然性
汉初时期,鉴于秦末暴政,民生凋敝,出于恢复生产与巩固统治的需要,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更能适应汉初的统治及民心需要。但至汉武帝时期,生产力得到发展,诸侯割据现象严重,“大一统”迫在眉睫,董仲舒适时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理论适得其时,经过发展与融合的新儒学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思想。然而儒家思想并没有成为立法思想,汉律是以充斥着法家思想的《法经》为蓝本制订,主张“性恶论”的法律与主张“性善论”儒家思想必然出现对峙,人们的主观意志与行为也会产生矛盾,必会威胁统治。但是无论儒家思想对规范人们行为,维护国家统一作用大小,仍然不能舍弃法律对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在古代法律作为政治的附属品,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强制力。而汉律的制订有着严格的制订程序,是不能随意更改的,这就给司法审判人员在审判案件时遇到有悖情理的案件时而无所适从。所以,儒家经义便成为了司法审判的依据,汉代的法律儒家化也是最先由此展开。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主要表现——春秋决狱
汉代的司法层面的儒家化开启了立法层面儒家化的先河,若没有产生审判案件时制定法与儒家思想的矛盾,则不会有春秋决狱的出现。瞿同祖先生说:“董仲舒以《春秋》作判案的依据,是以儒家经义应用于法律的第一人。”[2]有鉴于此,春秋决狱推动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是汉代法律儒家化的主要表现,对汉代法律儒家化进行研究,就要对春秋决狱这个司法审判制度如何与儒家经义融合进行分析。
(一)春秋决狱的来源
学界通说,春秋决狱这一司法审判制度来源于西汉初期,然而笔者却认为春秋决狱之“雏形”实际上在汉前便已存在,只是尚未形成正式的司法制度。据陈胜起义之案即可考证,“陈胜起于山东,使者得闻之,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3]可见当时的儒生便以《春秋》经中“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的道理评判陈胜起义之事。然而在当时儒学不是显学,不能完成秦的统一事业,因此儒学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反遭被罢黜。因而春秋决狱这一制度在未成形时便被扼杀,法律儒家化并没有真正形成。直到西汉汉武帝时期,大汉武帝将儒学经典国家法定化,立五经博士,并将儒学定为官学,同时董仲舒提出了系统化的一儒治国的方法,儒家经典才成为审判断案的理论依据。
这种系统性的引礼入律的方法便叫做春秋决狱。但是作为一种抽象的司法审判的运作机制,春秋决狱之名的形成有两个来源。来源之一是,当司法官判案时,根据案件事实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明显与儒家经义相违背,司法官应从儒家经典中抽象出法律原则,据此定罪量刑,追究罪责。在当时能被引来作为决事依据的儒家中的微观大义和儒家经典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但以孔子所著《春秋》为主,因此概称为春秋决狱。来源之二是,《春秋决狱》是董仲舒所作的司法判决汇编,由“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4]即可考证。然而时代更替,至今能找到的零散史迹也仅余六事。
从春秋决狱的来源我们可以看出,春秋决狱无论是在汉之前作为定义判理的方式,还是西汉盛行的审判制度,或是董仲舒整理的判例汇编,都是儒家经义渗入司法审判这一法律活动的表现,都足以作为我们以司法实践的视角审视法律儒家化在汉代的表现。
(二)春秋决狱的形成原因
春秋决狱形成的原因实际是对上文提到的春秋决狱来源之一的具体分析,西汉时司法技术过于薄弱,仅凭汉律的成文规定无法断案,这给了儒家思想渗入司法程序的契机,形成了开启汉代法律儒家化进程的春秋决狱。
原因之一是,法律规定有漏洞需要引经补缺。西汉时仅靠固定的律令制度难以维护封建统治,而引礼入法,儒法结合使用才能弥补制定法的疏漏,充分发挥成文法律的规制作用。實际上,更容易出现无相关法规的规定情况多存在于君臣制度中,因此接下来会举出典型的君臣案件来对此论点进行论证。
比较耳熟能详的缓解君臣关系的案子就是假冒卫太子案。汉昭帝时,一个叫方遂的巫道因长相酷似汉武帝之废太子卫,而集结兵士,骗取富贵,威胁统治。朝廷上下查遍律令,也未能找到证明方遂身份为假的方法,对此案束手无策。而当时的京兆从《春秋》中找到了与假卫太子情况类似的蒯聩的故事。《春秋》中的蒯聩实际上就与假太子方遂的情况相似,无需证明方遂是假太子,只需根据“得罪先帝者,罪人也”的法律原则,便可阻止方遂继位,弥补了汉律的缺漏,维护了政权稳定。 由此可见,在君臣关系中,春秋决狱在法律出现阙如时用《春秋》中记载的充满儒家以“君”为尊思想的经典故事来类比适用。
原因之二是,法律规定有悖情理时即以儒释法。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已经渐占主位,以德治国,德主刑辅,认为“人性本善”,刑罚之外要通人常伦理,参考“动机”对其定罪。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法与儒家思想势必会发生冲突,若以成文法进行审判难免会导致人心不服,若以儒家思想进行判决,必会造成法律虚置的现象。此时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即只有根据从包罗万象的《春秋》经中提取充满儒家伦理道德的经义去选择更有利的法条,才能更好地解决法理与情理矛盾的案件。
有一个纵麋为傅的故事,能够具体为我们展现当法律与道德出现矛盾时,以春秋决狱作为审判方式的原因。故事中君主猎获了一只幼鹿,让大夫带回去,大夫在带回去的路上,遇到母鹿,母鹿与幼鹿互相啼鸣,引起大夫恻隐之心,大夫遂将小鹿放掉与母鹿团聚,后来君主大怒,欲治大夫违君命之罪。此时董仲舒论断说大夫心怀恩义,感念母恩,动机纯良,虽然违反君命,也应减轻处罚。后来君主病危,临危托孤,顿时感其亲幼相连,赦免大夫,并升其为太子傅。此例是体现法律与伦理相矛盾的典型案例,按照律例,大夫应将其弃市,但若不顾大夫怜母鹿丧幼之痛,幼鹿离母之苦,必会民心不服,倡导“仁孝”的儒家伦理也难以真正深入人心。因此若既要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又不违反成文法的规定,就要根据《春秋》经义,从动机出发,考虑矜免情节,灵活选择合适的法律条文,适当减轻或加重刑罚。
春秋决狱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在随着法律与道德的矛盾愈演愈烈时历史的必然需要而产生。将道德法律化,以道德和成文法来维护政治统治,实际上是规范秩序的双保险。当法律条文对复杂的案件事实无法完全使用时,便引用儒家经义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和选择,既有利于案件的判决,又有利于人心的归服,政权的稳定。
三、从“许止进药”案看“原心定罪”
对春秋决狱的掌握还要重点理解其核心宗旨——原心定罪。“子误伤父”案是记载在《春秋决狱》中一件能体现“君子原心”原则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件。甲父乙与丙相殴,丙用匕首刺向乙,乙为了保护父亲用杖挥向丙,却误伤父亲乙。这本应属于殴父,甲应当枭首。而按照董仲舒断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挟杖而救之,非所以欲殴父也。”[5]乙殴父本是为了救父而误伤父,其原意并不违背儒家的伦理道德,这与《春秋》中“许止进药”的故事相类似。无论是在司法实践案件中的乙还是在《春秋》经中的许止,按照法家的犯罪构成理论来讲,他们都有犯罪行为,并都产生了犯罪结果即致父死伤,但是若按照成文法律的规定,他们必要承受弃市之刑,而他们的本始出发点——孝这一儒家的道德伦理精神却得不到赞扬。符合儒家思想的行为因为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危害结果而没有得到保护,反问儒家思想又如何产生支配人们行为的影响力,因此在司法审判中必须要延伸出符合儒家经义的法律观,在行为结果之外加上主观动机的考量,实际是原心定罪的功能所在。
结语:法律儒家化在西汉展开是历史的必然性,春秋决狱的应用是当时法制进步的重要表现,笔者从春秋决狱的来源、形成原因以及“原心定罪”对这一制度的历史成因进入剖析,论证了春秋决狱是汉代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表现,然而春秋决狱的技术规则以及在现代的司法价值仍具有研究的意义,需要学者们的深入剖析,才能将西汉时期这一司法制度完整再现。
[参考文献]
[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袁辉.以法杀人,更以理杀人——试析汉武帝时期的“春秋决狱”[J].理论界,2009(10):65-67
[4]武树臣.法家的师承:出乎儒而返乎儒[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1-17.
[注釋]
[1]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7页。
[2]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5页。
[3]参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4]参见《后汉书·应劭传》。
[5]参见《太平御览》。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