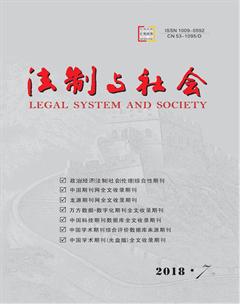乞讨者的生存现状及社会处遇实证研究
孙伟
摘 要 本文以在银川三区两县观察到的乞讨者为例,通过个案观察的实证研究方式,力图揭示真实的乞讨者的生存现状及社会处遇,以期更好地为大众所知,甚至为国家相关机构和政策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 乞讨者 生存现状 社会处遇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7.189
關于乞讨者的地位,国内外现在均没有成熟的定位。在乞讨者的社会处遇问题上,国内外则展现了不同的风格。我国是从“管制”、“救助”到“平衡”,经历了漫长时间才使得政府部门与乞讨者理想关系模式的建构并完成了其制度化。经历了痛苦的变身才实现从片面注重“政府管制”的权威主义工具性目标到片面强调“自愿救助”的自由主义价值性目标。 国外则是“安全网救济”、“政府允许主义”和“就业教育”三相结合的办法。尽管这些办法看起来很“高大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办法在执行过程中似乎有更大的阻力,在很多的案例中,政府都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果。
近年来国外围绕乞讨者的社会生存与地位等做的探索越来越多,思想也越来越成熟,我国在这一方面则明显不足。人权的发展问题也越来越使得乞讨者的社会生存问题亟待提上日程。同时社会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底层的人们开始渐渐进入人们的视角,人们对乞讨者的生存问题也渐渐地深入起来。本文即在这种环境下通过对乞讨人员的跟踪调查, 揭露其乞讨行为的特征,剖析与他们的关系最近的救助管理制度的不足,希冀为国家政策的改革、执法者更好执法以及公众知晓。
一、乞讨者的生存现状
乞讨者的生存环境是我们在研究乞讨者这一话题时应该最先研究的问题。掌握了乞讨者的生存环境,才能抓住研究乞讨者的命脉,从而掌握乞讨者之所以为乞讨者的原因,以及他们行乞的特点。这有利于我们从全局上了解掌握乞讨者的实际生存问题。
在银川,大概有350名职业乞讨者。况且,银川的两市三区还生活着数目众多的兼职乞讨者,数目不可谓不多。乞讨者的收入来源方式是固定的,他们大都靠着每天的乞讨和微薄的运气维持着生活。如预测所言,不同的乞讨者收入数目是不一致的——我们通过对四名乞讨者的长期观察总结了如下规律:
(一)乞讨者的生存环境
1.乞讨者的收入与其地理位置有关
在商业区、居住区等人的区位因素较大的位置,越是人员密集的场所,乞讨收入所得可能性越大。可以看到,在人员较密集的西夏区怀远市场、兴庆区鼓楼步行街、新华街以及各大公园里,乞讨者的存在呈“要么没有,要么很多”的规律。甚至在封闭狭窄约30米长的天桥上可以同时存在5名乞讨者。他们或间隔五米,或间隔十米,从不会紧紧地挨在一起。
但一些即使人员比较密集的地区且又相对富裕、交通便利的地区却几乎没有乞讨者。例如金凤区万达广场写字楼等。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上述位置管理比较严格,乞讨人员不得进入;另一方面可能是在这里蹲守所获得的收益较小。
与此相对的,在人员比较稀疏的地区、行政部门所在的地区特别是救助站、工商局、政府、消防队等具有管理性质的部门周围,乞讨者很少出现。一方面可能是受制于这些部门的权威,一方面可能是来这里的人员并不能使乞讨者们产生在他们身上取得收入的想法。
2.乞讨者的收入与其行讨时间的关系并不亲密
乞讨时长并不是制约他们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对于其乞讨时长来讲,在正确的地点向正确的人乞讨似乎效率更高。
乞讨者的乞讨时间具有很显著的特点,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时间可循的,他们基本上是围绕“饭点”时间。这类乞讨者多是兼职乞讨,以游动乞讨为主。他们有着固定的居所,家庭也有收入,一般在附近居住。银川市的生活节奏与武汉城市典型的过早文化不同,银川更偏向夜生活,商铺也大多在9时以后开门。在这一段时间内,乞讨者们面对的更多的是开私家车、坐公交车上班的上班族,他们行色匆匆,身上的零钱或许是为了坐公交车刻意准备的,与他们周旋,并不能获得良好的收益。另一类乞讨者是全天候乞讨的职业乞讨者,他们以固定乞讨为主。虽然一天之中他们的位置不断变化,但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他们的位置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是基本重合的(比如在早上会在一个位置出现,到了中午换到更温暖或更凉爽的位置,到了晚上又专挑有灯光的位置了)。
需要指出的是,冬季和夏季的交替基本上不会影响他们的收入,这在我们的统计结果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在冬季,他们从早上11时就在各商场、步行街出现,直到晚上9时,一天下来他们多的可以收入200元,少的也有30元。到了夏季,他们的乞讨时长变得比冬季长,从早上10时到晚上22时延长了两个小时。但是他们的收入并不包含这两个小时的溢价,或许因为冬季日照缩短的缘故,使得人们行程更紧凑,也使得乞讨者的乞讨行为密度大。到了夏季,银川的高纬度使得日照时间有效延长,但与此而来的是人们的作息时间改变了,睡午觉在夏季已经达成了共识,同时由于白天的时间比较长,人们的选择时间和实践时间也变长了,可能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满足人们的马斯洛需求曲线,因此必须要去某一地方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综合下来,乞讨者们的乞讨收入并没有增加,反而延长了“工作”时间。
(二)乞讨的原因分析
1.生存
生存是马斯洛需求层次中最低级的需求,也是最应该满足的一项需求。当这种需求无法由自身的劳动和创造满足时,从别人那里获得需求资料无疑是最为正确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包括犯罪、寄生、乞讨在内的众多,其中最简单、风险性最小的就是乞讨,它既没有寄生那种将自己命运和宿主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危机感,又没有犯罪那种随时受到法律制裁的彷徨感,相反,乞讨更称得上是“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
2.利益
利益,更具体的来说,是利润。乞讨的物力成本支出为零(虽然时间成本高昂,但谁又能说整日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以度日的人不付出时间成本呢?),但收入却是一个正数。这在任何一个行业都称得上是暴利的存在。然而除了少数聪明有能力的乞讨者外,几乎没有哪个乞讨者会把乞讨同他们的幸福生活挂在一起,但是这种收入对于他们来说太容易了。
3.放逐自我
只有一小部分人出于放逐自我的原因而乞讨。在我们的采访中仅仅有一位似乎符合这个原因。这位乞讨者自称四川人。由于父母离异,他十几岁便一个人辗转各地寻求生活,因怀揣穿越中国的梦想,一直在外漂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徒步穿越了半个甘肃。在中国似乎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或是因为路途的艰难而放弃了,或是因为突发情况而被迫改变目标,或是一开始就准备穷游,把自己的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人的同情和自己的运气上。认清现实很难,放弃梦想却相当容易。他们有的半路做了职业乞讨者,有的的确凭借着好运气改头换面,有的则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活脱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浪者。
(三)乞讨者的特点
乞讨者以其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明显的外部特征很容易被辨认出来。根据我们的采访结果和调查结果,我们总结了几条内部特征如下:
1.以独自乞讨为主,不论兼职乞讨还是职业乞讨
之前的法制不健全,国家针对内外部事件的应接不暇,乞讨者便铤而走险形成了具有违法性质的乞讨组织。这些组织甚至诱骗未成年人或女性,做成专门收取利润的工具。但这种组织在当下中国俨然已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即使放在过去也一样是非法组织)。乞讨者们暗地里组织时也要考虑风险和收益。风险是:乞讨者们以其人与人的组织面对精良的国家机器,在于国家机器的对峙中他们不能取得沟通上的优势,其在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民众支持率上也都远远不及国家机器;另外,假如运气稍微差一些,他们将会暂时性的不得从事乞讨行为,他们或者将被送往救助站,由救助站护送返乡,或者因为违法行为或者违规行为暂时住进监狱或者看守所。在这种博弈下,聪明的乞讨者应该会选择独自安生,在法律的限度内进行乞讨。
2.乞讨者大多受到过救助管理站的救助和帮扶,但是他们更反感救助站对他们的救助帮扶
救助站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针对乞讨者,他们会组织进行护送返乡、介绍工作、安置代养、购票返乡等工作。总之,原则是让乞讨者们放弃乞讨,从事其他业务。但这一宗旨与乞讨者的目标相悖,因此乞讨者并不会轻易悔改,他们通常会无视救助站提供的帮助。因此在几番救助之后,救助站对已经救助过但还是从事乞讨行为的乞讨者不再进行收入返乡,而是一种放任的心态,任由其行讨。可以说,乞讨者在对救助站的战争中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
3.乞讨者们善于将他们的乞讨行为与宗教行为联系在一起
这是银川的乞讨者很有特征性的一点。银川市是回族同胞的聚集地宁夏的首府,但这里的乞讨者展示的宗教并不仅仅是伊斯兰教,还有基督教。在怀远街头,时常有带着白帽子的老者背着一个白色的挎肩包走来走去。他们脚步健硕,但还是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呈讨要的姿势。对于这种既有乞讨性质也有宗教性质的行为我们可以把这些归为乞讨行为。
4.相对于兼职乞讨者,职业乞讨者具有更强烈的反社会(政府)人格
这多半是因为职业乞讨者全天候、流动性不强的特点,更容易引起国家救助机关的关注。在救助机关,他们不仅没有了收入,还会被送回到家乡。如果家乡乞讨也能像这里一样维持收入也就好了,这样他们也就没有如此强烈的向大城市聚集乞讨的想法了。很不幸,入不敷出是原因,不是结果。因为在家乡乞讨无法维持生计,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来到这里乞讨;并不是因为从这里乞讨收入多,家乡收入少所以才会选择来这里乞讨。因此乞讨者们对于国家机关的反感我们可以理解了。另外一个原因是职业乞讨者多半是上访专业户,受《上访法》规制之后无法宣泄自己内心积压的不满情绪,转而自暴自弃,希望引起社会重视。
5.乞讨是长期行为
虽然乞讨在外人看来很没面子,但乞讨是一项无任何物力成本支出却能享受到多倍收益的活动,因此很受失能老人的欢迎。他们或三或五走上街头,然后分散开来,赚取一天的外快,然后再聚合回家。这样的行为可以持续好几年,我们可以在银川的街头看见很多这样的行乞者。他们大多头发花白,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做行乞状。
二、乞讨者的社会处遇
乞讨者的社会处遇,是乞讨者在各个关系中对方对他们的看法和做法。社会处遇的问题,是人文社会追求的最后答案,是揭开实质利益链条的抓手。本文以对乞讨者联系最为密切的机构和人员的调查为根本,总结对乞讨者的评价如下:
(一)救助管理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1号即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此收容遣送制度真正成为中国大众茶余饭后的众矢之的。取而代之的,是救助管理站的诞生。
救助站的本质,是一个落脚点,是回家的车票。通过对身份的识别和对信息的协调处理,救助站可以轻易破解乞讨者真假谜团。凭借着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可以在现场分辨真假,对于真正有需要救助的乞讨者,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对于假扮的乞讨者,他们除了驱除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在长时间的斗争中,他们对乞讨者的评价鲜明地呈现出比较低的趋势。这是可以預见的。
(二)公安、城管等执法部门
公安、城管在社会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事务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有时他们会联合执法,走上大街小巷,针对占道流浪乞讨者给予处理。假如救助管理站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公安、城管等拥有一定执法权的执法机关就是“发现美丽的眼睛”。公安、城管拥有行政法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可以针对违规乞讨者以适当的处理。
那么,他们对于乞讨者的评价如何呢?针对我们在街头的采访,我们发现,公安、城管等部门,特别是城管,是最反感乞讨者的。在他们眼中,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市容是最直接的政绩。其与乞讨者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目前能做的也只有占道乞讨为名驱逐乞讨者,对于“没收乞讨所得”或者“乞讨用物”,除了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在道义上看来也是不能容忍的。在笔者看来,公安、城管依法驱逐乞讨者是分内之事,但很容易遭到社会上不明真相群众的围观,只会加剧人们心中对公安、城管坏的刻板印象,进而引起愈为激烈的人民内部矛盾。
(三)社会公众
前面说到,公安、城管依法驱逐乞讨者时,很容易遭到社会上不明真相群众的围观。这一方面是群众的好奇心在作祟,另一方面源于人们对乞讨者的同情。
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人们对“乞讨者真假参半”的说法深信不疑,但面对每一个乞讨者时民众显然都希望他们是真正的乞讨者,或者说人们都不希望自己被假的乞讨者骗取钱财。与此相似的是,尽管民众认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面对“你愿意将一部分善良给予乞讨者吗”的问题时,民众大多数还是选择了“是”并表达了他们对乞讨者的同情。但有意思的是,民众表示他们不会对“乞讨者的未来感到担忧”。另外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尽管民众认为“乞讨者随时随地行乞的现象需要被整治”,但面对具体的问题时他们似乎没有更好的答案。
尽管矛盾重重,但面对“乞讨者的尊严”模块时人们大多数都选择了“乞讨者也有尊严”的选项,并表示自己将在无路可走时会去选择“当一名乞讨者”。当采访问道“你会看不起假扮的乞讨者吗”这样的问题时,他们大多数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
对于乞讨者行乞区域的商家而言,乞讨者的存在只会妨碍到他们店铺的客流量,因此他们对乞讨者也表现了足够的反感。街头采访中也有几位商家明确地表示对乞讨者“并不关心”。
这样看来,社会大众对于乞讨者的乞讨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并会对他们表示同情或者做金钱表示。底线在于,乞讨者必须是真正的乞讨者,且他们的乞讨行为不能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样的意义在于,既可以满足公众的善良支出,又可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
总而观之,人们对于乞讨者的看法不一,自身在对待乞讨者如何的问题上也表现了深刻的两面性、矛盾性。
三、对有关乞讨者几个问题的反思
(一)乞讨权
秩序、自由、平等、人权、正义与效率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法律的核心价值。关于乞讨权属于人权、乞讨权是不是真正存在的问题,大多数学者在讨论时几乎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乞讨权并不存在。
少数学者以“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理否认这种观点,但更多学者持“无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的法谚批判这种观点。更多的学者认为以“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理去推翻乞讨权并不存在的观点是有着逻辑上的漏洞的:对于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事项,公民享有的仅仅是自由,不是权利,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对权力来说,最重要的特征是获得救济。西谚有语:“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乞讨者虽然有请求他人予以施舍的自由,但都被请求者既可以同意请求,也可以拒绝请求。而乞讨者无权对被请求人的拒绝行为,寻求法定的救济途径。因此,乞讨并不是一种权利,至多是一种自由。 更有学者在法理上深入讨论了乞讨权。他们认为“乞讨权”的提法不甚科学,乞讨不是人权或者权利,而是一种“自然自由”和实现“救济权”的手段。他们指出乞讨不是人权,也不是目的,单一乞讨为手段实现的社会“救济权”却是人权。在政府设置“禁讨区”的问题上,他们指出:自由的行使都是有限度的,即不能侵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手段的行使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别,这为政府“限制乞讨”提供了道德基础和法律基础。容忍乞讨是行善和文明的表现,适度地限制乞讨则是一种更大的文明,而且也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原则和规定。
笔者认为,乞讨是一种遭遇,就像饥饿一样,不存在着“饥饿的权利”,同样不存在着“乞讨的权利”。单纯的乞讨权是不存在的,至少在中国国家法律的框架之内,乞讨权的存在是不能容忍的。中国政府以管理者向服务者的地位转变,管理的权限逐渐被限制,管理的事项也逐步减少。相比之下,政府为民服务的范围在扩大,在“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指导下,政府关注各个阶层的人民的生存、生活。我国政府以其明确的措施表明了它的态度:服务,而非管理。这在当下是难能可贵的情怀,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二)救助管理制度运行的困境
救助管理制度自诞生以来一直饱受人们的争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代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自此收容遣送制度消灭,救助管理制度诞生,其取得的成就自然不提。但是,由于其更像是一针安慰剂,出台有些仓促,相比之下的科学性和操作性也远远超出了社会现实,导致其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不少的困难问题。
1.相关执法权缺失
以银川市救助管理站为例,该站救助管理的工作流程是:来站(包括街头直接救助来站,自愿求助来站,城管、公安等部门、组织、个人引导护送来站,救助站护送来站、协作救助来站)、接待讯问、核查甄别、入站、服务(包括查询亲属,食宿、通讯,医疗救治、康复服务、心理辅导、卫生教育、法制教育、文体活动和发布就业信息等)及离站(包括介绍工作、汇款返乡、购票返乡、亲属接回、护送返乡、安置代养、终止救护、放弃救助和擅自离站)。
可以看到,对待乞讨者,救助管理站的做法是呼吁乞讨者到救助站接受救助,否则不进入救助流程。问题是,救助站的宗旨是“自愿救助”:对于愿意接受救助的乞讨者救助站当然不会拒绝提供救助,救助站也乐于救助。但同时,对于不愿意接受救助的乞讨者救助站是没有办法的,救助站能做的只有在天寒地冻之时送上被子和大衣,确保他们度过寒冬。前面提到,收容遣送站更名之后连相应的执法权也一并带走了——救助管理站没有执法权。没有了牙齿,骨头是啃不动的。
这显然与救助站的设立初衷完全相左。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保障其基本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制定本办法。”第二条规定:“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性救助措施。”这里提出的“临时性”救济不仅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社会,而且特别强调了站内的人身安全。第九条规定:“救助站应当保障受助人员在站内的人身安全和随身携带物品的安全,维持站内秩序。”第十三条规定:“救助站应当建立、健全站内管理的各项制度,施行规范化管理。”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救助站工作人员应当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有关规章制度,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不准敲诈、勒索、侵吞受助人员的财物;不准克扣受助人员的生活供应品;不准扣押受助人员的证件、申诉控告材料;不准任用受助人员担任管理工作;不准使用受助人员为工作人员干私活;不准调戏妇女。”可以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把受助人员的人身安全防范到了极致。在一共十八条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光是强调受助人员的人身安全的篇章就占用了近六分之一,去掉原则、辅助性条款和总纲等,针对救助管理站的行政权限则所剩无几。而在民政部下发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民政部特意在第二十二条作出了要求:“救助站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救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违反规定的,由该救助站的上级民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追究责任”。法律规范对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规避的措施,这的确保障了寻求保障的乞讨者的权利,但同时又从权力上限制了救助站。对于前来寻求救助的乞讨者,救助管理站除了进行必要的救治和管理外,都无一例外护送返乡了。救助站的困境,就是属于自己权限内的事务没有权力去做。
2.救助对象时常混乱
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堆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制定本办法”。开章明义地指出对象为“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为了避免混乱,民政部在下发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条中又阐述了救助对象的内涵和外延:“《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第二条第二款又规定:“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欠款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从文本立意上来看,救助管理制度的对象应该是很明确的,但是实际中的情况并不如此。
通过对银川市救助管理站的调查以及对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的采访,我们发现救助管理站的救助对象很混乱:当中既有上访多次未果的人员,也有身患疾病无力自存的病人,既有精神健康正常的人,也有精神病、智力不健全的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标准不明确导致执行结果有差异的原因,也有现实工作中对标准的变通执行的原因。
3.相关标准不够明确
“自身无力解决食宿”的标准是什么?是一日三餐只能吃两顿饭,还是没有睡觉的地方还是两个都是?是有固定的居所但没有住宿的环境,还是无力负担食宿所需的费用?“无亲友投靠”指的是什么?是自己不想投靠还是亲友不愿意接纳?还是只要有名义上的亲友就可以?还有些是因为无法执行或者只能变通执行。以“无亲友投靠”为例,由于救助管理机关不具有相当的管理权限,对于身份不明的投靠者救助管理机关只能通过各个机构之间的数据交流和投靠者对自身信息的表露。倘若投靠者拒不交代或者交代不清有无亲友,即使实际上存在着一定数目的亲友,救助管理机关也只能认定为“无亲友投靠”。“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则根本无操作的空间。现实生活中会有许多情况会使得一个正常人摇身一变成为“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例如外出旅游手机钱包不慎丢失,身边有没有可以投靠的人。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他们需要的不是救助管理站的登记救助,而更可能是一个电话或者一张回家的车票。假如把他们安排为“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则要贻笑大方了。标准的不明确,带来的是结果的多样化。而操作的不能,带来的是可远观而不可执行的尴尬。
4.救助管理制度与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等衔接不力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救助站应当建立、健全站内管理的各项制度,实行规范化管理。”第十六条:“救助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受助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应当依法处理。”第十六条第二款:“受助人员应当遵守救助站的各项规章制度。”不留情地说,这些都只是泛泛而谈,对于一些实质性问题根本没有给出答复。例如,受助人员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就(才)依法处理?受助人员违法依什么法处理?由谁处理?受助人员不遵守救助站内的各项规章制度怎么办等等,如今看来,这些问题仍然缺少必要的答案。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缺失带来的不仅使得合法性有漏洞,更使得部分權力缺失。
救助管理站的权力缺失导致执法困难。“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现象正在救助管理站的身上发生着。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缺失带来的部分权力缺失带来的执法硬伤,使得救助管理站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三)对相关工作改进的设想
针对以上国家对乞讨者问题的相关工作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隐患,笔者认为,为了实现救助管理制度的最大功效,应该至少从两个方面出发。
1.执权者、执法者
国家不仅要完善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令相关执法者有法可依,并给予其中模糊性的标准以明确,对其中现阶段没有办法施行或者现阶段施行效果可能不好的,要创造好营造好适宜治理的环境;更要给予一线工作者以权力,“把指挥权交给离炮火最近的人”。 在明确了标准之后,相关执法者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严格执行,把纸上落实到实际里,严格明确责任与权利。各级执法者要加强数据交流,保持信息畅通,运用大数据、小个体的跟踪方法,切实关怀流浪乞讨者,把问题解决在摇篮里。国家要完善相关的配套设施,使得乞讨者在不接受的社会管理的情况下不至于生活如此落魄,至少要在人道主义上表示关怀。继续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持之以恒的从数量和质量上使得乞讨者逐步减少。
2.社会公众
各位社会工作的参与者以及社会公众要认清自己在社会各项工作中的作用。银川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救助困难群体,可通过各级民政部门或慈善机构进行捐助,也可直接向银川市民政局下设的社会捐赠接收工作站捐助。这样,不仅可避免爱心被利用,也保证了真正需要资助的流浪行乞者能够得到救助。类似的,各级政府可以发挥宣传优势,引导社会公众正确对待流浪乞讨者。
四、结语
乞丐的命运被描写的就像跷跷板的两端,是两个极端:一点高高在上,是富足者的位置,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乞讨者;一段在地下,艰难的活着,这是真正的乞讨者:他们或许为躺在病床上的家属艰难的筹钱, 或许因为物力维艰而争取活下去的希望。我们的制度要明确自己的责任,真切了解从立法到执法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要一味回避。要真正把东西送到每一个真正需要的人手里。要去伪存真,克服困难,实现制度创设的最初目的。
注释:
刘岩、刘威.从“管制”、“救助”到“平衡”——政府部门与乞讨者理想关系模式的建构及其制度化.理论与现代化.2006(1).43-47.
该课题采用以下方法开展研究工作:(1)发放问卷800份,由调查人员对银川市救助管理站、受救助人员、流浪乞讨人员进行调查,实际完成并回收有效问卷537份;(2)对流浪乞讨人员有选择性的进行跟踪,其中夏日跟踪乞讨者两人,冬日跟踪乞讨者两人,为期各一个月(仅周六周日)。目的是调查了解他们的乞讨方式、乞讨原因,总结归纳他们的乞讨特点;(3)对有关乞讨政策的中外文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搜集整理。
采访语录.因为这些乞讨者相信,“零钱的准备是需要时间的,普通人的手里并不会给每个乞讨者都准备了钱,所以间隔越远,给人们准备零钱的时间越长,他们的收入机会也就越多,相应的收入也会增加”。不得不承认,乞讨者们并没有想象中的单纯,他们“甚至成群结队,专挑过往的恋人或者看上去并不着急的行人下手”。因為他们知道,恋人要想维持对方心中的形象,必须要付出足够的善良;相比于行色匆匆的人,看起来并不那么着急的人或许会从钱包里掏出一块两块的零钱。
对张伏财情况的说明.银川市救助管理站.比较鲜明的例子是步行街的张伏财(化名)。张伏财原是平罗县渠口乡人。该人因车祸造成下肢瘫痪,治疗中断后因对事故处理不满意,自2009年6月开始以上访为名在银川街头乞讨。其以兴庆区鼓楼南步行街、新华街路口为主要地点,用改装的三轮摩托车占道搭建窝棚露宿街头。他将上访材料满地摆放,将未治愈的伤口故意裸露,用高音喇叭播放音乐和摆放其曾经服役时的照片等多种手段吸引过往行人围观和施舍。2009年7月7日,张伏财被银川市救助管理站护送至平罗县,交由该县信访局处置。此后不久,张再次返回银川,依然在繁华路口摆摊乞讨。2010年,随着《银川市加强流量乞讨人员救助与管理暂行办法》的印发与实施,张多次被公安。城管联合工作组护送到银川市救助管理站,有银川市救助管理站护送返乡。为此,银川市政法委还专门协调石嘴山市政法委一起协商过张伏财的处置事宜,均没有达到好的效果。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与管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多次向平罗县发出告知函,告知平罗县对张伏财加强管理,避免其再次外出乞讨,如此反复,至今多达十余次。并且随着事情的反复无果,张伏财态度越来越强硬,乞讨方式越来越张扬露骨。2015年2月12日,市公安、城管联合工作组在街头集中整治中,再次发现张伏财在步行街乞讨,不但上访材料摆满一地,还让其妻子在步行街口支起了炉子做起了饭。工作组旋即对其进行劝阻,当爱人不但不同意接受救助,还用剪刀威胁执法人员,称要采取强制措施就用剪刀自残,当即引来一片不明真相群众围观。考虑到步行街人流量大,且围观群众过多,工作组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2016年“盂兰盆”节期间,张伏财在北塔放着音响铺摊乞讨,经银川市救助管理站联合丽景街派出所民警联合救助送其返乡,张用石头砸坏了救助站的车辆的玻璃,并辱骂公安和救助人员。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可以看出,他们对国家有关政策或者调整关系的不满只能停留在和基层人员对抗的层面。
郑春燕.“乞讨权”存在吗?.法制日报.2004-03-18.
肖艳辉、王保庆.“乞讨权”的法理分析——从人权和自由的角度.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1).66-70.
李迎生、吕朝华.矫枉过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的实证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7(5).5-10.
银川市救助管理站宣传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