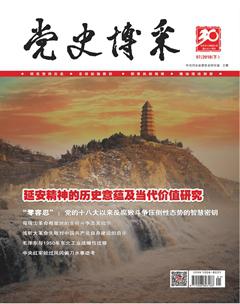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斗争及其启示
闫丽娟
[摘要]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在琼崖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曾经两次保存革命的火种,被誉为“琼崖革命的摇篮”。在国民党两次派兵“围剿”母瑞山期间,琼崖红军在母瑞山上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其生存的残酷性举世罕见。面对残酷的生存考验,琼崖红军没有屈服,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采取了一系列生存斗争措施,展示出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把这种革命精神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关键词]母瑞山;琼崖革命;生存斗争
母瑞山位于海南省定安县南部,是五指山向东北延伸的山脉,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在土地革命时期,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琼崖红军独立师曾迁入母瑞山,领导全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期间,母瑞山根据地经历了国民党两次“围剿”与封锁,这段时期是琼崖革命最艰苦的岁月。为了生存下去,琼崖红军采取了很多生存斗争措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成为重要的党性教育基地。对母瑞山的革命斗争精神进行挖掘,对于推进党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经历的两次“围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琼崖共产党人开展了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斗争,琼崖红军的人数越来越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琼崖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惕,先后两次“围剿”琼崖革命。琼崖革命队伍在“围剿”之时两次撤入母瑞山,依靠山高林密和险要地形与国民党进行不屈的斗争。
(一)国民党第一次“围剿”母瑞山根据地。1928年3月中旬,国民党第11军蔡廷锴师和谭启秀独立团来琼,对琼崖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据冯白驹回忆,“革命力量经过和敌人不断搏斗后,在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下,琼山、文昌二县的革命武装队伍,便向东路(乐会、万宁地区)移动,向军事头脑部集中,退入山区。武装力量撤退后,我仍在琼山坚持工作。由于武装力量撤离,敌人的白色恐怖特别厉害,摧残组织,屠杀群众,无所不用其极。”①这个时期,革命力量遭受到严重损失和削弱,到“1928年夏秋时,3000多人的红军队伍只剩下几百人”②,国民党的“围剿”不久就使琼崖革命陷入低潮。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省委对形势作出判断,在1928年9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团广东省委在致琼崖特委的信中指出:“琼崖革命潮流大体上说起来,在目前无疑义是向下的,群众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的热忱与勇气。但一定要知道,琼崖并不是已经完全失败,我们仍保留一部分红军,保留一部分政权。”“特委要有计划地保留武装力量,以影响帮助周围的群众工作。”③为保存革命力量,琼崖革命领导人王文明、梁秉枢等人于1928年12月率领红军和琼苏直属机关转移到母瑞山上,开辟了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冯白驹也在自传中讲到:“到一九二八年底,全島斗争已陷于全面失败,所剩一些武装力量和苏维埃领导机关,便撤入母瑞山作长期坚持。”④这样,母瑞山就成为琼崖革命的根据地,红军依据险要地形,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至1929年秋,琼崖红军的力量得到恢复,并扩大为独立团。到1930年8月,“琼崖特委决定在琼崖红军独立团的基础上,统一组编各县红军和赤卫队,在母瑞山上建立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个驳壳队,共有2000多人。”⑤到了1930年底,“红军师部随同特委、琼苏机关迁移往内洞山,最后迁到琼东四区。同时留下红一团巩固和发展母瑞山革命根据地”⑥从1928年底到1930年底,琼崖红军在母瑞山上的时间总共大约是两年,粉碎了敌人妄图扑灭琼崖革命的企图,这是母瑞山根据地第一次保留革命火种。
(二)国民党第二次“围剿”母瑞山根据地。1932年7月,国民党陈汉光部“围剿”琼崖革命根据地,琼崖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失利,红军独立师解体。特委书记冯白驹、琼苏主席符明经和秘书长王业熹带领党政机关和红军警卫连100多人又被迫撤回到母瑞山根据地,坚持斗争,天天与敌周旋。⑦在母瑞山期间,琼崖红军也试图突围,但没有成功。冯白驹回忆:“在母瑞山突围失败后,我和几十个干部在母瑞山继续坚持,后因不断地派出查看各县情况的同志均没有归来,结果几十个人就只存下二十多人,在母瑞山坚持了近一年,这一年可以说是最艰苦的年头,不仅无衣无食,又和外边完全失去联系,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且敌人又不断地搜山进击,驱逐山地居民,迁移边缘村庄,封锁山路,企图打不到我们,也使我们饿死于深山中。”⑧直到1933年4月,琼崖特委才成功突破敌人的封锁。冯白驹给中央的报告:“特委在1932年开始被敌人围困于山中,直到一九三三年四月才冒险迁出琼文界来。在特委被困的时期中,特委和各县党都断绝关系,特委失去领导各县党工作的作用”,⑨这与1932年8月13日中共两广工委给中央的报告是吻合的,报告称:“琼崖关系到现在仍无法打通,此地没有适当的人可派去,我们知道他的两个通讯处,写了几封信去,都没有答复,我们通讯处他们是晓得的,不知什么缘故没有人来。据反动报载和琼崖商人传来消息及我们的推测,琼崖情形是很严重的。”⑩从陈汉光1934年7月抵琼到冯白驹1933年4月从母瑞山突围,大约是9个月,“琼崖特委机关被敌人围困在母瑞山上长达8个多月之久。”?从1932年8月冯白驹带领革命队伍上母瑞山到1934年突围,革命队伍在母瑞山上的时间大概是8个月,这是母瑞山第二次保留革命火种。
在国民党两次“围剿”母瑞山期间,琼崖红军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有敌人的围堵剿杀,还有残酷的生存斗争。国民党的“围剿”和封锁没有扑灭革命的火种,革命队伍在母瑞山上保存下来了,创造了琼崖革命“红旗二三十年不倒”的奇迹,母瑞山根据地因此被称为“琼崖革命的摇篮”。
二、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生存斗争的残酷性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生存环境非常残酷,革命队伍要生存下去,除了武装斗争之外,还必须获取足够的生存资料。根据有关记载,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生存的残酷性主要表现为粮食、衣物、住所和用品等四个方面。
(一)粮食奇缺。在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琼崖革命时,革命队伍在母瑞山上的人数达到600多人,粮食供给成为重大问题。开始时是派人下山购买粮食,但随着敌人的经济封锁,粮食供给越来越困难。母瑞山的红军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吃饭问题,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比如,挖外迁村民遗留下来的番薯,但由于人数太多,很快番薯被挖尽;有些同志就冒险下山,去摘椰子,结果遭到敌人枪杀;会抓鱼的同志下到山沟小河里摸鱼虾;有的同志把南椰树心和槟郎树心弄出来充饥;有些会爬树的同志爬到树上掏鸟窝;有的同志到山林里面去采些蘑菇,摘点木耳,割些竹笋。?当然,这些食物不能作为主食,且其数量也有限,能解燃眉之急,不能作长期需要。曾经“100多人在山上没吃过一顿饱饭,有时十几天吃不上一碗稀粥,只好靠野菜充饥。”?有一种野菜在山上吃的最多,后来被命名为“革命菜”,据李爱花回忆:“野果吃光了,我们就吃山兰地里生长的‘革命菜和‘糯米藤叶,接着又以山芭蕉心为主食。山芭蕉心寒冷,许多同志吃后拉肚子,领导人看到这种情况劝同志们不要多吃山芭蕉心。于是,大家改为凡是软嫩的树叶都摘下来放在嘴里嚼。感觉到不苦的就咽;没有食盐,我们就用加冬叶烧焦当盐。”?据冯白驹回忆:“然而我们仅有的这些同志始终是不屈服于任何困难和艰险的。在这一年中,我们吃‘革命菜,盖香蕉叶,忍饥受寒,终于战胜了困难。”?
(二)衣物匮乏。在陈汉光部“围剿”母瑞山期间,由于“敌人经常搜山‘围剿,使我们的人员处境极其艰难。”?由于长期和搜剿的敌人转战,在山林中串来串去,战士们的衣服被山林的树枝、荆条撕破。虽然母瑞山在亚热带地区,但山上的冬天仍然比较冷,在无衣可穿的情况下,冯白驹就带领众人用树叶和树皮披在身上。“由于个个衣服破烂,脸黄嘴尖,满身长虱,头发披肩,犹如野人一般。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绝大多数同志病倒、饿倒。在马翁岭北面的岭岩、棺材沟、塘岭村一带就有一二百具红军尸体”。?
(三)住所恶劣。在母瑞山上居无定所,“没有固定住的地方,因敌人不断分片搜山,我们的同志不得不经常流动转移,只好住在山洞里。”?根据李爱花回忆:“由于敌人和苗人天天搜山,白天我们有些人睡在石洞里,有些人躺在篓丛里,太阳落山后才出来活动。”?琼崖红军在山上搭建一些茅草屋,敌人一来被放火烧掉;台风一来,被刮掉、刮坏。风雨过后,战士再用树枝、树叶重新搭起小棚子来住,而这样的小棚子虽然能够遮阳,但挡不了风雨的侵袭,挡不住山蚊子、山蚂蟥、山蚂蚁和毒蛇的侵扰,这样的居住条件反映出根据地的生存困境。
(四)用品缺乏。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最重要也是最缺乏的用品是药品和武器。由于药品的缺乏,士兵受伤,皆因乏药医治而死。据李汉回忆,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个个骨瘦如柴,头发像一堆乱草,胡子长长的,一双双眼睛布满了血丝,不少人得了水肿病。”?野菜吃多了,有的同志拉肚子;被山里蚊子叮咬,有人得了疟疾;还有的同志出现烂脚、生疥疮等疾病,很多人因此病死。据梁秉枢回忆:“由于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在我们队伍中有200多人病故。军械厂60多人,竟尽死无存,红军医院的数十人也无一病愈。有一天,竟死7人。”1930年1月17日,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也因病逝世。武器也是极为缺乏,在每次的战斗中,都不能发挥较高的战斗力。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生存斗争的残酷性,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甚至到了要钻木取火的地步。关于这段艰苦岁月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冯白驹等历尽艰辛万苦,在母瑞山上支撑了8个多月,过着大地为床,树叶为被,野菜为粮的野人生活,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生动地说明了这段时期生存的残酷性。为了生存下去,琼崖红军在母瑞山上也曾经采取过很多生存斗争措施。
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生存斗争的措施
为解决生存问题,母瑞山的琼崖红军采取了一系列的生存斗争措施。这些生存斗争措施大致分为两类,一方面是开展自救活动,即依靠自身的力量获取生存资料。另一方面是从外部获取生存资料。母瑞山根据地的生存斗争措施也是红军面对艰苦条件被迫采取的办法,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红军在艰苦的环境中保存下来。
(一)依靠琼崖红军自身开展生存自救活动。在琼崖革命领导人王文明的倡导下,根据地的官兵发起过生产自救的活动,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办起三个红军农场,一个军械厂,一个粮食加工厂,一个缝衣组,一个军政学校,一个红军医院,一个印刷厂,一个供销合作社等。1932年国民党陈汉光部“围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强迫群众把农场毁坏,农场自此停办。在1932年8月,母瑞山根据地被敌人进攻后,红军机械厂、医院、粮食加工厂等茅房400多间均被敌军烧毁,大批粮食财产被抢走。军械厂在南牛岭脚下的一个山坳里,有十几间草屋,其中三四间厂房,说是厂房,其实就是一种简易的草屋,一共有几十个工人,设备相当简陋,没有机器,有风箱、锤、钳等简单工具,能够制造的武器有地雷、手榴弹、炸药和翻装子弹。红军的军械厂规模不大,但是制造的武器却使敌人胆寒,在保卫母瑞山根据地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在1932年国民党陈汉光部“围剿”母瑞山时,军械厂的工人全部被饿死。没有工人,军械厂自然无法再办下去。这一系列生存自救活动的规模都不大,并且大多自救的项目也相当简陋,只能勉强解决生存问题。对于革命队伍而言,解决生存问题、开展自救活动并不是份内任务,琼崖红军的这些自救活动,是对异常残酷的生存环境的回击,从侧面最真实地反映出母瑞山根据地的生存状况。
(二)琼崖红军通过打没、战争缴获、税收、派粮催粮、捐献这些方式获取生存资料。一是打没。打没也叫作经,这是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比如1929年春,母瑞山的红军打没了南闾乡田肚村的反动地主,没收了30多头水牛;1930年秋,琼苏委员陈玉候带领30多名红军,打没了屯昌墟的奸商,运回一大批布匹、藥材、食品等物资。二是战争缴获。比如,1930年5月1日,红军独立团长梁秉枢带领第一营红军和军政学校学员共300多人,攻打定安县城,县长逃走。缴获步枪20余支,光洋1000多元,没收了反动商号的一大批物资。三是税收。在母瑞山周围地区设置了石壁、万泉河、岭口、翰林、南闾、乌坡等征收站,比如,万泉河征收站每月就征收光洋400元。四是派粮催粮。派粮催粮的方式是由苏维埃政府写信给地主豪绅,限额限期把粮食送到指定地点,否则就去打没。如1928年,大山乡苏维埃政府一次就向楼坡村地主吴俊承派了10石谷。五是捐献。捐献完全是群众的自愿行为,农民群众宁愿自己不吃少吃,也愿意把粮食捐献给红军,他们知道这是革命的队伍、穷人的队伍。但是捐献这种方式获取生存资料的数量非常有限,因为农民的手上并没有太多粮食。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斗争措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琼崖红军的生存问题,在母瑞山根据地始终面临的困难是生存资料的匮乏。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缺少群众的支持。一方面,敌人的封锁使革命队伍和广大群众被迫隔离开了。本来琼崖地区就地广人稀,狡猾的敌人还强迫一些群众迁走,不允许群众接触革命队伍。除此以外,国民党还对群众进行恐吓,如“剿村捕人拷打并唱‘通共者杀戮全家等口号恐吓群众;制造种种诡言来污蔑本党,使群众脱离本党的政治影响,由他们仍使用改良主义来欺骗群众。”另一方面,从生存斗争的措施来看,革命队伍主要依靠的也是自身。如琼崖红军的自救活动与措施主要依靠广大官兵;打没、缴获、税收、派粮购粮这些行动基本上也和群众的关系不大。
四、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生存斗争的启示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残酷的生存斗争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笔精神财富对于新时期进行党性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既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要紧密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同样,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要继续发扬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共产党人的灵魂之中,成为支撑共产党人前进的源源不竭的动力。当前弘扬母瑞山根据地的斗争精神成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对进行革命教育、党性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革命队伍自身的建设上,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面对外有敌人残酷的“围剿”与封锁、内有严峻的生存困难的状况,母瑞山根据地的红军能够始终坚持斗争,靠的就是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毫不动摇,坚信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定将到来。冯白驹经常给干部战士讲革命道理,坚定大家的信心,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在环境允许时,他还带领大家唱革命歌曲,活跃大家的情绪。”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残酷的生存环境中,没有理想信念的支撑革命队伍是无法坚持下去。在敌人重兵围困母瑞山期间,王业熹对革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他鼓励同志们说:“革命运动就像大海里的潮汐,有退潮,也有来潮。我们革命战士要像在海洋里行船的水手那样:来潮不让风浪翻了船;退潮不让船搁浅。要前进!我们的任务更加重了。我们的党会像舵手一样,指引我们驶向胜利。”表现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要想取得革命成功,还必须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母瑞山根据地生活很艰苦,但是琼崖红军仍然苦中作乐,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在敌人搜剿的空隙,冯白驹同志依然坚定乐观,他哼琼戏,请王业熹同志吹笛子,其他同志敲石头,借以伴奏,鼓舞大家斗志。他还诙谐地对大家说‘敌人把我们关进了炼丹炉,我们都像孙大圣一样练就金睛火眼,钢身铁骨,待日冲破炼丹炉,我们的神通就更广大了。”在艰苦的岁月里,王业熹吹笛子的原型被艺术家创作成雕塑,而且还长期进入小学语文教材,如今被存放于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展览馆。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各种娱乐活动很少,为了丰富精神生活,琼崖红军还组织了琼剧团,利用空闲时间给群众唱琼剧,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给那段黑色的岁月添了光彩。
(二)在革命队伍的外部依靠力量上,必须依靠群众和坚持群众路线。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队伍对群众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根据史料记载,中共广东省委在总结琼崖过去教训的时候指出:“已经起来的群众始终多是在红军后面呐喊助威,战斗总是要红军为唯一的主力。敌人乡村的群众与敌军士兵,则完全在敌人的欺骗之下,丝毫不动摇地与我们为敌。城市工人如隔岸观火,完全无起来领导暴动的意志与准备。这使琼崖的暴动在敌人势力弱的时候,始终都只是部分的,而不能成为全岛的高涨。一到敌人势力加强,蔡廷锴、陈铭枢的兵到后,便立刻受到大的挫折了。”这是对群众作用的肯定和认可,表现出对群众的重视,特别在经历残酷的生存斗争之后,革命领导人认识到一个朴素的道理——“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没有群众,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更不会取得革命事业的成功。这是思想认识上的深化,这种认识比早期的认识要更深刻。比如革命领导人早期曾认为,垦山种粮是增加给养的最好办法,又是减轻人民负担的根本措施。事实证明,依靠群众才是进行革命斗争的最好办法。可以说,正是为了走向群众、依靠群众,革命队伍在剩下26个人的时候,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突围下山。这是经历生死考验之后,选择的一条正确道路。下山之后,母瑞山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保存下来,靠的就是群众支持,靠的就是能够始终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走的再远也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今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也要紧紧依靠群众,真正做到践行群众路线,把革命先烈开创的事业坚持下去,发扬光大。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在琼崖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始终把加强教育作为重要武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斗争虽然异常艰苦,但革命队伍有顽强的斗志能够坚持下来,也是因为琼崖党组织一直没有中断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琼崖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也十分重视日常党内教育工作,编印了党内书刊,中共琼崖特委编印了《红潮周报》《特委通讯》等内部刊物,出版了《琼崖红旗》《布尔塞维克生活》《工農兵小报》和《党团生活》,除了琼崖特委,各市县均有出刊物。这些党内书刊,对于进行党内教育,坚定党员理想信念、增强党员党性起到了重要作用。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越要注重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纪律教育。在敌人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时期,进行党性教育对党员坚定革命信念,保持革命气节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理想信念的弱化成为导致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而理想信念的弱化又与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弱化有关系。因此,发扬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精神,也要在新时期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
[注释]
①冯白驹研究史料[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1页.
②冯白驹和他的战友们[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③中共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档案馆编.琼崖土地革命战争史料选编[M].1987年8月(第一版):第110-111页.
④冯白驹研究史料[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1页.
⑤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⑥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⑦???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⑧冯白驹研究史料[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⑨冯白驹研究史料[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⑩中共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档案馆编.琼崖土地革命战争史料选编[M].1987年8月(第一版):第271頁.
?琼崖革命研究论文选[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145页.
?冯白驹研究史料[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87-88页.
中共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档案馆编.琼崖土地革命战争史料选编[M].1987年8月(第一版):第388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页.
冯白驹研究史料[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6页.
中共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档案馆编.琼崖土地革命战争史料选编[M].1987年8月(第一版):第109页.
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M].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琼崖革命研究论文选[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