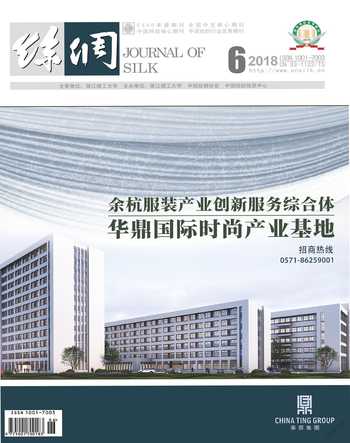论女红活态化与乡村特色小镇协同发展路径
宋眉 俞晓群
摘要: 乡村特色小镇的发展促进了女红资源的开掘和转化,女红亦在乡村特色小镇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中承载着重要的功能,由此为女红提供了生存空间与发展契机。文章基于女红的传承与发展规律、乡村特色小镇建设规律,探寻女红活态化与乡村特色小镇产业繁荣、文化塑造、社會发展之间的协同机制与路径,并针对现存的问题探讨相应的对策。文章以乡村特色小镇建设为背景,立足于女红的现实生存与多层面实践,探寻当代女红的活态化传承与创新路径,弥补了既有女红研究之不足,也能够为乡村特色小镇发展提供借鉴与参照。
关键词: 女红;活态化生存;乡村特色小镇;协同发展;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 TS941.742;F30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7003(2018)06-0052-07
引用页码: 061109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towns promotes the exca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eedle crafts resources, and the needle crafts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towns, thus providing the survival space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for needle crafts. Based on the law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eedle crafts and construction rules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tow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synergy mechanism and path between the viable survival of needle crafts and industrial prosperity, cultural shaping & social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towns. Moreover,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explores 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also on the realistic survival and multi-layered practice of needle crafts, the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viable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needle crafts, makes up for existing shortages of needle crafts studies, and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the for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towns.
Key words: needle crafts; viable survival; rural characteristic towns;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ath
当代女红日益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之中,通过承载多元功能促进社会建设,同时也实现自身的活态化传承和发展。在乡村特色小镇建设中,女红的活态化与小镇发展之间逐渐呈现出协同性规律,其内部机制和路径都有待挖掘和梳理。从目前学界成果来看,多关注女红的视觉要素与图案的呈现,涉及色彩、造型等审美元素,侧重于探讨女红物质形态的审美功能,主要有《中国丝绸图案》[1]、《中国历代丝绸纹样》[2]、《女红——中国女性闺房艺术》[3]、《中国最美云肩——情思回味之文化》[4]等;此外,《工艺美术论集》[5]、《中国传统工艺》[6]、《中国丝绸艺术史》[7]等成果基于传统工艺与社会文化、习俗观念、经济生活的关联,探及了女红的发展历史、品类谱系及其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但未针对女红做出专门的、系统化的研究。总体上看,既有研究对女红的现实生存与发展规律探讨不足,而对乡村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女红实践则更是缺乏关注。基于此,笔者从女红活态化与乡村特色小镇协同发展的需求及趋向、机制、路径及存在的问题、对策等,全面探讨二者的协同性问题,力图为二者的共生共赢提供借鉴与参照。
1 女红活态化与乡村特色小镇协同发展的需求及趋向
1.1 乡村女红传承与发展的现实际遇与基本规律
当代乡村女红的生存生态与现实际遇是较为复杂的。一方面,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及现代文明对乡村的不断渗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普遍出现在我国乡村的社会文化结构、价值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现代商品经济、工业生产、物质消费等对传统女红的生产模式、文化基因、审美范式都形成了巨大冲击,导致传统女红的生存空间被大幅挤压,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使女红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但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非遗文化保护的重视,乡村在区域城镇经济发展中的节点功能凸显,以及乡村社会组织结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上的整体变迁,也为女红的生存提供了新的空间,促使其通过承载新的价值功能、生成新的文化内涵,积极融入当代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之中,实现自身的活态化传承与发展。
“女红”与“女工”谐音,主要指刺绣、纺织、缝纫等手工技艺,以衣、帽、鞋、饰物等生活用品为物质载体。所谓“女红活态化”,即不局限于静态固化的保存和延续,而是更重视向前发展,注重在衍生、开发中传承女红,通过让女红融入当代社会经济文化之中,通过保护性传承与发展性创新相结合,賦予女红新的生命活力。女红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积淀,是女红生产与社会文化互动形成的智慧结晶,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产物,也是创造者与使用者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积极实践的成果。就女红传承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言,在历时性维度上,女红实践呈现出人、社会、自然相互融合的思维方式,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生命情调的交融深化、造化与心源的合一;在共时性维度上,女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则是时代赋予女红的使命,是主体对情感的需求、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渴望,以及主体存于世间所依赖的社会身份建构和社会文化认同。因此,女红工艺技术、符号体系与民俗文化中蕴含的意义世界,呈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地域、阶层与个体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承载了特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社会文化功能,也体现了特定的主体生存方式、价值理念与审美观念。女红的传承与发展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交叉融汇下不断生成与演进的过程;女红的“活态化”生存,正是在时代为之提供的“语义场”中不断书写自身,在承继核心基因、发扬文化优势的同时,不断生产出新的、多样化的话语形态与审美范式。所以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女红发展不仅有待于真正融入当代设计理念之中,实现美学创新,同时需要在文化层面上开拓其当下性与普世性的价值”[8]。“活态化”生存构成了女红的普遍性价值与意义世界,构成了女红传承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乡村特色小镇中的女红发展现状与二者的协同化趋向
对于乡村女红而言,“活态化”生存是其能够融入当代乡村社会文明肌体之中、继续保持活力的根源。例如顾绣自家道败落之时开办刺绣学习班,由家庭女红转向商品绣,尝试融艺术性于装饰性、欣赏性之中,苏州镇湖刺绣等当代刺绣更是借助乡镇的经济转型,依托于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生产方式,通过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来获得经济效益。如今,中国不同地域省份的乡村女红都在与服饰时尚行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积极融合,试图从中发掘生存空间,一些乡村女红还积极发挥其“符号”生产与话语空间功能,在构筑地方特色文化、承载华夏子孙“乡愁”情思中产生出巨大能量,也为传统村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助力。从总体上看,当代乡村女红的生存日益与社会生产生活之间形成密切关联,甚至逐渐与乡村社会经济文化事态之间构成了互荣共生的协同发展模式。
当代乡村产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赋予了女红新的价值,令女红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让女红的优势基因得以传承和发扬,而作为这一过程展开的具体空间——乡村,不仅作为地理空间和生活空间,也作为女红进行实践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支撑着女红的“活态化”生长。在当代乡村发展建设中,女红等传统文化不再仅作为产业资源被开掘,而是不断拓展其功能,全面地融入到社会生态之中,通过显性文化形态的建构及隐性历史文脉、社会规范、观念精神等的当代转化,参与到乡村经济发展、地方风貌形态塑造、社会空间建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女红的艺术之美、民俗之美、道德之美、智慧之美得以绽放,女红工艺、艺术与文化所具有的丰富潜质得以开掘,由此形成了女红发展与城镇建设之间的全面协同。
2 女红活态化与乡村特色小镇协同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2.1 女红资源转化与乡村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的协同
从浙江、江苏、四川、湖南等女红文化与蚕桑丝织文化资源聚集地来看,都致力于从多个渠道将女红资源融入乡村经济发展之中,使之成为完善产业链的“黏合剂”。例如在各类丝绸画、各种服饰甚至是家居设计、各类现代创意设计中,传统女红的精细手作、内容及形式等都能满足现代消费者对欣赏性、装饰性、创意性的需求,拓展了女红的商品价值与市场空间,为乡村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效益。例如浙江海宁这座江南“丝绸之府”,依据其自然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特色优势,聚集当地乡村女红文化资源,建构了“中国蚕桑丝织文化遗产生态园”,打造育苗、制种、养蚕、缫丝、织绸、刺绣、服饰设计等配套设施完善的茧丝绸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圈,而女红工艺及文化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要素,同时也在这一产业链与生态圈中发掘出自身的潜力。例如,生态园内陆续进驻了一些纺织和服装品牌企业,不仅以丝织物为生产原料,同时也注重发掘女红工艺与艺术的魅力,生产出大量具有创意的现代女红服饰精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女红产业链;蚕桑丝织国家文化公园、丝绸创意园蚕桑记忆展示区则对女红的生态智慧、文化精神进行了全面展示,为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感性体验,提升了生态园的文化品质。
再如湖州“丝绸小镇”,集丝绸产业、历史遗存、生态旅游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的“丝绸文创度假小镇”,绣坊、织造坊、染坊及各类女红民俗文化资源在旅游产业中的开发,向世人充分呈现了女红工艺与文化的丰富类型和地域特色,有利于女红的传承、保护和传播,营构了地方文化生态,同时形成了以女红文化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圈;湖南“湘绣小镇”融丝织技术非遗传博览园区、丝织刺绣生态园区与创意设计产业园区于一体,从非遗保护、研发设计、创意文化消费、休闲度假等多个方面对女红进行了功能拓展与功能组合,将地方特色女红文化全面渗透到产业生态之中,实现了地方文化生态与产业生态的共生共荣。
以众创发掘集体智慧,以地方文化艺术资源改善民生,成为当下诸多乡村特色小镇实现经济与社会共赢的一种重要途径。对于女红的活态化生存而言,以源生地群落民众为创造主体来复兴女红,不仅重构了女红生产的民间乡野生态,为地方女红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同时从内部激发了女红的创新活力;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等产业经营发展模式,则为这种创造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便利的渠道。例如,2015年,长沙县开慧镇女红文化创客营开班传授扎染、蜡染等传统工艺,集培训、生产展示、商贸于一体,致力于打造最具特色的“湘女创客基地”与产业大平台,开创低碳环保、生态文明的创业创新发展新模式;湖南省女红协会于2016年成立,它团结广大手工编织民间艺人和从业妇女,聚集湖湘特色女红工艺技术,挖掘民间制作人才,定期提供技能培训,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和现代商务平台,形成了湖湘女红文化众创空间,推动了湖南手工编织产业的发展,还吸纳妇女就业,拓宽妇女就业创业渠道,帮扶贫困妇女脱贫致富,这些举措都为乡村女红与产业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从整体上看,这种立足于地方女红资源发掘、以女红自身的发展创新为内核的产业生产机制,结合“互联网+”时代的各种有利生产条件,为女红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也促使地方传统女红能够在创新中延续和壮大自身的生命力。而对于以女红为生计的小镇居民而言,这种生产模式为他们融入现代生产生活、接受并内化现代文化价值观念创造了适宜的环境,也为他们实现自身社会价值、文化想象与身份认同提供了途径,因此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有利于小镇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建构,充分实现了女红活态化与小镇发展之间的协同。
2.2 女红文化发展与乡村特色小镇文化塑造的协同
如果说女红资源转化与乡村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的协同充分体现了对女红工艺及艺术资源的转化,实现了物态上的创造,那么女红文化及民俗则在乡村特色小镇的“文化特色”塑造中发挥出巨大价值,为女红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推动了女红文化的繁衍。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城镇文化中的“识别危机”“记忆危机”“认同危机”等问题作出了深刻反思,充分显示了特色文化对于城镇发展的重要性。相比较而言,特色小镇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和复杂,它不仅以特色文化为形貌特征,以特色文化塑造小镇品牌、打造小镇人文魅力,为主体提供文化想象;它更以特色文化塑造小镇空间,为主体提供社会认同的渠道,为生产提供文化动力与结构。基于上述目的,运用诸多地理/人文、物质/精神要素及资源,在多元生活场域中建构社会空间,成为了特色小镇文化塑造的主要内容。这一文化塑造过程尤为强调内在的文化与主体及环境因素之间的和谐与互动,注重文化的社会功能与话语场域的建构和拓展,因此对女红等地方文化与小镇社会文化之间的紧密融合与协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诚如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对文化的定义:“文化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9]也正如国内学者所言:“文化不仅是历史沿袭的符号传递,还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建构行动。”[10]无论乡村特色文化的形成与创新,还是地方女红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是以文化生产为基本途径的。如前面所述,女红是主体在特定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环境中进行创造实践的产物,凝聚着主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俗、审美取向等因素,同时也作为一种发生在日常生活界面中的生动事态,呈现和传达着主体的情感思绪和生命体验,因此女红并非一种凝固、静止的形态,而是在主体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演进的文化形态;女红的传承不是、也不可能复现其原生文化形态,而是在文化书写中不断建构自身,在“以文化人”的过程中不断建构着人类主体和社会,这便形成了其与社会文化协同并行的内部机制。
通过女红文化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意象”建构和“情境”想象,女红与乡村特色小镇社会文化塑造之间形成了互融共生的关联。例如,湖南“湘绣小镇”注重以景观塑造女红文化意蕴,在点点滴滴之中流露出女红的精致与秀美;海宁在旅游文化中尽显刺绣、挑花、织带、织被、剪纸等女红文化习俗的魅力,并以一种符合年轻一代想象的“日常情境”,通过互动性的文化活动(如新年节、朱鸟节、女儿节、吹凉节等)彰显了越地女红原生态文化的特色魅力,成功地将当代大众对于越地女红的历史记忆、集体记忆与地域文化想象、跨文化认知及形而下的体验融为一体,实现了对地方原生态文化的重塑。事实上,尽管当代资本与媒介景观、快餐消费的情境化体验、全球化无地域的“类空间想象”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女红文化内蕴,但是也赋予了女红文化建构当代社会肌体和文化想象的契机。从总体上看,当代乡村特色小镇文化塑造为女红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女红在当代乡村特色小镇塑造记忆、彰显文脉、打造特色、构筑品牌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活态化”的传承和发展。
2.3 女红精神发掘与乡村特色小镇社会发展的协同
诚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无论是对城市文化的重视还是损毁,文化传承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内化到城市发展本身来考虑,而是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美其名曰‘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11];而特色小镇文化资源开掘和转化的重点正在于并非将文化资源仅视为塑造小镇意象的形态要素,而是把它们当成活态的生产力要素与精神要素,着眼于文化资源在小镇社会生态建构和主体建构中的功能,可谓对中国城镇文化发展症结的深刻反思。无论作为造物精神还是生存哲学,女红文化的根底皆在于其蕴含的道德内涵与生态智慧,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质与品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为现代人文精神建构提供了资源,成为了当代主体体验生命存在、实现审美生存、完善社会人格、营构精神世界的重要根基。当代乡村特色小镇迫切需要借助一切文化资源来建构公共精神,形成精神凝聚力,因此,作为一种精神生產形态的女红文化便具有了自身独特的功能与使命。
例如,作为修心养性工具的佛堂女红和精英女红,其精神内蕴中包含着禅宗思想和佛教元素,呈现出闲适生活理念和平衡身心的东方美学追求,在休闲旅游和审美语境下成为了主体陶冶性情、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审美生存方式”,有助于主体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异化下恢复生命体验、抗拒庸俗商品文化,也与乡村空间这一现代文明中的“精神净土”相契合,因此传统女红精神在当下乡村小镇各类女红体验馆与生态旅游消费中呈现出极大的活力与潜力。与此同时,女红精神中蕴含着积极的道德伦理观念、生态观念、生存智慧等内涵,也为乡村特色小镇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女红借助这些内涵与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间发生着广泛的关联,其道德示范效应辐射至各个社会角落。例如岁时节日与人生礼仪(如婚礼、庆生、丧礼、贺寿等)中的女红文化,积淀着深厚的道德伦理观念,作为德行与地方文化代码构成的综合意识形态,参与建构小镇的“公共精神”。这种建构不仅实现了地方女红精神的传承,也促使其转化为现代社会文明价值理念中的构成要素,满足了居民的内在文化需求。
从社会认同的机制来看,“人们都希望归属于拥有独特且正面认同的群体。一旦获得这种心理认知,人们会更加肯定自我群体,增强群体凝聚力和自豪感,进而完成社会认同这一心理认知过程”[12]。当下特色小镇面临着传统社会链接纽带的断裂,社会整合的传统基础弱化等问题,如何打造成员共同的精神纽带、共同的文化体验、共同的家园感和归属感,已成为特色小镇建设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语境下,女红文化精神价值凸显,它通过积极与小镇公共文化与精神文明融合,开掘和提练女红精神中具有时代性和普适性的内涵,“再造并形塑出一个既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又包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精神”[13],从而渗入小镇公共文化之中,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化氛围。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借助女红精神的熏染,他们不仅能够实现当下的审美生存,同时也能将社会文化精神、价值观念更好地内化为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精神境界,最终实现对社会文化的认同,积极投入到社会建设之中。
3 女红活态化与乡村特色小镇协同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3.1 女红资源的产业化开发需要强化顶层设计
陈立旭[14]指出:“特色小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镇,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区域,而是一个以某种新兴产业或历史经典产业为基础,汇聚相关企业、机构和人员,具有某种要素集聚功能的区域,是一个功能再聚焦、人才再集聚的‘重新联合或聚合的新聚落、‘产城融合共生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实践形式。”在这种背景下,产业发展不仅仅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是以整体策划、精准布局为指导,以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发掘为依托,以成员的共同利益为根本,并致力于建构良好的产业生态圈。因此,特色小镇模式下的女红资源转化,不能仅仅依赖于对原有功能的拓展,还需要结合小镇的产业聚集方式、地方文化生态与区域特色,对女红资源进行功能、形式、内容等要素的深入分化和重组。
从目前不少“女红小镇”存在的问题来看,大多并未充分依托自身优势资源,在“非遗”+“文创”这一基本模式下进一步探索自己的特色、地方产业化道路,而是出现了盲目跟风的趋向,只顾“做大”产业,不顾小镇自身的基础与产业结构特点,缺乏对产业链、产业群的合理建构与组合;一些小镇一味强调经济效益,忽视对女红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文脉的延续,缺乏建设文化生态的自觉意识,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女红文化精神的价值。基于这些问题,一方面,当下大多数“女红小镇”还需要在总体规划、文化定位上作出更加科学的设计和精准的布局,女红资源的产业化开发需要结合小镇节点功能与产业结构,依据产业与文化生态的整体需求来自觉对女红的功能进行定位和设计。另一方面,不能仅仅满足于物化形态的创造,还应该加强对女红文化产品的开发力度,力图丰富女红产品的文化内涵,比如借助其他文化艺术形态来丰富女红产品的内涵;在服饰与香囊、屏扇等传统陈设物和工艺品创造之外,还可以在其他类型的工艺品、生活用品生产及影视动漫、文教等领域中开发女红资源,不断促使地方女红资源在产业经济中实现合理、高效地转化,才能实现女红活态化传承与小镇经济发展共赢。
3.2 女红文化的塑造需要深入挖掘人文内涵
在当代全球城镇化发展与竞争中,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文化生产机制的科学性、高效性,成为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因素,新的文化结构不断被塑造出来以增强“城镇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空间与能力,由此也带来社会组织现代观念、生产、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化[15]。就此而言,“宜居”“品质”“智慧”等当代城镇文化理念与生活理念不仅是与当代社会文明及主体需求的对接,更意在以人为本,建构新的社会文化结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促进文化生产生态的整体建构。因此,从目的上看,女红文化塑造需要积极投入当代文化生态系统建构之中,增强“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空间与能力,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符合当代小镇文明肌体需求的精神价值和符号意象,契合特色小镇“多元汇聚、开拓创新、国际化”等整体发展理念;从途径上看,则需要以精神观念为内核,以本土现实和主体生活经验为根基,依托小镇自身的文化根基,在继承传统女红文化优秀基因的同时,也与其他本地文化、外来文化及当代文化之间进行合理互融互补。
目前多数特色小镇注重对女红文化生态的立体呈现与“情境化”体验,采用静态展陈与动态体验融合等模式,促进了女红文化的传播,但是总体上缺乏对女红文化内蕴与地方特色的凝练及深层意象的呈现,女红文化内核与精神特质仍有待深入发掘,在整体策划、对外宣传等方面也缺乏针对小镇特定文化生态进行层次化与体系化的设计。这一症结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反映了目前特色小镇存在的普遍问题,即缺乏对当地人文的聚合凝练,缺乏对小镇文化空间的精准治理[16]。就此而言,湖南省永州市的“女书小镇”提供了许多有效经验。该小镇以独特的女书文化为引领,打造女书文化产业园、女书文化体验区,注重特殊女红物品、建筑景观与女书文化精神之间的意象关联,注重开掘和塑造“绣字”等集合做女红、唱读、传授女书于一体的特色民俗形态,并使女书文化与当地“女杰之乡”“红色文旅”等文化品牌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从而实现了女红文化与地方特色优势文化资源的整合,最终在女红文化传承、地方文化塑造与社会道德观念培育等方面实现了共赢。
此外,面對日渐勃兴的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对女红文化地域差异的消解,如何趋利去弊,塑造地方女红文化的特色,促使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推动地方女红文化复苏、增强地方文化认同,也有待研究者们深入探究其规律。有学者[17]指出,旅游等场域中的“文化认同”具有多元嬗变性,是由其“牵涉的多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之间博弈与权衡的过程中,最终以社会共识和社会协商为基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认同。伴随旅游的发展,文化认同是在原生性/传统性与商品化/现代化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而在人文景观、公共艺术、文化产品及各类节庆仪式活动、媒体报道中,女红文化蕴含的精神观念和智慧也都在不断与现代文化价值观念发生对撞和交融,地方女红精神也在不断与外来异质文化观念进行对话。
就目前来看,面对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冲击与考验,女红文化尚未找到普遍有效的经验与模式来应对,其重构仍处于碎片化的阶段,其架构中心时常偏离原生文化的基本内蕴,导致女红面临丧失自身底蕴、被边缘化的困境。因此,女红文化的活态化传承仍任重而道远,需要在乡村特色小镇文化生态布局和总体设计下,合理把握传统与现代、原生与衍生、传承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遵循主体的审美心理与文化需求,积极探索各类空间形态的意象表征机制与审美特征,才能更好地发挥女红文化意象与精神传播对于增强社会文化理念、建构主体生存观与审美观的效能。
4 结 论
随着女红在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生产、社会文明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女红的活态传承与发展创新都将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展开,其与当代社会肌体之间的关联也将更为复杂。目前乡村特色小镇尚处于发展阶段,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规律皆有待探索,因而女红活态化与乡村特色小镇建设的协同机制与路径仍需深入研究,而这些研究不仅能为女红等非遗文化的活态化传承提供借鉴,也能够为当代乡村的发展路径提供参照。
参考文献:
[1]沈从文, 王家树. 中国丝绸图案[M]. 北京: 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7.
SHEN Congwen, WANG Jiashu. Chinese Silk Patterns [M]. Beijing: China Classical Art Press, 1957.
[2]缪良云. 中国历代丝绸纹样[M]. 北京: 纺织工业出版社, 1988.
MIAO Liangyun. Chinese Silk Patterns of All Previous Dynasties [M]. Beijing: China Textile & Apparel Press, 1988.
[3]潘健华. 女红:中国女性闺房艺术[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
PAN Jianhua. Needle Crafts: a Boudior Arts of Chinese Women [M].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9.
[4]梁慧娥. 中国最美云肩:情思回味之文化[M].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
LIANG Huie. Chinas Most Beautiful Yunjian: the Culture of Emotional Aftertaste [M]. Zhengzhou: He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3.
[5]张道一. 工艺美术论集[M].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6.
ZHANG Daoyi. Proceedings of Art and Craft [M]. Xian: Shanxi Pepo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86.
[6]杭间, 郭秋惠. 中国传统工艺[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HAN Jian, GUO Qiuhui. Chinese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M]. Beijing: Wuzhou Communication Press, 2006.
[7]赵丰. 中国丝绸艺术史[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ZHAO Feng. A History of Chinese Silk Art [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05.
[8]俞曉群. 明清江南女红的本体特征与当代价值[J]. 新美术, 2015(4): 62.
YU Xiaoqun. The on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jiangnan needle craf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 New Arts, 2015(4): 62.
[9]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62-64.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M]. Translated by HAN Li. Nanjin: Yilin Press, 1999: 62-64.
[10]马翀炜. 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J]. 民族研究, 2006(5): 61-69.
MA Chongwei. Building and interpreting cultural symbols: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tourist exploitation in an ethnic village of the Hani people [J].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06(5): 61-69.
[11]曾军. 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J]. 学术界, 2007, 125(4): 22.
ZENG Jun.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and the inheritance of urban culture [J]. Academics in China, 2007, 125(4): 22.
[12]王歆. 认同理论的起源、发展与评述[J]. 新疆社科论坛, 2009(2): 78-83.
WANG Xin.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omment of identity theory [J].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in Xinjiang, 2009(2):78-83.
[13]郑迦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模式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4): 245.
ZHENG Jiawen.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model of the protection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J].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16(4): 245.
[14]陈立旭. 论特色小镇建设的文化支撑[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6(5): 15.
CHEN Lixu. On the cultural suppo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J]. Journal of Zhejiang Party School of CPC, 2016(5): 15.
[15]宋眉. 新型城镇化和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传统文化资源[J].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2017, 29(4): 267.
SONG Mei. On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style urba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29(4): 267.
[16]闵学勤. 精准治理视角下的特色小镇及其创建路径[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7(5): 58.
MIN Xueqin.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their building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curate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ction), 2016, 27(5): 58.
[17]杨骏, 马耀峰. 全球化场域的旅游与民族文化认同[J]. 甘肃社会科学, 2017(1): 225.
YANG Jun, MA Yaofeng. Tourism and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field of globalization [J]. Gansu Social Sciences, 2017(1): 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