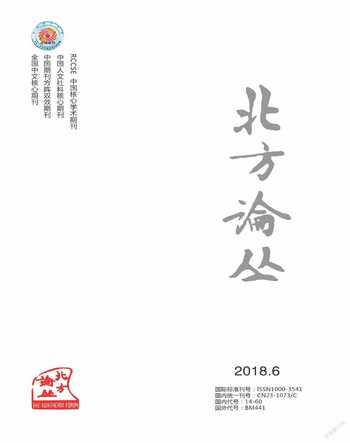考古学视角下隋唐时期犹太人入华再讨论
莫玉梅
[摘要]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了扰太人在宋朝以前已经入华的观.点,但对扰太人入华的具体时间尚未有定论。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及邻近国家和地区陆续出土了与入华犹太人相关的文物,包括新疆和田地区出土的两封犹太波斯文信件、洛阳出土的犹太侨民墓志、中巴友谊公路两侧的希伯来文题记等。通过考查断代,这些是隋唐时期、主要是唐朝时期留下的文物,充分证明犹太人早在隋唐时期已经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并深入内陆腹地。
[关键词]犹太人;考古学;隋唐时期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6-0105-06
犹太人是著名的世界商业民族,自圣经时代就和周边国家与地区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之囚”事件发生后,犹太人开始向东流散,在波斯帝国时期进入中亚地区。丝绸之路贸易兴起后,犹太人与其他各国商人一道成为这条国际商路上的重要参与者。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深深吸引着犹太人,成为他们贸易的对象。随着入华犹太人人数和次数的增加,中国也算得上是犹太人的流散地之一。因此,入华犹太人研究一直是中国犹太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关于犹太人入华的研究
徐新认为,中国的犹太研究在1949-1978年没有得到真正开展,1978年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犹太研究的重新开展,但有意义、具有学术性的中国犹太研究应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1](pp.54-55)。在华犹太人是中国犹太研究最早关注且著述最为丰富的课题,许多学者对犹太人何时入华提出不同看法,形成周代以前说、周代说、汉代说、唐代说和宋代说等学说。正如龚方震所指出的,其中的一些说法只是猜测或根据某种传说,缺乏物证,也有的是对某些记载或文物的错误解释[2](p.246)。例如,周代以前说是沙俄时代一个东正教主教看到开封的明弘治二年(1489年)碑文而提出的。碑文中写道:“那其间立教本至今传,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这位主教望文生义,再加以引申,得出“犹太人在摩西以前就到中国了”的结论。这种说法在犹太人自己看来都太“大胆”了[3](p.27)。周代说主要源自开封犹太人在康熙二年(1663年)留下的《重建清真寺记》:“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陈垣指出,这是写碑记的人读了弘治碑和正德碑上的话,断章取义,以讹传讹[3](p.27)。正德碑上还记载:“厥后原教自汉时人居中国”,这不仅说明陈垣的观点是正确的,还说明立碑人认为犹太人是在汉朝时期进入中国的。此即汉代说唯一的文字根据。尽管清朝来华的几位传教士和一些西方作家相信汉代说,但他们留下的记载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语焉不详,没有提出更有力的证据[3](pp.31-34)。因此,汉代说尚无法证实。
宋代说可谓几种犹太人入华学说中证据最为充足的。开封犹太社团存续800余年,留下很多历史文档,包括经书牒谱、著作、教碑、会堂、各种遗址和文物,充分证实了宋代犹太人入华的说法。但是,随着中国犹太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唐代说已逐渐为许多国内学者所接受,主要证据来自1901年英国匈牙利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地区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一封犹太一波斯文信件,以及1908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一篇希伯来语祈祷文。也有学者提到其他证据,如著有《中国的犹太人》一书的加拿大学者怀履光(W.C.White)收集的四个唐三彩俑有着明显的闪米特族特征[4](p.51);成书于7世纪的中文景教教典《世尊布施论第三》中,数次提到石忽人(唐代对犹太人的称呼)[2](p.247)。
然而,就犹太人在唐代的具体入华时间和路线,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潘光等人认为,犹太人约8世纪前后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此后也有从海路来到中国沿海再进入内地[5](p.349)。张倩红等人认为,犹太人最早来到中国大约是在8-10世纪之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业群体之一[6](p.49);犹太人通过四条国际商业路线在东西方之间从事转运贸易,其中两条为陆路、两条为海路[7]。龚方震根据上面提到的两件出土文物推断,至少在6-8世纪已有犹太人入华[2](p.247)。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中出现更多的与入华犹太人相关的文物和碑记,如新疆和田地区再次出土一封犹太一波斯文信件、中巴友谊公路巴基斯坦一侧发现希伯来文题记等。虽说犹太人阿罗憾墓志跋早在20世纪初已在洛阳出土,但国内学者对阿罗憾的犹太人身份尚存质疑或不知道此墓志跋的存在,所以,相关论著中几乎没有提及。这些发现将进一步推动对入华犹太人的研究,对犹太人入华时间、路线、身份等有了更多的了解。
二、和田地区出土的两封犹太一波斯文信件
和田古称于阗,是古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交通要点之一,初见于《汉书·西域传》。作为南道交通局域网络的中心,东西方的使者、客商、僧侣、士兵等往来于阗,络绎不绝,留下了大量的语种丰富的文字史料。从上个世纪初至今,和田地区出土了两封犹太一波斯文信件,为研究犹太人入华提供了切实的证据。
第一封为上文提到的丹丹乌里克犹太一波斯文信件。丹丹乌里克在维吾尔语中意为“象牙房”,位于和田市以北%千米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曾是唐代于阗六镇之一杰谢镇所在地。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途中,意外发现了一处唐代佛寺遗址,即丹丹乌里克遗址,使该遗址首次出现在世人眼前。1900-1905年,斯坦因对中亚进行第一次考察。按照赫定绘制的地图,他找到了丹丹乌里克并对此展开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佛教艺术品、古代钱币、唐代文书和婆罗谜文写本[s](p.203)。文物中有一封犹太一波斯文信件,是于阗出土的第一封犹太一波斯文信件,现存于大英博物馆。信件残缺,存留部分有37行文字,长40.64厘米,宽10.16-20.32厘米不等,因信件边缘缺损所致。
剑桥大学教授马戈柳思(D.S.Margoliouth)是第一位对这封信件断代的学者。他根据信中提到一位泰伯里斯坦(Tabaristan)统治者伊斯巾白巴德(Isbahbudh)而断其书写年代为公元718年[9](pp.735-760)。后来,这封犹太一波斯文信件为许多学者所引证,多沿用这一断代。1968年,瑞典伊朗学家乌塔斯(Bo Utas)对此断代提出异议。他认为,该信件的断代应为8世纪后半期,主要证据如下:其一,丹丹乌里克即为唐代的杰谢镇,8世纪后半期,那里有一座佛寺和一小支唐朝驻军;其二,考古证明杰谢镇大约在8世纪末荒弃,原因可能是唐朝在此地的统治最终崩溃、吐蕃的人侵,以及塔里木盆地大面积干旱造成和田绿洲可耕地逐渐缩减;其三,斯坦因从丹丹乌里克带走的其他汉文文书断代大致为781年、782年、787年、789年和792年;其四,从古文字学角度来看,这封信件上的文字与阿富汗坦格·阿兆(Tang-i Azao)出土的752-753年的石刻相似[10](pp.124-125)。张湛博士赞同乌塔斯的判断,同时认为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封信件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其英文译文较为可靠,而且注释详细,成为研究该信件最重要的文献[11](pp.74-79)。2016年,李大伟博士重新对这封信件进行了考据与释读,认为写信时间最晚不会超过717年或在717年之后不久[12](p.106)。这一断代倒是与马戈柳思教授的相去不远,都在8世纪前期。此外,李大伟断代的立足点也在信件中提到的“伊斯帕巴德”一词上。据考证,伊斯帕巴德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为军事长官的徽号和衔阶,库思老一世(531-579年在位)时期起为地区执政官之号,帝国四方各有一位,北方的伊斯帕巴德统辖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赖伊、阿穆勒、泰伯里斯坦等地;阿拉伯帝国建立后,伊斯帕巴德则为泰伯里斯坦列王的徽号[13](p.126)。6世纪前半期,波斯萨珊王卡瓦德一世(488一31年)吞并泰伯里斯坦,将其纳人帝国版图。651年,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由萨珊王室余部统治的泰伯里斯坦保持独立到765年,历经戈巴拉(626-690年)、达布瓦(650-711年)、法爾罕(711-751年)、米尔、萨鲁雅(739-740年)、库尔希德(740-761年)等国王的统治。该信第23行提到:“叶齐德赠送给伊斯帕巴德一条皮鞭”,而叶齐德在哈里发苏莱曼(715-717年)统治时期曾出兵征讨泰伯里斯坦,但信中未提及叶齐德征讨之举,显然写信之时征讨未曾发生[12](p.106),或刚发生,但未传到写信人处。
第二封犹太一波斯文信件的出现时间晚得多。2004年秋,一批新疆和田地区出土的写本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包括一封犹太一波斯文信件。这些写本是不是同一地点和同一时间出土,或者具体在何时何地由何人挖掘出土,尚不清楚。不过,这显然是一封新的犹太-波斯文信件,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的专家在2005年秋完成对此信件的修复。经检视,此信件保存较为完好,只有最后一部分略有破损;上面的文字有38行,长40厘米,宽28厘米,与斯坦因获得的那封极为相似[11](p.71)。张湛、时光两位博士对这两封信进行了比对,从用纸、书写、正字法、语言、内容五个方面做了细致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两封信出自同一时代同一地区,且有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11](p.79)。也就是说,这封新的犹太一波斯文信件也写于8世纪后半期。该信中第31-33行是这一断代的重要证据,因为这里提到喀什噶尔的情况:吐蕃人被杀光,军副使带着500步骑去增援,有官员派出了信使。喀什噶尔即安西四镇之一的疏勒。张湛等人使用了《大正藏》第五十一卷中的证据,上面提到唐代高僧悟空于788-789年间经由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回国时,疏勒和于阗尚有唐军驻守。他们以此推测,疏勒被吐蕃占据及吐蕃人被杀应该晚于788-789年。该信提及这些事件,证明其书写时间要晚于788-789年。
其实,还有一个事实可以有助于对这两封信件进行断代。这两封信件显然没能送出去,而是滞留在和田地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龚方震推测,可能是唐王朝与吐蕃在西域争夺安西四镇,战争爆发,交通受阻所致[2](p.247)。从史实来看,与吐蕃争夺西域的主要势力不仅仅是唐王朝,还有回鹘。这一争夺战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前期吐蕃主要与唐朝争夺西域,后期则与回鹘展开争夺。吐蕃与唐朝的西域之争导致西域在安史之乱前经历了三失三复,吐蕃每次占据西域的时间都不算长(第一次:670-673年;第二次:677-679年;第三次:687-692年)。692年,武則天派王孝杰和阿史那领兵“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此后,吐蕃一直未能染指西域,而安史之乱是一个转折点。如果说第一封信件的断代在717年或718年是正确的,那么其滞留原因有可能不是战乱。《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上元元年,河西军多为吐蕃所陷。有旧将李元忠守北庭,郭听守安西,二镇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其后,吐蕃急攻沙陀、回鹘部落,北庭、安西无援,贞元三年,竟陷吐蕃。”显然,吐蕃与回鹘的西域之争主要发生在安史之乱后,因战乱导致信件滞留出现在8世纪后半期是说得通的。
实际上,无论这两封信件的断代是在8世纪初,还是在8世纪后半期,都清楚地表明,犹太人在唐朝中期已经生活在和田地区,从事商业活动,与原居住地的同族人关系密切。从两封信件的内容来看,写信人不仅仅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也是同族人在该地区的商业代理。这与流散时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商业经营方式相似。
三、洛阳出土的阿罗憾墓志
清朝末年,一方唐景云元年(710年)的墓志出土于洛阳东南郊楼子村附近;后流人日本,现存于东京上野日本国立博物馆。1909年,端方在《陶斋臧石记》中首次将墓志录文公布;1917年,罗振玉辑《芒洛冢墓遗文》收入此墓志录文。羽田亨、桑原骘藏、张星烺、向达、朱杰勤、林梅村等先后撰文论及此墓志。墓志录文如下:
1 大唐故波斯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
2 金城开郡公、波斯君丘之铭。
3 君讳阿罗憾,族望,波斯国人也。显庆年中,
4 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有称,名闻[西域],出使
5 召来至此,即授将军北门[右]领使,侍卫驱驰。
6 又差充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菻西界
7 立碑,峨峨尚在。宣传圣教,实称蕃心。
8 诸国肃清,于今无事。岂不由将军善导者,为
9 功之大矣。又为则天大圣皇后召诸
10 蕃王,建造天枢,及诸军立功,非其一也。此则
11 永题麟阁,其于识终。方画云台,没而须录。以
12 景云元年四月一日,暴憎过隙。春秋九十有
13 五。终于东都之私第也。风悲垄首,日惨云端,
14 声哀乌集,泪[落]松干。恨泉扁之寂寂,嗟去路
15 之长叹。呜呼哀哉!以其年口月口日,有之俱
16 罗等,号天罔极,叩地无从。惊雷绕坟,衔泪[刊]石,
17 四序增慕,无辍于春秋;二《礼》剋修,不忘子生死。
18 卜君宅屯,葬于建春门外,遣丘安之,礼也。[14](pp.95-6)
从以上录文来看,阿罗憾来自波斯无疑,且曾为波斯大酋长。人唐后,因出使西域、担任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等功绩,他官至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据此墓志铭,诸多史家开始考证阿罗憾的身份,提出阿罗憾为波斯入华犹太人的观点。
实际上,阿罗憾为犹太人的主要依据有两个:其一,阿罗憾的名字。阿罗憾为Abraham的音译,其子俱罗为Korah的音译。这两个名字都来自《圣经·旧约》,是犹太人的常用名。有《新唐书·孝友传》记载为证:“程俱罗者,灵州灵武人。居亲丧,穿扩作冢,皆身执其劳,乡人助者,即哭而却之。庐坟次,哭泣无节……俱罗三年不止。”灵武位于现在的宁夏,唐时为中西交通枢纽之一,许多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胡商聚集于此。程俱罗很有可能是犹太人或与来往通商的犹太人过从甚密者,或其先祖为犹太人[15](p.24)。林梅村认为,俱罗不一定是Ko-rah的音译,也有可能是Kara的音译;Kara的本义为“读者(即精读《圣经》者)”,有可能是指犹太教牧师(即拉比),那么程俱罗完全可能是一位入华的犹太牧师[14](p.97)。唐朝的景教徒中也有人名为阿罗憾,排除所说阿罗憾非景教徒的根据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该碑出土于西安附近,记录了贞观十二年到建中二年(638-781年)近150年中国景教史。如果阿罗憾确为景教徒,那么碑文撰写者肯定不会漏掉这样一位地位显赫的大人物。实际上,碑文对阿罗憾只字未提,恰恰证明他信仰的不是景教而是犹太教,即他是一个犹太人[14](p.98)
其二,阿罗憾来自波斯。墓志录文明确指出,阿罗憾为“故波斯大酋长”。“故波斯”指的是波斯萨珊王朝,该王朝于224年立国,651年为阿拉伯帝国所灭。《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伊嗣俟不君,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半道,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免。遣使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伊嗣俟(634-651年在位)即为萨珊王朝最后一任君主,在641年涅哈温之战中战败,逃往吐火罗,但在651年死于中亚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里)。伊嗣俟之子卑路斯避难吐火罗,派出使臣向唐朝求援。林梅村认为,这位使臣就是阿罗憾,大约在654年到达长安[14](p.99)。唐高宗以路远为由,拒绝出兵援助。阿罗憾没有完成使命,不得已留滞长安,以期徐徐图之。后来,卑路斯见复国无望,在唐咸亨年间(670-673年)来到长安,官拜右武卫将军。
能够随波斯王子卑路斯逃亡至吐火罗,阿罗憾至少是朝中大臣;能够作为使臣被派遣至唐朝,说明阿罗憾深得卑路斯的信任,而且颇有才干。萨珊王朝以袄教为国教,波斯帝国和安息帝国时期几乎没有出现的宗教迫害行为时有发生,如阿尔达希尔一世(224-241年在位)、伊嗣俟二世(438-457年在位)、卑路斯一世(459-484年在位)统治时期。袄教马吉迫害所有与自己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信仰其他宗教的人。虽然非袄教信徒担任公职成为不可能的事,但犹太人的情况有特殊之处。自波斯帝国以来,犹太人与历朝统治者的关系密切,许多犹太人在朝为官,有的深受国王宠信,如《尼希米记》中的波斯酒政尼希米,有的甚至官至宰相,如《以斯帖记》中的末底改。安息帝国时期,安息骑兵军官和行政人员名单中出现取波斯名字的犹太人[16](p.19)。有些国王娶犹太女子为王后,使犹太人与王室的关系更加密切,也提升了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据《以斯帖记》(2:16-17)记载,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废掉王后瓦实提后,立犹太女子以斯帖为后。萨珊王朝时期,伊嗣俟一世(399420年在位)娶犹太流放者领袖女儿肖珊(Shoshan-dokht)为妻[16](p.19),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犹太人权利受到限制的不利条件。此外,阿罗憾有“大酋长”的头衔,应该是某个族群的头儿,而自公元前6世纪流散至波斯的犹太人正好创立了“流散地领袖”的职位,由大卫王家族的后裔担任。萨珊王朝时期,流散地领袖在宫廷中有了一个永久性的职位[17](p.38)。所以,随卑路斯出逃的阿罗憾是犹太人的可能性高于是基督徒(即景教徒)的可能性。
四、巴基斯坦的希伯来文题记
希伯来文题记的发现与中巴友谊公路的修建息息相关。这条公路在1966-1978年修建,跨越喀喇昆仑山脉,北傍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喜马拉雅山脉,沿印度河支流洪札河、吉尔吉特河而下,三跨印度河,被誉为“现代丝绸之路”。实际上,这条公路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南道支线之一,但不完全重合,因为中巴友谊公路的重要地标,即红其拉甫山口和盖孜河谷,“峡谷狭窄险峻、水流汹涌,驮货的驴、马、驼等行走极其困难、危险”[18]。
1979年,中巴友谊公路开通后,德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考古学者在巴基斯坦一侧进行了细致的考古调查。他们在印度河上游沿古丝绸之路前行,从喀喇昆仑山口到奇拉斯(Chilas)都发现了大量的题记。这些题记涉及不同文字,有佉卢文、婆罗米文、粟特文、汉文、藏文、大夏文、帕提亞文、中古波斯文、叙利亚文和希伯来文[19](p.9)。题记内容很简短,大多是过往旅人的题名,如“某某的儿子某某曾到过此处”;也有些记录了在位的王,但都是小王国的国王,几无人知晓他们的名字[2介](p.37)。由于题记中没有明确的年代记载,所以,学者们根据各种文字的字母形状断代,大致推断出它们是1-8世纪之间留下的,也有人认为,奇拉斯题记的书写年代在4-6世纪[21](pp.131-137),比前一种推断大大缩短了时间范畴。希伯来文题记数量极少,其中有一条是奇拉斯所有题记中最晚刻录的,只写了两个人的名字[20](p.39)。根据前面的题记断代,这条希伯来文题记应是6世纪留下的,最晚不超过8世纪,表明这个时期有犹太商人从这条路走过。
从喀喇昆仑山口到奇拉斯一带今属于克什米尔地区,汉魏时称之为罽宾,隋唐时称之为迦湿弥罗。《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国……东至乌秅国二千二百五十里,西南与乌戈山离接”;称皮山国“西南至乌秅国千三百四十里……西南当罽宾,乌戈山离”。《汉书·西域传》又载:“自武帝始通罽宾”。《后汉书·西域传》亦云:“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戈山离。”综合上述史料,中原王朝与罽宾的往来始于汉武帝时期,将丝路南道从于阗经皮山、乌秅延至罽宾、乌戈山离,史称“罽宾丝道”。《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于阗(瞿萨旦那国)与罽宾(迦湿弥罗)的密切往来:毗卢折那阿罗汉自迦湿弥罗将佛法传至于阗,或于阗人“逾雪山”攻打迦湿弥罗。两国之间甚至存在血缘关系,因迦湿弥罗的属国咀叉始罗的一些辅臣被王室内斗牵连,或黜或放,“诸豪世禄移居雪山东北沙债之中”,成为于阗王室的宰辅大臣。《洛阳伽蓝记》记载,第一个将佛法传到于阗的毗卢折那正是跟着商队而来。公元前1世纪,咀叉始罗出现于阗玉,塔里木盆地南部最迟在东汉末年已经开始使用棉织物[22](p.98)。可见,自两汉以来,于阗与罽宾之间人员和货物往来频繁,使于阗不仅成为丝路南道的佛教中心和商贸中转中心,而且也使中原的丝绸、漆器、铁器、皮毛、玉石等通过罽宾进入南亚次大陆。一般来说,僧侣或商人大多经由罽宾丝道或瓦罕南道来往于阗、罽宾两地。罽宾丝道始于汉代,经过鄯善、于阗、皮山、乌秅、难兜、罽宾、乌戈山离诸国,由乌戈山离南至印度,西通犁靳、条支,西北可至大月氏。瓦罕南道由于阗西南行至葱岭,再经葱岭西行至勃律,然后再从勃律越雪山入罽宾[23](pp.57-s8)。
然而,这都不是犹太商人走过的路线,因为罽宾丝道和瓦罕南道都没有经过喀喇昆仑山口。那么,犹太商人走的是哪条路线呢?据《北史·土谷浑传》记载,公元444年,土谷浑国王慕利延西进攻占于阗,并从此南征罽宾,曾抵达女国。女国即《唐书》中的东女国,位于今拉达克一带,与罽宾相邻。据考证,慕利延南征路线如下:由于阗或皮山南行至赛图拉,向西南越过喀喇昆仑山口,至拉达克的中心列城,再折向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22](p.93)。显然,这就是犹太商人行走的路线。但是,汉魏之后这条路线再不见于史书,显见遭受冷落,主要原因在于丝道南路的衰微。魏晋以后,由于塔里木盆地南部及东南部生态环境恶化,和田河、克里雅河、尼雅河改道或水流减小,加上流沙侵袭,丝路南道通行不畅,导致以于阗为中心的丝路贸易日渐衰落,交通路线也“门前冷落鞍马稀”。
经由此道入华的犹太人很可能来自波斯。《以斯帖记》(8:9)记载,波斯王薛西斯一世的谕旨“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太人的文字方言写……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实一百二十七省的犹太人”。这说明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初期就已经遍布整个帝国。波斯帝国极盛时,疆域东起印度河平原和帕米尔高原,统治了中亚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萨珊王朝时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南地区也处于波斯人的统治之下。犹太人自然而然地迁人中亚地区,繁衍生息。20世纪60年代初,阿富汗加兹尼出土的许多犹太一波斯文墓志即为明证。加兹尼这个地名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史书上,《汉书·西域传》中称之为乌戈山离,《北史》中为伽色尼(加兹尼一名的来源),《隋书·西域传》中为漕国,《大唐西域记》中为槽矩咤,后二者用梵文复原为Jaguda,为Jahada(犹太)附会而来[24](p.77)。5世纪末,嚈哒人占据喀布尔至坎大哈地区,称之为Jawada(犹太)[25](p.956)。这表明,犹太人5世纪时已定居加兹尼,且有了一定的规模。波斯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商业发达。波斯犹太人以商业为生的不在少数,大多从事地区性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周边,但是,也有少数犹太商人与更远的东方有过交易,如从中国进口丝绸,从印度进口各种其他的奢侈品[26](P.227)。这些参与远程贸易的波斯犹太人就有可能通过上述商道进人中国。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希伯来语祈祷文,也是古代犹太人入华的重要文物。祷文现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原本有18行,现残存17行,皆引自《圣经·诗篇》;有多次折叠的痕迹,可能是被当作护身符从巴比伦带到中国的[20](彩插”)。伯希和认为,这篇祷文是9或10世纪的手稿[14](p.109),但其他学者的断代要早一些。施瓦卜认为,此为8世纪的遗物[27](p.28);波拉克推断为8或9世纪,托卡耶断为6世纪[28](p.407)。
上述文物的发现地点涉及和田(于阗)、洛阳(或者还有灵武)、敦煌和克什米尔地区,都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贸易中转地或交通要道。文物断代范围在6世纪到10世纪之间,大致属于隋唐时期。这说明犹太人通过丝绸之路入华的时间可以往前推至隋朝时期,可能人数不多,只在西域活动,尚未深人中国腹地。到了唐朝时期,犹太人的活动范围不再仅限于西域,已经来到唐朝的政治中心之一洛阳,而且还有商人以外的身份,甚至入朝為官,深受重用。
[参考文献]
[1]徐新.中国的犹太研究[J].西亚非洲,2010(4).
[2]龚方震.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C]//朱威烈,等主编.90中国犹太学研究总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3]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L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4]徐伯勇.开封犹太人的几个问题[J].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2).
[5]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张倩红,贾森.丝绸之路视域下的犹太商人[J].国际汉学,2015(3).
[7]张倩红,贾森.犹太人与丝绸之路[N].光明日报:理论版,2015-09-12.
[8]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Margoliouth,D. S. An Early Judaeo-Persian Document fromKhota,in the Stein Collection,with Other Early Persian Docu-ments[J].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and Ireland,1903(Oct.).
[10]Was,Bo,The Jewish-Persian Fragment from Dandan-Uiliq[J].Orientalia Sueeana,1968(17).
[11]张湛,时光.一件新发现犹太波斯语信札的断代与释读[J].敦煌吐鲁番研究,2008(11).
[12]李大伟.丹丹乌里克犹太—波斯文信件考释[J].敦煌研究,2016(1).
[13][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M].宋岘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
[14]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15][日]桑原骘藏.隋庸时代西域入华化考[M].何健民译.北京:中华书局,1939.
[16]Amanat,Mehrdad,Jewish Identity in Iran:Resistance and Coan-version to Islam and the BahaI Faith[M].London:I.B.Tauris&Co. Ltd,2011.
[17]徐新.犹太文化史: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8]侯杨方.穿越葱岭的丝绸之路:帕米尔高原故道寻踪[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5-16.
[19]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0][美]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M].张湛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21]Jettmar,Karl(ed.),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Reportsand Studies,Vol. 1:Rock Inscriptions in the Indus Valley[M].Mainz: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1989.
[22]殷晴.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J].历史研究,1992(3).
[23]陈良伟.帕米尔丝道初探[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4).
[24]林梅村.犹太入华考[J].文物,1991(6).
[25]玄奘.大唐西域记[M].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26]Grayzel,Solomon,A History of the Jews[M].Philadelphia:The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47.
[27]蔡桂林.东方际遇:中国犹太人千年历史揭秘[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8]Pollak,M. Mandarins,Jews and Missionaries[M].Philadel-phia:The Jewish 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