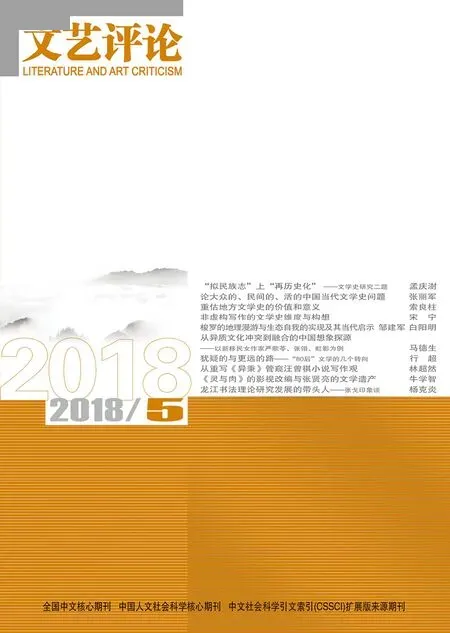犹疑的与更远的路
——“80后”文学的几个转向
○行 超
“80后”文学的崛起,几乎与21世纪的开启同时,1998年,上海《萌芽》杂志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一起举办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以“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为宗旨,号召写作者要用真情实感,写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文章,这在当时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犹如一声惊雷,号召了许多以“80后”为主体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前来参赛。几年间,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周嘉宁、蒋峰、那多等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这次比赛成为一代“80后”写作者步入文坛的敲门砖,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个比赛,让一批年龄相仿但文风各异的年轻人,以群体的姿态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1998年至今,时间过去了整整20年,这20年,既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潮、价值取向发生巨大转变的20年,也是“80后”一代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成长为家庭支柱和社会中坚力量的20年。一代在生理和精神上的全面成长,必然导致如今的“80后”文学与此前呈现出若干显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恰恰构成了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发展流变的一个面向。
一、告别对技巧与才华的迷恋
世纪之初,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几乎成为“80后”作家共同的座右铭。的确,与他们的前辈“50后”“60后”们相比,这一代写作者大多经历了相对完整的人文教育,广泛的阅读和写作练习让他们较早习得了语言文字的掌控能力。新世纪以来,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多元化选拔机制的出现,更让这些年轻人的文学“才华”享有充分的施展空间。然而,在文学的长跑中,“才华”固然可以为刚出道的写作者赢得一个不错的开局,但是,此后漫长的行进过程中坚持不懈的耐力与不断自省的精神,往往成为影响一个作家最终写作成就的决定因素。
2004年,蒋峰出版了长篇小说处女作《维以不永伤》,这一年,他还不满二十岁。据说蒋峰写作这部长篇时已有上千本西方小说的阅读背景,而且常常把小说拆开来看,研究作者怎样讲故事、怎样推进叙事。诚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一本大杂烩的小说,魔幻现实、侦探故事、诉讼小说、拼贴元素、罗曼斯情节,充满一二三人称的叙述,4部里悬念由小到大,不过还是一个事儿”。这个年轻的写作者,在大部分同龄人还沉迷于书写自我的小悲戚、小迷茫之时,已经显示出他不俗的叙事能力和文学野心。在这部以谋杀案贯穿全局的长篇小说中,蒋峰对于叙事视角、文本拼接等写作技巧的痴迷几乎弥漫在整个文本之中。多线索、多视角的复杂推进,使得这部作品颇具推理小说的吸引力。但与此同时,小说叙事中过于密集、繁复的技巧,某种程度上也损伤了其本身的艺术性、文学性,留下了这位年轻的作家在这段写作中过于刻意的、用力过猛的痕迹。
十年后的蒋峰在回顾自己的这部处女作时曾坦言:“我当时就想写一个技巧上严密得可以做教材的小说,任何一个细节都能被拎出来,变成一个故事。《维以不永伤》中的技巧可能是我到现在为止所有小说中用得最多的,比如换视角、平行、换文体等等。现在我更多的是反向的磨练,我想把表面的技巧打磨得更成熟,让别人看不出来这是技巧。我现在慢慢知道,技巧用多了会伤害小说本身。在电影中这种问题叫做‘跳戏’,技巧太多会让观众没办法真正入戏。技巧是为小说的叙述服务的,不能太明显、太生硬。”①十几年过去了,蒋峰虽不算高产,但陆续推出的一些中短篇作品,都始终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线之上。长篇小说《白色流淌一片》由《遗腹子》《花园酒店》《六十号信箱》《手语者》《我私人的林宝儿》《和许佳明的六次星巴克》6个中篇连缀而成,与《维以不永伤》相似,蒋峰依然致力于为读者讲一个“好故事”,他依然钟情于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的推进方式,但是在这部作品中,语言的简洁、技巧的圆融、情绪的克制,成为他文学成长的重要标志。就像蒋峰自己说的,“其实这些年以来,我最大的改变应该是语言和写作态度”。
2013年,《外滩画报》发起了一个“‘80后’作家群像”的访谈,采访对象包括周嘉宁、张悦然、郭敬明、颜歌等。周嘉宁回想自己刚出道的作品时说:“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在不该拿出来的时候,被拿出来了。要不是很多媒体的炒作和无良书商的介入,之前很多书都是不应该被出版的。可以写,但那些东西不应该被发表。”②周嘉宁的自我反思,表现出一个文学习作者向写作者的真正转变,显示了这一代作家在精神世界中正在走向成熟。蒋峰曾经出版过一个短篇小说集《才华是通行证》,“80后”作家刚出道时,对于“才华”的过分渲染,使得他们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沉迷于简单的技巧与辞藻呈现。20年时间倏忽过去,在“80后”作家笔下,我们已经很难再寻得他们早期作品中所习见的辞藻堆砌、技巧迷恋。对于个体写作者来说,这应该是从自发走向自觉,进而走向自省的重要标志。
二、从大写的“我”到渺小的个人
“80后”作家的初登文坛,与其说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审美或文学思潮,不如说,这一代作家之所以能够制造所谓的“轰动”效益,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反抗并试图打破既有的文学表达方式、教育制度和青年人的价值观。很难说彼时的“80后”文学是否具有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其叛逆的精神、无畏的青春姿态,让他们的作品成为备受瞩目的一种文化现象,撼动了当时文学的生产模式和评价体系。
与此同时,“80后”作家出现的那个时代,恰好是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版社和书商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商业契机。多方合力之下,“80后”作家及其作品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市场上最畅销的书籍。退学在家从事写作的韩寒,从2000年到2002年,连续三年推出三部长篇小说《三重门》《零下一度》《像少年啦飞驰》,三本书无一例外,都登上了当年全国图书畅销排行榜第一名。所有这一切,催生了这一代作家在短时间内的自信甚至自大、自恋,与文坛前辈的笔战,不断地口出狂言,让韩寒成了同龄人心中挑战权威的“英雄”,这种盲目而疯狂的拥护,也进一步导致“80后”作家对自我定位的错位,结果便是膨胀与迷失。
如今,20年前韩寒所代表的那种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的精神,在“80后”作家笔下几乎绝迹。青春期转瞬即逝,真正牢固而长久的,是现实生活的坚不可摧。于是,早年间“80后”作家笔下那些大写的“我”变得越来越犹疑、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举棋不定——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近年来,在很多“80后”作家笔下,我们见到的人物形象几乎是清一色的“失败青年”,如甫跃辉的“顾零洲”系列、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马小淘的《章某某》……这种“失败”不同于所谓的“小人物”,他们缺乏的恰恰是小人物在逆境中所透出的最后一丝光芒,他们的“失败”不仅在于物质生活的窘迫、现实社会的挤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失败者”在自我内心世界和精神深处,是完全消极的、颓靡的、迷惘的,甚至对生活充满了绝望。
1986年出生的小说家祁媛,其作品多书写社会现实中的精神流浪者、颓废的青年等等,她的作品具有一种冷而硬的质地,小说《眩晕》的主人公“他”是北京一所师范院校艺术系导演专业的学生,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比自己大20岁的女制片人,本以为可以与“她”聊聊电影、学习学习专业知识,谁知“他”与“她”之间却最终形成了一种简单的身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看着身下俨然已经被他征服的属于另一阶层的女人,感到自己不是在搞她,而是在搞这个高于他的阶层,甚至在搞近来总是和自己作对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失意和失败在这样一种畸形的关系中得到了释放,似乎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够在心理层面实现对自己失意生活的反转以及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报复。小说中“他”的处境和遭遇是当下“80后”一代的精神写照。他们也曾经有理想、有抱负,然而梦想一旦照进现实,看到的却是“信仰的快速崩塌”,物质层面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情感世界中,在异乡生活艰难、难以立足的他们几乎不敢妄谈感情,情感的需求不得不退缩到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和最渺小的心理慰藉。
与祁媛笔下的年轻人相似,随着年龄的增长,少不经事的“80后”少男少女们逐渐步入社会,20年间,他们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层的逐渐固化和生活压力的倍增。早年间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变成了眼前时刻都要面对的结结实实的现实重压,这样的重压,让“80后”一代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再加上虚无主义的滋生,几乎让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自我的怀疑甚至是否定越来越成为时下“80后”作家写作的常态,“失败青年”成为他们笔下异常重要和普遍的人物形象。
以“80后”的写作为窗口,我们可以照见,这一代年轻人从舍我其谁的自信到不断地自我否定,不过短短20年时间。这种巨大的转变,是当代青年内心世界的一种写照,更是当下时代的一种精神症候,以自我放逐、随波逐流为核心的“丧”文化、“佛系”文化因而悄然兴起。应该承认,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定位,是“80后”写作再次出发的起点。对于底层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的关注,也理当是文学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当这种对于“失败”的书写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时,它是否也构成了一种简单的、极易模仿并且滑向惯性的写作?
三、从残酷青春到历史叙事
“80后”批评家、学者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这本书中讨论了时代转型中“80后”生存的现状与困境,恰如他在其中提到的,“因为意识到了个人的‘失败’,并把这种‘失败’放置到一个非个人的境况中去理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寻找历史,在历史中找到一些确定不移的支撑点,来把个人从‘失败’中拯救出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疗愈方式,同时也似乎是中国这一深具文史传统的国度所惯常的行为方式”。对于历史的好奇与探索热情,一方面是“80后”一代疗救自我现实生活中“失败”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也是在生理年龄上已届中年的“80后”摆脱“无根”的困扰,寻找自我身份确认的内在需要。
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被视为“80后”写作转向历史与公共领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早期的《十爱》《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作品中,张悦然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内心脆弱敏感的文艺青年,与他人、与外界格格不入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对于现实的不满以及被伤害的感受,是他们共同的内心写照。早期张悦然所钟情书写的,正是这些文艺青年内心深处的所谓“创伤”。而在《茧》中,作者将目光从个体的内心与精神世界抽离出来,转而看向他人,看向自己的祖辈、家族以及绝大多数“80后”并无太大兴趣也并不擅长面对的“大历史”。小说中,主人公程恭、李佳栖两人被纠缠进自己父亲以及祖父一辈复杂的历史恩怨中:“文革”时期,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程恭的爷爷)被人从太阳穴锲一颗钉子,这颗钉子让他成了植物人,程恭一家由此走向落魄;另一边,李佳栖的爷爷李冀生人品、医术有口皆碑,看起来家庭和睦、事业有成,然而,随着李佳栖不断地发现,当年的真相逐渐水落石出:爷爷李冀生才是30年前那个残忍的罪犯。
《茧》的出现,不仅成为以张悦然为代表的“80后”作家写作视野转型的一大标志,更反映了“80后”一代由狭窄的个体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由被动“抛入”转向主动“直面”的选择与勇气。小说中,李佳栖寻找真相的过程,让她和她的同代人们回溯到文革以及更早的中国历史之中,这一伴随着与想当然的历史、与确信的过去相决裂的过程,其实并不轻松,甚至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此同时,当他们逐渐确证历史即“怪兽”时,以李佳栖为代表的“80后”的自我身份确认也隐约建立了起来。事实上,历史感的缺失是“80后”一代的共同特征,这一代人,出生、成长在中国社会面对巨大转型的时代,父辈们所确信的宏大叙事在“80后”生长的时代已经失效,个人主义开始泛滥,新的、具有同一性和整体的话语到现在也尚未完全形成。历史感的缺失也逐渐成了“80后”写作者在创作中所面临的巨大焦虑。
世纪之初,“80后”作家初登文坛之时,青春期的叛逆、反抗,让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出逃现实,遑论历史。个体的爱恨、疼痛、受伤经验被无限放大,反复咀嚼,这就导致“80后”作家早期写作的内容是大多所谓的“残酷青春”,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写作几乎等同于青春期的私密日记,上文中周嘉宁所说的“可以写,但不应该被发表”大约也包含着这个层面的意义。文学当然是个体的活动,它理当面对自我、面对内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对总体性的生活以及现实的认识逐步深入,曾经对于“无根”的自我安之若素的“80后”们开始反思,自我真的可以脱离历史与现实而独立存在吗?在历史的长河中,“我”的位置到底在哪?“我”之所以长成现在的样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来路?在这样的背景下,“80后”作家开始朝向历史而追问、书写,世纪之初那些叛逆的、离家出走的孩子们,在经历了现实的磨难和精神的成长之后,终于“回家”了。
①《蒋峰:拒绝无趣的小说》[N],《文艺报》,2013年 8月21日。
②《告别青春文学之后:“80后作家”群像》[J],《外滩画报》,2013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