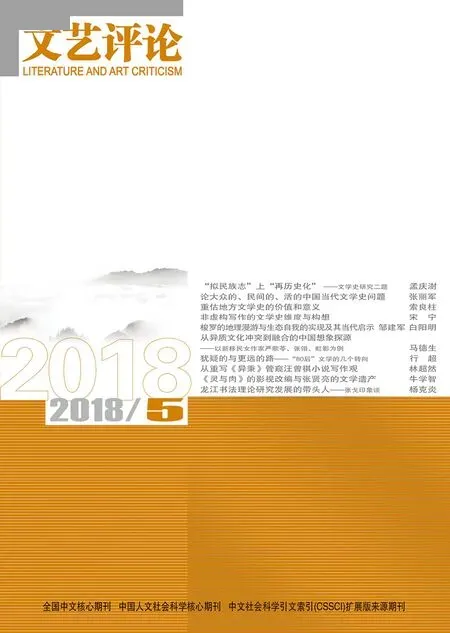多维度的“叙事性”阐发
——评杨亮的《新时期先锋诗歌的“叙事性”研究》
○崔 筱
虽然叙事学并不是在诗歌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但“叙事性”的引入无疑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注入新的力量,拓展了新的话语空间,进而上升为一个极富创造力的热点问题。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诗学探索,研究者们往往将目光集中于创作中的具体叙事现象而非理论层面的建构,这也致使研究流于零散化和表面化。从这一角度上,青年学者杨亮的新作《新时期先锋诗歌的“叙事性”研究》,不仅将“叙事性”作为先锋诗歌的一种为实现特定写作目的而采取的策略转向,更是直指“叙事性”的内部,将其看作一种具有综合属性的诗学观念并纳入到现代诗学的范畴之中。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维度的考量,作者梳理了“叙事性”问题发展的内因及其在不同时期、不同诗人群落中所呈现出的特殊形态,并细致地分析它的理论内涵及其对于现代汉诗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因而,本书对于“叙事性”问题的动态历史和理论内涵的把握,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理创新。
《新时期先锋诗歌的“叙事性”研究》一书对于先锋诗歌“叙事性”问题的阐发,是建立在对其产生动因、历史脉络、发展经过的细致梳理基础上展开的,这也组成了本书为更好地把握“叙事性”这一热点议题而率先展开和呈现的内容。作者凭借具体文本的深入分析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认可与补充,归纳新时期先锋诗歌“叙事性”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阶段性特征,试图还原一个较为真实客观的历史现场,从而勾勒出先锋诗歌“叙事性”明晰的成长轨迹和内在的逻辑线索,无疑具有较强的思想启迪力。
可以说,对于诗歌“叙事性”问题的关注和热议,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诗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始终占据着重要的篇章。而无论是具体文本的创作实践还是持续不断的理论建构,“叙事性”的概念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这一时期所独有的写作范式。因此,面对先锋诗歌的“叙事性”问题,我们不能将其仅仅视为一种艺术手法或表现特色进行考量。而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从而展开论述的。在她看来,无论是归来诗人群落在以物抒情的过程中呈现个体的精神与思考,还是朦胧新诗人借助意象的叠加和铺陈从而折射历史与现实的真实面貌,都可以让我们或多或少地看到诗人已然将叙事因子纳入到诗歌抒情的维度。他们在“托物言志”传统的基础之上,在“忠于现实”美学理念的统摄之下,在对“人的精神”不断追寻和发扬的过程之中,将客观写实叙事与主观情感抒发融为一体,借助想象的力量,不断挖掘日常情境或事件中的诗意,对拓宽诗歌情感传达与表现手法进行了诸多积极大胆的尝试。20世纪80年代中期步入文坛的一批“新生代”青年诗人笔下,“叙事性”不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于抒情方式的延伸,更成为了他们试图还原世俗美学价值、呈现语言异质属性、颠覆诗歌崇高境界的一件具有先锋意义的反叛利器。他们将日常的细节和思绪以一种日常化叙事的模式的方式进入诗歌话语之中,竭力消解文学想象与生存现实的边界,消解意象和隐喻的深度开掘。除了在创作实践中建立起了诗歌与生活新的勾连模式,“第三代”诗人们所主张的“去意象化”或“反意象”倾向、“冷风景”式的反抒情方式、“口语化”的语言实践,“为90年代先锋诗歌的‘叙事性’创作实绩的大规模涌现及内涵的生成预设了一系列的理论铺垫”①。进入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的“叙事性”问题也从一种朦胧的、抽象的、零散的创作倾向,逐渐进入到了一种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理论化的过程,同该时期特殊社会文化心理所形成的独特诗学语境,共同引领了“90年代诗歌”的发展和转变。
面对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的无情挤压,诗歌在面对日趋“边缘化”的窘境之时,唯有从诗歌内部出发,加速诗歌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转变,建构新的言说模式与艺术形态,方能真正实现诗歌的有效创作和稳步发展。由此,“诗歌终结了高蹈的‘非历史性’写作姿态,转而以‘及物’的方式,沟通诗歌与时代的关联”②成为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重要潮流。在这一背景下,先锋诗歌的“叙事性”所呈现出的大范围“介入”生活、文本包容开放、抒情主体日渐消隐的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网络诗歌写作的繁荣,“新世纪诗歌”的创作和批评中继续发力的“叙事性”问题,则以一种“狂欢化”的特质与态势呈现,能指的无限膨胀、追求快感的肉体宣泄、庸俗口语的机械复制,在将诗歌拉下神坛、走入现实的同时,也拖入到了一种集体性喧嚣与复制的危机之中。这一系列对“叙事”无节制的滥用,也进一步昭示着诗人和研究者们应该反思诗歌写作的初衷,回归理性的叙事诗学建构。作者在考量先锋诗歌中所包含的“叙事性”问题之时,并没有满足于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对其所呈现出的变化和性质进行简单的比对和厘定,而是将“叙事性”自身的演进态势和具体形态,作为反映先锋诗歌变迁的一个重要依据,无疑更能够凸显出新时期先锋诗歌叙事“史”的书写价值,也为进一步展开“论”的深度提升做好铺垫。
如果说透过对新时期叙事诗学演进过程的梳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先锋诗歌“叙事性”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发生、发展和现状,那么将这一问题还原至具体的文本和流派,即真实的诗歌创作现场之中,则可以使“叙事性”诗学话语内部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得以突出而逼真地呈现。《新时期先锋诗歌的“叙事性”研究》一书除了对“叙事性”问题进行了“史”的考察之外,更在对一手资料进行甄别、组织和运用的基础上,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创作群体(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女性主义诗歌)对于“叙事性”问题探讨和实践的共性与差异性进行横向的对比研究,不仅展现了新时期先锋诗歌写作的真实面貌和多样形态,更反映出了“叙事性”问题的复杂多变的独特内涵。
在争鸣与对抗中逐渐形成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阵营,可谓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两个诗歌群体。他们在写作立场和审美取向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致使其诗歌的表现手法和风格大相径庭。作者经过耐心甄别和精心比对之后发现,这两个看似水火互不容的两支诗歌队伍,在面对“叙事性”问题上均秉持着积极的求索态度。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努力挖掘“叙事性”因子的表现方法,着力思考和实践与之相关的理论命题。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诗作中及物性叙事的倾向、互文性叙事的角度、技术性叙事的特征,还是“民间写作”诗人们表现具有事态化叙事倾向的内容、择取解构的叙事性立场、采用口语化的语言形式,其本质上都是对于“叙事性”问题的理论探求和积极实践。而在同一时期性别视角烛照下的女性主义诗人们,积极寻求多元化、个人化写作路径,努力表现女性主体经验和精神世界,试图构建一种包容、开放的“交流诗学”,愈发呈现出“智性化”的诗学特征。在本书中,作者则从叙事角度切入女性主义的诗歌肌理,借助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文本,细致分析其在“叙事性”诗学的实践和运用中所呈现的独特色彩,阐发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中所呈现出的有别于一般男性诗人诗作的诸多特点,不仅揭示出女性主义诗歌思维方式和行为法则的独特所在,更在性别话语和叙事话语之间建立起了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虽然20世纪90年代不同诗歌团体、诗歌流派对“叙事性”问题的阐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分歧,但正是在这样多维度的探索中,在体现其多元共生的表现特征的同时,也为这一概念内涵的整合与挖掘带来重重困难。面对这样的研究状况,作者将“叙事性”作为一个诗学问题为立论基点进行解读,关注“叙事性”所引发的诗学变革及其深远的诗学内涵,认为正是“叙事性”的出现,才使得20世纪90年代诗歌获得了有效性诗学发展空间。在对“叙事性”问题的探索过程中,现实经验世界被重新纳入到诗歌话语中,促使诗歌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单方面支配走向互动和对话。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叙事性”这一诗学话语“扭转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格局,是诗歌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境况下,作出一次必要而有效的调整”③。作者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比对中,完成了对“叙事性”问题的真实面貌和内在规律的深挖和提炼,做出了一名诗学批评者应有的学术贡献。
除此之外,本书在中西诗学的广阔视域之下,借鉴而又不过度依赖西方批评理论,形成自己对于“叙事性”理论内涵的整合与凝练,也体现出了研究者宽广的理论视野。无论是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与韩东等人诗歌作品中实验性的“反抒情”尝试,还是巴赫金的“狂欢化”与20世纪90年代的“及物性”写作倾向,无论是借助福柯与鲍曼对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的解读来剖析新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内在驱动力,还是结合克里斯蒂娃和布鲁姆的“互文性”概念去阐释异质文本的多元姿态,都体现出了作者对西方诗学理论的充分吸收,运用多种批评方法,从而实现对先锋诗歌“叙事性”问题进行宏观整合与微观探析。本书借鉴了这一系列文学理论,但并未完全拘泥于此,而是在吸纳的同时努力建构个人的价值系统和评判标准,这不仅体现出作者所进行的诗学研究贴近当下、贴近创作的现实性,更体现了研究者构建个性化批评范式的前瞻性。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杨亮的《新时期先锋诗歌的“叙事性”研究》从具体文本的考察出发,梳理从新时期初期到新世纪“叙事性”问题的草创、成熟与发展的阶段性演进过程,比对不同诗学立场、写作风格之下对于“叙事性”的多维度呈现,进而挖掘“叙事性”作为一种独特诗学话语的真实面貌与内在规律,并最终实现对新时期至今三十余年中先锋诗歌中鲜明的“叙事性”问题的学理性梳理及其诗学内涵的立体式解读。
①②③杨亮《新时期先锋诗歌的“叙事性”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第52页,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