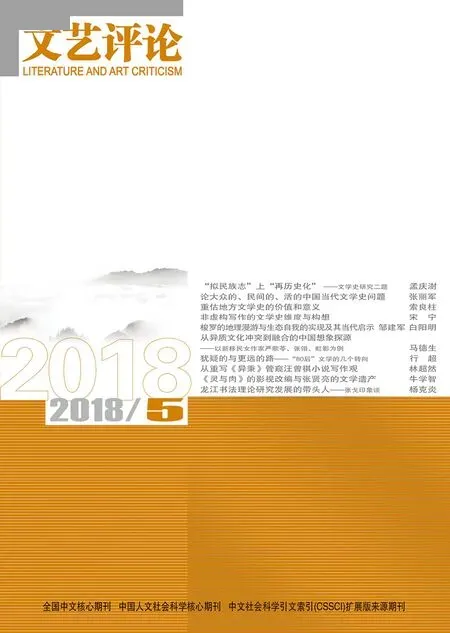以梅喻文的多重审美意蕴
○王顺娣
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赏花品花、咏花叹花,以花入文,在文艺园地留下诸多芬芳灿烂、意蕴丰厚的花意象。其中,梅(包括梅花)是各类艺术表现较多的花卉之一,长期以来备受文人学者关注。较为瞩目的研究成果有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张建军、周延《踏雪寻梅——中国梅文化探寻》、王莹《唐宋国花与中国文化》等,带来了梅文化研究的繁荣,使我们透过梅文化更深刻地去理解与感悟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内蕴。但是上述研究大多仅仅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梅(包括梅花)意象,探讨梅的象征意蕴及精神内涵,由此兼论梅与文人、梅与时代、梅与艺术、梅与工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很少顾及古代文论中的梅(包括梅花)意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梅喻文。一些代表性文论家如刘勰、苏轼等以梅喻文的重要见解在上述研究中几乎未见提及,这段空白无论对于梅文化研究的整体观照还是古代文论美学特质的内在把握来说都不无缺憾。
基于此,本文以古代文论中的梅(包括梅花)意象为研究对象,即以梅喻文现象为专题,从梅味、梅格、梅韵、梅境以及梅文人合一的层面,对古代文论不同历史阶段的以梅喻文现象作一纵向的历时观照,既具体反映以梅喻文的历史发展过程,又清晰展现其文论内涵和多重美学意蕴的演变脉络。
一、梅之味:喻对立和谐、味外之味的诗味论
“梅”是我国特有的花果,在先秦文献如《尚书》《诗经》中早有记载,历史极其悠久。据程杰《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论述,考古学家曾在1979年河南裴李岗遗址发现梅核,裴李岗遗址是北方新石器的一个代表,距今约七千年。①“梅”的栽培历史可追溯到七千年前,可以说涵盖了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全进程。从裴李岗遗址中梅核的发现来看,我国先民从那时起就已开始使用梅的果实,说明首先注意到的是梅子的实用价值。如《尚书·说命下》曰:“王曰……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盐梅就是咸盐和酸梅,梅子含有果酸,能够增酸味,催肉熟,是商周时期古人调制肉羹的必备调味品。这里王(武丁)把傅说之于国家复兴比作盐梅之于肉羹调制,突显傅说的重要性,这也是梅在比喻意义上的首度运用。《诗经·召南·摽有梅》曰:“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既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以树上梅子已然成熟、几欲落尽比喻自己怀春思嫁的美好愿望及急切心理,聚集点也在梅之果实上。
春秋末期晏子提出的“盐梅和羹”之喻不仅是从调味品角度,将盐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类比,而且更突出盐、梅之间对立冲突、相辅相济的特质,《左传·晏子对齐侯问》曰:
在晏子看来,鱼肉之羹是需要盐、梅、醯、醢等不同调味品相互协调、中和调制而成的,“和”的思想亦是如此,它不是以水济水之“同”,而是以他平他之“和”,是各种不同甚至对立因素的协调和谐。
晏子的盐梅和羹之喻直接开启了南朝刘勰在文论意义上对盐梅之喻的运用,富有重要意义。刘勰《文心雕龙·声律》曰:
赞曰: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割弃支离,宫商难隐。
刘勰认为诗歌语言的声律是复杂的,对复杂声律的调配更是繁复难明:“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违反声律配合的规律,念起来佶屈聱牙,就像得了口吃病一样。如何去调配它们?刘勰接着指出:“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左边有了障碍,可从右边去寻找毛病,末尾阻滞不畅,可从上面作调整。这正如他所说的“声得盐梅”之喻一样,盐咸梅酸,偏于任何一端,都会导致口感不好,只有酸咸的对立因素互相中和,味道才致新鲜和谐,真正产生声律上的滋味美。不难看出,他注重的正是晏子所崇尚的对立因素协调相济以达和谐的观念。这里他将盐梅之喻首先纳入文学理论领域,标志着真正文论意义上的以梅喻文的产生,完成了从实用性的调味到文学上的滋味美的蜕变。而且,他从语言本体角度出发,论证声律美要像盐梅相济相谐才有无穷滋味一样,将盐梅之喻与诗歌滋味联系起来,触及到文学的审美本质,与当时诗论主流如陆机“阙大羹之遗味”的遗味说、钟嵘“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的滋味说相契合,显示出刘勰盐梅之喻重要的美学意义。
至唐代,刘勰“声得盐梅”的隐喻在司空图那里有一定的继承,其《与李生论诗书》曰:“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醯即醋,鹾即盐,司空图以醋酸盐咸之味论诗,这与刘勰以梅酸盐咸之味论诗相比,其思维机制一样,体现出承传的一面,但二人更有不同,刘勰突出的是梅酸盐咸之味的对立中和因素,以此比喻声律调和臻于和谐的美境;司空图强调的则是诗文要像食物一样,不但要有咸酸之味,更要有咸酸之外的味道,即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景外之景,象外之象,注重的是由诗歌具体形象暗示、诱发出来的巨大审美空间和审美张力。有意思的是,司空图的醯鹾之喻到了北宋苏轼时,演变成了盐梅之喻,其《书黄子思诗集后》曰:“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虽然主旨精神并未改变,依然强调味外之味,但司空图的具体表述,在苏轼这里却由醯变成了梅,鹾变成了盐,这也显示出以梅喻文在古代文论中的强大生命力。
二、梅之格:喻遗形取神的创作论
如果说宋人林逋名句“疏野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使得人们对梅花的欣赏突破梅实滋味和物色芳菲的层面,深入其精神特质,将梅花上升为闲静淡泊、素淡清雅的精神象征,那么,梅花在文论意义上的拓展与深化则要归功于苏轼,前引他转述改造过的司空图的盐梅之喻,在后世文论中影响深远,如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曰:“司空表圣云:‘梅止于酸,盐止于咸,而美在酸咸之外。’严沧浪云:‘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此皆论诗也,词亦以得此境为超诣。”引用经苏轼改造过的司空图的盐梅之喻,倡导词境也要有味外之味。郭沫若《创造十年》十三也引盐梅之喻表达类似的观点:“外来稿件不加减一下盐梅,它是不肯入口的。”
更进一步地,苏轼由梅实转向梅花,提出“梅格”这一重要概念,丰富了以梅喻文的隐喻角度和文论形态。其《红梅三首》(其一)云: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
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
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诗老”是指宋仁宗朝著名诗人石延年,其《红梅》诗中有这样两句:“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意思是说,与桃花相比,红梅无绿叶映衬;与红杏相比,红梅又多了份青枝条秀之美。苏轼认为这只在形色上作文章,是浅薄拙劣的,正如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中所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应当由形似到神似,看到梅花所内蕴的清高而不孤介、傲岸而不怪异的品性,并将其概括提升为“梅格”一词,以此隐喻和提倡遗貌取神的文学创作理念,也为后世咏梅、画梅艺术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如姚勉《黄端可诗序》有云:“‘吟诗必工诗,定知非诗人’,坡仙语也。诗固主于咏物,然在于自然之工,而不在于工于求似。‘疏野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真梅矣,亦真梅诗矣。‘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梅乎哉?诗乎哉?”以梅为喻,进一步申述了苏轼由形而神的创作理念。
姚勉《梅涧吟稿序》更是从“梅涧”题名发论,兼以梅花万千风姿比喻唐代大诗人的创作风格,成为以梅花比喻遗形取神之创作观念的典型论述:
友人胡明可以其邑彭君仲章诗一编示予,题其编之端曰《梅涧吟稿》。未论其诗,视其编之题曰“梅涧”,清已可知矣。玉立冰臞,耐寒如铁石,不与春风桃李争艳媚,此梅之盛德事,魁百花而调羹鼎不数也。梅之在涧,其硕人之在涧乎?有诗人于此,踏雪于冻晓,立月于寂宵,无非天地间诗思。郊寒岛瘦,由浅溪横影得之;瘐新鲍逸,由疏花冷蕊得之;李太白出语皆神仙,由轶尘拔俗之韵得之;杜子美一生寒饿,穷老忠义,由禁雪耐霜之操得之。果能是,则可与言诗矣。然则求诗于诗,不若求诗于梅;观梅于梅,不若观梅于涧。
“求诗于诗”,说到底还是“吟诗必工诗”、强调形似的思维机制的具体表露;“求诗于梅”,则是以梅格观照诗格,求得梅与诗在精神意蕴、审美趣味的相通:或是郊寒岛瘦之浅溪横影,或是瘐新鲍逸之疏花冷蕊,或是李太白之轶尘拔俗,或是杜子美之禁雪耐霜,这正是追求神似的诗学观念的生动体现。
在画梅艺术上,宋人也提倡从神似角度把握画理。北宋释仲仁《华光梅谱》是流传最早的有关画梅理法的专文,据传他常住衡山华光寺,寺内外多种梅花,咏梅画梅,不亦乐乎。某次偶见月光将梅花影子洒落于纸窗上,其景象一如他在《华光梅谱》中所说的“临风带雪,干老枝稀,只要墨拨,淡荡花闲”,遂创造出以墨晕作梅花的画法,自成一派,注重的正是梅之神似。他还引用苏轼“梅格”一词,进一步阐述梅在绘画上的丰富意态和不同风姿:“学者须要审此梅有数家之格,或有疏而娇,或有繁而劲,或有老而媚,或有清而健,岂有类哉?”
三、梅之韵:喻平淡含蓄的诗美论
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有云:“物类虽同,格韵不等。同是花也,而梅花与桃李异观。”梅花与桃李诸花虽同为天地之精华,但梅花却能早春而发,以其孤霜瘦枝、雪骨冰魂、凌寒不屈、清奇卓绝高标特立,与桃李诸花绝异,故要作“异观”。这里张戒提出梅花与桃李不同,不仅在于“格”,还在于“韵”。
“韵”成为美学范畴,始于魏晋时代对人物风姿风貌、精神气度的品评,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称扬向秀有“拔俗之韵”;六朝以来逐渐用以谈文论画,如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绘画六法”,首倡“气韵生动”;宋人论“韵”,不仅更加广泛,遍及书、画、诗歌等各类艺术,如苏轼《论沈辽米芾书》评米芾行书“颇有高韵”,道潜《赠潜照月师》赞贾岛、无可的诗“自然韵胜”,具有普遍意义,而且把“韵”作为创作、鉴赏的首要原则和核心标准,置于很高的地位,如黄庭坚《题摹燕郭尚书图》:“凡书画当观韵”、《北齐校书图》:“书画以韵为主”,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凡画必周气韵,方号世珍”,韩拙《论用笔墨格法气韵之病》:“凡用笔先求气韵”、“凡阅诸画,先看风势气韵”,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炼句,句中炼言,及得二耳,以气韵清高深妙者绝,以格力雄健者胜”。那么,什么是“韵”,宋人认为,传统所说的雅致的人品境界、自然的表现手法和和谐的生命律动这些还不足以概括“韵”的核心内涵。这一点以范温《潜溪诗眼》中的论述最为典型:
定观曰:“不俗之谓韵。”余曰:“夫俗者,恶之先;韵者,美之极。书画之不俗,譬如人之不为恶。自不为恶至于圣贤,其间等级固多,而不俗之去韵也远矣。”定观曰:“潇洒之谓韵。”余曰:“夫潇洒者,清也。清乃一长,安得为尽美之韵乎?”定观曰:“古人谓气韵生动,若吴生笔势飞动,可以为韵乎?”予曰:“夫生动者,是得其神;曰神则尽之,不必谓之韵也。”定观曰:“如探陆微数笔作狻猊,可以为韵乎?”余曰:“夫数笔作狻猊,是简而穷其理。曰理则尽之,亦不必谓之韵也。”
他否定了“不俗”“潇洒”“生动”等为“韵”之本质的流行说法之后,接着指出:
定观请余发其端,乃告之曰:“有余意之谓韵。”……且以文章言之,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稳,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则可以立于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备焉,不足以为韵,众善皆备而露才用长,亦不足为韵,必也备众善而自蹈晦,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观于世俗,若出寻常……故巧丽者发之于平淡,奇伟有余者行之于简易,如此之类是也。
众妙皆备却又含而不露,外表简易闲淡,内里却风味蕴藉,从而产生深远无穷之味,这就是“韵”,它必须要具备两点特质:一是淡然的风貌(平淡),二是深远的余味(含蓄)。宋人论“韵”,多作如是观,如王柏《朱子诗选跋》评朱熹的诗“皆气韵疏越,趣味深永”,“疏越”指其淡然的风貌,“趣味深永”正是说具有无穷的余味。又如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原序》:“大凡观画而神会者鲜矣,不过视其形似,其或洞达气韵,超出端倪,用笔精致,不谓之工,傅采炳缛,不谓之丽,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始可品绘工于彀中,揖画圣于方外,有造物者思,唯一是得之。”“不工”“不丽”正是“韵”之淡然风貌的体现,“观乎象而忘象”“揖画圣于方外”则是提倡要超脱具体形象,富有味外之味。这其实也正是宋人审美风尚和美学理想——平淡美的体现。如苏轼称陶、柳诗“外枯而中膏”(《评韩柳诗》、韦应物的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姜夔赞陶诗“散而庄、淡而腴”(《白石道人诗说》),刘克庄标举刘诗“枯槁之中含腴泽,舒肆之中富揫敛”(《刘圻父诗序》),无不如此。
正是在这样的美学思想背景下,理学家包恢以韵观梅,又以梅韵观照诗歌,建立梅与韵在隐喻上深刻的内在关系,其《书徐致远无弦稿后》云:
诗有表里浅深,人直见其表而浅者,孰为能见其里而深者哉?犹之花焉,凡其华彩光焰,漏泄呈露,晔然尽发于表,而其里索然,绝无余蕴者,浅也。若其意味风韵,含蓄蕴藉,隐然潜寓于里,而其表淡然若无外饰者,深也。然浅者歆羡常多,而深者玩嗜反少,何也?知花斯知诗矣……夫以四时之花,其华彩光焰漏泄呈露者,名品固非一,若春兰夏莲,秋菊冬梅,则皆意味风韵、含蓄蕴藉而与众花异者。惟其似之,是以爱之……其视桃李辈,华彩光焰,徒有余于表,意味风韵实不足于里,而反人人爱之至,以俗花为俗诗者,其相去又不亦远乎!②
“梅”能从众多名品花卉中脱颖而出,正以其“意味风韵”。在包恢看来,“梅”之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表淡然若无外饰”,即淡然的风貌。平淡自然,不似桃李诸花,华彩光焰,漏泄呈露,徒有余于表,若人生厌;二是“含蓄蕴藉,隐然潜寓于里”“有余意”,富有深远无穷的余味,不似桃李辈,一览无遗,绝无余蕴。可以看出,包恢的梅韵之喻完全契合宋人对“韵”的认识以及他们崇尚“平淡美”的审美理想,使得梅韵成为宋人诗歌审美理想的典型隐喻。
四、梅之境:喻立体交叠的意境论
经过宋人的艺术构造与全民树立,“梅”在人们心目中愈发可亲,成为千载不衰的花中至宠,咏梅之作在中国文学中高居榜首,以梅喻文在宋之后的文论中亦方兴未艾,其隐喻角度和文论形态也有了新的变化。如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评道:“纪君祥之词,如雪里梅花。”“石君宝之词,如罗浮梅雪”,以梅、雪构境,取梅雪的洁白同色、寒心自持比喻二人词作的素雅明洁、冷艳独幽,突破了之前单纯从梅花取喻的角度,更加形象生动,丰富深邃。
李梦阳则以梅、雪、月、日、风、云构境整体隐喻,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其《梅月先生诗序》曰:
情者动乎遇者也。幽岩寂滨,深野旷林,百卉既痱,乃有缟焉之英,媚枯缀疏,横斜嵚崎清浅之区,则何遇之不动矣。是故雪益之色,动色则雪;风阐之香,动香则风;日助之颜,动颜则日;云增之韵,动韵则云;月与之神,动神则月;故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遇而发者也。“梅月”者,遇乎月者也。遇乎月,则见之目怡,聆之耳悦,嗅之鼻安。口之为吟,手之为诗。诗不言月,月为之色;诗不言梅,梅为之馨。何也?契者,会乎心者也。会由乎动,动由乎遇,然未有不情者也,故曰:情者动乎遇者也。
梅月先生何许人也?不详待考。李壮鹰以明人朱熊拥有梅月轩书室,亦或为是,姑存一解。这里值得讨论的是,李梦阳以梅为喻,提出新的文论命题,颇有新意。首先,他突出创作主体情感的主导作用,所谓“快乐潜之中,而后感触应于外”,有了内心的情感,才会生出外在的感触,主体情感是更为根本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是仅仅看到主客体之间单纯的双向运动,更认识到这种双向运动的复杂样态。从创作客体来说,梅本身媚枯缀疏、横斜嵚崎、风姿不一、情态无二,加之在“雪、月、风、云等其他因素的干预、影响下所呈现出来的由色、香、颜、韵所组成的立体意象”③,更是昭晰互进,层出不穷;就创作主体而言,或有身修弗庸之怀才不遇,或有独立端行的高尚人格,或有耀而当夜之闲适旷达;如此,物与物相遇,情与情相动,物与情又交相共感、交融契合,主体之“当时所怀的特定心态,适与眼前的立体意象相遇合、相共鸣、相冥契”④,它们之间所生发的美感形态、情感内蕴便是立体交叠、生动丰富的。这比之单纯的物我互动来,其理论深度无疑更进一层。
似从唐代开始,文人惯于在其作品中以梅命名、命题,取其丰富的象征内蕴,如唐曹邺传奇《梅妃传》、明邓志谟寓言体小说《梅雪传奇》,汤显祖《牡丹亭》男主人公名为柳梦梅,清人任璇《梅花缘》女主人公呼为方素梅,人花互寓,含蕴无限。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这是一部以家庭伦理和社会众生相为题材的长篇世情小说,小说以“金瓶梅”为题名,最通俗的解释是它是小说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缩名,而这三人“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富有典型意义。然而一如清代才子张竹坡所生之疑惑:潘金莲乃《水浒传》中原有之人,又“何以有瓶、梅哉?”故他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中为该题名阐释尤为精深。再结合今人看法,我们总结出“金瓶梅”之题名除了人名缩写之外还饱有如下含义:(一)瓶中之梅。瓶里梅花,虽芬芳灿烂,富贵奢华,却春光无几,衰朽在即;或朵朵梅花,费尽春工,当注之金瓶,流香芝室,为才子把玩,不可沦为俗人之物;(二)雪中之梅。梅雪不相下,故春梅宠而雪娥辱,春梅正位而雪娥愈辱;(三)月中之梅。月为梅花主人,月娘为月,故为正室,遍照诸花,表面温婉,实则暗藏心机;(四)金莲之梅。瓶死莲辱,零落惨淡,独有春梅,脱颖而出,争相吐艳;(五)霉变之梅。金瓶梅者,金瓶霉也。金瓶已然变质,世间何物能不变质?(六)瓶插之梅。梅乃自然化生,瓶为人为加工,金瓶梅花,全凭人力以补天工,处处以人工夺化工之巧。种种阐释,全以金、瓶、梅三者交错展开,杂以雪、月构境,立体交叠,含蓄深沉,意境浓厚,诚为以梅境喻多重立体之意境论的绝佳例子。
五、梅之魂:喻梅、人、文的三位合一
从梅实的品尝、梅树的培植、梅花的欣赏,至咏梅、叹梅、画梅在各类艺术门类的出现,经过几千年人们的加工栽植、精神建构、文化积淀和传统承传,梅及梅花已然成为冰清玉洁、坚毅幽雅的人格象征、传统审美理想的重要标志以及华夏民族精神的典型载体,其艺术魅力光景常新、经久不衰。以梅喻文现象在近、现当代文论中依然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近人徐盛持《题郑向谷香雪论诗图》云:“放翁愿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段魂。”虽然本身化用爱梅入微的陆放翁《梅花绝句》中的诗句:“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不过这里他提炼出“梅魂”一词更凸显陆游与梅与诗心心相印、高标绝俗的伟大人格;“梅魂”成为这一时期文论中富有时代气息和个性特征的隐喻。它将梅花高度人格化,人即是梅,梅即是人,梅也是诗,也是文,人、梅、文三位合一,人的精神意蕴、诗学境界、文论思想甚至身世遭遇都与梅花心心契合。如近代著名僧人八指头陀一生就与梅花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他酷爱梅花,写下了诸多咏梅诗,他生前将出版的诗集定名为“嚼梅吟”,既有以梅花为题材的表现内容,又有以梅花为象征的情感世界,还有以梅花为去俗的诗思媒介。太虚大师以花总结八指头陀一生的因缘:“梦兰而生,睹桃而悟,伴梅而终。”梅花是其心灵的最后归宿。故当今学者陈望衡在评其咏梅诗的意境时,直以“前身多半是梅花”为题概之。文章以梅论人、论诗,具体探讨了八指头陀咏梅诗中独特的梅姿及与月、雪、水的构境,借梅咏叹思念、孤洁等丰富的情感世界,认为“他的咏梅诗有他独自的情感体验,独自的境界,因而也就自成一格”⑤,其最大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诗总体品格上“绝去尘俗,天然为真门妙谛”,但封建社会的内忧外患、行将就木令其无法完全封闭自己,故时时在诗中透露“万树梅花是泪痕”(《平山堂谒史阁部墓》)的痛楚以及“报国捐躯义已成”(《题孤山林典史墓》)的心愿,依然葆有一位爱国志士的洁白。文章最后总结道:“诚然,国势如此衰颓,人的生存只能是艰难的,然而虽然艰难,却绝不放弃,而且愈是艰难,愈见坚贞,亦如寒梅,傲霜迎冰。而祖国,这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故国,在历尽劫难之后,定然会有一个如同红梅般的灿烂的未来。”⑥只有历经傲立迎霜的寒梅,才能成就美好灿烂的红梅,这既是对八指头陀爱梅精神的隔世呼应,也是在倡导梅之凌寒不屈、高雅绝俗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回归。
又如《文学报》2014年7月24日载有庞然对卢前《冀野文钞》的一篇短评,题名为“谁记江南瘦梅花”。卢前1905年生于南京诗书世家,时人号称“江南才子”,1951年病逝,年仅46岁。据资料显示,卢前生前并未以梅花自名,此文却以“江南瘦梅花”括其一生,盖取其与梅花之相似遭遇吧。南宋杨万里曾对梅花的发迹史做过精辟总结:
梅肇于炎帝之经,著于说命之书、《召南》之诗。然以滋,不以象;以实,不以华也。岂古之人皆质而不尚其华欤,然“华如桃李”“颜如舜华”,不尚华哉?而独遗梅之华,何也?至楚之骚人,饮芳而食菲,佩芳馨而食葩藻,尽掇天下之香草嘉木,以苾芬其四体而金玉其言语,文章尽远取江篱、杜若,而近舍梅,岂偶遗之欤?抑亦梅之未遭欤?南北诸子如阴铿、何逊、苏子卿,诗人之风流至此极矣。梅于是时始以花闻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苏黄崛起,千载之下而躏籍,千载之上遂主风月花草之夏盟,而于其间始出桃李、兰蕙而居客之左,盖梅之有遭未有盛于此时者也。
而据《冀野文钞》出版说明介绍:“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中,卢前无疑是很值得瞩目的人物之一。在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卢前在当时的文坛和学术界,特别是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文化圈,是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但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似乎被人们渐渐淡忘了。”⑦庞然的该评论亦言,卢前曾“风靡一时”、英年早逝后,“文与人都不再被提起,逐渐模糊湮灭,直到五十五年后,中华书局才发掘出版了一套《冀野文钞》”⑧,梅花的长时遭沉寂与卢前的长久被埋没何其相似乃尔!庞然以“谁忆江南瘦梅花”道之,情辞切切,令人扼腕叹息。除此之外,亦当取梅花与卢前精神品格上的息息相通,包括十足的学识才气、丰富的人格意趣和不屈的乐观精神,等等。
要之,在我国古代文论以梅喻文的历史长流中,历代文论家对梅不断地开发、挖掘,从梅的实用性调味到美学滋味论、从以梅格比喻遗形取神的创作观念到以梅韵隐喻平淡含蓄的审美理想,从以梅境喻立体交叠的诗境论到以梅魂喻人、文、梅的三位合一,梅的意象内涵、美学范式、审美趣味及其精神内核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丰富,遂致形成一个厚重深沉、多元灵动的“梅花”意象,以梅喻文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极为重要、极具典型的草木隐喻之一,生动展现中国文论整体的人文精神和审美心态。
①程杰《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5页。
②李壮鹰《中华古文论释林·南宋金元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③④李壮鹰《中国古代文论读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01页,第301页。
⑤⑥陈望衡《美在境界》[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页,第388页。
⑦卢前《冀野文钞·卢前曲学四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⑧庞然《谁忆江南瘦梅花》[N],《文学报》,2014年 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