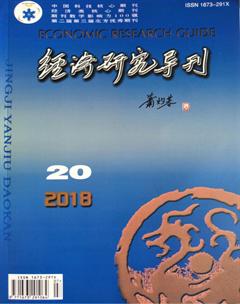环境类邻避设施的风险感知与冲突治理策略分析
邵青
摘 要:风险分配不公正、风险感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建构视角,客观上造成政府—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完全不同的风险感知结果。环境类邻避设施选址建设过程中分配正义、承认正义的缺失,经过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促使国内环境类邻避冲突呈越演越烈的趋势。因此,建议从风险沟通、协商民主参与角度,创新环境类邻避冲突的治理策略。
关键词:邻避冲突;风险感知;协商参与;正义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8)20-0171-03
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的开篇即提出,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稀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开始向发达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转变[1]2。人类生活于自身所创造的风险社会中,因风险分配不公、风险感知差异、风险管理者“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决策等因素,导致以有毒废弃物处置、垃圾焚烧(填埋)、核设施等为典型的土地利用项目,易于遭到地方居民强烈的抵制情绪或冲突抗争。这一现象即邻避冲突行为(Not In My Backyard,NIMBY),当前在我国形成愈演愈烈的态势。本文围绕着垃圾焚烧(填埋)、PX、核设施等邻避设施蕴含的客观风险、周边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等主题,探讨环境类邻避冲突的心理基础、行动逻辑及治理策略。
一、环境类邻避冲突的心理基础:风险感知的二维视角
(一)风险分配的不公正与普遍性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不同形态的风险。贝克认为,工业社会自身的生产逻辑蕴含了潜在的风险,凸显为科技的副作用对环境的破坏和人类健康状况的损害,如化工厂毒气泄漏、核设施废弃物放射性造成的危害,在风险分配逻辑上呈现了内在的张力。一方面,风险分配同财富分配具有一致性,与人群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联,越是偏僻、落后地区越承受了更多的风险,富裕、发达地区(国家)具有更强的风险规避能力,后者将风险向前者转移。正如贝克所说,“财富在顶层积聚,而风险在底层积聚”;“风险分配的编组站特别偏爱位于欠发达的穷乡僻壤的小车站”[1]25。另一方面,工业社会制造的风险又具有“回旋镖效应”,它打破了社会阶层差异,风险的制造者(受益者)迟早会受到风险的冲击,正如生态灾难、核泄漏向来无视国界。因而,风险的普遍性、全球性,使得任何忽略、规避风险的行为变得更加困难。
(二)风险感知的二维视角
对于何为风险,理论界尚未达成一致,争议的焦点在于风险究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还是基于人的主观认知的建构,由此形成了风险感知的两种视角。客观主义视角强调了工业化生产所带来潜在风险的真实性、可计算性,即风险(R)=损害的程度(H)×损害的概率(P)[2]。客观风险(objective risk)是等着人们去认知的客观实体,风险感知即在风险知识把握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理性评估客观风险给人类带来影响的大小,而且只有具备科学素质和专业知识的专家才能进行正确的风险感知和评估。建构主义认为,风险不是客观实在物,而是由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建构物,是个体对外在事件的感知行为。事实上,罗杰·卡斯帕森认为,风险既是对人们的一种客观的伤害威胁,又是文化和社会经验的一个结果[3]36。贝克强调,“风险和风险感知正在逐渐汇合,互为条件、彼此加强”[1]56。因此,合理的风险感知应该融合客观主义和主观建构的二维视角。尤金·A.罗莎将风险定义为,具有某种人类价值的事物(包括人类自身)在其中处于危急关头,而其结果不确定的一种局面或事件。这一定义强调了人们在风险本体论上观点的一致性,即承认风险的客观性;但在认识论上,认为由于不同人群知识能力上的差异,存在等级制的风险感知差异[3]36。
我国近年来以PX项目、垃圾焚烧(填埋)、核电为典型的环境类邻避冲突,一方面因设施的负外部性,通常对项目周边的空气、水源、房产、产业等带来潜在负面影响,表现为对居民的经济利益、健康利益带来损害的风险,因而易于遭到居民的反对;另一方面,成本与收益的非均衡性,即邻避设施的收益为更广泛社会成员共享,负外部性成本卻由项目周边公众承担。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作为小集体的项目周边公众更易于组织抗议活动。从根源上看,政府与社会公众在环境类邻避设施的风险感知上存在较大差异,加上公众对政府及专家群体的不信任,进一步拉大了二者间的差距,这便构成了公众反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心理基础。
二、环境类邻避冲突的行动逻辑:环境正义与风险放大
(一)环境分配正义与承认正义的缺失
公众反对在其居住地附近建造有毒废弃物处置场、垃圾焚烧(填埋)场、化工厂等的抗议活动,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1982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沃伦县居民抗议在阿夫顿社区附近建造有毒废弃物填埋场,标志着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有色人种、低收入阶层及其他弱势群体暴露于有毒或危险物质“机会”的不平等,即环境风险分配不正义这一社会现实,是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直接起因[4]。长久以来,美国有色人种居住区、经济落后地区成为各种环境有害物处置场的优先选址地。罗杰·卡斯帕森指出,“在高放射性核废料的产生地与内华达州尤卡山乏燃料处理场之间,地域上损益的不匹配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5]环境风险不公正地向落后地区分配的特征明显。
从分配正义角度来看,环境正义运动从早期关注种族、收入与有毒废弃物填埋场选址关联性,到中期探讨不同主体面对环境利益与负担分配时的不公正对待问题,揭示了空气和水污染、有毒废弃物污染、放射性和化学性污染等环境恶物在空间区域上的不正义分配事实。从承认正义的角度来看,承认弱势群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尊严和价值,维护他们的生存权、生命权和环境权,符合社会正义的内在要求[6]4。实践上,环境分配正义和承认正义的缺失是公众反对环境类邻避设施选址建设的现实基础。
从国内垃圾焚烧(填埋)项目选址和建设区位选择来看,一方面,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如地级市区域),城乡结合部、偏远农村地区或人口分布稀少的经济开发区等成为这些设施的选址地;另一方面,在不同行政区域内,经济发达地区通过经济手段将垃圾输送到落后地区。因此,环境类邻避设施一定程度上存在空间分配不正义现象;承认正义上,环境类邻避设施规划、选址决策过程中,周边公众难以获得平等性对待和实质性参与,政府习惯于从社会整体利益角度阐释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意忽略了周边公众的信息需求和决策参与权利,没有赋予他们应获得的承认正义。
(二)风险感知差异及社会放大效应
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本身具有一定水平的客观风险,如化工厂毒气泄漏(印度博帕尔事件)、核设施事故造成的放射性(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垃圾焚烧发电超标排放的二英类有毒气体。因此,需要通过科学的手段对科技带来的副作用——客观风险进行监测和管控。环境类邻避设施选址建设运营过程中的风险评估,政府和设施运营单位主要依赖于掌握专业知识的技术专家,基于科学理性、运用概率统计等方法评估出风险的大小及提出相应的管控策略。这种风险评估做法是当前我国环境类邻避设施选址决策中,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和社会稳定评价的行动逻辑。然而,仅仅针对环境类邻避设施本身具有的客观风险进行评估,得出的结论通常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可。
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风险感知与专家的科学理性计算不同,他们遵循的是社会理性。这是基于公众自身的个体特征、生活经验、风险知识理解、群体行为意识等形成的风险建构。通常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风险感知水平远远高于专家的客观风险计算,在对政府、专家缺乏信任的背景下,政府的选址决策易于遭到周边公众的强烈反对。贝克认为,在一项风险决策过程中,由于风险的决策者(政府)、评估者(专家)、制造者(运营企业)与风险的承担者(设施周边公众)间的分离,易于形成风险决策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他们忽略了风险承担者的心理感受及对其应享有的承认正义。罗杰·卡斯帕森构建的风险社会放大框架,反映了公众针对一项风险或风险事件,经由社会的放大站和个体放大站,将风险信号经过放大或弱化,对受到直接影响者、当地社区、专业群体、利益相关者群体、整个社会等产生涟漪效应,进而产生不同的影响,如财政损失、风险增加或减少、对公共机构丧失信心等[6]79。其中,邻避设施的污名化和对政府机构及运营商的不信任,加剧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
以国内近些年上马PX项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公众针对此类项目的抵制席卷大中小城市,PX有毒、二英致癌等与项目相关的词语描述,使得PX走向妖魔化、垃圾焚烧遭到非理性抵制。网络信息时代,一地爆发的邻避冲突消息经网络渠道迅速传播,有关项目的风险感知在公众意识里不断放大,污名化印象加深,对其他地方的项目选址建设造成涟漪效应。可以说,由于当前政府在环境类邻避设施选址建设过程中,信息公开、决策参与、风险沟通的严重不足,导致经过风险社会放大效应的公众风险感知水平偏高,基于对自身所处风险的担忧,邻避冲突诉求的目标单一,即取消或停建项目。
三、环境类邻避冲突化解的源头治理策略:风险沟通与协商民主参与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需求呈扩大趋势。鉴于此类设施具有的污染性、风险性,对设施的安全运营和健康风险担忧是周边公众最为关心的两大问题。由于政府在环境类邻避设施的规划、选址、建设等阶段单纯依赖专家群体对项目风险进行评估,形成政府内部封闭式决策模式,忽略乃至有意规避项目周边公众的信息需求和决策参与渠道,否认周边公众经风险放大所形成的项目风险感知水平,由此导致二者间在环境类邻避设施选址建设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风险沟通是风险评估和风险决策的前提,只有通过有效的风险沟通,矛盾双方形成一致的风险评估意见,才能做出科学的风险决策。因此,风险沟通是化解我国环境类邻避冲突的首要策略,而要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必须创新公众的决策参与机制。
(一)有效的风险沟通
罗杰·卡斯帕森认为,政府(设施建设运营企业)与公众在风险沟通参与中存在预期手段——目的性差异冲突,政府仅仅将公众参与看作是赋予项目建设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公众则将参与视做反对项目建设或获得更多利益的目的性行为,这一差异突出体现在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功能变异。环境类邻避设施选址建设需要经过环境影响评价、社会稳定评价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让周边公众通过科学的评价知晓后,同意项目在本地的选址建设。实践中,这两项制度的功能变异为一种程序性设置,是进入政府下一道审批环节的一个必备要素,至于环评、稳评的科学性,是否充分调查分析了周边公众的态度等核心问题,则遭到有意的规避。这也是环境类邻避设施虽然通过了环评、稳评,而一些周边公众直到项目开工时才知晓的原因。另一方面,缺乏公众早期和持久的参与是项目失败的根源。政府、设施建设运营企业通常在项目规划、选址的后期才邀请周边公众参与,此时主要的决策已经做好,实际上已排除了可选择的余地。此外,政府机构的信誉、风险评估信息的可信度,也是影响公众风险沟通有效性的重要因素[6]79。
环境类邻避设施从规划、选址到开工建设,整个决策过程周期长,有的需要数年的时间。但在整个风险决策过程中,政府主要依赖专家群体得出的科学结论,公众通常是在政府风险决策即将实施的节点获得相关信息。此时,项目周边公众感觉被欺骗、愚弄的情绪急剧扩大,环境风险分配的不公平感快速上升,各种抗议活动在短期内爆发。此时政府再去宣传项目的必要性、风险可控性,要求周边公众保持理性克制等,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对于一些已建成的环境类邻避设施,由于政府、第三方风险评估机构公信力不足,周邊公众担心政府、第三方机构与运营企业进行合谋。例如,此前网络爆出国内针对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半年一次的二英排放检测,江苏省某第三方检测机构肆意篡改排放数据。因此,围绕着环境类邻避设施的风险沟通,让周边公众从规划、选址、建设到运营监管全过程实施有效参与,既有助于削弱公众偏高的风险感知,也利于提高政府和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公信力。
(二)广泛的协商民主参与
加强环境类邻避设施选址建设中公众的风险沟通和广泛参与,获得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较一致的认可,但在公众协商参与的渠道、载体、方法、效果等方面缺少深入分析。协商民主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以来,成为当前各国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重要途径,涵盖了从协商议题的确定、协商参与主体的选择、协商程序与方法的设计,到协商结果的达成与运用等参与过程,其中信息公开、平等参与、理性协商是其基本原则。实践上,公民会议、公民陪审团、协商民意测验等协商途径方法广泛地被欧盟、美国、日本等用于讨论环境政策、能源建设项目、食品安全等公共事务。
国内近年来在农村基层治理创新上,积极探索平安协会、和谐促进会、乡贤理事会等协商参与途径和载体,较好地化解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矛盾。环境类邻避设施的特征,决定了其规划选址、建设运营必然落实到城乡基层社会单元,与周边公众必然保持着空间上的近距离。一定区域内,公众对于此类设施用地需求的意见态度、经过风险沟通后是否有条件同意、需要哪些补偿措施等焦点问题,政府部门要想准确地获得此类信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广泛发动公众协商民主参与。在公开、平等、理性的基础上,开展深入持久的协商,最终达成是否建设、如何建设的决策共识。杭州市中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从公众强烈的抗争到项目原地建成运营,成为近年来国内少见的成功化解邻避冲突的案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公众协商参与在其中发挥的有效作用。而且通过协商民主参与形式促进环境类邻避设施的选址建设,也契合了环境承认正义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2] 张贵祥.风险认知的两种哲学视角及其融合趋势[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4).
[3] 尤金·A.罗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逻辑结构:超理论基础和政策含义[G]//尼克.皮金.风险的社会放大.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36.
[4] 腾海键.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5] 朱力,龙永红.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的凸显与调控[J].南京大学学报,2012,(1).
[6] 珍妮·卡斯帕森,罗杰·卡斯帕森.风险的社会视野(上)[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