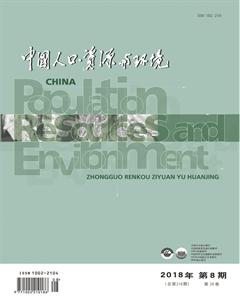环境分权与经济竞争背景下河流跨界污染的县域证据
宋德勇 张麒
摘要在环境地方分权治理和县域经济竞争体制下,县级政府间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可能存在“以邻为壑”的行为,这使得同一流域上下游县域间更容易产生跨界污染问题。本文通过引入污染“累积效应”和河流“自净效应”,建立了河流污染的外部性模型,并推导出相应的假说,再从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和行政分割前后两个维度,对河流污染程度的动态变化进行了情景模拟。基于2004—2014年七大流域中国国控监测断面的周数据,本文对河流污染程度与“县边界-监测站”沿河距离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了环境分权体制下不同行政分割程度对“跨界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随着河流接近县域下游边界,在更强“累积效应”作用下,河流污染指标COD和NH3-N呈现加速递增趋势,河流“跨界污染”问题显著;②在河流跨越县域边界后,由于更强“自净效应”和相对严苛的环境监管,COD和NH3-N增长放缓乃至局部下降,县边界两侧污染程度呈现出结构性差异,且这种差异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③河流跨越的行政边界越多,所面临的沟通与协调难度就越大,潜在的利益冲突下“以邻为壑”动机就更强,因而污染排放就更加严重。据此,本文建议加快推进“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和“河长制”河湖管理模式,改革现行以块为主的环境治理方式,从制度层面解决好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推行环保督查的同时,从官员绩效考核层面提升环保激励;建立组织架构完备、各级监测站点分布合理、衡量指标齐全的河流水质监测体系。
关键词环境分权;累积效应;自净效应;跨界污染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8-0068-11DOI:10.12062/cpre.20180308
河流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然而,水资源作为流域内的一种公共物品,兼具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大特征,这决定着流域水资源的利用存在着“拥挤效应”和“过度使用”等矛盾。许多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学者推崇环境地方分权治理来改善公共服务[1-2],而约旦河、印度河、太湖等诸多流域的冲突,尤其是国内嘉兴—盛泽“零点事件”和近年来流域水质的急剧恶化等,使學术界不得不重新审视环境地方分权治理体制带来的影响。在分权治理体制下,县级行政区与流域整体之间存在着收益与成本的非一致性,这可能触发各地区在流域水环境治理方面对下游“以邻为壑”的行为,而这也使得很多合乎流域集体利益的行动并没有产生,反而被各个地区的自利行为所代替[1],下游买单似乎是“最好”的自利策略。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种由“以邻为壑”所引发的河流“跨界污染”问题,显然有悖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要实现绿色发展,就需要深入研究当前中国环境地方分权治理体制与河流跨界污染两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解决中国河流水污染的结构性问题。
1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地方分权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争论激烈,而更大程度行政自主权下放至地方政府能否促进环境治理效果的改善则是争论的焦点。其中,部分学者认为通过环境地方分权可以改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主要依据是在环境监管标准与程序设定上,地方政府能够因地制宜制定环境政策,同时决策权力的下放也给不同的环境管理方法提供了试验机会[3-4],围绕着中央到州一级环境地方分权方面的部分实证研究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5-6]。然而,也有部分实证研究发现环境地方分权并没有带来环境治理效果的改善,反而导致一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其他非预期结果[7-8]。这些不同结论可能不依赖于分权本身,而是分权制度下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9]、政策实施模式[10]等,根本上还在于各级政府、企业和民众关系的调整[9]。
河流社会价值与社会成本具有不对称性,相比于空气污染,河流污染的单向溢出似乎更加突出,跨界污染常常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尤其是Sigman开创性地发现国际河流存在显著的跨界污染掀起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热潮[11]。国际河流的跨界污染研究多以欧洲和北美为对象[12-13],而一国内部河流跨界污染则主要集中于对美国和巴西府际关系的研究[14-15]。由于国际河流与国内河流利益主体的差异,在作用机理上跨界污染问题也存在着差异,民主、超国家机构、贸易关系和国家间的政治压力承诺被认为是影响国际跨界水污染的重要原因[16],而国内跨界水污染则归因于国内边界地区的搭便车行为和相对宽松的环境执法行动[17]。在中国河流跨界污染的研究中,则以定性分析和理论阐述居多,主要是阐述污染背后的法律和行政制度[18]、流域管理模式[19-20]和地方政府竞争行为[21],而实证方面则集中于从中国环境政策目标执行力度和地方激励变化的角度来研究省域跨界污染[22-23]。
综上,国外关于环境地方分权与水污染治理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集中于分析环境分权治理模式与地方环境监管行为的变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以及对欧美跨国河流和国家内部河流跨界污染的检验,还有法律和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而中国学者虽然已经认识到跨界河流污染治理的困境,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和理论研究之上。虽然少数学者对中国河流跨界污染的边界效应进行了检验,但主要是从政策实施效果评估视角来研究省级层面的跨界污染问题,缺乏从全国范围内对地级市乃至县跨界水污染的研究。事实上,各县(区)作为各项环境法规、政策、经济规划的直接实施者,对河流水质也具有重大影响。此外,已有研究在检验河流跨界污染时,样本点的边界变量更多采用的是虚拟变量的方法,缺乏对边界距离的测度。
本文希望在如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在内容上,探讨县域层面跨界污染的机制与证据,通过分析2004—2014年中国国控重点断面水质的变化,进一步验证环境分权和行政分割对跨界污染的影响;第二,在边界变量测度上,采用边界距离的连续性数据,即监测站点距离县上、下边界的沿河曲线距离,来替代传统的虚拟变量,缓解估计的内生性问题。
宋德勇等:环境分权与经济竞争背景下河流跨界污染的县域证据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8期2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2.1分权治理与跨界污染
(1)工业企业布局与流域污染。中国长江、黄河、珠江、淮河、松花江、海河、辽河七大流域占国土总面积51%的份额,却承担着全国84%的GDP贡献率。然而,在巨大经济贡献背后,中国河流污染面临着严重的污染问题,仍有近1/3的水质达不到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标准[24]。2016年底中央第二次环境督查结果也发现被督查省份流域污染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很多地方政府凭借着优质港口和腹地滩涂等先天资源优势,通过招商引资争相布局大量化工企业及产业园区,其中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化工产业因其纳税数额巨大则是地方政府争夺的重点。
以长江流域为例,从上游云南到下游上海,化工企业星罗棋布,重庆长寿、安徽东至、江苏扬州等大量化工产业园区相继建成。据统计,整个长江流域布局了化工企业40多万家,且越接近下游地区,密集程度越高,而其产量占到整个中国产量的近50%。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在长江沿岸的化工产业园区中,仅省级以上化工产业园区就有50余个,其中近80%布局在更靠近下游边界地区。如图1,根据长江沿岸化工产业园布局相对位置的核密度图可以看出,产业园区集中布局于[0.6,0.9]區间内,即更倾向于布局于靠近下游边界地区,进一步说明在强烈的工业企业下游布局动机下,县域行政单位间可能存在明显的河流跨界污染特征。
(2)流域管理体制与水污染监测。在流域管理体制方面,根据《水法》和《环保法》规定,中国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体制,从国家级层面来看,主要是由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和水利部及其下设流域管理机构进行管理。但现有法律下,保护和改善流域生态环境的责任又划归给各级地方政府,这就形成了环境地方分权下的“碎片化治理”模式[25],即当前中国流域水污染治理模式仍然是由各级地方政府对流域水污染按行政边界分割后进行治理。在河流污染监测方面,1980年中国成立环境监测总站,1999年环保总局(现生态环境部)在松花江、淮河、长江、黄河及太湖流域的重点断面建设了10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并于2004年开始实行水质自动监测周报制度。2017年,国控监测站点已达149个,中国初步形成了覆盖主要水体的水质自动监测网络。但在监测技术、站点数量、应急预测、数据发布等方面处于探索阶段,相比于巴西、美国和欧洲成熟的监测体系,差距仍然较大。
(3)环境分权和经济竞争背景下的县级政府环境治理行为。一方面,环境分权导致县级政府环境治理的本位主义和污染溢出。从环境地方分权体制看,这种由行政刚性分割而衍生出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导致各县级政府只对上级政府和流域管理机构负责,缺乏同级政府间有效的横向协调机制,在水污染排放、监控、治理等方面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而县级政府作为国家环保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执行的基层行政单位,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权责落实情况,往往直接决定当地的环境质量。这种治理模式与环境权责的不匹配,使得各县级政府无需关注下游地区的水环境质量,只需要对当地的水环境质量负责,进而导致县域水污染治理有更大“以邻为壑”的可能。此外,从环保职能部门组织结构看,当前中国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县级环保职能部门仍然处于两难的境地,不仅受到上级职能部门的垂直领导,还受到同级政府的领导和党委会议精神的指示,许多环境执法行为被迫屈从于水污染企业所带来的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县域环保职能部门在事前环境评估、事中环境监管和事后事故处罚等方面的作用可能会大大折扣。
另一方面,县域经济竞争导致当地政府对污染项目激烈的招商竞争。从经济利益来看,自21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县级政府在享受更大行政自主权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绩效考核的压力。围绕着GDP所开展的县域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化工、冶炼、造纸等高耗水、重污染行业纷纷落户,县域行政分割越严重,围绕着河流的潜在利益冲突和绩效竞争就越激烈。这进一步刺激了各县级政府通过“以邻为壑”行为,通过污染企业的布局向下游地区转移污染物而获得本地发展的经济优势。
(4)“累积效应”与“自净效应”对流域污染的动态影响。各县域地区的“以邻为壑”行为引发了河流污染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各县域地区通过事前的经济计划和产业规划,使得污染企业更容易倾向性地被布局在当地下游地区而非上游地区,并在下游地区实施宽松环境监管与弹性执法,这使得随着不断接近下游边界,相对于河流“自净效应”,污染的“累积效应”居于主导地位,河流污染程度加速递增。同时,县上游边界地区由于相对清洁的经济计划和产业规划,以及相对严格的环境监管和执法,污染“累积效应”减弱,河流“自净效应”相对较强并居于相对主导地位,因此,在跨越县边界之后,污染速度开始放缓乃至出现污染加速下降的趋势。综合以上分析,中国河流存在显著的县域跨界污染问题。
2.2河流污染的外部模型及假设
本文参考Lipscomb and Mobarak[15]的监管者效用成本权衡模型,并通过设定效用函数具体形式,将污染排放量的最优解显性化。假设在[0, 1]的区间上存在一条自西向东流的河流,该河流流经两个同级行政管辖区,点s为这两个行政管辖区的边界,即s∈[0,1]。x为河流[0, s]区间上任意一点,坐落于x处人口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为g(x)。此外,假设在x处,每个人以单价p消费qx单位消费品,所产生的个体效用为u(qx )。考虑到常相对风险规避(CRRA)效用函数在度量消费者个体风险偏好程度、跨期替代以及显性解上的独特优势,故令个体效用函数u(qx )=q1-θx1-θ,0<θ<1,u′<0, u″>0, u<0,与此相对,每个人消费的成本为p·qx。
在该行政管辖区内,人口的集聚和生产会给河流带来不可避免的污染情况,假设污染的排放量与消费一一对应,即qx单位消费对应着qx单位污染排放。考虑到河流自身具有一定的“自净效应”,通过沉淀、稀释、微生物分解和耗氧-复氧等作用,使得既定污染物随着向下游的流动呈现出指数式衰减的特征。根据StreeterPhelps模型,下游ν处感受到上游x排放的污染为qx·e-(ν-x)。与此同时,在“累积效应”作用下,随着河流流向下游,污染物呈现逐步累积的趋势。在河流“自净效应”和污染“累积效应”的交互作用下,[x,s]河段内最终河流污染程度为∫sxqx e-α(v-x) g(v)dv。在其管辖范围[0,s]内,每位监管者将通过对消费效用和对下游污染的福利成本进行权衡,来决定每个位置允许排放的污染限额(消费限额),直到其下游管辖边界s点处,即x∈[0,s]。
在x处的福利水平为:
ω(x,qx )=g(x)q1-θx1-θ-pqx-∫sxqxe-α(v-x)g(v)dv(1)
在管辖区[0,s]内的总福利为:
W(x,qx )=∫s0g(x)q1-θx1-θ-pqx-∫sxqx e-α(v-x)g(v)dvdx(2)
假设W(x,qx )在q*x处达到局部最大值,且η(x)为任意函数,ε→0,存在W(q*x)≥W(q*x+εη),定义Φ(ε)=W(q*x+εη)。
因为W(x,qx )在qx=q*x处取最大值,即max{Φ(ε)}=Φ(0),则根据变分法取一阶条件:Φ′(0)=dΦdε|ε=0=∫s0[g(x)(q*-θx-p)-
∫sxe-α(v-x) g(v)dv]ηdx(3)
从而推出,g(x)(q*-θx-p)-∫sxe-α(v-x)g(v)dv=0,(4)
即:q*-θx-p=∫sxe-α(v-x)g(v)dvg(x)(5)根据上式可进一步求出最优污染排放量q*x与位置x的关系,并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随着河流流向下游边界,污染递增
(limx→sq*xx>0)。
假設2:随着河流流向下游边界,污染递增速度越来越快(limx→s2q*xx2 >0)。假设3:河流边界两侧污染程度,存在结构性变化
(limx↑sκq*sx>limx↓sκ q*sx)。
假设4:河流跨越的行政边界越多,污染排放越大
(∫sk+2skqxdx<∫sk+1skqx dx+∫sk+2sk+1qx dx)。
2.3污染函数情景模拟
在外部性模型的一般化分析过程中,并没有对人口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做特殊设定。考虑到中国城镇化也是人口集聚的过程,县与县之间人口的集聚往往以县城为中心,呈现“多点集聚式”的人口分布特征。因此,较之于均匀分布和三角分布,三角双峰分布的人口密度分布函数可能更加贴近中国人口的实际分布特征,故假定人口密度g(x)服从三角双峰分布。
此外,由于污染函数的特征不仅与人口分布的概率密度有关,还与环境规制程度和县域行政分割有关。因此,这里考虑两个维度下的情景模拟,即维度一:是否存在行政分割;维度二,环境规制程度。便于理论分析,在不考虑地区异质性条件下,本文采用排污限额q来度量规制严苛程度,分别考虑q=∞(无环境规制)、q=80(宽松的环境规制)、q=40(适中的环境规制)和q=10(严苛的环境规制)的情况。综合以上维度,根据q的不同值设立四种情景进行模拟,对比行政分割前后的差异。
从图2可以发现,四张子图的河流污染都存在非常明显的“跨界效应”,即随着河流流向下游边界地区,污染程图2不同环境规制程度下(q=∞,10,40,80)河流污染情况
Fig.2River pollution situation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q=∞,10,40,80)
注:区间[0,1]只囊括了靠近边界s处部分行政区域,0并非上游县的上边界,同理点1处也并非下游县的下边界。度逐步上升且增速加快,而且在边界两侧污染函数存在结构性变化——随着河流跨过边界污染程度有一个小幅下降的趋势。这直接为假设1、2、3的提出提供了支撑,并为本文检验假设4,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
此外,根据图2还可以发现,不论政府的环境规制程度如何,宽松(q=80)、适中(q=40)还是严厉(q=10),乃至是否进行环境规制(q=∞),并没有对河流的跨界污染造成较为显著的影响。换句话说,限额型环境规制手段可能对解决河流污染排放总量的问题具有积极作用,但无法解决河流跨界污染等结构性问题。
3研究设计
3.1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根据河流污染的外部模型及假设,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lnPollutioni,t=β1·(D1)i,t+β2·(D1)2i,t+
β3·(U1)i,t+β4·(U1)2i,t+∑kλk·Xki,t+
∑γyear+∑δquarterly+θt+μi+μi·θt+εi,t(6)
其中,lnPollution∈{lnCOD, lnNH3-N, lnDO, lnpHabs},U1、D1分别表示监测站距离所在县级行政单位上游和下游的沿河曲线距离,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国控水质监测站并非完全位于边界分界线上,处于省界处的监测站距离边界线仍有一定的距离,因而仅仅使用是否位于省界上的二值模型(1表示在省界,0表示其他情况),无法更加精准地量化跨界污染的问题,也无法测度一个省内部的跨界污染。因而,采用监测站同县边界的距离作为边界变量的测度指标是一个更佳地选择。
X是可能影响水质和县域跨界污染的控制变量, γyear代表影响河流水质变化的年度效应,δquarterly代表四季轮换所带来的季度效应,θt控制时间的固定效应,以便根据监测站与县界距离的变化来识别边界变量的估计系数(β1,β2,β3,β4),μi·θt则代表了每个监测站特有的趋势,它考虑了经济活动、地理位置和人口等因素的影响。详细变量的定义及数据来源见表1。
3.2样本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衡量河流水质的衡量指标(COD、NH3-N、DO、pH),其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国控水质监测站点的周数据,研究区间为2004—2014年,共计624个周。考虑到研究问题的特点,主要选取四级和三级以上河流的水质监测站点,并对周报数据的一些错处进行了校正。另外,相比于废水排放量等总量指标,国控监测站的断面数据为末端监测的流量数据,不仅将传统工业对河流水质的影响考虑了进来,而且还考虑了农业、服务业等部门和居民生活对河流的影响,河流的自净能力以及其他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也充分体现在水质衡量指标之中。因此,该数据类型能够更好地衡量河流水质的具体差异,并具有更大的样本选择空间。此外,国控监测站数据为实时监测数据,并直接由环保部(现生态环境部)负责,因而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的可能性更小,而庞大的数据量也导致人工干预成本巨大。因此,数据来源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数据基本情况及各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4河流污染“跨界效应”检验
4.1单个站点下的“跨界效应”检验
表3列出了以COD和NH3-N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其中,第(1)和(3)列代表水质指标COD和
变量性质变量名称变量含义数据来源被解释变量lnPollution水质指标:COD(mg/L)、NH3-N(mg/L)、DO(mg/L)、pHabs的自然对数值,其中pHabs=|pH-7|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核心解释变量D1、(D1)2边界变量:县下游边界到监测站沿河曲线距离及平方项的向量值(km),即D1=-|D1|根据ArcGis 10.2软件的测算得到U1、(U1)2边界变量:县上游边界到监测站沿河曲线距离及平方项的向量值(km),即U1=|U1|根据ArcGis 10.2软件的测算得到控制变量lnPop县域社会特征:常住人口(万人)的自然对数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县统计公报、各级政府统计年鉴等lnGDP1县域经济特征:第一产业增加值(万元)的自然对数lnGDP2县域经济特征:第二产业增加值(万元)的自然对数lnGDP3县域经济特征:第三产业增加值(万元)的自然对数lnArea县域自然特征:土地面积(km2)的自然对数lnRain县域自然特征:年降水量(mm)的自然对数lnTem县域自然特征:年均气温(℃)的自然对数lnLength县域自然特征:河长(km)的自然对数NH3-N对边界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和(4)列则添加了县域社会、经济和自然特征等控制变量,第(3)和(6)列则进一步考虑了年度效应和季度效应的影响。
在估计式(3)和(6)中可以发现,对于D1的估计系数,随着河流每接近县下游边界1 km(D1上升),COD上升近0.012%、NH3-N上升近0.013%,与假设1随着河流流向县下游边界地区污染递增相一致(见图2)。此外,(D1)2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河流越来越接近下游边界,COD和NH3-N的污染程度加速递增,与假设2随着河流流向下游边界地区污染递增速度越来越快相一致(见图2)。
此外,本文通过比较D1和U1的估计系数,来检验假设3河流边界两侧的污染程度存在着结构性的变化。由于观测站样本限制,数据不提供污染测量边界,因此无法直接进行回归不连续性检验,但是通过对D1和U1的系数进行推断,间接地度量污染函数在边界左边和右边的斜率。U1的COD和NH3-N估计系数为负,可以间接地说明跨越县域边界后,污染程度随着与该边界的距离增加(U1越来越大)而降低,即在边界左侧污染函数斜率为正、边界右侧污染函数斜率为负,假设3成立。此外,表3中(D1)2和(U1)2的系数均为正,也在假设3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随着河流不断接近下游边界,污染增速不断增加,而跨界边界以后,污染开始减缓,并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
此外,根据表3的估计结果,县域社会特征、经济特征和自然特征的指标系数也与预期基本一致。尤其是,表3
4.2环境分权与“跨界效应”检验
考虑到单个观测站无法检验假设4,即在当前中国环境地方分权体制下,各县域的碎片化治理模式是否会使得河流跨界污染程度随河流穿越边界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本文通过引入变量Crossings来衡量两个相邻观测站间同一条河流穿越的边境数量,将它作为环境地方分权程度的间接衡量指标,并以ΔPollutioni,t来衡量同一条河流上相邻监测站的水质差异,其中,ΔPollutioni,t=ln(Pollution2i,t)-ln(Pollution1i,t),Pollution1i,t和Pollution2i,t分別代表上游和下游监测站水质。此外,本文还引入交互项Crossings·D1探讨行政分割与边界变量间是否存在交互效应。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Pollutioni,t=β1·Crossingsi+β2·(D1)i,t+
β3·(U2)i,t+β4·(U1)i,t+
β5·(D2)i,t+β6·(Crossings·D1)i+
∑kλk·Xki,t+∑δmonth+∑γyear+
θt+μi+μi·θt+εi,t(7)
在该模型中,解释变量Crossings、D1、U2涉及到站组(上下游两个相邻站点)在地方分权体制下跨界污染的度量问题,为核心解释变量。根据假设4,预期Crossings的估计系数β1>0,而根据假设1和本文第四部分可知,随着河流越接近下游边界(D1越来越大),污染水平Pollution1i,t越来越高,进而导致ΔPollutioni,t越来越小,预期β2<0。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差异,此处D1的估计系数与4.1节相反。同理根据假设3,边界两侧存在污染存在结构性变化可知β2≠β3,或者,更理想的预期是β3<0。
控制变量包括:相邻两个监测站所在县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特征衡量指标,以及河流长度。根据公式(7)的设定,本部分分别以水质监测指标COD、NH3-N为被解释变量,做了对应的估计和检验,并在跨界数量之外,纳入核心距离变量D1、U1,以及Crossings·D1、控制变量、季度效应和年度效应,得出ΔCOD和ΔNH3-N的估计式。
根据表4回归结果,各估计式中Crossings的系数在1%水平下均显著为正,与预期一致。在(3)和(6)中,随着河流穿越县域边界数量每增加1条,下游COD比上游高出0.016 55%,而NH3-N高出0.025 26%,这表明在环境地方分权下,县域跨界污染问题较为明显,两者具有一种正相关关系,与假设4一致。D1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U1估计系数符号为负,与前预期的β2和β3符号一致,与假设1和假设3预测一致,也印证了县边界两侧污染存在
5稳健性和异质性分析
通过对假设1~4的证明,可以发现在地方分权治理体制下,县域之间存在明显的跨界效应,但本文还应该谨慎地考虑其他可能对结论产生影响的问题。比如,是否存在少数国控监测站距离排污口较近,导致这些站点的断面水质数据异常;约束性指标和非约束性指标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估计结论;地区异质性是否会带来的“自净效应”和“累积效应”的变化,进而导致跨界污染差异等。
5.1稳健性分析
考虑到部分监测站可能由于距离排污口较近或受重大水污染事件的影响,水质数据可能存在异常,因此,本文对被解释变量lnPollutioni,t和ΔPollutioni,t分别剔除1%、5%和10%端点值,进行更为“纯净”的估计。另外,中国“十一五”计划将COD和NH3-N作为地方政府考核的约束性指标,而DO和pH仅为非约束性指标,这种度量指标的不同可能影响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因此,本文以DO和pH替代COD和NH3-N来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
其中,溶解氧DO是衡量河流自净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与COD、NH3-N相反,其含量越低,表明河流水质条件越差,故公式(6)估计系数预期符号也应与COD和
NH3-N相反(β1<0,β3>0)。此外,pH作为酸碱度的衡量指标,其数值越大或者越小并不意味着水质的好坏。换句话说,pH值作为衡量河流酸碱度的指标,在测度河流污染情况时,更应该考虑其对于中性水的偏离值,即pHabs=|pH-7|,pHabs越大,河流污染情越重,而这也是很多学者所忽视的。
根据表5的估计结果,D1 、U1以及平方项的估计系数符号与假设相符,进一步证明了随着河流流向下游地区,污染程度逐步加深且污染增速不断加快,边界两侧污染函数存在着结构性变化,中国河流存在着显著的跨界污染,而且这些结论也是稳健的。
5.2地区异质性检验
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在经济结构、发展水平以及要素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污染“累积效应”和河流“自净效应”的大小及其相互作用可能存在不同,最终导致地区河流的跨界污染存在异质性差异。因此,本文按照国控监测站所在地区进行分类,分别检验东、中、西部的跨界污染问题,在控制了年度效应和季度效应后,实证结果见表6。综合来看,表6中COD和NH3-N的估计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下与前面结论基本一致,随着河流流向下游地区,在较强的“累积效应”和相对偏弱的“自净效应”作用下,东、中、西部污染程度不断加深且增速加快,但跨越边界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污染函数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由于中西部相对偏弱的产业密集度和较好的生态环境,中西部县域上游地区“自净效应”主导作用强于东部地区,随着跨越边界,污染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U1<0,(U1)2>0)。而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园区和人口集聚更密集,使得东部河流“自净效应”较弱,进而使得河流在跨越边界后污染程度继续上升但增速放缓(U1>0,(U1)2<0)。因此,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污染函数在边界两侧的结构性差异更大,但整体而言东、中、西部均表现出县域跨界污染的问题,与假设一致。
6结论与启示
6.1结论
本文以环境地方分权和县域经济竞争为背景,通过国内外文献的梳理、相关制度框架和理论的介绍,纳入河流的“自净效应”和污染的“累积效应”,并建立河流污染的外部模型,提出了4个重要假设来检验和进一步量化河流的跨界污染问题。从县域视角,以2004—2014年七大流域国控监测断面周数据为基础,对单个站点的边界距离与水质指标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纳入监测站所在县域的社会特征、经济特征和自然特征等控制变量,对假设1~3进行检验,并将监测站之間穿越的边界数量作为环境地方分权程度的重要指标,来检验假设4。
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河流县域跨界污染明显,河流每接近下游县边界1 km,COD上升近0.012%、NH3-N上升近0.013%,表明随着河流流向下游边界,污染程度呈现出递增的态势。②与下游县边界的距离影响着河流“跨界污染”的趋势,在污染“累积效应”作用下,随着河流越来越接近下游边界,COD和NH3-N的污染程度加速递增。③由于行政边界两侧河流“自净效应”和污染“累积效应”的差异,河流在县边界两侧存在着结构性的变化,在跨越县边界后,在县上界地区严格的环境监管和相对较强的河流“自净效应”作用下,中西部地区污染函数在县域上游地区会呈现加速下降的态势,而东部地区则会呈现污染增速明显放缓的趋势,均表现出县边界两侧河流污染的结构性差异。④在集体行动的困境下,河流跨越的行政边界越多,所面临的沟通与协调难度就越大,潜在的利益冲表5lnDO、lnpHabs回归估计结果
突下“以邻为壑”动机就更强,因而污染排放就更加严重。
6.2启示
本文建议:①加快建立条块结合、权责明确、权威高效的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针对目前国控监测站数量仍然较少的情况,在重点流域和重点河段增加监测站点,并在现有4类衡量指标上增加公布其他衡量指标。②加快构建省、市、县、镇四级“河长制”的水环境行政治理模式,科学构建环境问责、政策协同和有效执法等方面的具体实施办法,提升治理模式的长效性、社会性和可推广性。③进一步完善流域政府横向协调机制。结合科层型、市场型、府际型协调机制各自的优势,解决好流域治理机构与行政机构、行政机构与经济主体等各方内在的利益冲突。④进一步完善官员离任环境审计和绿色发展激励办法,制定更加科学的地方考核和官员晋升机制,鼓励区域环境联合执法与联合治理机制,建立健全环境联防联控体系。
(编辑:刘照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WOLF A T, KRAMER A, CARIUS A, et al. Managing water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J]. State of the world 2005:redefining global security,2005:80-95.
[3]OATES W E. 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9, 37(3): 1120-1149.
[4]OATES W E. A reconsi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federalism[M].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2001.
[5]JOHNSSON R M F, KEMPER K.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analysis of river basin management: the Jaguaribe river basin, Ceara, Brazil[R].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2005.
[6]SIGNMAN H.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water pollution levels and variation[J]. Land economics, 2014, 90(1): 114-130.
[7]胡若隱. 地方行政分割与流域水污染治理悖论分析[J]. 环境保护, 2006 (3B): 65-68. [HU Ruoyin. Analyse of the absurdity of the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and the river basin water pollution mending[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6 (3B): 65-68.]
[8]BURGESS R, HANSEN M, OLKEN B A, et 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forestation in the tropic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127(4): 1707-1754.
[9]BRANNSTROM C. Decentralising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n Brazil[J].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4, 16(1): 214-234.
[10]KONISKY D M, WOODS N D. Environmental policy, federalism, and the Obama presidency[J]. Publiu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2016, 46(3): 366-391.
[11]SIGNMAN H.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and water quality in rivers: do countries free ri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4):1152-1159.
[12]GRAY W B, SHADBEGIAN R J. ‘Optimalpollution abatement:whose benefits matter, and how much?[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4, 47(3): 510-534.
[13]KONISKY D M, WOODS N D. Environmental free riding in state water pollution enforcement[J]. State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2012, 12(3): 227-251.
[14]SIGNMAN H. Transboundary spillovers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5, 50(1): 82-101.
[15]LIPSCOMB M, MOBARAK A M.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lution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the redrawing of county borders in Brazil[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7, 84(1): 464-502.
[16]BERNAUER T, KUHN P M. Is there an environmental version of the Kantian peace? insights from water pollution in Europe[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 16(1): 77-102.
[17]HELLAND E, WHITFORD A B. Pollution incidence and political jurisdiction: evidence from the TRI[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3, 46(3): 403-424.
[18]TYLER Z.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in China:an analysis of the failure of the legal framework to protect downstream jurisdictions[J].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2005, 19(2): 572-613.
[19]沈大军, 王浩, 蒋云钟. 流域管理机构:国际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的建议[J]. 自然资源学报, 2004, 19(1):86-95. [SHEN Dajun, WANG Hao, JIANG Yunzhong. Riverbasi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suggestions on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4, 19(1):86-95.]
[20]施祖麟, 毕亮亮. 我国跨行政区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的研究——以江浙边界水污染治理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 17(3):3-9. [SHI Zulin, BI Liangliang. The study on transjurisdictional water pollution management and cooperation pattern of river basin in China: a case study water pollution managemen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Jiangsu Province and Zhejiang Provinc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7, 17(3):3-9.]
[21]李胜,陈晓春. 基于府际博弈的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困境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12):104-109. [LI Sheng, CHEN Xiaochun. Governance dilemma of transdistrict water pollution: an intergovernmental game perspectiv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12):104-109.]
[22]李静, 杨娜, 陶璐. 跨境河流污染的“边界效应”与减排政策效果研究——基于重点断面水质监测周数据的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3):31-43. [LI Jing, YANG Na, TAO Lu. Study on the ‘boundary emissions mitigation policy effect of transboundary river pollution and impact: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key monitoring sections weekly data[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5(3):31-43.]
[23]李静, 陶璐, 杨娜. 淮河流域污染的“行政边界效应”与新环境政策影响[J].中国软科学,2015(6):91-102. [LI Jing, TAO Lu, YANG Na.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effect of the Huaihe River Basin pollu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effect[J]. China soft science,2015(6):91-102.]
[24]中国环境保护部. 201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R]. 2017-06-05: 5-6. [Chines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6 China environmental status bulletin[R]. 2017-06-05: 5-6.]
[25]王圣君. 政府治理跨界水污染模式研究[D]. 上海:東华大学, 2015:38-41. [WANG Shengjun. The model research of government in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D].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2015: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