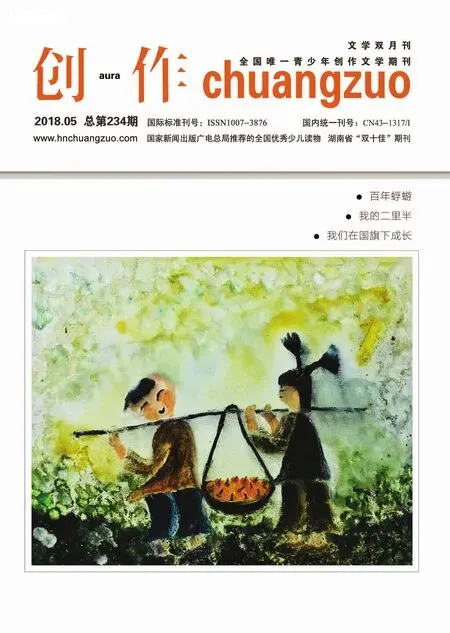我的二里半
作者:周子曦
学校: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
题记:我怕来不及,我要记住你。——谨以此文,献给伴随我成长的二里半与活跃在二里半记忆里的你们。
二里半于我而言,就像坐标轴上的中点,一端是我的家,一端是外婆的家。
从家顺着曲曲折折的小路到二里半——妈妈上班的地方,再横穿麓山路到老校门口,一直上坡上坡,快到尽头的地方,便是外婆家了。我十三岁,在二里半上走走停停,兜兜转转也有十三个年头了。
二里半地名的由来,大抵就是从 湾镇到师大老校门,距离刚刚好二里半。是的,地名就是如此顺手拈来,随意而又任性。
我熟悉的二里半,是从茶山路左转出来的雅韵琴行和莫家毛笔店开始的。
第一次去“莫家毛笔店”是跟着老妈带着我的胎毛去做胎毛笔,老板漠漠的,看着我妈宝贝似地捧着的胎毛一脸嫌弃说怎么这么少,我妈说这娃生下来毛发就特别稀少。莫老板说可以做,但不能保证做得满意,结果,我妈觉得老板态度倨傲,扯着我并带着我那束屈指可数的胎毛施施然走了。
我妈那时始料未及的是,莫老板的拒绝在多年以后却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全。十二年后我弟弟出生,他随我,出生时头发也很少,于是我妈就把我和他的胎毛合二为一,做了一支胎毛笔,从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后来看了一些资料,莫老板是有家传的,他是“莫家毛笔店”的第四代传人,从1984年父母带着他从老家益阳到二里半开店安家,至今已经三十四年了。我后来学书法虽然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我却经常借着买笔的名义去逛莫家毛笔店,尤其享受那满屋墨香的感觉,好像那儿的时间也要慢些。
和莫家毛笔店相邻的雅韵琴行常常架子鼓狂响连天,我被吸引也脑子发热想学一门乐器。我选择了吉他,主要因为教吉他的老师太帅,他边弹边唱的样子,让我想抱着吉他当一名流浪歌手浪迹天涯。
过了这两家店,爬上麓山路的一段陡坡,坡的左边挨着生命科学院的是一家卖日杂用品的百货店,一家复印店和沙县小吃。百货店很大,东西塞得满满当当,乱七八糟,看上去毫无头绪可言,但老板娘却总能第一时间麻利地翻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从15元一双的白球鞋到800元一只的泰迪狗崽,当真是无奇不有。沙县小吃很亲民,老板和老板娘态度尤其好,老板亲手包的馅儿满是温暖的味道,我最爱是冬天在这吃一碗热乎乎的馄饨,瞬间满血复活。
过了生命科学院1号楼,左拐上坡一点点便是师大菜市场,从早到晚,这是二里半人气最火爆的地方,卖菜的、买菜的川流不息,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菜市场是我外公外婆的主战场,每天二老起个大早,带着买菜的拖车,敏捷地穿过鱼龙混杂的菜摊子,为一家人采购全天所需的生鲜食材。当然,买回来的不仅是一车新鲜水灵的菜,更有一箩刚刚出炉的八卦,比如“甲教授家的儿子离婚了”“乙教授家的大龄女儿嫁了个老外,生了个混血儿”“前一栋的老张头住院了”等等诸如此类,总让热气腾腾的饭桌前充满着聊不完的话题。
菜市场进门有一溜小店,卖猪脚的、卖糕点的、卖炒粉的……岳阳烧烤的茄子平摊来满是香葱、小米椒、蒜蓉,流油的茄肉挑衅着我的味蕾。外婆最喜欢给我买猫耳朵、芝麻饼、甜蛋糕,货架上的小风扇总是挂着红飘带摇啊摇,每次路过,有点强迫症地想把它扯下来。
菜场出来下坡是“咏红水果店”,生意超级好,365天不打烊。老板娘精明能干,说话麻溜,动作迅速。上小学的时候,一放学到办公室找不到我妈就找老板娘蹭电话打,老板娘和我妈熟,宠我宠得厉害,免费的橘子香蕉苹果没少吃她的,一路过就顺走的棒棒糖和口香糖,也许是我数颗虫牙的祖宗。
咏红水果店旁的小小的店面换了很多个主,最开始是“七杯茶”,酷暑时倚在柜台上东问问西指指,老板不厌其烦地回答着。每当榨好的果汁随着长长的胶带被包好的那一瞬间,我心里便迸发出无尽的欢喜。后来是“烧烤串串”,串串并不卖串串,而是卖麻辣烫,记忆中没有比那更好吃的红薯粉了。挤在小小的柜台上吸溜吸溜地满身热汗,回家再打着饱嗝被外婆训话,嘴里不合时宜地喷出热腾腾的香气。

再往前走一些,便是“梦幻摄影社”,从我两岁到十三岁的证件照无一不是在那儿拍的,总是正襟危坐,偷眼瞄着两旁明晃晃的一片,忍不住闭了闭眼,留下史上最丑的笑颜。
梦幻摄影社旁“三棵树饭馆”以门外的三棵巨大香樟得名,倒是不曾进去过,只傻傻地在门口与三棵樟树合了个影,后来听闻味道极好,想去品尝,却已是无缘了。
再往前走下几阶楼梯的旮旯窝里藏着个校园理发店,老板总是着一身黑色显得杀气腾腾的,挂着大金链像江湖上某个似曾相识的黑社会老大。剪刀却秀气得很,剪掉的刘海总是只有一丢丢,然后继续被老师责令整改。第二次嬉皮笑脸说剪短了变成西瓜皮就不好看了。
二里半靠菜市场旁的那一溜复印店是新化人的天下,号称长沙最便宜的打印店聚集地,五分钱一张的复印价格让好多土豪都惊愕掉下巴。“师生打印社”老板人憨憨的,从小到大的作业都是他一手帮我打印的。傻乎乎地忘带钱,他也只是爽朗地摆摆手。
过个马路。
“慢慢的奶茶屋”店面超小,名气却很大,但我从未进去过,总是遥遥张望着,富有趣味的装修风格和鬈毛大叔,在我的记忆中充满神秘感。
“杭州小笼包”开了一年多了,我爱吃他们的海带汤,咂着嘴看着老板揉着面粉,好不惬意。
“功夫小吃”的豆腐尤为美味,咬下去满口都是汤汁儿,浓郁而回味无穷。
继续往前走,“新精华眼镜店”是最不能忽视的存在,装修超有特色,店面前还整了块花圃,在寸土寸金的二里半,这已经是奢侈中的奢华了。老板很潮,卖的眼镜也很有范儿,我从小到大的游泳镜墨镜都是在那买的,最特别的是,店里面整了一个大鱼缸,色彩艳丽的热带鱼游来游去,五彩斑斓的活珊瑚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煞是好看。老板究竟通过什么途径将这些活珊瑚弄到二里半,这是我至今未想明白的问题。当然,后来眼镜店老板易主,“新精华”变成了“鑫精华”,我也再没进去过,此为后话。
“新精华”旁边的“石林家菜馆”生意也不错,不过我不爱吃,感觉厨师味精当盐撒,口味太重。同排的五金日杂店也开了有年头了,电灯电线电扇烤火炉拖把铁钉啥都有,为了完成从小到大奇葩的手工作业,我没少厚着脸皮到那讨电线钉子之类的小东西,老板每次笑着不收我的钱。
在一众烟火气十足的小店中,“芊蕙花艺”就显得特别有情调了。心情好的时候,我会不时在那买几朵玫瑰、雏菊或康乃馨,假装自己也是内心丰盈有情调的淑女。
老校门口常年驻守着庞大的摩的群,基本都混了个面熟,哪个车技如何,哪个爱占便宜都心知肚明。
作为一名资深烤饼控,二里半周边的霉干菜扣肉饼,土家酱香饼,印度飞饼,老上海烤饼以及偶尔出现的锅馕地摊,还有只要往门口一站老板就知道我要吃两串里脊肉加番茄酱的“粮全其美”手抓饼,所有口味都让我尝了个够。但我最钟情的还是老校门左侧一家只有三四个平方的小店——北方烤饼,吃甜的还是咸的,我总是纠结于此。而老妈则常常穿梭于二里半的一众美味粉店中,为吃扁粉还是吃圆粉左右为难。
“向博士包子店”前的排队长龙也是二里半的一道特色风景线,只是我常常排到一半就没有耐心地去别处觅食了。
而二里半的黄焖鸡米饭、醉骨气、熊猫餐厅,我总是远远眺望着想去试试,现在常常懊恼十三年来没有为它们留步。
再往前走是邮局,妈妈常带我来寄信,小时候我连柜台都够不上,全靠妈妈抱着瞅瞅邮局的阿姨,后来下巴可以搁到柜台上了,好奇地摆弄着长长扭扭的栓笔绳子。现在,我已经和妈妈一样高了。阿姨能干会推销,哄得我妈把1992年到2016年所有的猴年套票都买了,毕竟,咱家有两只猴啊。
邮局旁的小报刊亭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意林·小淑女”有没有到货啦,老板。来了,来了。然后老板笑嘻嘻地给我拿,又来礼品了,项链,哈哈哈谢谢老板。常常我都会被粉红的少女心弄得雀跃不已。
在二里半温情的目光下,咿呀学语的蒙童跌跌撞撞地往幼儿园疯跑;内向的小女孩躲在妈妈的雨伞下哼哼唧唧发着起床气;背着吉他的少女在生命科学院前急吼吼地去吃麻辣烫……
故事,到这里,不得不画上句号了。
2018年3月,随着挖掘机轰鸣声中的师大邮局轰然倒地,二里半周边的整体拆迁正式告一段落。
图纸中重建的二里半是美丽的、宏伟的、整洁的、干净的,只是,已然不是陪伴我成长的二里半了,那些活色生香的画面,生机勃勃的场景,记忆深刻的人、事、物,终究会遗失在二里半重建的钢筋水泥里,慢慢地,变得含混不清了。
然,
最亲不过二里半。
点评:读完此文,眼前一亮,感叹作者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文学创作中许多的技巧,在这里能够很好地呈现。写人、描景、叙事、记物,几乎是水到渠成,让人从中读出亲切,读出脉脉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