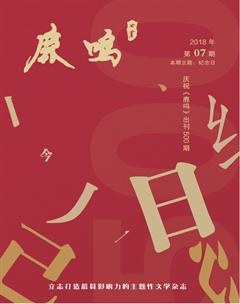我与《鹿鸣》二三事
我搬离赵家营的时候,春天已经来了,漫天的风沙随时准备席卷这座城市。我在那个不到十平米的小出租屋住了整整一个冬天,离开的时候,我想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甚至不会去想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一切,美好或者不美好,都已经与我无关。
但是在一个夜晚,我还是骑着自行车来到这个熟悉的小院,出租屋已经转租他人,屋门紧锁,茫然四顾,今夕何夕。蹲在院门口的巷子里,抽完一根烟,我转身离开了。小巷依然人声鼎沸,村子里窄窄的街道依然人来人往。
在那个晚上,我打开了电脑,写下了一组6000多字的散文—《赵家营的冬天》,那个出租屋与那个小院,以及那个曾经被我鄙夷、让我自卑的城中村,再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些早出晚归的邻居,那些遁入小巷深处的性工作者,那个持刀捂着鲜血淋漓的胸口的青年……
那一年,是我来包头的第三年,搬出赵家营的第二年。
文章写出来后,它们安静地躺在我的电脑里,直到有一天,我觉得应该给它们找一个去处。当时,我在柏青老师主办的西部作家论坛做版主,在此之前,我因为偶然的机会参加了第二届河北散文大赛,而且鬼使神差地获了三等奖,前去领奖时认识了很多已经在文坛非常有名气的作家,这也有了我进入西部作家论坛当版主的契机。网络只是自我安慰的平台,我知道,我还没有真正走上文学这条道路。
因此,当《赵家营的冬天》一文在我的电脑里静静地躺了几个月之后,我鼓足勇气准备投稿,国字号刊物不敢想,省刊也没有勇气,有一天在同事的办公桌上,我偶尔看到了《鹿鸣》杂志,才知道原来包头就有一份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那时候我在想,什么时候能在这本杂志上出现自己的名字,那该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
此时,与我同时获得河北散文大赛等级奖的很多作家都在《鹿鸣》杂志刊发过稿件,于是我将写出的文章交给这些老师看,并让他们提意见,然而最终也没有征来多少意见,最终也未经修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这篇文章被投到了《鹿鸣》杂志的邮箱里。
2014年4月的一个周末,突然接到杂志社马端刚老师的电话,说我的文章发表在《鹿鸣》杂志第4期,还没到吃晚饭的时间,他约我去赵家营西门对面的一个饭馆见面。这让我惊讶不已,没想到自己的文章能够在正规文学刊物发表,打发掉正在逛街的女友,我立马蹬着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马老师指定的地方。
因为之前从未谋面,我并不知道马老师模样,一进饭馆,一个身高马大的男人朝我走来,并带笑问我:你就是李亚强吧,我是马端刚,你看,对面就是你写的赵家营,熟悉吧。顺着他的手指看去,透过饭店的橱窗,赵家营村已经锈迹斑斑的大門就在眼前,那些烟火气息还在升腾。回过头来,我感觉到有些局促,虽然在报社工作,但是与陌生人接触还是有些不自觉的难为情,我尴尬地笑笑,跟着他走到饭馆一楼的一个角落里,光线暗淡,桌子上摆放着几瓶已开启和未开启的啤酒,走到近处才看见,凳子上还坐着一个人。“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青年作家,写小说的王鹏飞。”我跟王鹏飞礼貌性握了握手,然后接过了他递过来的一瓶啤酒。
很显然,他们从中午喝到了晚上,在我的意识里,这就是作家的正常状态,兴之所至,勿论时辰,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还未吃饭,几瓶啤酒已经下肚,如我所想,马老师开始点评我的作品:赵家营是什么地方,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你的文章只是浅尝辄止,没有写出活灵活现的人物,但是本地作者我们一定要支持。他说,好的题材是一次性的,写好写坏就一次,你再不可能翻过去重复自己,所以一定要珍惜自己手中的题材。
那几句话,点到了我的要害。在此之前,我在黑暗中写下了数万字的习作,但都羞于示人。例外的是,不知何时向《青年作家》杂志投过一次稿件,发表半年后才得知稿件被刊用,等我知道的时候,也已经在《鹿鸣》刊发文章之后。
多么难得啊,初次见面就能够直指问题所在,没有丝毫隐瞒和忌讳,让我在羞愧的同时也对这本杂志有了全新的认识。
扶持本地作者,这不是马老师口上说的,实际中确实是这么做的。那时候在网上认识了与我同龄的包头作者端木赐,他在北京的一家基层卫生院工作,但是我们经常能够在网络上有所交流,在我之前,他已经在《鹿鸣》杂志露过脸,我也向他请教,将我的文章发去让他批评,后来我俩的文章一同出现在《鹿鸣》杂志2014年第6期,再后来我们的文章多次一同在这本杂志上共同出现。
也是那几年,包头出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作者,包括万巧娇、王江江、李亚男、王阳、王维、于学涛等,不管是写散文、小说还是诗歌,我们类似的是,都从《鹿鸣》杂志起步。端木赐在北京工作,有时回包头家乡,我们也要在外面小坐一下,很多时候都在马老师家楼下的小饭馆。后来,端木赐逐渐走向全国,成为九零后散文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也在《青年文学》《天涯》《散文》《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重要纯文学刊物发表稿件。我的作品也不断向外投去,在《美文》《广西文学》《草原》等杂志刊发作品。王江江也在《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刊发稿件,李亚男的剧本则直接发到了《中国作家》杂志,后来起步的王维、于学涛,恰逢《鹿鸣》杂志改版,在第一期“鹿鸣册页”中惊艳亮相,包头师范学院教授、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伟配发评论,在当时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
可以说,《鹿鸣》杂志在扶持本地作者、帮助年轻作者成长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给了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往外走出去的勇气和信心,也见证了我们这些年轻作者的一路成长。
2
老旧的房屋,灯光昏暗,屋外的大街上,行人车辆川流不息。我时常会去昆都仑河边走走,像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坐在波光粼粼的河边抽烟,眺望远方,包钢厂区的浓烟顺着风的方向,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但是更多的时间是打发不掉的,在钢32小区的出租屋内,总有些灵动的词语闪烁在晨光里,闪烁在夕照里,闪烁在屋外经年的白杨树影里,闪烁在烟雾缭绕的日子里。
在阳光慵懒的午后,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在从噩梦中惊醒的午夜,那些难抒的胸臆,如同一块巨石压在心头。于是,我开始了最为原始的写作,一遍遍把自己进行解剖,那些过去的岁月如同倒放的电影,一幕幕掠过心头,落在电脑的键盘上。
多么好的年华,一支香烟,一台电脑,一个无所事事的我,在电脑上码出一篇篇文章来。也就是那几年,还未成家,有大把大把时间等着我去浪费,创作状态也是最好的时候,脑中有了轮廓,立马构思写作,两三个小时之内,一篇数千字的文章写成。在钢32的出租屋内,我陆续写出了《畢业映像》《酒瓶里的父亲》《坍塌》等散文作品,无一例外全部发表在《鹿鸣》杂志,改版后的《鹿鸣》杂志也表现出了对文学作品的最大尊重,直接体现在稿费标准上,一篇文章发表相当于一个月的柴米油盐钱。
我还记得第一篇文章在《鹿鸣》杂志发表后,领取到1200多元的稿费,兴奋地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就叫上朋友胡吃海喝了一顿,剩余的钱都存下当作生活费,要知道,那时候我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000多元。那几年,我刚来包头不久,生活还十分窘迫,每月工资除了支付房租水电费和开销,往往所剩无几,剩余的还要贴补家里。稿费的诱惑,也是我不断鞭策自己、不断进行创作的一个现实原因。
也正是因为稿酬标准的提高,也因为《鹿鸣》杂志原有的影响,一本地市级刊物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迅速吸引了大量外地作家尤其是一线实力作家的青睐,包括庞培、余秀华、杨献平、春树、王族、谢荣盛、凌鹰等作家也纷纷投稿,杂志办刊水平不断提高,在国内文坛的知名度也不断提升,为《鹿鸣》杂志主办各类活动提供了坚强的作家资源和基础。
2015年6月,《鹿鸣》杂志与石拐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合作,成功举办“魅力喜桂图,祈福五当召”文学笔会,邀请到《中华文学选刊》《山东文学》《飞天》《中国诗歌》《延安文学》《山西文学》等期刊的主编、编辑十余人、本地作家数十位参加笔会,这在包头历史上也是极少的。
我们当然也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在几天的行程里,我们与这些期刊主编、编辑同吃同住同游,在五当召,在达茂旗草原,在固阳秦长城,逐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本地作家走出包头搭建了良好的平台。笔会结束后,2015年9月,《鹿鸣》杂志推出了喜桂图笔会专号,专门刊登了这次笔会的采风作品,这在《鹿鸣》杂志的历史上想必也是少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当然,笔会的影响并未随着笔会的结束而结束,部分本地作家也通过这次笔会的契机和桥梁,大量在外地刊物刊发稿件。
也是在那次活动上,我认识了当时的《西南军事文学》编辑、后来转职《星星诗刊》的著名作家杨献平,所以有了后来很愉快的交往,而他也在此次活动后,对包头作家有了额外的关照。
这是大规模的集中采风活动,小规模的活动在不断进行。
2014年左右,全国各地文学刊物推出微信公众号,《鹿鸣》杂志也不例外,而且先于很多文学刊物创办微信公众号,进一步将《鹿鸣》的影响力向外扩散。2015年底,以微信公众号为基础,《鹿鸣》杂志推出了“2015年度最佳作品评选”,一时吸引众多作家参与,微信公众号人气爆棚,随后杂志社趁热打铁,立足微信平台,推出“鹿鸣星座”这一品牌栏目,虽然不同纸刊也没有稿费,但是也引起了很多作家的极大兴趣,微信公众号运营越来越有特色和亮点。
作为立志打造北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主题性刊物的一本杂志,《鹿鸣》从改版后一直坚持主题为主的思路,从平常的过年、高考、成长、毕业等主题,到钢铁、草原、安居、土豆等本土特色主题,再到网事、微时代、电影等新时代主题,命题作文的方式杜绝了一稿多投,保证了作品的独家性和杂志的独特性。近年来,全国各地杂志开始推出各类包括90作家、女作家专号,2017年开始,《鹿鸣》杂志也在主题性之外,以专号的形式大规模展示某一群体或某一类别的作品,例如2017年第2期的散文专号、第4期的本土作家专号、第6期的80、90专号、第8期的女作家专号、第10期的小说专号和第12期的诗歌专号,以集体亮相的方式强化杂志的影响力,从我认识的很多外地作家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这些专号的推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进一步扩大了《鹿鸣》的影响力。
而在本地,在《鹿鸣》杂志的影响下,很多在民间默默写作的写作者都被挖掘出来,不断在杂志上亮相,也不断走向全国,包头作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文化的发展,这些年,很多地方的纯文学刊物要么被撤销刊号、要么直接关停,《鹿鸣》杂志作为包头文学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一面旗子,始终屹立在祖国北疆,成为一道独特而又亮丽的风景线,可以说,《鹿鸣》杂志为这个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直到现在,依然有不少外地作家告诉我,他们都是通过《鹿鸣》杂志才知道有包头这样一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