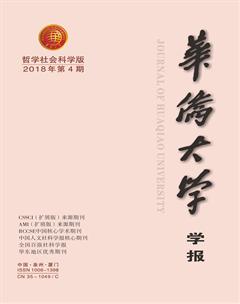马克思与阿马蒂亚·森正义思想的耦合与分野
摘要:
马克思与阿马蒂亚·森的正义思想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二者都蕴含实践正义的成分,存在着相似的理论起点、相像的内在动力与相同的价值目标。但在二者的研究方法以及关于实现方式方面存在明显的分歧。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制度正义论,其关于正义的实现是建立在消灭分工和私有制前提下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阿马蒂亚·森则在现实领域的比较研究中建立具体正义理论,对正义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关怀。其实现正义的两个基本路径包括作为公共理性的民主以及作为自由主张的人权。前者试图对人类社会的制度重构,后者则希望在现有制度体系下建立包容性、中立性的公共理性。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阿马蒂亚·森的正义思想为我们解决现实社会的具体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借鉴的同时,也应看到其缺陷与局限:由于固守着自由主义窠臼,回避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其正义思想存在一定逻辑缺陷,其实现正义的两个基本路径之间存在“二律背反”。通过比较,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森的正义思想,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正义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阿马蒂亚·森;正义理论;公共理性
作者简介:[HTF]郑元凯,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福建 福州 350018)。
基金项目:[HTF]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6JDSZ3014);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6C069);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研究项目(JAS171018)。
中图分类号:A811;B3515;B08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4-0005-10
近年来,印度经济学家、哲学家阿马蒂亚·森的正义思想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他以其独特的微观视角与全球性视野对全球性正义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将抽象的制度正义转换为具体的实践正义,并从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出发,提出实现正义的途径。森的正义思想为当前作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正义思想研究注入了一阵强心剂,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森的正义理论更加彰显了对于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他坚决反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先验制度正义论,主张通过对具体的全球性非正义问题进行理智的思考达成共识。对此,他构建了具有包容性、中立性与开放性的民主与人权路径,希望通过公共理性解决各种社会的非正义问题,而不是像先驗制度主义者那样通过一个主权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执行绝对化的社会契约。
作为实践正义思想的遵循者,马克思与阿马蒂亚·森的正义思想存在一定相似之处,他们都对现实领域的非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究,并且都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实现正义的价值旨归。森对马克思实践正义的方法论表现出十分推崇的态度。在他看来,马克思“在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进行比较”
[印度]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致力于对现实的或可能出现的社会进行比较,而并非局限于先验地去寻找绝对公正的社会。”
[印度]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第5页。
这种实践视角为森的正义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对此,森通过洞察到了现实中的种种非正义现象,对马克思正义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丰富与发展。然而,由于森彻底抛弃制度视角,过度依赖于从实践中探索正义,忽视了导致这些非正义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同时,森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缺失导致森在阐述正义问题时仅仅处于一种静态的分析模式,缺乏对人类历史发展、社会形态演变内在根源的根本认识,不论是对非正义现象解构,还是对实现正义路径的构建,都局限在自由主义的思想桎梏之中。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和森的正义思想何以关联? 两种正义思想又具有哪些异同之处?森的正义思想究竟是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丰富与发展,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否定?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之下,森的正义思想存在哪些局限?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入到二人正义思想的深处,挖掘二者的基本特质与异同之处,实现身处不同时代的思想巨匠的隔空对话。这既是对正义思想的厘清,又能为当代中国社会公正建设提供必要的启示。
一马克思与阿马蒂亚·森正义思想的耦合
马克思与森都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视角提出了构建正义社会的现实目标,并且都对现实社会的非正义问题进行了具体、详尽的研究。因此,从对正义的目标以及研究正义问题的理论视角、实现目标以及关注领域来看,二者的正义思想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
(一)研究起点相似:对社会现实正义问题的关注
对现实正义问题的关注与受到非正义对待弱势群体的关怀是各种正义哲学思想中一个永恒命题。在马克思与森的公正思想中,同样充满了对现实正义问题的关注与审视,将对正义问题的关注作为自身的理论起点。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充满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鞭挞以及对无产阶级生活处境的关照与同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种种非正义现象的审视与解构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理论起点。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所导致的各种异化现象是引发非正义的根源。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生存境遇的关注,马克思深刻揭露了隐藏在资本主义各种看似公正的社会现象本后的非正义本质。通过对异化、物化以及商品拜物教等问题的不断揭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物与人之间的颠倒关系,人的关系被物象关系所掩盖,物对人的支配与占有关系等现象深刻的呈现出来。虽然在青年马克思阶段,马克思本人也曾将社会正义寄托于资产阶级的立法与法律,但随着马克思自身理论体系的不断成熟,马克思逐步洞悉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非正义本质,并试图通过构建一个超越法权正义、彻底颠覆现有的法权制度的社会正义体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中的法权正义予以讽刺,他认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然而,一旦脱离流通领域,便会发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马克思这段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流通领域的等价交换原则掩盖了商品生产领域的非正义的现象。他认为,在完成了政治解放的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从表面上看,能够体现权利的平等与人的自由,并遵守一定程度的互惠原则。但是,一旦将视角切入生产领域,公正则荡然无存。古典哲学家们所倡导的法权公正则成为了一纸空谈。因此,德国古典哲学所倡导的法权正义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私有财产制度的体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种制度本身,不论从历史发展规律上讲,还是从一贯的伦理学逻辑上讲,都是不公正的。
被誉为“穷人经济学家”的阿马蒂亚·森也将研究目光集中在现实的社会群体与非正义问题上。森尤其关注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弱势群体,致力于解决各种贫困问题。他从伦理与道德视角审视了当今社会的非正义现象,将伦理与道德作为影响人们基本行为的重要依据,对现实中的其他不平等现象也予以了高度关注,他认为,“对于困境的“隐忍”使得那些传统的无助的受压迫者对生活习以为常,如对立情绪严重的社区中受到压制的少数族裔、血汗工厂中受到剥削的工人、靠天吃饭却又缺乏保障的佃农、存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的家庭妇女。这些受到剥夺的人也许缺乏企望根本改变的勇气,因此通常会根据自己觉得可能得到的事物,来调整他们的愿望和预期。”
[印度]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第167页。
在众多弱势群体中,残障人士与妇女是森重点关注的对象,关于残障问题,森认为,他们“是收入最低的群体,他们对于收入的需求比健全人更为迫切,因为他们需要这些来过上正常的生活并克服生理上的障碍。”
[印度]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第155页。
对于残障人士而言,由于受到“转化障碍”(conversion handicap)的影响,他们将收入和资源转化为良好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加困难。在谈及妇女问题时,他指出,“妇女在家庭之外寻求就业的自由,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是一个重要问题。 这种自由在很多文化中被系统地否定了,这种否定本身就是对妇女自由权和性别平等的严重侵犯。这一自 由的缺乏,阻碍了妇女经济地位的提升,而且还产生了很多其他后果。”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二)研究动力相像:对主流正义思想的批判
对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正义思想的批判是马克思正义思想发展沿革的内在动力。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针对拉萨尔主义者“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8页。
拉萨尔忽视了自然界与生产资料在生产与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正是由于如此,拉萨尔无法触及到资本主义非正义的本质。由于劳动和
生产资料以及自然界等外部因素都是财富创造的源泉,那些无产者就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从而维持基本的生活。正是由于劳动并非财富的一切源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非正义本质才能得以呈现。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针对蒲鲁东“颠倒了观念范畴和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错误在于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因果关系。他认为,蒲鲁东将正义从人的意识中抽象出来,进而独立化。然而,從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不是人们对脑海中孤立的、抽象的正义观念的不懈追求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运动,恰恰相反,是社会生产的及其存在方式的变革决定了社会成员的正义观念。因此,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正义,永恒的正义是不存在的。
对先验主义正义思想的批判是阿马蒂亚·森正义思想生成的重要内在动力。其中,对罗尔斯的批判最为深入。森认为,罗尔斯过度关注制度的正确性,却忽略了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互动性,同时,罗尔斯对于制度正义的假设条件也存在逻辑上的局限性。首先,在森看来,完美的制度设计是难以实现的,先验制度主义正义观“致力于探寻完美的正义,而不是相对而言的正义与非正义, 即仅仅探寻终极的社会正义的特征, 而不是对现实并非完美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它致力于探究‘正义的本质,而不是寻找用以评判哪种社会相对而言‘更为公正的标准。”
[印度]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第5页。
因此,罗尔斯的正义思想将正义问题绝对化与抽象化。而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绝对化的制度设计不可能持之以恒,更加不可能放之四海皆准。其次,森指出,先验制度主义忽视了非制度因素的影响。理想的制度在实现过程中往往会受到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罗尔斯并没有充分考虑那些诸如人的具体行为。事实上,社会制度的方案是多元的,人们是否遵从这些方案,如何选择这些合理的方案均存在不确定性。第三,森认为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前提缺乏必要的逻辑依据。罗尔斯为了论证“两种正义原则”的合理性,构建了“原初状态”的条件假设。然而,且不论“原初状态”是否符合基本人性使然,即便是这种状态成立,也无法论证人们选择“两个正义原则”的必然性。即人们即便处于“原初状态”,也无法断定他们必然会放弃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理性,而做出符合正义原则的行为选择。
(三)价值目标相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虽然马克思与森在实现正义的途径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手段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将正义目标设定在人的自由发展这个维度上。马克思认为,只有人的彻底解放才是社会正义的最终目标,才能实现属于全体人的正义。正义的最高境界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这种自由人联合体所规定的“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是因为其实现的基本条件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与物质财富的极大富裕。正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诉求才能逐步淡化,继而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可见,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并以此作为社会正义的最终目标。这种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是让人成为全能的人才,而是实现人摆脱奴役,达到个性的解放的一种状态。
在正义的目标向度上,森也注意到了人的自由与发展对于实现正义的重要意义,对此,他将人的自由与发展定义为获得具有自由选择和自由发展的能力,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他指出:
“人不仅是生产的手段,而且是其目的。”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294页。
他认为人不应只作为劳动力或者人力资本而存在,不应只从财富创造与商品生产中获得自身的实现,而应当回归人的本质,从功能与能力的获得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森看来,自由并不是用生活的物质水平来衡量,而应当从人们能够实现的生活方式的多少及其能否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进行跨越与选择。自由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能够让人们获得他们希望获得的事物,这些事物包括了财富、地位,也包括了自身的兴趣与生活方式;其次,获得自由的人可以不受他人的制约,自主决定想要获得的事物。可见,森和马克思都超越了物质财富水平高低,从人的全方面发展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人的最终目标,同时也以此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价值归宿。
二马克思与阿马蒂亚·森正义思想的分野
虽然森的正义思想在某些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正义思想,但由于森并没有继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二者的理论依据不同。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一定的区别与分歧。
(一)阐释正义的语境之异
森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没有继承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也使得他与马克思在阐述正义内涵时所处的语境截然不同。
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语境之上的。他“将思维的触角伸向历史实在关系,克服了以往古典哲学进而通过对历史实在关系的批判来揭示发生于世俗世界中的各种异化,并由之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李佃来:《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正义观的三个转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6页。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马克思将历史辩证法科学运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正问题研究当中,形成了一种事实陈述与价值规范的统一,以及基于特定发展阶段的静态分析与基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动态分析的结合。马克思并没有正面回答“何为正义”的问题,而是通过回答了“正义有何特点”“正义与不义如何区分”以及“正义何以实现”这样一系列更加现实的具体问题,从侧面阐述了正义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正义是历史性、阶级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不同社会形态、不同阶级意识中,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而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沿革,社会正义总是取决于当时的物质生产,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随着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正义的存在形式以及人们关于正义的观念也会随之变化。因而,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社会正义表现形式与正义观念。人们总是不自觉地从现有的经济关系与历史关系中寻找公正的认知支点。同时,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由于存在相互对立的不同社会阶级,也难以形成统一的公正观念。通过文本考察可以看出,唯物史观始终是马克思解构正义的逻辑主线。马克思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给予了肯定。认为,“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页。
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伦理与道德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进行了猛烈地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值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9页。
。在分配领域,这种非正义集中表现在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上,也表现在这种无偿占有被等价交换的资本逻辑所掩盖的现实假象。可见,马克思将动态分析法与静态分析法相结合,在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公正的实质。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正义,一方面,是对过去社会形态中各种非正义的扬弃,因此,它相对于过去的社会形态而言,是正义的;然而,另一方面,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又显示出了极大的非正义性。他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人的伦理学意义上的本体性意义两个方面审视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实现了对社会正义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
相比于马克思而言,森的正义思想发端于资本主义社会,铭刻着自由主义烙印。虽然森在研究视域上超越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制度正义,同时也破除了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遗留下来的先验主义观念,将正义研究引向实践领域。然而,由于森并非唯物主义者,更没有深入洞悉马克思正义观背后的唯物史观旨趣。因此,森对于现实正义问题所作的研究是静态。他并没有真正走进历史发展的深处审视正义问题,而是更多从非正义现象的表象出发探讨解决之道,这种方式虽然能够迎合绝大多数贫困国家、特殊群体。但是却难以把握产生非正义现象背后那些具有历史发展规律性以及符合社会规定性的存在方式。森的正义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也致使在论证实现正义的具体路径上,在通森同样走了一条与马克思迥异的变革之路。虽然森并沒有在其著作中具体阐述正义的概念,事实上,他本人也十分反对对正义进行规范性的释义,那样做无异于等同于罗尔斯的先验主义。然而,从他对可行能力的推崇与个人自由的不懈追求来看,森所谓的正义可以看作是个人对人权与自由的追求与实现。从这一点上看,森的正义思想始终无法掩盖深刻的自由主义主张。
(二)解构正义的视角之异
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在先后不同的人那里,正义被赋予的内涵并非全然相同。”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5页。
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正义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态。在古希腊思想先贤那里,正义属于道德哲学范畴,是关乎个人德性的重要标准。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眼中,正义是制度的首要准则,是执行规则与政策的重要依据。而当代西方学界以罗尔斯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与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阵营关于正义的制度属性与道德属性之争也日趋激烈。通过对森的正义思想解构可见,伦理与道德关怀在其中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众所周知,森的正义思想主要受到來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作为重点关注弱势群体、贫困人群的“穷人经济学家”,森更多从伦理与道德视角审视了当今社会的非正义现象,将伦理与道德作为影响人们基本行为的重要依据。从森所关注的对象来看,多集中在家庭妇女、残障人士以及外来族裔等特定人群以及饥饿、疾病、贫困等极端现象。相比于由具体社会制度所引发的普遍性非正义现象,这些游走于社会制度之外的特殊群体的生活困境属于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话题。对这类人群的研究,能够巧妙回避自由主义的内在隐疾,从而超越社会制度与阶级意识的范畴,从纯粹的道德层面与人性的关怀层面审视正义。透过这个略显避重就轻的研究视角,可以发现,森对制度正义的排斥并非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排斥,恰恰相反,森之所以反对制度正义论,坚持实践正义、具体正义视角,正是基于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由是,森的正义思想是一元性的,是建立在道德关怀基础上的实践考量。或者说,森的正义思想可以归结为一种道德正义。与社群主义不同的是,森是将道德作为审视正义的标准看待,而非将道德作为正义的本体。
马克思也主张正义的实践性,并通过对具体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群体考察构建正义主张。然而,与森不同的是,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并非一元性,具体正义与实践正义并不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全部内涵。他对正义问题的关注并不局限于特定群体的特定现象,而是将具体现象与其背后的特定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对非正义问题的解构也并非局限于纯粹的伦理情怀与道德关照,而是置于历史发展深处,从历史规律出发审视各个阶段的制度建构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性。因此,制度正义、历史正义与道德正义在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中形成了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首先表现为一种制度主张。马克思同历史上的其他思想家一样,都将正义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原则。不同于先验主义正义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将正义向前追溯到一种既定的社会契约状态,而是置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进行解构,具有明显历史向度,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辩证法,是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否定之否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中也确实蕴含着深刻的道德主张。但不同于西方自柏拉图以降的“重叠共识”,在更多场合,马克思所述的“道德”是经唯物史观浸染的具有科学意义的道德。首先,道德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非公正的批判。马克思所提到的作为“虚假之物”的道德仅仅是对资产阶级道德批判的表现。其次,马克思的道德主张与其唯物史观也是高度一致的。正如著名伦理学家李奇所说,“由于唯物辩证法在历史领域里的运用,道德的科学实质才被揭示出来。”
李奇:《道德科学初学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唯物史观的思想内核决定了马克思的道德主张。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也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所决定,是根植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共同意识。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是以历史分析为主线的,以制度构建为最终落脚,而道德则是隐含在历史分析与制度构建中一个重要的逻辑线索。
(三)实践正义的路径之异
虽然森与马克思都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最终旨归,但在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具体路径设置上,二者存在着很大差异。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动物性都占据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奴隶主占有奴隶,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0页。
资产阶级只不过把无产阶级当做财富创造与财富增值的工具,这种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关系,最终指向的是劳动者的全面异化以及自身作为人的本质的丧失。而这一切的制度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只要这种制度继续存在,资本家通过剥削积累起来的巨大非正义财富便会实现代代相传。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不仅没有正义可言,更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与非正义。因此,马克思认为,要达到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权制度。
由于森坚持自由主义,因此在关于正义的实现路径上,森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意识建构一条革命之路。虽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当下的民主制度也予以了批判,但这种批判更大程度是基于民主制度自身的不完善及其同理想民主制度之间的差距,而并非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本身的否定与摈弃。同时,森对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森看来,“每个个体被看成仅仅是为了工具性的作用而聚集在一起的原子;对社会安排的评价主要取决于它对提高和确保个人自由所起的作用。”
Amartya Sen.Freedom and Social Choice: the Arrow Lectures.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85
森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因此,本着进一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消除社会非正义问题。森提出了两个方面的主张,即“作为公共理性的民主和作为自由主张的人权”
[印度]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第13页。
。他认为,自由必须是一种实质性的自由,而不是仅仅关注财富与收入等福利方面,实质性自由包括了“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术,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页。。
获得实质自由必须重视自由的本质是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可行能力,即每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功能性的活动。森进一步强调,这种“可行能力”虽然与财富、收入有关,但财富并不是可行能力的全部。除了财富之外,更应当关注获得经济的各种条件与能力,以及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森称之为社会机会)以及保障性自由(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森将每个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保障方面的自由称为工具性自由。因此,他将代表人的实质自由的可行能力范围的不断扩大作为实现公正的一个重要路径。可以看出,与马克思不同,森旨在通过进一步完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并通过扩大可行能力实现人权的发展,进而达到社会公正的理想状态。同时,森对于民主的前提是一种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的公共理性原则,他认为,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或将个人行为的全部动机归为自身利益,这样一来,有可能出现个人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排除了承担他人利益的义务。要实现真实的正义与自由,人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与他人可行能力的实现。必须通过自身情况的衡量,行使那些帮助他人实现自由的行为。对此,森提出以更广阔的视野构建一种理性选择,即将我们的选择置于一种可持续的理智思考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广义的理性。这种公共理性具有包容性的原则,它使得那些选择“合理地拒绝”的行为显得缺乏依据。这种公共理性甚至可以是不完全符合自身利益的。这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公共理性可以用开放的中立性、缘由的多元性,以及方法的比较性三者共同组成。可见,森的正义主张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一种改良,虽然他本人十分反对福利主义,但是他的正义主张依然只是福利主义的一种内容扩充。
三阿马蒂亚·森正义思想的局限性
通过与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森的正义主张在某些方面可以视为马克思正义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对现实正义问题的关照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罗尔斯先验制度主义正义论在实践方面的局限性。然而,由于对唯物史观的漠视使得其正义思想虽然能够直面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非正义问题,但却无法对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科学的现实途径。总结马克思与森正义思想的理论分野,可以看出,森的正义理论存在的局限。
(一)忽视了制度正义的作用
森过分强调了具体正义,而忽视了制度正义对矫正现实中非正义现象的作用。森批判罗尔斯的制度正义,认为制度正义无法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非正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正义研究的方法论转向。但是,正义的制度设计固然无法解决到现实中纷繁复杂的非正义现象,但这些非正义现象要想得到解决,同样不能忽视合理的制度安排。马克思所提出的正义的实现路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一种针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规范性的制度安排。也只有基于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人才能朝着合乎本质的方向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若只考虑通过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理性实现现实世界非正义现象的调剂与矫正,显然是不够的。個体的行为选择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的理性,要实现个体行为选择朝着符合社会理性的方向发展,除了依靠非法律的因素之外,还必须通过较为清晰的制度建构,即通过符合正义方向的立法制度,使这种个体行为能够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真实的正义应当是制度正义与具体正义的统一。
(二)忽视了正义的地域性与阶级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具有鲜明的历史性、阶级性与相对性的特点。由于唯物史观的的理论缺失,森忽视了正义的这些最本质特征。他一方面反对罗尔斯将正义绝对化,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用统一的开放性的中立原则建立公共理性,实现不同地域、社会背景与文化的通过自发建立公共理性来实现对一些问题的统一认识与共识。可以看出,森的正义观始终坚持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实现正义,而没有考虑中立原则、公共理性以及民主方式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兼容性。森没有考虑到正义的历史性与阶级性。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正义具有历史性与阶级性的特点。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社会正义表现形式与正义观念,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阶级也持有不同目标向度的社会正义观。当今全球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经济不平衡与社会形态差异。即便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经济关系与经济生产方式也不尽相同。应当说,同一种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本质与根源,归根结底,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比如,贫困与饥饿问题,在非洲大陆与美洲大陆都同样存在,但他们生成的社会本质却是不同的,非洲大陆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北美地区位于世界前列的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他们社会意识中正义观念绝对无法通过建立一种统一的公共理性实现融合与统一。由于阶级社会的长期存在,公正的阶级性特点难以改变,要想通过人自身的理性构建各国家、民族、阶层、文化之间的思想连接,彻底消除差异与分歧,显然是无法实现的,除非这种阶级差异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重构而得以消亡。
(三)实现正义的两条路径之间存在“二律背反”
正是由于森并非唯物主义者,其正义思想始终没有跳出自由主义的窠臼,因此,他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当中思考正义的实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在探讨正义的实现方式时所设计的公共理性的民主和作为自由主张的人权两条路径存在着自身理论结构无法克服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森提出的“自由主张的人权”是一种超越法律的实质自由的权利,是一种非利益的道德主张。从这个方面来说,森的人权思想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具有一致性。也正因为如此,森的人权思想中所倡导的可行能力与实质自由,必须通过构建一个消除一切剥削与私有财产制度的自由人联合体得以实现。然而,另一方面,森提出的实现正义的另一条路径“公共理性”原则则从相反的方向对这种超越法权的人权思想进行了消解。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意识当中,构建开放性中立原则的公共理性,无异于强化了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的全球化传播,进而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时,他对于实现这种中立性原则而推崇的“积极而又充满活力的媒体”实质上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宣传的工具而已,通过新闻、报道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工具实现自由人权,是具有虚幻性的不切实际。这种方式反而会使得实现自由人权的制度基础——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组织形式无法实现。因此,虽然森的正义思想扩大了正义的具体内涵,并且寄希望于通过形成全球性的共识达到制度正义所不能实现的正义实质,但由于森缺乏一种基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考,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缺陷,因此森的正义思想无法真正从制度缺陷上消解当前普遍存在的全球性非正义问题。
四启示:坚持马克思正义思想指导,借鉴吸收阿马蒂亚·森正义思想的合理部分
通过马克思与森正义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虽然森的正义思想在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上与马克思有相似之处,但二者所运用的方法论基础以及具体的政策主张却截然不同。森仅仅借鉴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外壳,却没有深入到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唯物史观内核当中,因此,森的正义思想具有一定局限性。对此,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阿马蒂亚·森的正义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对森的正义思想进行扬弃。一方面,我国当前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马克思所阐述的真实的正义目标在现阶段还无法实现。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共同表现的具体性非正义问题在我国也普遍存在。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亟需解决一些具体的民生与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森提出如何实现正义,特别是如何实现自由人权的一些具体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首先,森的具体正义思想以及比较的方法对当前推动我国司法改革,提升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度,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其次,森提出的人权思想可以视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一种补充。森将人权定位于超越个人利益的权利,并且是一种不以法律为强制手段的权利,这种思想可以视为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从政治、经济、社会保障等更加全面、具体的方面去实现实质自由的主张,为当前我国加强社会民生建设,提升公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实现共享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上看,我们依然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包含科学的历史辩证逻辑以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论证方法,紧紧抓住了物质生产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线,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正义的不同表现以及发展规律进行科学论证,并基于历史发展规律上建构一种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真实的正义社会。相比之下,森的静态分析法彻底抛弃了马克思、罗尔斯等人曾经继承下来的制度分析路径,让比较方法形成的行为选择缺乏一种强有力的说服力,这也表明森的公正思想缺乏一种必要的理论张力。同时,由于对唯物史观的缺乏以及对自由主义的坚守,以至于他寄希望于通过改良的方式解决非正义问题,没有触及到决定正义实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等问题上,无法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上提出构建正义社会的有效主张。
Coupling and Divergence Between Marxs Justice Thought andAmartya Sens Justice Thought Thought
——Comment on the Limitations of Amartya Sens Justice Thought
ZHENG Yuan-kai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in justice in practice,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the internal motive and value goal between Marx and Amaetya Sens justice thought, but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ir research methods and ways of realization. Marxs justice thought is essentially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justice 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realization is based on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under the premise of eliminating the devision of labor and private owership. Amaetya Sen set up the concrete theory of justice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eality, giving more ethical care to justice, and wanted to realize the justice through the two ways of democracy as a public reason and human rights as freedom.The form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system of human society, while the latter wants to establish inclusive and neutral public rationality under the existing system. At present, our country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So we should see that Amaetya Sens thought of justiceprovides us with the methodology for solving the concrete problems of the real society and at the same time see the defects and limitations: as a result of sticking to the stereotype of liberalism and avoiding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m, there are some logical defects in his justice thought, and the “antinomy” exists in the two basic paths of realizing justice. Through comparison, we can develop and enrich the justice theory in observing the Sens theory with Marxs view.
Keywords: Marx; Amaetya Sen; justice theory; public reason
【責任编辑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