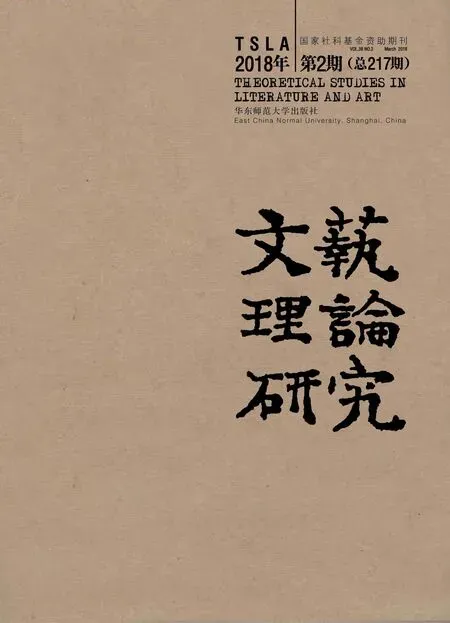论康德鉴赏判断的先验理据
胡友峰
鉴赏判断的“先验”问题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学界之前的研究中对《判断力批判》中的“先验”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鉴赏判断的先验问题直接关系到康德判断力能否进行批判的核心问题,鉴赏判断是否具有先验原理直接涉及到鉴赏判断能否纳入到批判哲学体系之中,如果找不到鉴赏判断的先验原理,判断力批判就不能成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并没有从主观的普遍必然性出发去解决鉴赏判断的先验原理问题,而从主观普遍必然性出发去解决问题是他在前两大批判中惯用的方法论原则。在第三批判中康德将鉴赏判断与反思判断力关联在一起,通过为反思判断力寻求先验原理来解决鉴赏判断的先验依据问题。康德为什么不直接为鉴赏判断寻求先验原理而要借助反思判断力来为鉴赏判断寻求先验依据呢?这涉及到康德对鉴赏判断的态度转变以及康德《判断力批判》体系的构成问题,因而在对康德美学进行研究时,我们首先需要弄厘清鉴赏判断先验理据这一康德美学的核心问题。
一、鉴赏判断何以是先验的
鉴赏判断何以是先验的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的原因以及《判断力批判》体系构成问题。按照康德自己的说法,在写作完成《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后,他意识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讨论的经验世界的自然概念领域与《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讨论的超验世界的自由概念领域存在着一条鸿沟,如果这条鸿沟不加以贯通,作为完整体系的康德先验哲学就不能成立。因而,康德特别的强调了鸿沟问题:“现在,虽然在作为感性东西的自然概念领域和作为超感性东西的自由概念领域之间强化了一道明显的鸿沟,[……]所以,毕竟必须存在着作为自然之基础的超感性东西与自由概念实践上所包含的东西的统一性的某种依据,这个依据的概念虽然即没有理论上的也没有实践上达到对这个根据的一种认识,因而不拥有特有的领域,但却仍然使按照一方的原则的思维方式向按照另一方原则的思维方式的过渡成为可能”(康德,“判断力注释本”9)。之所以援引康德这么长的一段引文,主要在于这一段话说明了康德写作《判断了批判》的一个缘由,即自然概念与自由概念之间存在着这样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自然概念通过理论的理性运用是无法通达自由概念的,自然概念如果企图通过理论理性的工具去把握自由这一超感性的概念,就会产生二律背反。但是自由概念在超感性领地中所遵循的法则必须并且“应当”在感性世界中得以实现,自由概念的意志自由法则通过其实践理性的“目的”意愿与感性的经验现象界“形式合法则性”相互协调,也就是说,超感性的自由概念通过实践理性法则与自然的感性世界获得某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就成为沟通自然与自由的一座桥梁,为这种统一性寻求先验依据也就成为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一个首要任务,虽然获得这种统一性的先验依据即没有理论上的认识功能,也没有实践上的范导功能,但是这种统一性却让自然向自由过渡成为可能。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统一性的依据是什么?这种统一性的依据在《判断力批判》中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这种统一性依据与鉴赏判断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就必须考察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体系问题以及康德对鉴赏判断的态度问题。
我们先来分析康德对鉴赏判断的态度问题。康德对鉴赏判断的态度是有着一个巨大转变的,他开始认为鉴赏判断是没有先验依据的,鉴赏判断仅仅具有经验性,并没有普遍必然性。写于1763年,出版于1764年的《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是康德写作的第一部美学著作。在写作该部著作的时候,康德批判哲学的思路和体系还没有形成,因而在这部著作中康德对优美与崇高两大美学范畴采用的是经验分析和感性直观感受描述的方法。也就是说,在该部著作中,康德主要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阐述两大美学核心范畴的,通过对优美和崇高这两大美学范畴的经验描述,康德深入地分析了人类情感的多样性,从经验的角度从研究美学问题是当时的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趋向,康德也不例外。1750年,鲍姆嘉通出版了《美学》第一卷,这被认为是美学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1758年,《美学》第二卷发表,鲍姆嘉通的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构。鲍姆嘉通改造了希腊词“aisthesis”(感性)为“aesthetica”(改词直译为感性学),翻译成汉语为美学。他根据人的心理机能知、情、意三分法把研究“情”的学问定义为“aesthetica”,在传统的哲学体系中,研究知的是逻辑学,研究意的是伦理学,现在将研究情的学问界定为美学,这是一门专门研究感性认识和情感的学科,美学“感性认识的科学”是他对美学这门新的学科的界定。鲍姆嘉通通过“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一定义将美学界定在认识论的范围内,美学是一种感性认识,但这种感性认识需要达到完善的程度就需要理性的参与,因为完善毕竟是一种理性的目标,这是当时理性主义者对美学的一个基本的看法。而源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则从主体的心理经验出发,从主体的生理和心理方面来揭示审美意识的结构和功能。休谟、博克等对“趣味”问题作出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解释成为当时美学研究的一股浪潮,康德在1763年写作《观察》的时候,正处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风卷欧洲大陆的时候,康德显然是受到了这股浪潮的影响。在《观察》中,他完全的遵循了经验主义美学的观察和分析的方法,对优美和崇高两大美学范畴进行了心理和生理学的解释,几乎看不到当时德国理性派美学对其的影响。
可以看出,康德在写作《观察》一书时,他明显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影响,认为鉴赏判断是经验性的,可以通过心理分析的方法去解决鉴赏判断的难题,他对美学的这一基本看法即使到了1781年出版《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时候也没有多少的改变,到1787年出版《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时候康德对鉴赏判断是否具有先验性的看法有了一点松动,在一个注释中康德说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上述规则或者标准就其最主要的来源而言仅仅是经验性的,因而绝不能充当我们的鉴赏判断必须遵循的确定的(“确定的”一词为第二版所加——译者注)先天规律;毋宁说,鉴赏判断构成了那些规则的正确性的试金石,因此可取的是,要么(“要么”一词为第二版所加——译者注)使这一称谓再次死亡,并把它保留给是真正的科学的学说(这样以来,人们也就会更为接近古人的语言和意义,在古人那里把知识划分为[可感觉的和可思想的]是很著名的),要么与思辨哲学分享这一称谓,并部分地在先验的意义上,部分地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接受感性论(括号及“要么……感性论”为第二版所加。——译者注)(康德,“纯粹”53)。比较一下第一版和第二版这段话在文字表述上的变化,我们发现康德在鉴赏判断是否是先验的这一问题上有一些让步,在李秋零的注解中我们发现,第二版增加了一些字词,“确定的”先天规律增加的“确定的”一词说明鉴赏判断中即使有很少部分的先验因素也还是有先验性的,康德并没有彻底地排除鉴赏问题的先验性,在后面增加的这一整句话中,谈及感性论部分可以在先验意义上使用,这就是先验的感性时空问题,部分地在心理学上使用实际上就是鉴赏问题了,在这里,康德虽然对鉴赏先验问题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是从整体来看,康德对鉴赏判断的先验问题还有持怀疑态度的。
康德认为鉴赏判断是经验性的,也就说明了鉴赏判断是没有普遍必然性的,也就没有先验原理。康德为什么最终还是要寻求鉴赏判断的先验原理呢?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之前我们需要看1787年12月28日康德写给莱因霍尔德这封书信,在这封书信中康德明确地提及他在写作鉴赏力批判这部著作,并且找到了鉴赏力的先天原理:“现在我试图发现第二种能力的先天原则。虽然我过去曾经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它使我认识到哲学有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先天原则,人们可以一一列举它们,可以确切地规定以这种方式可能的知识范围——理论哲学、目的论、实践哲学,其中目的论被认为是最缺乏先天根据的”(康德,“书信”110—11)。这封信对于理解康德对鉴赏判断态度的转变十分重要,在这封信中,“他就《关于康德哲学的通信》向莱因霍尔德表示感谢,同时把关于目的论原则的文章寄给他用于《德意志信使报》,这封信使人毫不怀疑,康德在研究鉴赏判断时获得的新认识在根本上返回到对以前所考察能力的解析”(威廉·文德尔班 5)。就这封信中这段话而言,它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康德在1787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开始从事鉴赏力批判的写作,并且已经发现了鉴赏力批判的先天原则,而鉴赏力在过去康德认为是一种经验事实,根本就不可能有先验原则,而康德在这里明确地提及到他已经找到这条先验原理,那么,是什么契机促使康德发现了这条先验原理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人的心灵结构的划分问题。第二、康德在这里还是提到了西方哲学中人的心理机能的三分法问题,人的心理机能可以分为知、情、意三种结构,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发现并且论证了认识能力即知性的先验原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已经发现和论证了欲求能力即理性的先验原理,那么,根据类比的法则,作为心灵结构之一种的情感也应该有先验的法则,这样,康德在鉴赏力批判中就需要为情感寻找先验的法则,为情感寻找到先验法则后才能够将鉴赏问题纳入到其先验哲学体系当中。第三,经常被我们所忽视的问题是,认识能力是康德通过为知性寻求先验法则获得进入批判哲学体系的门票,欲求能力是康德通过为理性寻求先验法则获得进入批判哲学体系的机会,而快乐与不快乐的情感能力康德通过为判断力寻求先验法则来解决情感的先验问题,这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情感的先验是如何与判断力相互关联的呢?康德要解决的是情感的先验问题,为什么他所请来的认识工具是判断力呢?第四、康德在这封信中谈及到他的哲学体系问题,人的心灵结构三分法的划分让康德认识到其哲学有三个部分,理论哲学、目的论和实践哲学,而目的论是最缺乏先验根据的,因而康德希望在复活节前出版这部《鉴赏力批判》的著作,来解决其哲学体系的完整性问题。然而问题在于:按照人的心灵结构的三分法,康德哲学的三个部分应该是理论哲学、美学(鉴赏判断)和实践哲学,而康德在这里却用目的论取代了美学,康德在这里提及他这部著作的名称为《鉴赏力批判》,而最终出版的时候,书名确定为《判断力批判》,这又是为什么呢?
表面上看,康德在表明鉴赏判断具有先验性的这封信的表述上具有非常多的矛盾,而事实上,只有我们深入到康德哲学体系之中,就会发现在这封信中已经隐藏了康德解决其哲学体系裂变的某种尝试。前面已经提到康德在其哲学体系的分裂中说道,“毕竟存在着作为自然之基础的超感性的东西与自由概念实践上所包含的东西的统一性的某种根据”。这种统一性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它与鉴赏判断是何种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前面书信当中所提出的问题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在这里可以合并起来一起分析。
那么,这种统一性的依据是什么呢?这种依据就是反思判断力的先验原理,找到了这种先验原理,其统一性的就有了共同的基础。即自然基础的超感性的东西与自由概念的实践基础因为这一共同的基础而具有了沟通的可能性。那么,反思判断力的先验原理是什么呢?康德于是论及了自然形式多样性的经验法则中蕴藏着统一性的某种依据,而这种依据可以提供反思自然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仅仅是而反思自然而存在,并不能为自然颁发任何的法则,否则它就是规定的判断力了,“所以这样一条先验原则,反思性的判断力只能作为规律自己给予自己,而不能从别处拿来(因为否则它就是规定性的判断力了),更不能颁布给自然:因为有关自然规律的反思取决于自然,而自然并不取决于我们据以努力去获得一个就这些规律而言完全是偶然的自然概念的那些条件”(康德,“判断力”14)。康德认为,经验的自然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也应该有统一性的基础。康德把“自然合目的性”作为一种先验原理,从而把经验性的多样化的自然规律统一起来。在这里,“自然合目的性”就成为康德思考反思判断力的先验原理的一个因素,“自然的合目的性是一个特殊的先天概念,它只在反思性的判断力中有其根源,[……]而且这个概念与实践的合目的性(人类艺术的,或者也有道德的)也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它是按照和这种合目的性的类比而被思考的”(“判断力”15)。自然合目的性作为反思判断力的先验原理,是通过与人类艺术的类比法则来确定其规定性的,它是用来反思自然的一条法则,并不能为自然增加任何的内容,自然好像是有目的的,与艺术一样,只不过艺术的目的是人(艺术家)赋予的,而自然的目的是自己给予自己,自己给予自己的目的就是自然目的论问题。
我们再回到康德写给莱因霍尔德的这封信中,康德在这封信中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已经开始从事了鉴赏力的批判,这种鉴赏力的批判是为人类心灵结构中的情感寻求一种新的先验原理。在写作《判断力批判》的时候,康德将鉴赏力与作为高级认识能力的判断力联系在一起,这里的判断力只能是反思判断力,反思判断力又划分为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鉴赏判断是一个反思判断,是审美判断。这样,在康德先验哲学体系的来源的心意机能划分中知、情、意中的情就有了鉴赏判断与之相连接,为情感寻求先验原理转换为了为审美判断力寻求先验原理了。值得关注的是,康德在写给莱茵赫尔德的信中美学并不是其判断哲学的组成部分,相反,目的论则是其三大哲学体系中居于中间地位的选项,这说明在康德的心目中目的论一直是其批判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鉴赏判断(美学)在其批判哲学体系中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而隶属于目的论当中,但是由于为目的论寻求先验原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而要把目的论纳入到其批判哲学体系之中就必须解决目的论的先验原理问题,这里康德采取了一种“倒逼”的方式,他首先解决的是鉴赏判断的先验原理,而鉴赏判断又是目的论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鉴赏判断是一种主观的合目的性,与人的心灵结构中的情感相互联系在一起,康德通过类比的原则找到了鉴赏判断(情感)的先验原理——自然形式的目的性原理,这样目的论的先验原理问题“假借”鉴赏判断的先验原理得以解决,目的论的先验原理找到了,目的论进入到康德哲学体系之中的难题也得以解决。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将目的论纳入到其批判哲学体系中,从而完成他批判哲学体系的建构,也为后来他写作历史理性批判的一系列文章做出铺垫。因此,在《判断力批判》中,“鉴赏判断”通过与情感问题连接,找到其先验原理——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先验原理的解决为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论证提供了奠基性的工作,但是作为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在鉴赏判断中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它的实在性问题需要在目的论判断力批判中加以解决,目的论判断力作为自然客观的合目的性通过自然向人的道德的生成以及自然神学的设定获得了实在性。因而鉴赏判断的先验问题即为审美寻找到先验原理,也为目的论问题在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中获得应有的位置作出了铺垫,这也是为什么康德没有最后把书名定为《鉴赏力批判》,而定为《判断力批判》的原因。
鉴赏判断通过与情感问题的连接获得了与人的心理机能进行类比的机会,从而找到了鉴赏判断的先验原理——自然合目的性原理,而鉴赏判断所寻求到的先验原理是为目的论问题作出铺垫,即通过为鉴赏判断寻求先验原理而“代替”为目的论判断力寻求先验原理,因为鉴赏判断就是目的论的初步形式,从而能够将目的论问题纳入到康德的先验哲学体系当中,在鉴赏判断中,自然合目的性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其实在性需要在目的论判断力批判中得以解决,因而康德美学是其目的论“倒逼”的结果,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着力解决的并不是鉴赏判断的美学问题,而是关系到后来康德写作社会历史发展等问题相关的目的论问题。
二、鉴赏判断的先验演绎
当康德将鉴赏判断纳入到其批判哲学体系之中以后,根据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要求,要论证鉴赏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就必须寻求鉴赏判断的普遍必然性问题。鉴赏判断作为一种单称判断,如何才具有普遍必然性呢?康德寻找鉴赏判断的先验原理,就是为了论证鉴赏判断的普遍必然性问题,虽然康德在“美的分析”的部分不断地论证审美与认识,与道德之间的区别,说明了鉴赏判断的主观普遍必然性问题,但是从康德哲学体系出发,就必须对鉴赏判断进行演绎。所谓“演绎”,就是一种推论,用推论的方式来证明鉴赏判断的普遍必然性。单称的鉴赏判断能否纳入到“先天综合判断”之中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地去加以探讨,因而演绎在康德鉴赏判断中是必须的,这样能够更有力地说明鉴赏判断的普遍必然性。
那么,康德要做“鉴赏判断”的演绎,其目的性何在呢?康德认为:“它(指鉴赏判断——作者加)就必须以某个(不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先天原则作为基础,这个先天原则是人们通过探查心灵变化的经验性法则所永远无法达到的,因为这些经验性的法则只是让人认识判断是如何作出的,而不是要求判断应当如何作出,确切地说,这要求根本就是无条件的;这类要求是鉴赏判断以之为前提条件的,因为鉴赏判断要懂得把愉悦与一个表象直接地连接起来,因此,尽管对审美判断的经验性说明总是作为开端,以便为一种更高的研究提供素材,但对这种能力的先验的讨论却毕竟是可能的,并且在本质上属于鉴赏的判断。因为若不是鉴赏拥有这些先天原则,它就不可能能够裁定别人的判断,并对别人的判断哪怕只是以某种权利的外表来作出赞同或者拒斥的表示”(康德,“全集”290)。康德需要论证的就是作为个人的鉴赏判断为何需要所有人都赞同,也就是要论证鉴赏判断的先验性问题,只有鉴赏判断是先验的,才能说明鉴赏判断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因而康德所谓的“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就是要论证鉴赏判断的先验性问题,那么,康德又是如何进行鉴赏判断演绎的呢?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30节的标题中明确指出:“关于自然对象审美判断的演绎不可以针对我们在自然中称为崇高的东西,而只能针对美者”(“判断力注释本”105)。对崇高的判断不需要演绎,原因在于在对崇高的判断中涉及到自然的无形式,而对这种无形式的把握已经与人类的理性思维范式有所关联,在与理性的思维关联中,理性自身已经具有了先验的原理,而不需要为其重新辩护,再去为其寻求先验原理,找到崇高判断的普遍必然性。但对具体的美的事物的审美判断中因为涉及到事物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又如何是具有合目的性的形式,则需要演绎,以便为审美判断寻求普遍必然性。也就是说:“惟有当判断提出必然性的要求时,才会出现一类判断的演绎,亦即保证其合法性的责任;当判断要求主观的普遍性,亦即要求每个人都赞同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判断力注释本”292)。鉴赏判断演绎的难度在于鉴赏判断要求的是一种主观的普遍必然性,它不是建立在客观的概念之上,要为鉴赏判断的主观合目的性进行论证,需要为单称的鉴赏判断寻找到普遍必然性。
既然鉴赏判断演绎的目的是为鉴赏判断寻求普遍必然性,那么,鉴赏判断又具有那些特征呢?鉴赏判断是通过愉快的情感来规定自己的对象,在对象形式的把握中感受到愉快就是美的,并且要求每一个人都普遍的赞同这种愉快,就好像是具有客观性一样。这样我们在鉴赏判断的先验演绎中就需要寻求愉快的普遍必然性问题。这事实上涉及到鉴赏判断“自律”的问题。“鉴赏只提出自律的要求”(“判断力注释本”294)。鉴赏针对的是个人的情感愉悦,而不是根据别人的判断作为自己判断的典范,否则鉴赏就成为“他律”的了。由于鉴赏判断不是通过概念来加以证明的,这说明鉴赏判断又是具有主观性的。“不存在某种经验性的证明根据去强迫某人作出鉴赏判断”(“判断力注释本”296)。知性的判断通过愉悦情感的传达可以作出一个全称的判断,但是这种判断是一个逻辑判断而不再是一个鉴赏的判断,康德举例说:“所有的郁金香都是美的”所作出的判断就是一个逻辑判断,而不是一个鉴赏判断。原因在于在对郁金香做判断的时候,你所加以判断的这支郁金香并不在眼前,并且所做出的判断美是一个概念,并不表现具体的审美主体面对郁金香时候所获得的审美感受,那么,“所有的郁金香都是美的”这一判断就是一个逻辑判断,而不是一个鉴赏判断,如果说:“这一支郁金香是美的”,这一判断就是一个鉴赏判断,原因在于是审美主体面对的是这一支郁金香,而不是别的,当主体面对这支郁金香时所做的判断依据就是自己所感受到的审美愉悦,通过这种审美愉悦,我们感受到这支郁金香的美,一个审美判断因之做出。
问题在于:我们是如何感受到这种愉快的?愉快从何而来?我感受到的这种愉快如何能够保证别人也能够感受的到?也就是说,愉快的普遍可传达性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康德鉴赏判断的普遍必然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审美如何可能就是一句空话,康德所进行的鉴赏判断的演绎就行不通。康德当然不会对这两个问题视而不见,他用“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和谐感”来解决愉快的来源的问题,用“审美共通感”来解决愉快的普遍可传达性问题。
康德认为:“一个人在单纯对一个对象的反思中不考虑概念而感到愉快,尽管他的判断是经验性的并且是个别判断,他也有权要求任何人同意,[……],愉快之成为这个判断的规定根据,毕竟只是由我们意识到它仅仅基于反思及其与一般客体知识协和一致的普遍的、虽然只是主观的诸条件之上,对这种反思来说客体的形式是合目的性的”(“判断力”26—27)。康德在这段话中交待了鉴赏判断看上去虽然是经验性的并且个别的判断,但是它有权利要求别人都赞同,这种判断的依据是对对象形式的反思,在反思中获得一种合目的性,这种合目的性就是知性与想象力之间的自由和谐,当我们在鉴赏判断中获得这种和谐,我们就会有一种愉悦的感觉,而愉快的来源是知性与想象力自由和谐所产生的。那么,在鉴赏判断中,知性与想象力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自由和谐呢?这就需要我们考察想象力在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地位,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想象力是感性与知性之间的粘合剂,想象力产生的图示连接了感性与知性,因而感性可以直观,是经验的来源,而知性是一种先验的范畴,经验与先验之间存在这一条鸿沟,这条鸿沟需要想象力产生的图示加以连通。但在这里,康德的想象力还是受到知性的控制,想象力要发挥作用还必须在知性的规范下去运作,想象力并不能脱离感性对象,因而是不自由的,知性也要受到对象感性形式的制约,应用范畴去整理对象的感性形式,知性也受到对象逻辑表象的制约,其活动也是不自由的。在认识活动中,想象力与知性并不能形成和谐一致的关系,知性对想象力具有支配作用。在伦理实践中,想象力的任务是从人的活动中获取感性的材料,交给理性的法庭加以审判,理性根据自己的先天立法原则对这些感性材料进行判断,看其是否符合伦理规范,因之,在这里,想象力也是不自由的,它受到了理性的制约。只有在《判断力批判》中,当反思判断力从规定的判断力中分离出来后,知性不需要受到对象逻辑表象的制约,想象力也不需要提供经验材料交给知性辨别,两者在对对象形式的反思中获得了和谐一致,在鉴赏判断中,当想象力与知性和谐一致时,愉悦感也由之产生。
解决了愉悦感的来源问题,康德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鉴赏判断的普遍必然性问题。鉴赏判断是个体的单称判断,你个人所感受到的愉悦感为何能保证别人也能感受得到?也就是说,你如何保证这种愉悦感的普遍可传达性?你凭什么来要求别人普遍赞同你的判断?在解决鉴赏判断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上,也就是在鉴赏判断先验演绎的结果上面,康德请出来的是“审美共通感”。审美不普遍必然的,但又不以来任何的知性概念,那么,审美愉悦普遍必然性的来源就需要在鉴赏主体的内在心理去发掘,而不能从客体对象上去寻找,康德说:“所以鉴赏判断必定具有一条主观原则,这条原则只通过情感而不通过概念,却可能普遍有效地规定什么是令人喜欢的、什么是令人讨厌的,但一条这样的原则只能被看作共通感,它是与人们有时称之为共通感的普通知性有本质不同的:后者并不是按照情感,而总是按照概念,尽管通常只有作为依模糊表象出来的原则的那些概念来作判断的”(“判断力”74)。鉴赏判断的这种主观来源只能是情感的普遍可传达性,也就是审美共通感,它与依照先验范畴概念来运作的知性有着本质的不同,知性是依据概念作出的,而审美共通感是依照情感逻辑来设定的。所以康德认为:“只有在这样一个共通感的前提下,才能做鉴赏判断”。
康德请出来的“审美共通感”是一种设定,是一种假设,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而对“审美共通感”存在的论证也显得比较粗糙,令人难以信服,这也是康德美学一直造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康德要解决审美如何可能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找到审美普遍必然性的最终根据,而康德所找到的最终根据则是一种“假设”,其论证过程是这样的:“知识是可以普遍传达的——认识知识的内心状态可以普遍传达——情感可以普遍传达——审美共同感是存在的”。当然,康德为了鉴赏判断先验演绎的成功,还进一步地去论证了“审美共同感”的合法性问题。“人们必须把sensus communis[共通感]理解为一种共同的感觉的理念,也就是一种评判能力的理念,这种评判能力在自己的反思中(先天地)考虑到每个别人在思维中的表象方式,以便把自己的判断仿佛依凭着全部人类理性”(“判断力”135)。审美共同感是一种“共同的感觉理念”,“是一种评判能力的理念”,在这里,康德将审美共同感上升到“理念”的高度,认为审美共同感是人类的一种“理性”,因而在判断中我们会过滤掉我们自身所带有的一些私人幻觉,同时也过滤掉鉴赏对象作为质料的因素,而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对象的形式特征上面。而这种共同感的理念就是一种先验原理,它可以保证个人的鉴赏判断具有普遍必然性,并且与人类共同的情感相互联通。
康德在鉴赏判断的先验演绎中,首先排除了对“崇高判断”的先验演绎,而把焦点放在对“美的先验分析”上面,通过先验演绎,为鉴赏判断寻求普遍必然性,最终找到了“审美共通感”作为鉴赏判断的先验根据,但是这种根据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是不稳固的,因而还需要对鉴赏判断的先验问题进行论证,这个任务落实在鉴赏判断的二律背反身上。
三、鉴赏判断的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宇宙论批判中,康德提出了他的二律背反理论。康德认为:人类的理性有一种逾越的冲动,理性试图跨越经验现象界对物自体世界进行把握,而使用的方法则是知性的先验范畴,用知性的概念去整理和规范那些超感性的概念,由之会导致理性的二律背反。康德在此提出了四对二律背反问题,并对其进行了解释,康德通过限制知性的超验使用,限制知识,解决人类理性的越界问题,最终也解决了这些二律背反。而这些二律背反的解决则需要辩证论的方式加以阐明。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当幸福与德性产生二律背反时,康德也加上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通过“至善”观念的提出来解决幸福与德性的统一问题。从批判哲学的统一性来看,在《判断力批判》中也需要加上辩证论,以寻求其哲学体系的平衡。在《判断力批判》第一部分“审美判断力的批判”的第二卷“审美判断力的辩证论”中,康德系统的分析了鉴赏判断的二律背反问题。在《判断力批判》第55节一开始,康德就提出:“一种判断力要是辩证的,就必须首先是推想的,也就是说,它的判断必须提出普遍必然性的要求,确切的说是提出先天普遍性的要求”(“全集”351)。对这一句话,康德有着自己的注释,在注释中康德再一次强调了推理的判断所具有的先验性,也就是普遍必然性问题。快感的判断是私人化的,没有普遍必然性,因而不存在判断的二律背反。只有鉴赏判断才能够提出普遍必然性的要求,也就是说,鉴赏判断是先验的,在这一前提下,“关于一般鉴赏判断的可能性的根据,自然而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相互抵触的概念。因此,鉴赏的先验批判就此而言将只包含一个可以使用审美判断力的辩证论之名称的部分”(“全集”351),如果鉴赏判断的先验性是可能的,抑或说,鉴赏判断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那么,在鉴赏判断中就会蕴藏着作为理性推理能力判断力的二律背反。因而康德所提出的在鉴赏判断中的二律背反就是作为审美判断的反思判断力的二律背反,这就涉及到鉴赏判断的普遍必然性从何而来的问题,康德通过对审美理念的分析提出了鉴赏判断二律背反的表现形式:
一、正论。鉴赏判断不是建立在概念之上;因为若不然,对此就可以争辩(通过证明来裁定)了。
二、反论。鉴赏判断是建立在概念之上的;因为若不然,尽管之中判断有差异,对此也根本不可以争执(要求别人必然赞同这个判断)。(“全集”353)
康德在这里提出的鉴赏判断的二律背反其实就是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英国经验主义美学(正题)与法德理性主义美学(反题)的基本观点,在当时看来,这两种美学上的观点是冲突而不能融合的,鉴赏判断是单称判断,是个体面对某一具体事物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愉悦感,它是没有任何概念作为判断依据的。当然,这里的概念主要是指一种知性意义上的概念,通过这种概念可以获得一种知识,审美不是认识,因而不需要这种概念。而鉴赏判断虽然是一种单称判断,但必须有普遍必然性作为保障,否则鉴赏判断就不可能纳入到先验哲学体系之中,既然要有普遍必然性,就需要一个概念作为基础,因而在反题中概念就有了依据。在这里,鉴赏判断的二律背反之所以能够成立,与前面分析的鉴赏判断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即鉴赏判断既是个体的单称判断,又必须有普遍必然性要求。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分析鉴赏判断的二律背反,其意味深长。在正题和反题中,作为“概念”的两者意义不同,在正题中,概念是一个知性概念,通过这一概念获得的是一种认识,审美不是知识论,因而不需要知性概念,因而正论是成立的;而在反论中,概念是一个“理性”的概念,是一个“超感性的纯粹理性概念”,这一概念是没有任何感性对象能与之相符合的,不能够感性直观,那么,这一“理性”的概念又该如何理解呢?
按照康德对审美的界定:鉴赏判断不是认识判断,不涉及概念,仅仅与情感的愉悦相关,是一种单称的情感判断,“鉴赏判断并不是认识判断,因而不是逻辑上的,而是感性的[审美的],我们把这种判断理解为其根据只能是主观的”(“判断力”37),在鉴赏判断中,其普遍必然性的根据只能来自于主体自身。这个普遍必然性上文已经提及是人类所具有的“审美共通感”,但这种所谓的“共通感”在康德这里还只能是一种假说,要想进一步地论证鉴赏判断的普遍必然性,必须将先验设定的共通感问题进一步提升,让这种假定获得一种“超感性的纯粹理性概念”的支持,这样鉴赏判断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也就是鉴赏判断的先验性问题就可以得到最终的解决。康德在这里请出来了超验的“理性”概念作为鉴赏判断的先验依据,把它作为鉴赏判断普遍必然性的确立依据。康德说:“鉴赏判断必须与不管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发生关系;因为否则它就绝不可能要求对每个人的必然有效性。但它又恰好不是可以从一个概念得到证明的,因为一个概念要么可能是可规定的,要么可能是本身未规定的同时又是不可规定的。前一种类型是知性概念,它是可以凭借能够与之相应的感性直观的谓词来规定的;但第二种类型是对超感官之物的先验的理性概念,这种超感官之物为所有那些直观奠定基础,所以这个概念不再是理论上可规定的”(“判断力”186)。鉴赏判断所依据的概念就是这种不可规定的超感官的先验理性概念,作为一种超感官的理性概念不能通过直观进行把握,但是却可以为感性直观的奠定基础。既然感官不能直接把握这种无法规定的理性概念,那么,这种理性概念又该如何去把握呢?
康德认为,概念的直观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图型法,这是对概念的一种直接表达方法,在时间先验形式的作用下先验范畴转化为图型,“图型”先验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成为人们认识的一个中介,连接着感性直观与知性范畴。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象征法,这是对概念的一种间接的表达方法,这是通过将象征物与概念的一种类比来表现概念的方法。“一切我们给先天概念所配备的直观,要么是图型物,要么是象征物,其中,前者包含对概念的直接演示,后者包含对概念的间接演示。前者是演证地做这件事,后者是借助于某种(我们把经验性的直观也应用于其上的)类比,在这种类比中判断力完成了双重的任务,一是把概念应用到一个感性直观的对象上,二是接着就把对那个直观的反思的单纯规则应用到一个完全另外的对象上,前一个对象只是这个对象的象征”(“判断力”200)。在《判断力批判》第一导论中,康德认为“知性直观”是必要的,通过“知性直观”可以达到对物自体的认识。这种“知性直观”不需要通过“图型”来加以连接,而是“艺术的方式”来加以类比,“艺术的方式”就是一种象征的方式。在鉴赏判断中,由于反思判断力从规定的判断力中分离出来而有了属于自身的先验原理——“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根据反思判断力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的原理,人们在对自然的对象的鉴赏判断中“看”(直观)到一种理念,这就是对象形式具有合目的性的要求,因而这种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需要一个“超感性的基础”,这是一种“象征”式的把握方式,在鉴赏判断中人们通过象征把握到这种无法规定的超感官的理性概念——道德(实践理性),因而康德提出了他伟大的美学命题“美是道德的象征”。
可以看出,康德通过鉴赏判断的二律背反最终解决的问题是为鉴赏判断寻找普遍必然性的终极根据——理性概念,在这里理性概念是一种不确定的概念,是人们无法通过知性的范畴加以把握的,而是通过“知性直观”“象征”地把握到这一理性概念——“道德”,从而为鉴赏判断寻找到先验的终极依据。
总的来说,康德对鉴赏判断先验理据的追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波三折,首先要解决的是鉴赏判断何以是先验的这一基本问题,为其目的论寻找先验原理。其次,通过对鉴赏判断的先验演绎,在人的心意状态中寻找鉴赏判断的先验依据,康德找到的是“审美共通感”。由于“审美共通感”是一种假设,要确保鉴赏判断的普遍必然性,必须要为其寻求终极依据,康德在鉴赏判断的二律背反中寻求到鉴赏判断的终极依据,这就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超感官之物的先验的理性概念”,也就是康德所强调的“实践理性”,最终得出康德对鉴赏判断的判定结论“美是道德的象征”。
注释[Notes]
①对《观察》一书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在拙著《康德美学中的自然与自由观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做了详细的说明和探讨,详见62—67页,这里不再赘述。
②关于这一论证过程可以参阅拙文“审美共通感”,《外国文学》3(2011): 122—29。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Kant, Immanuel.Kant: One Hundred Letters.Trans.Li Qiuling.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6.]
——:《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Trans.Deng Xiaomang.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判断力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Annotated Version).Trans&Annotatation.Li Qiuling.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1.]
——:《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nnotated Version).Trans &Annotation. Li Qiuling.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1.]
——:《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Works of Kant.Vol.5.Trans.Li Qiuling.Beiji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7.]
威廉·文德尔班:“判断力批判科学院版编者导言”,《判断力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Windelband, Wilhelm.Preface.The Critique of Judgment(Annotated Version).Trans &Annotation.Li Qiuling.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