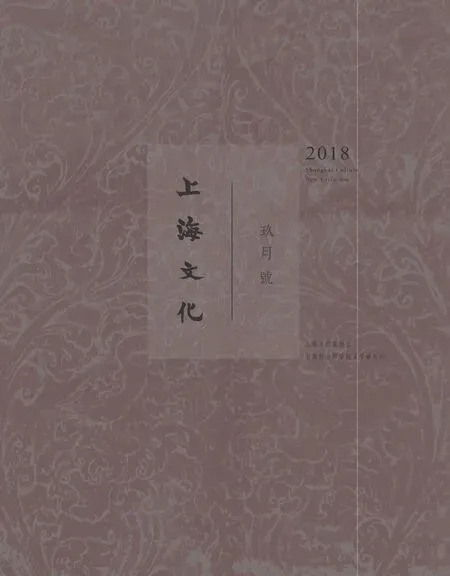“四子”的隐显和出处论《庄子》中一个师生组合
张文江
如果采取比较开放的读法,《庄子》全书,也可以看成一个戏剧大舞台,有众多人物在不同场合中出入。这些人物纷纷扰扰,彼此关联,呈现出奇妙的变化。其中有一个师生组合,细检其数据统计,会获得有益的启发。这个师生组合的成员,在《逍遥游》中首次出现,当时称为“四子”,没有说出姓名。全体姓名出现在《天地》,是本文依据的分析线索。原文如下: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 窅然丧其天下焉(《逍遥游》)。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天地》)。
首先作一些简单的解释:
一、四子。在《庄子》中,“四子”总共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虚指,即上引《逍遥游》。郭庆藩《庄子集释》引《释文》:“四子,司马、李云:王倪,啮缺,被衣,许由。”此注可以接受,次序当有所调整。从下文可以看出,《天地》排列的次序,不应该轻易颠倒。一次是实指,见《胠箧》:“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集释》于前注云:“四子本无其人,征名以实之则凿矣。”于后则无注。通观全书中“二子”、“三子”的称谓,皆对应具体之人,没有落实的只有此处。尧对四子深致景仰,司马彪、李颐等注家审察文意,以许由、啮缺、王倪、被衣相应之,完全合情合理。
二、出处谓进退,相关于隐显或默语。《周易·系辞上》:“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正义》孔颖达疏:“言同类相应,本在于心,不必共同一事。或此物而出,或彼物而处;或此物而默,或彼物而语。出处默语,其时虽异,其感应之事,其意则同。或处应于出,或默应于语。”
开宗明义,坚决划清的这道界限,是哲人与王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也是永远的向上引领
检索《庄子》全文,四子出场的次数如下:
许由7次,啮缺5次,王倪3次,被衣(或蒲衣子)2次。
这个师生组合之中,大体上认知程度越高,出场次数越少。在四人中,许由也出现在先秦其他典籍中(《吕氏春秋·孟夏纪·尊师》:“帝舜师许由”;又《慎行论》:“昔者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请属天下于夫子。”《荀子·成相》:“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传说(《史记·伯夷列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其余三人作为许由之师,应该是庄子点染的寓言人物。分析四人的隐显和出处,包含深刻的哲理。试逐段讨论:
一、许 由
1、《逍遥游》开篇不久,许由就出场了。尧对许由非常推崇,主动让天下给他,许由则坚决拒绝:书对三种人的指向(即天人、神人、至人,参见拙稿“《庄子·天下篇》讲记”)。以古希腊观念而言,许由逃尧以逃名,是因为哲人王的组接,几乎不可能(参见《理想国》473c—d,499b—d)。如果欢欢喜喜地组接成功,哲人的本性就丧失了。《逍遥游》论“神人”有云:“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那些人居住于藐姑射之山,远在天边,对世间事务不感兴趣(哲人和神人、至人的同异,另外分析)。庖人是国家的管理者(参见《老子》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尸祝从事于精神领域,两者各有职责,不可互相替代。
开宗明义,坚决划清的这道界限,是哲人与王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也是永远的向上引领。
2、《大宗师》接近结束的时候,许由有一段教育意而子的话。此段言辞发挥道家精义,是许由的见地所在,单单只是逃尧,不足以成为“四子”之一。其中“吾师乎!吾师乎!”一段,在《天道》中又出于庄子之口,是全书完全认同的理论: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以不合作姿态出场,主要行动为逃尧。贬低尧以抬高许由,表示了《庄子》全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意而子曰:“虽然,吾愿游于其藩。”许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意而子曰:“夫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炉捶之间耳。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许由曰:“噫!未可知也。我为汝言其大略: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
意而子是古之贤士(据《释文》和成玄英疏),许由教导意而子是往下讲(或往外讲),虽然精妙无比,却不自觉地扩大了名声。此段文意深邃,仅仅把许由定名为隐士,对其思想有所遮蔽。
3、《天地》四人出场,当另外讨论。许由扮演特殊的角色,他和尧有直接的接触。
4、《徐无鬼》。许由遇啮缺论逃尧,可见外界的传说,有其事实根据。许由和自己老师的对话,属于内部讨论。本节对尧的批评,也见于《庚桑楚》,真是惊世大预言:“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夫民不难聚也”云云,包含对民之本性的洞察,深刻而亲切。“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痛快淋漓,早已道出真相。“外乎贤者”指超越贤者之人,许由等“四子”都在其中。
啮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将逃尧。”曰:“奚谓邪?”曰:“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犹一覕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
5、《外物》。用其他人口气叙述:“尧与许由天下,许由逃之。”
6、《让王》。同样是一般陈述:“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云:“故许由娱于颍阳。”
7、《盗跖》。依然如此:“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
5、6、7三段意义相近,并无精义妙论,只是重复许由的隐士形象。可见他名声在外,是大众观瞻的对象,已成为类型化人物。
啮缺喜欢哲学思辨,思想比许由深刻,所以成为许由的老师。然而,长处即是短处,不知沉迷于思辨,依然还是局限
二、啮 缺
啮缺喜欢哲学思辨,思想比许由深刻,所以成为许由的老师。然而,长处即是短处,不知沉迷于思辨,依然还是局限,有待于进一步上出。“四子”从啮缺开始,上及王倪、被衣,所有讨论都发生在师生内部,此现象值得深思。啮缺五次出场,一次向上和王倪,一次通过王倪请出被衣(用“蒲衣子”的名号)。一次向下和许由,一次越过许由引起尧的注意。最后一次,没有王倪的中介而直接见到被衣,到达此一组合的最高处。
1、《齐物论》。三问而三不知,啮缺问的都是后世的哲学问题,可见他有思辨的爱好。这些问题很深刻,却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对于他的问题,王倪的回答是“吾恶乎知之”,以化解其亢。讨论的最后归结为至人,犹《大宗师》“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且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啮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至人神矣”的惊叹,隐含“至人”和“神人”的联系。《逍遥游》提及“四子”在“藐姑射之山”,那里恰恰是“神人”的居处。
2、《应帝王》。四问而四不知,似乎与《齐物论》相同(成玄英疏)。其实四问已成空位,可以用任何终极提问来填充。此一问答中,啮缺已完成抽象,认识发生根本性突破。“因跃而大喜”,身心间阻力得以消除,对《齐物论》中王倪指向的“至人”,已有具体的感受。由此上出,才见到老师的老师——被衣。最后讨论的问题极深,涉及政制的生物根源。此讨论发生在三人之间,可以说身居云端的极高处。名声在外的许由被洗去,没有获得参加讨论的资格。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3、《天地》。四人出场,另外解说。
4、《知北游》。啮缺见被衣,是四子讨论中最深的一段。《应帝王》由王倪的过渡而见到被衣,此处则直接见到被衣。内容由《应帝王》的外王,而至《知北游》的内圣,放在最后解说。
5、《徐无鬼》。啮缺问许由,是他唯一的往下问,许由也因为面对的是老师,谈得比较放开。其余三次都是往上问,一次比一次深。他没有保护好信息泄露,之所以被尧看见,非常可能是因为擅长思辨,引起君王的关注,所幸得到许由的适时掩护。
三、王 倪
1、《齐物论》。和啮缺讨论,是王倪唯一的正面发言。在全书中其余地方,他都是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有“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老子》四十一章)的风范。点出“至人”的指向,也是《庄子》的指向。引文见啮缺1。
2、在《应帝王》中他没有说话,与《齐物论》同而不同,由言而归于默。引文见啮缺2。
3、在《天地》中提到,而且可以被尧差遣,推测他处于僚属之中,已成功隐身。尧只知道他一般的好,而不知道他特殊的好。许由知道他特殊的好,当然不会揭穿。他是好的老师,也是好的弟子。和啮缺的两次交流,一次有言,指出向上的引领,一次无言,引导身体的发动。他能见到被衣,却始终未见交流,有些像颜回“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他第一次把啮缺引向被衣,第二次讨论中未见其人影,隔而不隔,功成身退天之道。引文另外解说。
四、被 衣
许由身处颍滨,啮缺在尧的视线之中,王倪位于臣列,大隐隐于朝。而被衣出场仅两次,没有描写具体的时位。以名号而言,被衣者,披衣也;而衣者隐也(《白虎通·衣裳》)。在《天地》中他被借用了一次名字,实际上没有出场。他的两次说法,一次安抚形而谈外王,一次安抚神而谈内圣。谈外王时洗去许由,已经极度秘密了,但还是借用“蒲衣子”的化名,加上一重保险(钟泰《庄子发微》云:“被、蒲一声之转”)。《庄子集释》引《释文》:“蒲衣子,《尸子》云:蒲衣八岁,舜让以天下。崔云:即被衣,王倪之师也。”尧时为王倪之师的被衣,不可能在舜时八岁,应该是后来人的捕风捉影。谈内圣是他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教育啮缺,因为王倪已不需要教育,或已不需要用语言教育。
1、《应帝王》,引文见啮缺2。
2、《知北游》,放在最后解说。
理解了四子的大致情况,可以来读《天地》全文: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尧问于许由曰:“啮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啮缺之为人也,聪明睿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与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知而火驰,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絯,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虽然,有族有祖,可以为众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师和友不同,友彼此砥砺,莫逆于心(《大宗师》述及子祀等四人相与为友,又有子桑户等三人相与为友)。师与弟子之间有差等,既有其相知为显,也有其不相知为隐。隐显互为阴阳,可示意上出的路线。《天地》排列的次序,在全书中仅此一处,也是本文成立的依据。
师与弟子之间有差等,既有其相知为显,也有其不相知为隐。隐显互为阴阳,可示意上出的路线
“啮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配天”,位于天人的顶端,指受天命为天子。尧已知许由是高人,目力极致可到达啮缺,而对身边的王倪则若知之、若不知之。尧于许由“自视缺然”,于啮缺惊其“配天”,而王倪的程度更高,尧却信任而未能识别。判断王倪居于僚属之位,已成功隐身。
“殆哉,圾乎天下!”许由尖锐地批评啮缺,指出其缺点,同时为其遮掩。如果真像他说的那么不堪,哪里还值得被尊为师?圾,岌。危险啊,天下岌岌可危啊。“啮缺之为人也,聪明睿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他为人聪明,反应迅速,能力高于一般人,恃才智勉强行事。“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他严厉地制止过错,却不知其来龙去脉,往往治标不治本。
“与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如果他当最高领导者,很可能胡作蛮来,因为他不知道人不能违反自然。“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知而火驰,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絯”,他急于应对不同的情况,崇尚巧智而无法收敛,被千头万绪牵着鼻子走,深受外物的束缚。“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物不能忘我,我也不能忘物,随外物变化而不能有恒。参见马王堆帛书《易》:“易有大恒。”《论语·述而》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
“虽然,有族有祖,可以为众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他还是学有本末的,用于局部或许有效,施于整体则危害天下。参见《老子》二十一章:“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父、甫通假,帛书本作父。徐梵澄《老子臆解》:“众父今语则当言‘万有’或‘万事万物’(事亦物也)。”众父父可当事物之根源,万化之大宗。“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治、乱都由他而起,当臣下也是祸害,当君王也是灾难。
“四子”的共同出现,在《庄子》中有两次,留下了解读的线索。一次隐而显(《逍遥游》),点出他们所在之地,是“藐姑射之山”,好比古希腊“乌托邦”(Utopia),在无限高远的非有之处。一次显而隐(《天地》),排出师生的高低位序,以画外音作提示,只有四子本人和读者知道,而包括尧在内的其他人都不知道。
除了这两次,四人从来没有同时出场。和社会有所交流的人是许由,主要对象是尧和他的追随者。啮缺被尧看见是其失,而仅仅被尧看见,又不能不说是其得。在“四子”的组合中,尧始终没有提到被衣,大概听都没有听说,也许因此被认为是舜时之人吧。被衣神龙见首不见尾,盖已入化境。
其余所有的活动,都是在师生之间。三人出场的有两次,《应帝王》一次是内部讨论,许由被洗去。《天地》一次是外部讨论,被衣未提及。二人单独讨论的次数较多,先后有许由、啮缺;啮缺、王倪;以及啮缺、被衣。检查其间所缺的链条,许由自始至终没有见到王倪、被衣,可见上出有一定的阻力。而王倪和被衣之间,彼此没有讨论,应该已不需要讨论。
尧是否终于见到“四子”呢?回过头来,再次细读篇首的引文。《逍遥游》记述,尧在完成治理天下以后,“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藐姑射之山”,据《释文》谓“远在北海中”,远在天边;“汾水之阳”,据成玄英疏即尧都,则近在眼前。注家由此讨论是否为两姑射,或谓先赴藐姑射之山,还归汾水之阳。本文将“往见”理解为上出,两处相通,出入无疾,有天下而未尝有,故“窅然丧其天下焉”。
在城邦之外,“四子”皆已成就,其身位为“神人”。在城邦之内,“四子”出处不同,在程度上有所差别:想见到啮缺,至少要到达许由的程度。想见到被衣,至少要到达啮缺的程度。那么,被衣的教导是什么呢?
至此可读《知北游》原文:
啮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
“正汝形,一汝视”、“摄汝知,一汝度”,乃道家的修养方法。可比较儒家“非礼勿视”的“四勿”(《论语·颜渊》)。后世或以为庄出于孔门(参见方以智《象环寤记》、《一贯问答》),当注意其相通的契机。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正汝形,一汝视,是忘其形体耳目也;摄汝知,一汝度,是去其思虑意识也。”“天和将至”、“神将来舍”,犹感应道交,体之于身。“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犹《大学》“富润屋,德润身”,又《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眸子清亮,反本还原。《孟子·离娄上》:“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无求其故”,破除所知障,乃得新生之气。
言未卒,啮缺睡寐。被衣大说,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足为患。“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有微观空间之交流,获取能量、信息的补充。“彼何人哉!”犹道家所修之本尊,彼者此也,此者彼也,乃成其象。此修法相对柔和,一旦沟通,其象可随进境逐步变化,所谓“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是也。
“啮缺睡寐”,乃休息之象,收视返听,惝恍入神,《楞严经》卷四所谓“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前文“因跃”而入命功,此处“睡寐”而入性功。被衣大说,行歌而去,乃道家风范,师弟交流,彼此亦无沾恋。“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庄书中屡见,为必经之境。“真其实知”,“实”犹“充实”,“真”再加提炼。并用“真实”二字,后世所谓“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五灯会元》卷五药山惟俨章次)。“不以故自持”,即上文“无求其故”,随世沉浮,与物俱化,江湖风波,或不
❶ “二子”有四例:1、《达生》谓单豹、张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2、《庚桑楚》谓尧舜,“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称扬哉!”3、《让王》谓伯夷、叔齐,“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4、《盗跖》谓王子比干、伍子胥,“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
“三子”有二例:1、《齐物论》谓宗、脍、胥敖:“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2、《齐物论》谓昭文、师旷、惠子,“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