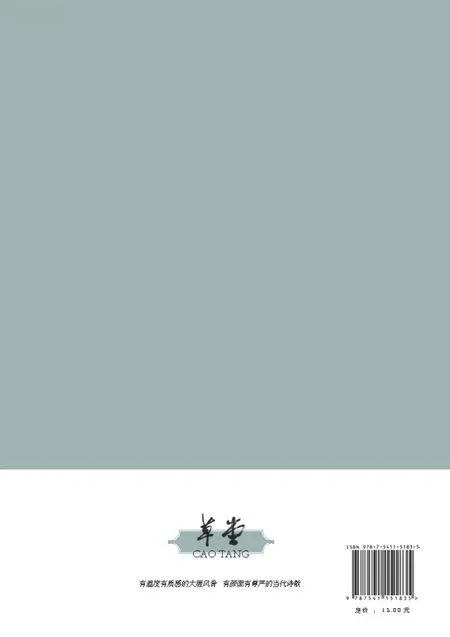求诸野(组诗)
马 嘶
在宿迁与敬文东夜饮
杯中见你,险饮为京城浩渺。半醉中
你脱口“斯文”一词。谁还配拥有?
寒雾佐酒。花海情欲奔突
年轻博士夸夸其谈。我们只管酣饮、啜饮
补饮……我们使用旧的嘴唇,身体里
荒废的米仓古道,寡言,慢条斯理
剑阁山高,巴河水长
仿佛我们在绝处,对饮了三百载
在省略失败者的时代,今夜我也
像你“意外饮得了一个虚胖的中年”
文东兄,乙亥大暑,蜀州,无根山下
再饮。见你是你,“见我当然还是我了”
戊戌八月十七日午后
流水反复照我,倦色
挂满天边,浑浑
噩噩。蟋蟀古调独弹,只留我一人聆听
音色如针,听得背脊发凉
那逝去的记忆再度
宽恕我
重温了片刻
午后桂花飘落时的鹤鸣
在眉州
就常识,而陷入争论
于今日轰鸣太多
回乡下,秋风中写诗
暴雨里临帖。祈阅后即焚
在沟洫中漫游
是哀鸿,搀扶着我,虚弱
如首新诗。正确的教育一直是
草木替我接受和领会
并冠以律法和经书
统领终生,而不敢妄自享用
目送岷江滔滔
还是子瞻兄啊幸运于我
坍塌的老宅
近四十年来,我第一次看见光
击破屋顶,在卧室砸出一口深井
屋后的香樟,与父亲同龄
光,同时卸下了它的半只手臂
幼小的老鼠掀起瓦砾上的灰
我内心的高楼在坍塌中早已重建
再过几年,高铁会从屋顶穿过
会再一次遮住光照耀的地面
而离开老宅的光体,在任何时候都会投向
无力的深渊,和幽闭中对于光的格外想象
求诸野
崖下枯坐,山川未能重新赋我衣钵
心有不甘,数日,数月,又数年
须眉垂坠光隙,石头开出花朵
我伸出的枝条穿过了白云
承认一生徒劳并不是一件不体面的事
明月照我一半身躯,另一半被山泉冲走
借时光之名,等逝者重返古松郁葱
——仿佛是我离去了很久
唯枯朽人间,还奴役着
故我,如新鲜的我
草木在体内发出哀鸣之声
但这已经不是我哭过的世界
在布拉格
乞丐的神色,等同于烤面包卷和落日
——我向卡夫卡比画着手势
这样也安慰自己,似乎我们同处在你那个
或我这个时代。在这里,谈论假象
也谈论我们的故乡。困境和绝望没有
减少,欲望也没有降低
甲虫爬行在大地
桥头的新人与水中的游鱼
互换了鳃,飞跃在波光粼粼的水面
山顶的城堡在暮色中漂移。嘿
老卡,我认同你说的
生命的意义,在于停止
夜宿青城山
黑袍里装满了星光,银色的风
抚摸着山脊
读枕边《列御寇》,孔子曰:“凡人心险
于山川。”这话
我并不认同
相反,真正令人心险的是我几十年来
在书房里没日没夜地伐木造船,偷渡在
字里行间
——那有着受驯,圣徒般的戒律
也有反叛者
时刻露出豹子尾巴的意志
与蝉说
每当我回到书桌前
你如影相随
并铺开群山和森林
仿佛我生活在另一种假象中
耳内的风,拍打着海浪和礁石
唯有我疲于奔命的时刻
你才躲得远远的
藏匿于撕裂我的暗地
我感受到了叠加的轰鸣
这些年,在自我的浮力中
写诗不超十行,读书不过半页
我的虚弱不止五月
树叶沙沙
如有神谕
冶勒雪
湖岸那顶灰色帐篷
安静地坐在蓝镜子身边
水面空囊如渊。微风吹过
轻盈的人,坠入白云间
朝圣的绵羊从雪山回到穹隆之下
暮色面露悔意
旷野回荡的,今夜是赞美诗
明日是送别曲
中年的暖阳
蜷缩在藤椅上的母亲
睡着了,像婴儿
阳光包裹着她
同样包裹着一旁的爱人隆起的腹部
年近不惑
我是一个儿子
也即将成为一位父亲
盛夏一来
只能是我的手
才可以翻越虎园的高墙
才可以摸向“黑夜那厚实的背脊”
养蝉的人
在耳中养蝉
并把时令保持在盛夏
是我近年在城市潜心修炼的
一门独家技艺
养得最久的有十七年
它们跟我活在千丘湾的时间一样长
破土而出、羽化成虫
在腹部装进一面大鼓,昼夜击之
——那是求偶的靡靡之音
也是食虫兽到来之前的恐惧与哀吼
而我现在
不过是固执地
延长着这生命的战栗,和杀机
·创作谈·
就写作而言,不论纳博科夫所说的“大作家无不具有高超的骗术,不过骗术最高的应首推大自然”,还是车前子“诗不是发现,它是发明”的观点,以及雷平阳“苦练屠龙术”的追求,都让我保持好奇。正如去年以来我常常待在一个叫无根山的地方,在山前我改建了一个乡村书院。一座古蜀州不知名的矮小的山,在千年前被谁命名?当年陆游步履于此和它交谈过些什么?我与它重逢在光阴之轴,重逢在汽车、无人机、铁皮屋和智能手机的时代,我为之着迷的是,我们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相遇?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交流?开门见山的景象中使我一次次穿梭在虚无和现实的两个世界,令我出神的一定是门前躬耕良田的身姿,一定是光在大地上的挪移,而绝不是那访客中“大人物”的律令。
为此我花了很长时间重新求之诸野和格物致知,一边疾驰在高楼的裂隙中,在谈判桌上振振有词、咄咄逼人,一边徒步于旷野、山谷和山林,在乡邻、蛙声和蝉鸣中失语,我试图打破两处的壁垒,让它们握手,生成出一种异质的拥有自己姓氏的诗歌。如何在我身处的无效的时间里找到自己有限的精神谱系,如何在古老的汉语中焕发在场的当代性,万物入诗,而脱离于诗,使我困顿、盲目,又乐此不疲。那驳杂、荒诞、不可告人和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那莫测、深掘的难度和毫无法度的自由,总会给我带来全新的兴奋,也带来深深的失望。我想,写诗对于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