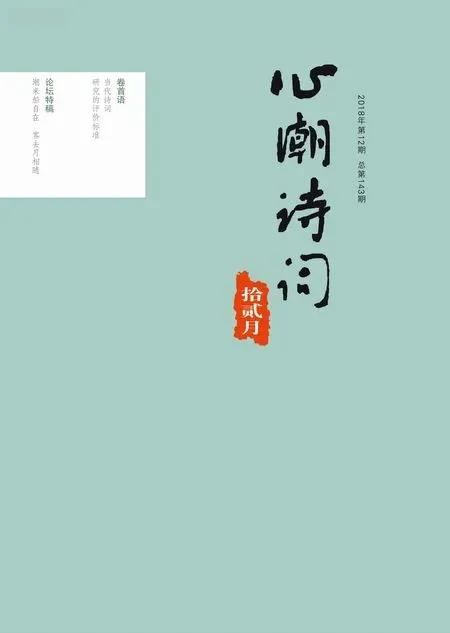星汉新边塞诗《天山韵语》平议
为诗人星汉赢得“当代岑参”这一称谓的,当然是他的诗集《天山韵语》中所收的那些成色上佳的新边塞诗。《天山韵语》,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一印1000册。该集作品按年代先后编排,起于1976年,迄于2005年,收各体诗作156题159首,词作34首,共收诗词193首。前有作者女公子王剑歌“序”,后有作者“后记”。星汉,本名王星汉,字浩之,1947年5月生,山东东阿人。12岁随父母进疆谋生。17岁参加铁路工作,为学徒工、信号工,历时13年。1978年考入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为中华诗词学会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新疆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现任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新疆诗词学会执行会长、中国散曲研究会理事。有学术著作和诗集《清代西域诗研究》《天山东望集》等20余种行世。
一
《天山韵语》如集名所示,内容构成主要是吟咏天山南北新疆地区的自然风貌、民族风情,兼及历史遗迹、人文景观,是一部地域色彩十分鲜明的当代旧体诗词集。作者少小投边,几十年的岁月里,放足天山南北,几乎走遍整个新疆地区,这从该集作品的标题即可见出,诸如《游天池》《丝绸古道偶成》《赛里木湖所见》《奎屯路上》《交河故城》《吐鲁番过火焰山》《五家渠路上》《巴克图路上》《赛里木湖》《伊犁河感怀》《过乌孙山》《过昭苏草原》《轮台路上》《过阿克苏河》《重游克孜尔千佛洞》《过阿尔泰山》《游喀纳斯湖》《题和田核桃王》《宿北庭故城》《过巴音布鲁克草原》等等,新疆各地的风景人情无不为作者所摄取。从这个角度看,该集也可以说是一部新疆地区记游纪行诗词集。
作者在表现雪山、冰川、戈壁、沙漠、草原风景的时候,在表现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民情、衣着长相、劳动方式、饮食习惯的时候,其实有两个潜在的参照系、两个潜在的参照视角:一是内地,二是江南。作者所着力凸显的,正是内地、江南与边地、西域的差异。在差异中,显示出新疆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这几乎是一种潜意识活动,但却无疑在最深层次上支配了星汉的全部边塞诗创作。作者笔下的这些自然风景,是内地寻常看不到的:“一鹰惊去疾如箭,射落残阳一捧红”(《丝绸古道偶成》),“一片板桥残月,几堆鄂博轻幡”(《西江月·喀纳斯河畔》),“沉静两山开碧落,奔忙一水送金雕。穹庐帘启青苍入,花草风来赤白摇”(《沿喀纳斯河》),“怒吞落日地将裂,狂扯飞云天欲倾。万里黄沙聚复散,千年白草死还生”(《过魔鬼城》),“长牵瀚海胡杨路,远借冰峰夕照天”(《庚辰秋重游水磨沟》),“塞外新秋,我又重来,笑倚雪山。正冰峰直上,青天湛湛。瀑流倾下,白浪悬悬。荒草拦腰,闲云遮路,不放游人再溯源。回眸处,瞰松林毡帐,犬吠雕盘”(《沁园春·重登喀纳斯湖观鱼亭》),“敲石马蹄冲寂静,破云鹰翅掠苍凉。清愁都阻穹庐外,一片残阳抹大荒”(《过巴音布鲁克草原》)“未歇红花,未老黄花,已放雪花”(《沁园春·癸未重九初雪晴后赋此》)。作者笔下的这些生活场景,是内地寻常看不到的:“驴车归处,炊烟渐起,葡萄新熟”(《桂枝香·高昌故城怀古》),“掀帘少妇抬头处,景色都收蒙古包”(《山中雨后》),“坦腹巴郎游泳后,拖泥带水笑骑驴”(《开都河农家小坐书所见》),“试马柳荫扬策,捉羊河岸开刀”(《西江月·喀什巴扎》),“崎岖山路尽,木屋自成群。奶茶新碗溢,羊肉大炉焚”(《白哈巴村小驻》),“系马穹庐外,围炉酒正酣”(《癸未冬游天山水西沟》),“葡萄架下煮砖茶,写字巴郎带看瓜”(《伊犁农家》),“避日行人来饮马,长天风过笑声憨”(《戈壁即事》)。作者笔下的这些声音,是内地寻常听不到的:“弹唱声中草色青,牧人马背拄颐听。多情阿肯未终曲,俯看湖中云已停”(《巴里坤湖边观阿肯弹唱》),“短笛风低荒草,大杯酒映新秋”(《西江月·喀纳斯湖听潮尔笛》),“知无人到喇嘛睡,时有清风误撞钟”(《昭苏圣佑寺》),“惊人何处泼天雨,却是松涛笑欲癫”(《松下偶眠》),“山骨高撑千仞外,苍鹘一声遥没”(《念奴娇·登铁门关楼》),“鞍桥稳坐牧鞭指,夕照群羊渡水鸣”(《托什干河即目》),“日夕牛羊下,月高儿女歌”(《游乌什柳树泉夜宿》),“草野翻边曲,松涛走戍鼙”(《宿天山緑野山庄》),“黑石高堆舞彩旌,夕阳垂地起边声”(《过乌伦古湖祭鄂博》),“莫道归程多寂寞,穹庐外有马蹄敲”(《天山水西沟夜话》),“石裂有声频入耳”(《己卯夏登冰达坂》),“星坠冰峰裂有声”(《寻他地古道,宿天山大龙沟口》)。作者笔下的这种长相妆扮,是内地寻常看不到的:“树荫碧染络腮胡,一马轻蹄意态舒”(《吐鲁番书所见》),“碧眼银须飘拂处,胡杨木火烤鱼香”(《尉犁罗布人村寨书所见》),“过街长辫步如舞,饮酒虬髯杯似浇”(《过库车》)。作者笔下的这种风味气息,是内地寻常闻不到的:“毡帐白烟红日远,奶茶香味阻征程”(《过和布克赛尔草原》),“水去游人流影俏,风来烤肉带歌香”(《自京归后次日登红山》),“牧人归处斜日晚,一缕清风马奶香”(《果子沟》)。作者笔下的这些路遇,是内地寻常不可能发生的:“相逢哈萨克,闲话夕阳迟”(《快活林》),“晴烟遥指处,毡帐又新家”(《南山遇哈萨克老牧人闲话》),“新货囊装握牧鞭,马缰轻勒跨归鞍。重逢我问新居地,笑指松青云起山”(《巴扎逢哈萨克牧人》)。以上这些斑斑可数的描写,都为内地读者提供了不曾寓目的异域风光,不曾领略的风俗民情,强化了作品的地域风格特色,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与吸引力。
潜在视角虽然隐藏于潜意识中,但也有浮出的时候,比如《咏沙枣花》二首之二:“不羡春风桃李枝,揺香莫道此时迟。离人赠别何须柳,沙枣攀来慰远思。”中原自古以来有折柳送别之习俗,这里写赠以沙枣花,正见出与内地不同的地域民俗风情。《过魔鬼城》云:“冷雨热风经此城,登高四顾一身轻。怒吞落日地将裂,狂扯飞云天欲倾。万里黄沙聚复散,千年白草死还生。纵然西去再西去,不羡江南莺燕声。”《石河子北湖观鱼亭二首》之一云:“春光此地旧曾谙,四望新秋意又酣。白雪山头红日压,蓝天云影碧波涵。棉田恋我犹怀抱,雁阵随风正漫谈。景自豪雄心自壮,何须出语比江南。”上引两首诗的尾联,两处出现“江南”意象,虽云“不羡”“何须比”,西陲的狂风松涛自异于南国的莺吭燕舌,边塞诗中的盘空硬语自异于南国词中的秀媚软语,但江南盘踞胸臆,形成览景观物志感时挥之不去的参照视角,亦属显而易见。《石河子北湖观鱼亭二首》之二云:“石城北望路深谙,湖荡清波饮已酣。踉跄雪山能倚赖,粗疏原野尽包涵。掌收落日休轻放,胸纳回风可畅谈。又见横秋远征雁,心随健翅欲图南。”此诗终于借远征雁翅,道及荒寒之地居留者的“图南”深层心理。归根结底,潜意识中可能还是觉得山青水绿、风景如画的“江南好”。作者一不小心之间,透漏了些许企羡江南的隐秘消息。
二
该集中的咏史怀古、登临凭吊之作,也值得特别拈出。《登额敏塔》《交河故城》《临江仙·登巴克图瞭望塔望域外》《桂枝香·高昌故城怀古》《念奴娇·伊犁河感怀》《满江红·登格登山》《苏木拜河西望》《登惠远钟鼓楼评志锐》《香妃墓》《水调歌头·临霍尔果斯河》《重登格登山》等都属此类作品。不消说,这类作品中满溢着作者的盛衰兴亡之感叹,如《桂枝香·高昌故城怀古》所写:“残城故屋。展历代兴亡,教我披读。闻说车师五战,山凝遗镞。法师驻马谈经日,纵肠空,气通天竺。侯姜威猛,戈挥雪止,马蹄轻速。 登临意,如城高筑。借莽荡边风,输情千斛。远望荒原一抹,无言翻绿。斜阳泼血依山久,见流霞天外如瀑。驴车归处,炊烟渐起,葡萄新熟。”除了盛衰兴亡之感叹,便是这片特殊的地缘所唤起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如《满江红·登岳公台步岳飞韵》所写:“人去台空,英雄气,冲霄未歇。豁眸处,远荒翻浪,晚风正烈。凝碧天山吞落日,扬尘大漠衔边月。看江山一统共金瓯,情何切。 马啮石,旗卷雪。千帐里,灯明灭。想戈挑泉出,剑挥山缺。盖地青松悬铁甲,接天蒲海盛忠血。使丝绸古道贯舆图,通京阙。”若依照通行的说法,上引词作中表现的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情感。对大一统的追求,对祖国领土完整的维护,对安边开疆的古代英雄豪杰的追怀赞美,对近代以来失去的领土难以割舍的牵念之情,是这些作品的主要内涵。再看一首《临江仙·登巴克图瞭望塔望域外》:
雪岭霞消碧落,春原草吐清波。牛羊背上夕阳多。炊烟缭绕处,是我旧山河。 一段人间老话,百年总驻心窝。南来征雁半空磨。随风犹北去,不去又如何。
这种情感横亘胸中,耿耿于怀,成了作者难以开释的强固的心结。大一统意识和家国天下意识,是传统士大夫文人的深度潜意识,该集作者显然也是念兹在兹。《登额敏塔》云:“彩云翻似向东旗,大漠金戈写史诗。登塔我来凝望久,蓝天尽处是京师”,仿佛古代文人“心存魏阙”;《赴京途中作》云:“轮台唐韵壮,送我玉关东。铁路车来啸,碧天鹰去空。群山抹残日,大漠鼓长风。收拾三千里,相携进故宫”,隐约似有“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之意;可能都是潜意识心理,在诗作中的不自觉流露。还有《谒尤素甫墓》:“西域多才俊,书开千古香。名声满宫阙,文采动君王。泉涌连思路,云来接翰芒。君看吐曼水,依旧续诗行。”颔联借对十一世纪维吾尔族诗人的赞美,折射一种以诗词文采干动天听的人生理想,这正是传统中国社会读书人的千古文人梦。
该集中的题咏诗也颇有可观。这类诗多是七言绝句,多用比兴寄托手法,一个自称“粗豪”、常以“雄豪”的超我面目示人的强者,在这类诗中不时回归本我,展示真实的面目性情,袒露真实的内心世界。这类诗作虽然使用比兴手法咏物,但借此手法传递出的往往是创作主体惆怅、忧思、困惑、感慨等较为个人化的心理情绪。佳者有《新疆铁陨石》《吐鲁番过火焰山作》《边塞清明》《坎儿井水》《过沙漠胡杨林》《经沙漠公路重到民丰》《昆仑山中拾得五彩石数枚,感赋》《泛舟布伦托海》《骆驼刺》《沿布尔津河赋向日葵》等。看一首《骆驼刺》:“根穿大漠向天争,每借逆风抒性灵。寂寞千年堪自慰,老来依旧愣头青。”这应是一幅托物寓己的自画像;再看一首《昆仑山中拾得五彩石数枚,感赋》:“深埋无语不知年,剖腹昆仑现大观。今日苍天何用补,依然西北伴寒山。”借赋昆仑彩石,发“弃材”之慨叹;还有《过沙漠胡杨林》:“飞沙起处任颠狂,自耐天涯四月凉。就简删繁也如我,苦撑诗骨向苍苍。”则喻示自己那一份时常刷在脸上的西部汉子的标准“酷”相,是“苦撑”出来的。于是便有了《望海潮·谒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墓》下片的心迹展露:“我来捧献心香。有诗情未老,意气犹狂。夜夜青灯,年年白饭,几人识得文章。囤货拜行商。纳贿争金印,君试评量。握笔明朝归去,依旧写苍凉。”在“犹狂”的意气中,流露出的是诗书生涯不谐于时的落寞苍凉之感。
内心的柔软处既被触及,《解连环·游千泪泉寄楣卿》《塔什萨依沙漠书楣卿姓名》《重游千泪泉》等纯粹私人化情感的抒写,也就为情所不免。看一首《解连环·游千泪泉寄楣卿》:“路平沙软。正蒹葭涌绿,小溪清浅。夕日下,身度春云,看冰泄雪消,石飞崖烂。一揖情生,思往事,血腾心颤。使悲风斜落,惊走群鸦,老树归晚。千年月光荏苒。奈人间儿女,尚萦幽怨。纵夜夜,魂托疏星,恨无赖天鸡,梦成虚幻。寄尽愁肠,却每每,薛笺嫌短。料这番,开书念我,泪泉万点。”透过词作追怀的伤心往事,可以窥见作为普通人的作者的真实而柔弱的人性悸动。由此联系《雪中五家渠郊外独酌》一诗:“独步频将野店敲,天山已惯酒杯浇。寒林风啸雪花舞,搅合诗情到九霄”,可知借酒助兴或者借酒浇愁,对久居边塞的作者来说,已是惯常,诗句亦豪迈,亦惆怅,亦无奈,亦凄凉,一旦卸下“雄豪粗犷”的超我人格面具,作者内心的真实感觉到底如何,在此已是不言而喻。该集末首《上元乌鲁木齐郊外泥饮,用荆公戏呈贡父韵》云:
纵是清光万里同,天涯无意待春风。
马鸣荒草河声外,人醉穹庐月影中。
寒树能扶青眼客,雪山莫笑白头翁。
心随大野长流韵,不向东君怨不公。
此作虽亦写景,但主要目的应是写心,首尾两联,透漏出作者感慨命运的深度心理。曰“无意”,曰“不怨”,不过以旷达聊作排遣而已。作者以此首为诗集殿后压卷,当有深意存焉。
三
在《天山韵语》的诗词文本中,出现最多的意象是鹰雕、雪山、冰峰、大漠、黄沙、驼铃、马蹄、牧人、牛羊、草原、穹庐、落日、残阳、红柳、胡杨、沙枣等,这些地域性鲜明的意象构成的景物画面,具有某种不可移易性。如《克孜尔水库》前两联“西指龟兹路,大堤横巨垣。高收千岭峻,远纳五河喧”,所写是西域高原、龟兹古道旁的大型水利工程,这个水库满蓄木扎提河、喀普斯浪河、台勒维丘克河、喀拉苏河、克孜勒河五条河流之水。再如《游克孜尔千佛洞》:
胡杨树下暂停征,东望龟兹一日程。
碧水长流接天渺,黑雕直起与云平。
石门彩画窟风冷,古寺青崖夕照晴。
指点南山春草绿,穹庐归骑牧烟轻。
汉魏以降,佛教传播日广,洞窟开凿各地多有,但有“胡杨、黑雕、穹庐、牧烟”等意象在场,有“东望龟兹一日程”的地名里程时限,这一处佛窟就有了确定无疑的地域归属。又如《过沙漠公路》:“今日有劳方向盘,迷濛划破指和田。远沙风里推千浪,大路空中挂一弦。喇叭鸣时冲碧落,日球坠处溅黄烟。昆仑山下良朋待,夜煮冰川火正燃。”所写的是西域沙漠公路风景,“和田”、“昆仑山”的地名,“远沙风里推千浪”、“日球坠处溅黄烟”、“夜煮冰川火正燃”的戈壁沙漠景观,断不可移作它处看觑。再看一首《天山阿尔萨沟小饮》:
相逢初歇马,毡帐便传杯。
雕翅卷云过,松梢唤雨回。
千山收乱水,一涧放轻雷。
天外虹霓起,弯腰远作陪。
虽曰“毡帐小饮”,亦复豪气干云,与古典诗词中经常写到的长亭饯别之类“帐饮”的缠绵感伤,大异其趣。要之,该集诗词撷取的是边塞风物,不是内地风物;是西北边塞风物,不是其他边塞地区风物;是新疆天山南北风物,不是西北陕甘宁青边地风物。该集不可移易的地域风格,鲜明特色,突出个性,就体现在这里。
该集诗词的主体风格是豪迈雄奇。这种风格几乎渗透在作者摄取的所有题材里面。这是他的《沿额尔齐斯河》:
拘束城垣久,今朝可放歌。
紫雕盘大漠,红日逐长波。
晴雪峰头远,雄风马背多。
行行尽诗句,不必费吟哦。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奧府。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得江山之助乎!”今观星汉此诗,正是“得江山之助”的形象写照。雪峰大漠,紫雕红日,马背雄风,即目所见无非是诗,这俯拾皆是、不费吟哦、自然得来的“诗句”,风格自然豪迈雄奇。在这一片神奇的地域上,不仅强大之物豪迈,柔弱之物也同样豪迈:野花“见人来,弹露猛开红萼”(《贺新郎·乙卯夏登观鱼亭》),马兰“情豪不惯小篱笆,远随奔马向天涯”(《达坂城见马兰花作》),沙枣“犹摇铁马裂云风”(《赤亭》),红柳面对“地号天吼”的大漠狂风,“畏惧何曾有”,在“饱看沧桑”之后,神貌依旧,不失娟娟秀色(《点绛唇·咏红柳》);不仅男人豪迈,女人也同样豪迈:“马蹄荡处大荒开,三两女郎香抹腮”(《阿图什书所见》),“饮马姑娘风落影,英姿随浪到伊犁”(《雅马渡书所见》);不仅成年人豪迈,小孩子也同样豪迈:因“家居边塞”,而生小“自有雄豪态”(《清平乐·春日将小女剑歌登妖魔山》)。作者忽而感觉自己的诗句挂在鹰翅上:“性情瞻马首,诗句挂鹰翎”(《再过荒漠》),忽而感觉自己的诗句挂在胡杨树上:“胡杨老去也新芽,似我诗句高挂”(《西江月·雨中游胡杨河》),忽而感觉自己的诗句被金雕衔去:“颇奈金雕翻健影,尽衔佳句剩无多”(《阿勒泰桦林公园寻诗》),这样的诗句怎能不雄奇豪迈!当作者酣饮,飞泻的瀑布是酒:“我出穹庐抬醉眼,狂流似向酒杯倾”(《白杨沟观瀑》),涌流的大河也是酒:“何必穹庐愁酒尽,帘掀即放大河来”(《布尔根河边痛饮》)。古代诗人豪放如太白,如《将进酒》所写,亦需当掉裘马换酒;作者只需掀帘放进大河即可,真可谓千秋饮豪,一世之雄也。当作者豪情涌起,任是邻国边界也关不住:“黄芦一阵边风起,吹送豪情过界河”(《登哈巴河鸣沙山》)。豪迈雄奇,正是该集的主体风格,重要特色。
豪放雄奇之外,作者亦能写淡远意境,如《宿查干郭愣,无寐,踏月赋此》:“星斗巡檐月远明,情怀暗向小河倾。雪山淡影风吹树,遥听穹庐犬一声。”或写悠闲情调,如《西江月·伊犁河南岸逢故人》:“摘得西坡熟豆,抱来南亩新瓜。伊犁河水煮清茶,人在葫芦架下。 只说一生难见,眼看三落春花。相逢今日莫思家,消尽天涯初夏。”或写透彻理悟,如《西江月·浴乌伦古湖》:“目送红霞百里,手推碧浪千层。冰峰吹下晚风轻,思绪尽倾无剩。 我本身心无垢,但来一洗痴情。沙滩回首看经行,已被清波抹净。”或写随遇而安,如《鹊桥仙·天山菊花台路上》:“林荫染首,清风爽口,野阔花繁草厚。书生老去眼昏花,直认作前程锦绣。 雪山寒瘦,松溪急骤,不尽白云苍狗。变牛作马又何妨,落得个荒原睡够。”凡此足见作者长才,拥有多副笔墨手腕,这些显得“另类”的作品,皆对该集边塞诗词的总体风格构成某种补充、丰富与调剂。
四
从古今诗学承传的角度看,该集无疑是以岑参等人为代表的古代边塞诗、西域诗之现代嗣响新声。作者本是历代边塞诗、西域诗方面的研究专家,在创作过程中自当别有会心,对之多所汲取吸摄。《沁园春·重登喀纳斯湖观鱼亭》下片云:“区区恩怨如烟,更远拓诗疆随牧鞭。想挥风送韵,江河联句。行杯对日,泰华张筵。两宋苏辛,三唐李杜,振羽谁曾至此间。微吟罢,但凭高酹酒,总觉清寒。”作者对自己“远拓诗疆”颇为自信,以为李杜苏辛所未及。从题材内容上看,作者所写确已突出李杜苏辛之范围;但在美感风格上,作者承继的正是李杜、高岑、苏辛的衣钵。太白之豪放,子美之沉雄,常侍之悲壮,嘉州之奇峭,东坡之超旷,稼轩之猛鸷,共同铸成了作者的诗胆词心。该集边塞诗把当代旧体诗词的阳刚风格推向极致,豪迈、雄奇、壮烈、粗犷乃至生猛,但不打油,不谐谑,作者终不失端人庄士、意气书生之本色。
与古代边塞诗相比,因作者生活在边烽尽熄的和平年代,且留居边塞,所以少去了边塞征战场面的描写和征人思妇之情的抒发,多出的是时代生活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新鲜经验和体验,如《甲申人日自乌鲁木齐乘机赴伊犁,下望天山》所写:
谈笑乘风逐日西,乱峰借我布雄奇。
红霞铺锦巡天路,白雪翻波落照时。
点点穹庐云淡淡,盘盘古道树离离。
前朝未必无佳作,这等情怀总不知。
乘坐飞机巡天俯瞰高山雪原、穹庐古道,这在古代边塞诗人,是梦里也不曾见过之事,那时他们在马背、驴背、驼背上。该集作者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观景点不同,视野和境界便与古代边塞诗人、诗作有了巨大差异。还有《念奴娇·戊寅夏陪马来西亚黄玉奎吟兄登塔勒奇岭》中写到的风景拍摄:“歇鞭停马,顺长风遥瞰,万壑千岩。数片寒云催白雪,浑欲吹破天蓝。飞瀑砰訇,苍松摇荡,声色满征衫。夕阳西下,紫霞来挂眉尖。 非是沽酒无钱。张筵填饿眼,又有何嫌。且把相机开巨口,特许今日贪婪。如此风光,环球诗友,未必不清馋。明朝归去,请君远运天南。”《克孜尔水库游艇上作》所写乘快艇游湖:“驱艇云天外,排山破碧痕。清波涵日月,大坝列乾坤。欢语喧林末,豪饮起石根。明朝归去路,染绿过千村。”这些都是古代边塞诗人不曾有过的阅历体验,该集边塞诗的时代色彩,借此得到彰显和强化。
作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崛起于天山南北的新边塞诗的代表性诗人,该集作者总体上配得起当代岑参之评。但二者的差异,似乎能予人更多的启示。该集作品的体裁择取,以律绝为主,间有词作,无长句大篇、开阖动荡之七言古风,这是与盛唐边塞诗代表诗人岑参的不同之处,岑参边塞诗代表作多为七言歌行,韵位繁密,且变韵频繁,形成急骤跳荡的强烈节奏,加之心理上的强烈好奇性带来的内容上的奇幻色彩,所以给读者留下的阅读记忆就是非同一般的陌生和新奇。该集作者多用律体,因律体讲求对仗,势必给人以某种工稳之感。而词体容量有限,即使慢词长调,也不过区区百十余字,不便恣肆蔓衍,腾挪跳荡,铺排展开,且词句长短参差,表现边塞题材就显得过于细碎,力度不足,不能形成如七言歌行那般以长句为主的大面积的力量感,大面积的不懈不歇的打击力和震撼力。作者出塞时年齿尚幼,及至成年写诗,已是久居边塞,虽然驰马高山,有过“胯下群峰震”的独特体验,面对荒原尽处拔地而起、突兀而立的雪峰,吟出过“荒原过尽一山抽”的奇句奇字,但总体而言,外来者的新奇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钝化,不复如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等,以内地之人乍临边塞,初度遭遇一片不曾梦见的异域风物,给其视知觉猝然带来那样一种充满神奇的激动,化为诗篇,仍保有初遇的新鲜刺激。仅以岑参《白雪歌》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为例略作剖析,就可看出,其创作心理机制实乃乍见时的新奇,直觉中的错愕。若是土著,司空见惯,面对此景,视同寻常,审美感觉早已钝化,这由美妙的联想、比喻所构成的千古名句也就无以产生了。类似的这种由奇景引起乍见者新奇的审美心理体验而生成的边塞风景诗句,因其景物意象选取的纯粹,而使得岑参等人的盛唐边塞诗的写景更见精彩,更为出色。相较而言,《天山韵语》的作者颇为自矜的“多年彩笔,长描西域,腕中圆熟”(《桂枝香·重九日登妖魔山》),这在一般意义上当然是长处,但过于“圆熟”,则必失生新之气。还有边荒旷远地域的神话传说元素、神秘惊悚感觉,诸如岑参《热海行》等诗的传奇性在诗中的缺位,也使此集边塞题材作品的艺术魅力有所减损。
五
讨论星汉的新边塞诗,除了以岑参为代表的古代边塞诗,还有一个参照系,就是当代的边塞新诗。这样,就必然会说到“新边塞诗派”的命名问题。当代“新边塞诗派”的概念,应该是由新诗界首先提出来的。来自西北的评论家周政保,注目当代诗坛现状,从古代诗歌史上的“边塞诗派”获得启示,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了“新边塞诗派”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在诗的见解上,在诗的风度和气质上比较共同的‘新边塞诗派’正在形成。”(周政保《大漠风度,天山气魄――读〈百家诗会〉中三位新疆诗人的诗》,《文学报》1981年11月26日。)这一提法得到了西北诗人、诗评家和整个诗歌界的回应。1982年3月,新疆大学中文系就“新边塞诗”问题召开了规模较大的学术讨论会,编选并出版了由谢冕作序的《边塞新诗选》。接着,甘肃的文学刊物《阳关》呼吁创立“敦煌艺术流派”,开辟“丝路上飞天的花瓣”专栏集中发表新边塞诗。著名诗评家谢冕为1982年最后一期《阳关》撰写了《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的文章以示支持。1983年春天,甘肃的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刊出了余开伟的《试谈“新边塞诗派”的形成及其特征》、高戈的《“边塞诗”的出新与“新边塞诗派”》等文章,回顾这一诗派形成的历史,阐释其特征和性质,并就这一诗派是否存在,其特征与前景如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此后,甘肃的《飞天》、新疆的《绿风》和新创刊的《中国西部文学》等刊物,都积极倡导、推动“新边塞诗”运动。《绿风》诗刊1986年开辟“西部坐标系”栏目,集中刊发了15位诗人的作品和相关评论文章。“新边塞诗”很快从新疆扩展开来,得到甘、青、宁、西等省区一些诗人的响应。对这一诗歌运动,诗坛也逐渐采用“西部诗歌”这一名称来称呼它。旧体诗词界对“新边塞诗派”这一概念的使用,时间上要晚一些,大约20世纪在80年代后期“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之后。可以这样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边塞诗派”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操持旧体和新体的两类诗人群体。只是在百年来旧体与新体互相排斥的惯性心理作用下,写作、研究旧体的诗人与诗评家,在谈论“新边塞诗派”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用新诗处理边塞题材的新诗人;同样,写作、研究新诗的诗人与诗评家,也往往无视用旧体处理边塞题材的诗人诗作。
拿星汉的旧体“新边塞诗”与当代的边塞新诗相比,有几点值得关注的地方。一是星汉的旧体“新边塞诗”与当代边塞新诗的同质性:诸如在题材内容上,建设与开拓的描写,基本取代了以盛唐边塞诗为代表的古代边塞诗的战争生活的描写;在感情抒发上,建设开拓的劳动热情的抒写,基本上取代了以盛唐边塞诗为代表的古代边塞诗抒写的追求功业功名的豪情,以及征人思妇、生离死别的幽怨之情;在地域风格上,由于含纳西北边地景观风貌和社会生活而显示出的豪放、雄奇、悲壮的特色等;这是二者的大致相同之处。
但是,二者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星汉的新边塞诗使用旧体,必然受到旧体体式的制约。由于旧体诗词除古体外,篇幅一般较为短小,而星汉《天山韵语》一集无古体歌行,这就使得星汉的新边塞诗,较少处理复杂、繁富的题材内容和思想感情。而当代的边塞新诗,在语言形式的选择上,与盛唐边塞诗为代表的古代边塞诗在不似之中存在着深刻相似性。盛唐边塞诗多用七言古诗和七言绝句两种诗体,这两种诗体的七言句子较五言为长,在节奏上更为流转、动宕。七古一体不仅每句字数较五言为多,而且篇无定句,篇幅一般较大,便于铺排驱遣,自由开合,驰骤腾挪。无独有偶,边塞新诗在语言形式上也多用长句,意象繁密,作品的篇幅一般也比较长,不像星汉多用近体的新边塞诗那样简明省净、约句准篇,因而显得形体延展,气局开张,便于容受和处理各种驳杂的题材内容和思想情感。其次,在诗人的主体意识上,写作旧体的星汉,更吻合长期宣传提倡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更多承继传统士大夫文人的情感心理图式,像他的颂美烈士和领袖的作品,他的咏史怀古、登临凭吊之作中的大一统意识,立功报主、心存魏阙的心理,以文采干动天听的人生理想,都是在边塞新诗中较少看到的。边塞新诗作者,如同在新疆的周涛、杨牧、章德益,居住青海的昌耀,居住西藏的马丽华,他们的作品诸如《神山》《大西北》《我是青年》《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地球赐给我一角荒原》《一百头雄牛》《青藏高原的形体》《慈航》《走向羌塘》《西部汉子》《百年雪灾》等,都能将个人的坎坷命运,融入地域和民族的历史、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进程,以现代人的意识,去发现和领略西部高原的社会自然、历史文化所包含的全部丰富、复杂、悲怆,不得不承认,这些边塞新诗代表作品,更富有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色彩,更具有内涵深度。复次,从景物描写(或曰情景关系)上看,星汉多把边塞的奇异景物视作单纯的风景意象摄入诗中,或以之渲染烘托背景氛围;边塞新诗则更注重于在自然景物中融入深度人性。当然,星汉新边塞诗的景物描写,虽说更多是作为背景存在于诗中,为渲染烘托作品的氛围服务的,但如前所论,他的个别篇章在景物描写中亦寓有比兴寄托之意,这是自不待言的。当代边塞新诗中,单纯的写景或借写景渲染氛围的情形已不多见,写作边塞新诗的诗人,更注重在自然景物的观照中揭示深度的人性内涵——人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的价值尊严、力量信念、爱恨生死,人与自然之间的理解亲和以及龃龉对立。试看周涛的《野马群》片段:
兀立荒原/任漠风吹散长鬃/引颈怅望远方天地之交/那永远不可企及的地平线/三五成群/以空旷天地间的鼎足之势/组成一幅相依为命的画面。
自然的严酷,塑造出生命的强悍和生存的伟力。野马群由于受渗入血液和骨髓的孤独与寂寥的驱使,曾在暮色苍茫中悄悄接近牧人的帐篷;但出于对同样渗入血液和骨髓的自由与无羁的捍卫,又在一声犬吠中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是野马群的性格,又何尝不是西部人的性格?这样的作品是写景,是咏物,是喻人,已很难截然区分,让人只觉得扑面而来的漠风中散发出的是浓重的人性的气息。简言之,写景在星汉边塞诗中是相对独立的,可以和抒情和叙事等成分相区分的;在边塞新诗中,写景已很难单独区分,它已和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因素糅合一处。因此,星汉的新边塞诗中的写景更纯粹,更富奇光异彩,更富地域性;边塞新诗的写景则更繁复,更富人文情思色彩,更富社会性。以上所谈的三点差异,既存在于星汉新边塞诗与边塞新诗之间;也可视为当代旧体诗人的新边塞诗,与新诗人的边塞新诗之间存在的整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