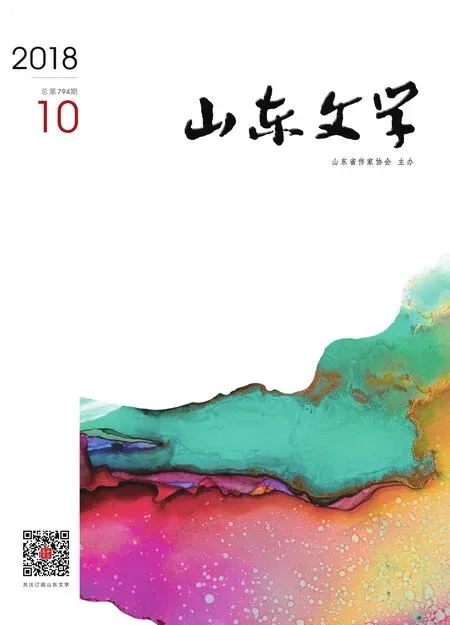天空有朵雨做的云
郭保林
一
从法兰克福到黑森洲符腾堡几百公里的路程,我们的大巴车出发了。公路并不宽阔也不平坦,婉蜒在阿尔卑斯山山麓,车速很慢,带着抒情般慢板,我们隔着玻璃窗,尽情地游览着沿途秀丽的风光。阿尔卑斯山脚下是一个接一个大大小小的湖泊,静幽幽地闪着蓝光,公路两旁是高高瘦瘦的山毛榉,拔天扯日,高得令人震惊。树木掩映着原野,洁净碧绿的草地,星星点点的野花,红、黄、蓝、白,斑斓多彩,德国被称为欧洲的花园国家,最美丽的国土,阳光明媚,空气纯净,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愉悦感、舒服感、幸福感。还有山坡上的村落,五颜六色的房子,像积木似的,你分不清是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或古典主义风格,大都是艺术性结构,但这些村落却讲求秩序,严肃、沉稳,不浮躁,不张扬,体现了大森林般的高贵和静穆。高高的教堂,尖尖的钟塔,清脆的钟声传来,带着宗教的神秘、深沉和内敛气质。
你看见了吗?那空旷的原野,洒满阳光的草场上,耸立着几棵枝蔓相连的橡树,古老、粗壮、巍峨,它们不是那种浅薄得阳光可以穿透、如轻纱般飘拂的树木,它们浓密、厚实、沉着,有着坚不可摧的稳重模样,显示着生命的旺盛和强大持久的力量,仿佛体现了一种理想化的人格。橡树被德国人誉为“英雄树”,既有德意志人浪漫温柔诗意的一面,又有一种不可摧毁、不可摇撼的刚强、坚毅,象征着日耳曼人沉雄、深广、强悍、敦厚的力量,庄严、博大、浑厚的风度。
这个民族和它的风景一样,富有丰富多彩的魅力。一路上,我饱览着德意志的山野、河流、田园、森林的壮美风光,脑海里迅速地翻阅着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失败者,又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这是具有怎样性格的民族啊!
海涅有一首诗《德国》。他把德国比喻一个小孩,她是阳光喂大的,阳光给它烈火,“吃烈火的孩子长得快,浑身上下还热血沸腾”。
二
德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罗马帝国时期,以狩猎、畜牧为业的日耳曼人在中欧定居下来,转而从事农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北方的邻居。莱茵河畔升起袅袅炊烟,阿尔卑斯山林响起狩猎弓箭的呼啸声,一片融融的劳作景象。后来(大概中国的汉朝时代)罗马派大军越过莱茵河,侵犯日耳曼部落,日耳曼人在首领阿尔米细斯率领下英勇抗击,利用山林地形,一举歼灭了来犯之敌。罗马帝国从此放弃了非分之想。此后,德国的历史打开了新的篇章,日耳曼人在莱茵河畔、多瑙河岸、阿尔卑斯山麓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公元8世纪,时值中国的唐代,西欧出现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查理大帝,几乎统一了整个西欧,他的几个孙子于公元843年三分其国,就是今日的德、法、意的雏形。当时,中欧逐渐形成德意志民族。公元911年(正是中国五代的后梁时期,大唐的太阳已经沉落),康拉德一世被推选为国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德意志国王,它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初,长达800多年。
那时的德意志统而不一,小邦林立,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统一的民族国家,有点像中国的周朝诸侯割据,各自称霸一方。18世纪末,法国拿破仑率大军横征竖伐,大举进攻德意志,风扫残云般地消灭了那些小邦,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德国历史上第一帝国寿终正寝。
拿破仑战败后,这片国土又出现了30多个小邦国,松散、隔膜,貌合神离,甚至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普鲁士王国是邦国之一,国力日益强大,出现了个铁血宰相俾斯麦。在“铁相”的率领下,普鲁士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战而胜丹麦,二战而胜奥地利,三战又胜强邻法兰西。俾斯麦凭着钢铁和热血统一了德国,并开疆扩土,成为欧洲一霸,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这就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
18世纪60年代,德国文学兴起“狂飚突进的运动”。德意志是个民族分合无定的国家,从古老的法兰克王国分离出来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是个徒具虚名的统一体,最多时全国有上千个邦国,最少时候也有几十个小邦国。
德意志这个国家是血统混乱的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的战乱,烽火不息,干戈不止,今天你依堡为王,明天我筑城为帝,一场场血肉迸溅的厮杀,一幕幕腥风血雨的悲剧。人种也出现芜杂的变异,宗教、婚姻、漂泊、流徒,再加上外来民族的殖民统治 ,原始的日耳曼再也没有纯净性,哥特人、汪达尔人、弗里芒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法兰克人,简直是一锅大杂烩,甚至还混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白人的血统,形成畸形、斑驳陆离的多人种的协奏乐章。说也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美丽的莱茵河,蜿蜒跌宕的阿尔卑斯山,苍茫浩瀚的黑森林却给不同人种赋予同一性格,尚武精神,文化精进,雄沉、内敛、沉静、坚毅、浑厚、强悍、血与火、诗与剑、抒情和狂飚式的情绪。
尼采对德国人有精辟的论述:
“德意志的灵魂,首先是多样性的,多源头的,混合重叠的……因此,德意志人比起其他民族来,更不可捉摸,更复杂,更为矛盾,更为不可知,更难预测,更令人吃惊,甚至更为可怕。”深刻、恰切、精譬。尼采认为德意志人灵魂长廊里带有各胴体,杂乱无章,又带有神秘之美,随意性、模糊性、朦胧性,像浮云,不稳定、不成熟,且成长着东西都有的深邃性,德国人还被尼采称之为“有角的牲畜”。
这个民族有巨大的胃口,他们把信仰与科学,基督教与博爱,反犹主义,权力意志,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五花八门的主义、教条,连骨头带肉,生吞活剥,吞噬而尽……从不感到消化不良,这简直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勇敢、最可怕、也是最亲近、最无私的民族!
铁相一登上政治舞台,就自我宣告:
“我将成为普鲁士最大的流氓或最杰出的人物。”他的强权政治就是靠钢铁和鲜血来维持,也就是暴力和杀戮。
三
俾斯麦任宰相时,公然批判官僚主义和立法的僵化,他说:“(政府)大脑和四肢长了肿瘤,只剩下腹部是健康的,它制定出的法律就是它在这个社会上最直接的排泄物”,在俾斯麦有生之年,德意志变成一个强大的帝国,这并非伏尔泰和康德教导的结果,这是德国历史是最经典的章节。
地理学就是人类学,不同的地区造就不同的种族,造成不同的动机和行为。苍莽的黑森林,美丽的莱蒙湖,巍峨的阿尔卑斯山赋予了德意志刚毅、雄浑、深沉、静谧、孤独的性格。黑森林是德国最令人注目的名片,森林是巨大的生态平衡,既有虎狼雄狮、鹰雕,也有糜鹿、山羊、野兔、虫豕,在这里共生共荣,万类霜天竞自由,物种的繁荣,恰恰证明生命的强旺。阳光、雨露、惠风,既给雄兽带来温暖,也给弱者以慈悲。黑森林不仅孕育了歌德、席勒、海涅、里尔克、荷尔德林这些伟大的诗人,贝多芬、巴赫、瓦格纳、舒曼、理查德·施特劳斯、门德尔松这些天才的音乐家,优美动人的旋律曾诗意地响彻莱茵河畔,阿尔卑斯山麓,多瑙河波光上。德国还是思想的国度,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一代圣哲开拓了人类的思想深度,拓宽了人类的精神空间。
自由,但孤寂。
哲学、音乐、诗歌是德国的“神三角”,这是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德国没产生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它只能孕育出贝多芬、歌德、尼采,他们在呀呀学语时,眼神中就充满了深沉、无限和永恒的东西。
还有一个叫莱布尼茨的科学家,他被誉为“万能大师”,他研究的领域之广,学识之渊博,超过凡人的想象,他的成果遍及数学、物理学、力学、逻辑学、生物学、化学、地理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气体学、航海学、地质学、语言学、法学、哲学、历史学,甚至外交,在哲学史上和亚里士多德齐名,他和牛顿一样,一生未婚。
尼采说:“世界是深沉的,比白昼假想的还要深。”他认为普鲁士军队和议会获得成功不是源于思想观点,更多的是“铁和血”的结果。
希特勒这个恶魔的出现,决非偶然,俾斯麦铁血政治直接影响了他。
法西斯希特勒的坦克、装甲车狂风暴雨般地席卷欧洲。波兰首当其冲,剑锋所指,败绩而亡。接着横扫丹麦,入侵挪威,继而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比利时吓得用颤抖的声音求饶:“我们中立”,希特勒只是睥睨地哼了一声。这个战争狂人以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野心,绕道马其顿防线,兵临巴黎城下,将战火引向法国,很快“高卢雄鸡”与德国战车的较量,遭到惨败。法国元帅贝当在巴黎城外签下投降书。贝当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签约时,德国专门将珍藏在博物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签订投降书的那节车箱运来,当面羞辱贝当。
又是尼采说:“在阿尔卑斯山,我是不可战胜的。”
希特勒走向德国政治舞台,开始俾斯麦铁血政治的统治。先是大造舆论,通过报刊、电台、演讲、集会、疯狂鼓吹民粹主义,鼓吹战争,煽动民间狂热的复仇火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人带来巨大的耻辱,也是永久的疼,希特勒利用这种狭隘的复仇心理,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把损失追寻回来。
德国这片土地太富有传奇了,既孕育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也涌现了贝多芬、巴赫、歌德、海涅这样杰出的艺术家、诗人;既延生了俾斯麦这样优秀的政治家,也造就了威廉二世、希特勒这种兽性的战争狂人……这是怎样的矛盾的复合体?那种温顺、随和来自斯拉夫人,庄重严谨的风度、注重外表又有罗马人的特征,精确、严刻,一丝不苟、执著、死板,是日耳曼人生命的基因,如果说这种精神用在正道上,会创作出举世瞩目的奇迹,反之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德国人除了那些优秀的品格,还有普遍的偏执、势利、顺从的小市民习性,这是产生歇斯底里的原因,滋生法西斯主义的土壤。狂热、自私、狭隘的心胸、偏见、非理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的急剧动荡中,在纳粹思想上找到了希望,于是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狂嚣、狂躁和举目皆空的狂妄。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一份科学杂志读过的《高空暴力云》。暴力云,脾气暴躁,是生成一团雷暴的云。雷暴是大气中一种放电现象,它出现时,通常会伴随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雹到来,电闪雷鸣,这种现象常发生在夏季,如果发生在冬季,往往是暴风雪随之而来。莫不是日耳曼民族性格注入了暴力云的毒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大地满目废墟,正如德国作家希特所言:“我们时代的标志是废墟。废墟环绕着我们的生活,包围着我们的城市和街道,是我们当前时代的真实,在断垣残壁的废墟上,没有浪漫派的‘兰花’盛开,而是毁灭、坍塌,末日的幽灵在日夜游荡。废墟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内心感到恐惧不安的外部征兆。我们不仅生活在废墟之中,废墟同时还堆压在我们的心头……”
废墟、绝望、饥饿、创伤。战后,德国人一边控诉纳粹的罪行,一边高奏希望的畅想曲,寄托对未来的憧憬。
四
尼采有句名言:“种族越纯洁,越经久不衰”,这成为希特勒排犹主义的理论基础。日耳曼民族精致而深沉,卓越而傲慢,高贵而静穆,居高临下,面对整个欧洲,大有“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希特勒就喜欢高山,是否有高山崇拜意识?他的别墅——“鹰堡”,就耸立在古尔史坦山顶上,沿途风景秀美,但要穿过五道令人窒息的隧道。他们有着奔放的激情,又有开朗明快的情怀,追求古希腊艺术美的最基本特征。诗意的民族,哲学的国度,科学的乐园,诺贝尔奖的摇篮。但他们又具有强烈的人性弱点。
是出于同行的嫉妒、排挤、打击?
是出于排犹主义,一种狭隘民族仇杀?
且不说纳粹建立了史无前例的集中营,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几乎造成了一个种族的灭亡,即使人类的精英,杰出的诗人、优秀的科学家也不放过,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也是人类史上的“绝唱”。海涅、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马克思的著作被焚毁,而其人被迫流亡国外。
爱因斯坦荣获诺贝尔奖,他的“相对论”为人类科学发展指出了道路,开拓人类对宇宙和自然广阔视野,没有相对论,怕我们今天不会有电视、手机以及原子弹、导弹等高端科技的出现。爱因斯坦获奖,举世出现“德国热”。但只有一个国家对爱因斯坦不遗余力地攻击,并把他赶出国外——这就是德国。
德国对犹太人的仇恨、敌视,几十年前就现端倪,犹太人聪明、睿智,他们占据着生活有利位置,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富贾大商,还有公职人员,而且各个行业都成就卓越,事业辉煌。他们的富有、高贵,引起日耳曼人的嫉恨,这个外来移民抢占他们的机会。所以爱因斯坦获奖,不仅没有引起德国神经的兴奋,反而激起仇恨的波澜。德国物理学界对爱因斯坦的迫害开始升温。最恨爱因斯坦的不是德国的老百姓,是德国的物理学家。莱纳德率领一大帮德国科学家组成神圣同盟,公开称“相对论”为“犹太物理学”,并对爱因斯坦进行人身攻击。莱纳德是个狂热的反犹种族主义分子。
爱因斯坦获得大奖,莱纳德气得发疯,甚至组织一百余名教授物理学家编写了一本书:《106位教授证明爱因斯坦错了》。
爱因斯坦几乎在德国无法生存,犹太人是“劣等种族”在德国甚嚣尘上,排犹、杀犹、恨犹,几乎占据了德意志日耳曼人的精神空间。
“人这个物种,天生充满各种缺点。”
正当爱因斯坦坐在卡普特小木屋里聚精会神地探究宇宙的堂奥:宇宙会膨涨吗?会萎缩吗?会消亡吗?这时,纳粹头子希特勒却把柏林折腾得一塌糊涂。《我的奋斗》的出版,纳粹已形成一片黑压压的乌云,德国的天空一片幽黯,战争的风暴在地中海上空咆哮、呼啸而来。
希特勒更痛恨爱因斯坦,认为爱因斯坦的巨大影响对他的统治构成巨大的威胁,纳粹是个恶魔,希特勒是个魔头。那么德意志人特别是日耳曼是什么呢?你仅仅是受骗上当者的角色吗?你灵魂深处没有纳粹情结吗?为什么一呼百应?
日耳曼民族很有特性,是“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他们体现在最浪漫,最柔美,最富有想象力的诗人情怀,世界文学的巨匠歌德,启蒙运动的宗师莱辛,欢乐英雄的席勒,身患疾病而歌咏不止的诗人荷尔德林,激进诗人海涅,还有格林兄弟的童话世界;音乐是人类的共同的感情语言,优美的旋律、明快的节奏或铿锵的音韵,不用翻译,都能激起人类灵魂的亢奋。日耳曼人喜欢唱歌,他们播种时唱歌,祷告时唱歌,作战时唱歌;日耳曼人既是战士又是音乐家,音乐之父巴赫,不朽的“乐圣”贝多芬,天才音乐家门德尔松,歌剧之王瓦格纳,还有音乐大师理查德·施特劳斯;当然还有绘画天才阿道夫·门采尔、威廉·莱博尔、弗朗茨·冯·伦,还有鲁迅先生赞誉的女版画家珂勒惠支,他们天才的光芒,智慧的灵泉,不仅照耀着德国,滋养着日耳曼民族丰富的精神世界,同时也照亮了欧洲,乃至整个人类。
更令人惊羡的是从黑森林,从阿尔卑斯山深处,从广袤的莱茵河的原野上走出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举世闻名的马克思、攀登古典哲学的顶峰的黑格尔、探索哲学星空的康德、“德国国家主义之父”的费希特、悲观主义的叔本华、“哲学超人”的尼采,还有近代哲学巨擘海德格尔,正是他们的智慧,像灯塔,像航标,导引了人类思想史,照耀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五
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她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她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她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取决于她的公民文明素养,即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两次世界大战被打败,输得很惨,惨不忍睹。1945年满目疮痍,遍地废墟的德国,迎来最严寒的冬天,数十万德国人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整个国家陷入“毁灭的绝境”。“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机构”,但德意志人凭着坚毅的意志,顽韧的精神,高度的人文素质,“他们低下了头,但并未颓丧”,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有个故事很感人:几个饥饿的女孩子手捧着父辈或祖辈战争中用鲜血和生命获得勋章和军功章来换取食物,不是乞讨。这时一个外国议员看到她们,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给大一点的女孩,大一点的女孩接过来,随即塞进小一点的女孩嘴里。那位议员深深感动了,感慨道:“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日耳曼人不仅有庄重、拘谨的风度,还有烈火般的激情,他们的音乐和诗歌对基督文化有着神性的崇拜和迷恋。这个国家1946年在一片废墟上欢度狂欢节,一群青年人自发组织起来,在瓦砾堆上演奏贝多芬的《英雄》和《月光奏鸣曲》,德意志人视音乐为至亲。在优美的旋律声中,该遗忘的就要遗忘,该奋争的就要奋争。
德国是诺贝尔奖的摇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45位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德国占10位,40位获得化学奖的科学家,德国占16位。海德堡大学迄今已有40余名教授获得诺贝尔奖。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德国人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一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领导欧洲的第一强国。但这个民族不浮躁、不轻薄,他们依然谦恭、谨慎,讷于言,敏于行,从不要别人监督,他们淳朴、善良、不会耍花招,不会勾心斗角,不会逢人便说三分话,不会尔虞我诈,更不懂“厚黑学”。他们的性格深沉、内向、静穆、高贵而又单纯;这个民族非常冷静、理智、沉稳,人生的悲、喜、怒、怨、恨、爱、情仇、善恶、理性和狂热,沉静和喧嚣,啜泣和吼啸,嘲讽和赞誉,欢乐和痛苦,伤感和欢忭,都深埋在心底,深深埋下头,神劳力绌,一言不发,工作、工作、再工作。
有则笑话说明德国人的刻板认真:你要聘一位德国厨师,他用食材会精确到克,做出的饭菜怕是世界上最难吃的。你要求德国人车一个零件,长短不得相差5毫米,他保证会做到不差2毫米,甚至不差1毫米。他们说懒惰是腐化的表现,他为工作而工作,只有工作才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六
一路上我在翻阅日耳曼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沸腾热烈的生命史。这里天蓝、水碧、山青、田绿、阳光纯净、空气像是原生态,清新得连肺腑都感到陌生。
我们的大巴车走进德国黑森林附近的一个小镇停下来,今晚我们就下榻这里。
夕阳西下,牛乳般的光芒倾泻在山坡草地上,浓绿铺展,无边无际。远近的教堂,高高的尖塔沾上几片夕辉,一闪一闪的,深沉肃穆的松柏,遒劲挺拔的橡树,枝丫勾连的栎树,情绪昂扬的灌木,绿茸茸的草坪像一张绿毯,潇洒地舖展开来。
我和旅伴散步在草地上,蓦然眼前出现一簇簇小花,蓝格莹莹,格外引人注目,导游说,这是矢车菊!德国的“国花”。我惊愕地叫了声,矢车菊!这极朴素的小花在河滩、沟壑、路旁、树下,随地而生,羞怯贴着地皮生长,高不过几英寸,车轧人踩,依然顽韧地生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吗?它既不美丽,更不华贵,德国人怎么视它为“国花”?我真不理解德国人为什么不用鲜艳美丽的玫瑰花作国花。大诗人歌德赞美玫瑰是“花中之王”,海涅是歌唱玫瑰和夜莺的歌手,里尔克爱到极致,专门用法文写了二十四首长诗歌颂玫瑰——《玫瑰集》,称玫瑰是“天使”,神圣之花,并阐释玫瑰的刺象征人类一路走来的艰难,而花的美丽和芬芳则是人类向往的天堂……怪哉,德国人!
导游给我们讲了个故事:拿破仑侵略普鲁士期间,柏林硝烟弥漫,普王后路易斯被迫带着两个孩子逃离柏林,途中车子发生故障,三人下车发现路旁有丛矢车菊,格外美丽,王后随手采摘编了个花环给小王子戴上。后来,小王子成为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个皇帝,想起童年的故事,认为矢车菊是一种吉祥的花,便定为“国花”。有一首《矢车菊之歌》连小学生也会唱。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小花,种子自我繁殖、发芽、生长,它象征着一种乐观,一种简朴,正如勤奋的日耳曼民族一样。蓝色给人无限深沉、辽远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