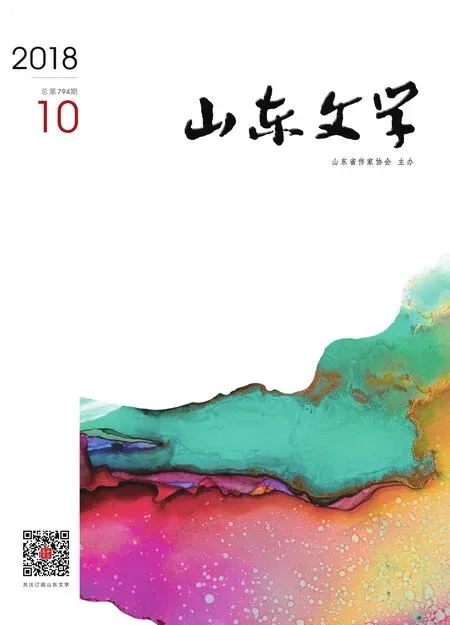改革小说中的道德视角
——以新时期山东作家创作为中心
孙 涛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工作重心开始由原来的抓阶级斗争转移到抓经济建设上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许多作家们纷纷告别了哭嚎宣泄的伤痕文学写作模式,由控诉历史转而开始描摹经济改革的时代现实,改革文学应运而生。可以说,改革文学是新时期中国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也是作为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又一次功利色彩突出、功利话语和审美话语结合的较为完美的小说思潮。从《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到《陈奂生上城》《鸡窝洼人家》,改革小说的视野横跨城市与农村,不仅全面细致地展现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阻碍与矛盾,更深入到了改革者以及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深刻细腻地挖掘出改革背后隐含的社会心理转型与文化变迁,超越了肤浅的简单叙事,达到了应有的文学深度。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山东作家们不落后于时代的大潮,迎来了继战争文学后又一个创作的繁荣时期,秉承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的山东作家对现实民生的哀乐疾苦具有着天然的敏感,在改革浪潮席卷全国的大背景下,他们特别把关注的目光对准了齐鲁大地上的底层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的生活与命运,写出了山东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拼搏、挣扎、希望与追求。可以说,1980年代山东农村改革小说的集体爆发给山东文学在全国带来了广泛的声誉,一方面,对深重历史事件的呼应与展示构成了山东改革小说与全国改革文学的同质性;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山东作家群面向农村的改革小说呈现出一种鲜明的道德化审视风貌,以坚定执着的道德理想追求带给读者一种强烈的阅读冲击力,最终标示了山东改革小说创作求同存异、人无我有的独特光芒。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如《老霜的苦闷》《圆环》《卖蟹》《鲁班的子孙》《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存钱》,无一例外地将思考的重点聚焦到改革中出现的道德观念转变与道德伦理困境上,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熠熠生辉的一笔。改革是必要的,而改革进程对传统道德秩序的冲击亦需关注。
一、集体观的艰难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的农村地区逐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最开始的互助组、初级社到后来的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村经济走过了一条不断加速且激进的“集体化”道路。1980年代初期,改革的浪潮在农村率先兴起,以包产到户为特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落实,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在中国农村贯彻执行了30多年的农业合作化生产试验宣告了它的结束,农村经济迎来了新的春天。
应当承认,中国农村在走集体化农业生产的道路上的确走过不少的弯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然而一分为二地看,在解放之初经济基础薄弱的历史时期,农业合作模式因采取集中管理调配、劳动成果共享等措施,却也很好地解决了我国因人口密度大而导致耕地相对较少的矛盾。因此,在80年代农村经济模式的转型期,新政策的实施与旧的集体主义道德伦理之间便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摩擦:很多农民对新政策带来的私心膨胀物欲横流不屑一顾,在道德观念上反而对集体生产抱以更多的认同,尽管他们无法阻止新政策的实施,但是却也以一种固执倔强的方式表现出不合作的姿态,这是合作化时期集体观念的巨大惯性,也是深化改革过程中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山东作家们在书写农村改革进程中,有不少作品便关注到了这种新时代语境下集体观念转型的复杂性与艰难性,纷纷用自己的故事表达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思索。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矫健的短篇小说《老霜的苦闷》,老霜是集体道路时期的一位积极分子,他是贫协主任、老贫农、老党员,一辈子对集体赤胆忠心,对“穷是光荣”的口号毫不怀疑。改革开放之后,老霜的朋友亲戚们纷纷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老霜却对此忿忿不平,终日觉得有人偷拿了集体的财产,于是在自家院子里加了一把梯子,利用枣树做隐蔽,暗中窥探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老霜的行为当然是可笑而不合时宜的,然而问题在于,他的这些让人看上去有失道德的行为却恰恰是源自于一个最具道德的初衷——保住集体的财产。可悲的是,他每天惦记着“爬上梯子是看老茂从集体的地里偷回几斤粮食,从集体的山上拿回几根草”,最后换来的却是“我这一片心,没人知道,他们都骂我,笑我”,这不禁让人哑然。对于老霜,估计很难能用认清形势、思想转弯来劝慰他使他想明白,老霜穷了一辈子,过去集体的道路让他感觉到踏实与光荣,而当这走了半辈子的道路突然要改,一个怀着朴素集体理想的农民注定会茫然无措。老霜曾在集体道路上获得了一箱子奖状,这是他的光荣、他一辈子的自信和念想,但是这些财富现在反而成为了一个个沉重的包袱,压得老霜喘不过气来,只好用自己的方式来自我救赎。
集体的产生和维护往往依赖于共同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利益,因此,集体生产方式较之于个体生产更容易生成先公后私、互帮互助的道德温床,这也正是集体生产方式能够使农民留恋的原因。集体是值得留恋的,而山东作家们正是深刻地了解到这一点,他们笔下的集体才会如此的动人与美好,公社、生产队不再是需要被淘汰的“旧”事物,而成为了一个个值得缅怀又不忍舍弃的美好回忆:刘玉堂《最后一个生产队》中,钓鱼台刚开始时兴分田到户,但坚持“集体道路天长地久”、硬顶着不分的仍旧有十来户。他们有的是需要集体帮助生产,有的是留恋集体劳动时的气氛,有的是迷恋集体宣传队中的热闹,因此不约而同地想恢复过去的时光。像这样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在沂蒙山地区其实不在少数,而最大的原因便是生产队对山东的革命老区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这些地区的人民和共产党解放军曾经一同生活过战斗过,他们在最困难贫穷的岁月中锻造出了最无私崇高的道德品质,这是这些老区子弟最值得骄傲的,也是最不能够舍弃的。在合作化时代,这些合作社是各地的模范、典型、先进、标杆,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资本,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够实现。因此可以说,集体化生产的结束尽管能够摆脱贫穷,但随之一同摆脱的还有在几十年的集体生产过程中所孕育生长出的道德信念与精神依托,而后者的丧失远不是金钱能够弥补的。再如《鲁班的子孙》中的公社木匠铺、《拂晓前的葬礼》中的大苇塘村、《老人仓》中的老人仓水库等等,这些集体的工作场地或是劳动成果无不凝聚了合作化时期的集体劳作,成为了农民心中永远难以忘怀的道德圣地。可见,新时期集体观念的转型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只能在时间的磨洗中才能渐渐地调整好姿态,从而继续凭借其伦理道德上的优势参与到改革的进程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过多干预未免小题大做,然而视而不见也亦非明智之举。
二、金钱与良知的博弈
众所周知,1980年代实行的承包制改革是对合作化制度已经无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而进行的一次必然性的调整与纠正,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土地承包制度就能够激起农民这么大的激情和动力?实际上,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够迅速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其根本原因便在于这个制度顺利激发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内心深处最大的欲望——通过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进而发家致富。可见,对金钱的攥取和富足生活的渴望自始至终都是农民劳动一种自发的内在动力,无需教育便可获得,农民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发家致富,这是一种单纯而朴素的伦理观念,无论如何无可厚非。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金钱除了能够让人们过上富足安逸的生活,其本身却也有着异化人心的巨大风险。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正义的道德观念渐渐摇摆、退位,而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利欲熏心等种种不良价值取向却慢慢滋生,于是,在利益与金钱的蛊惑之下,很多集体生产中被压制的道德问题便开始显现,当私有利益的笼子被打开,农民便不得不直面新的道德考验,在金钱与良知之间徘徊挣扎,最后做出选择。
1983年,山东作家王润滋发表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与当时一片讴歌赞美改革新浪潮新气象的作品不同,《鲁班的子孙》没有普遍作品表现出来的欢呼雀跃与喜形于色,而是呈现出一种冷静的审视姿态,从老、小两代木匠身上看到了新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与传统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变革在农村引起的骚动。老木匠黄老亮一辈子秉承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要成个好木匠得有两条,一条是良心,一条是手艺,少了哪一条都不成”而规规矩矩地干活,却因买不来便宜木料,打不出时兴家具致使大队木匠铺面临倒闭;儿子秀川在外打拼多年后依靠和县林业局长的关系赚了大钱,回来又着手开起了自己的木匠铺,建立在自私自利与偷工减料基础上的木匠铺换来了一家人自此不愁吃穿。显然,老木匠和小木匠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选择,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采取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非此即彼的道德评判,而是细致地呈现出黄老亮在面对金钱时的惊讶、喜悦乃至惶恐、矛盾的内心波动,给读者真实的阅读感受。一方面,黄老亮认为儿子凭手艺干活赚钱“不是资本主义”“走到天边也说得过去”,儿子在外边发了财,老木匠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谁和钱都没有冤仇,叫谁能不高兴?”“怎么就该那些吃饱饭没事干儿的人挣大钱,咱们也该!”然而,另一方面,当得知儿子以林业局张局长为后台走后门,他又觉得不妥:“老木匠心里像揣进个小老鼠,蹦一会儿,跳一会儿,七上八下,好焦急哩!”最终,儿子秀川被金钱吞没了良心,一味地唯利是图偷工减料终于导致了买主们的集体退货,木匠铺危在旦夕,而老木匠不推卸责任,终于悟出了“天底下最金贵的不是钱,是良心”的道理,毅然接起了儿子的烂摊子,用自己的诚实和良心挽救了生意,木匠铺渐渐恢复了生机。
与《鲁班的子孙》相似,矫健的《存钱》也是通过描写金钱与道德之间的艰难博弈达到了既定的伦理深度。北寨富了,窝窝老汉要去存钱,当得知存钱能涨利息后,老汉决定咬咬牙苦上五年,每个月存一百,一月不拉,过上“和工人一样每月领工资”的美滋滋的日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窝窝老汉起早贪黑,命令一家人省吃俭用,为了省两毛辣椒钱欺骗摊主,为了存钱不借钱给老朋友周大脚的老婆治病。“初五像个鬼影子,紧紧追着窝窝老汉,追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存上一笔钱,却欠了一笔债!”对于窝窝老汉来说,存钱的初衷是为了将来能过上好日子,然而在不断坚持存钱的过程中,存钱本身成为了全部意义所在,为了追逐一个用金钱所编织出的“美好未来”,窝窝老汉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现在。“唉唉,事情怎么会弄到这般地步!该挣就挣,该花就花,再加一句该存就存,那不就一切都好了吗?可怜窝窝老汉,穷了一辈子,好日子猛地一来,他倒不会过了!”可见,金钱在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同时也容易使人与人之间原本毫无介怀的情感掺杂上利益的杂质,甚至会破坏集体生活时期凝聚起来的深厚亲情与友谊,改革进程势必要承担金钱与良知之间博弈的风险,而小木匠变得唯利是图、窝窝老汉的存钱经历无疑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潜在的危害性,这是山东作家的忧虑,也是改革进程中无法规避的现实问题。
三、权利的嬗变与异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经济秩序与政治生态随之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改革的落实与深化引起了政治生态的裂变与整合,而政治权利的运作又影响到了经济政策的贯彻与实施。面对改革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巨变,山东作家们不仅为之欢欣鼓舞,更对其中显现出的新的复杂问题感到焦虑。山东作家以积淀在齐鲁大地上的儒家仁义观念为创作先导,既不肤浅地颂扬这场改革中涌现出的开拓者与新人,也不片面地批判落后与阴暗,而是秉承道德理想的坚定信念,敏锐地观察农村改革过程中政治经济权利的嬗变与异化,大胆地揭露出农村改革进程中新的道德陷阱与伦理困境,彰显了铁肩担道义的创作勇气。
张炜在他的两部中篇《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中共同关注到了当时文坛还较少注意的基层权利变异现象。《秋天的思索》中,在民主选举中落选的王三江在土地承包后成为了海滩葡萄园的负责人,他利用自己之前当大队长时的人脉搞定各种复杂的关系,但又在葡萄丰收之后只从超产中抽出一小部分平均分配,剩下全部交公。从表面上看,王三江重义轻财、一心为公,但实际上,他这样做却是为了垄断葡萄的买卖权,自己借此从中牟利。王三江正是一个表面大义凛然内里却腐化蜕变了基层干部形象,他用自己的权利给开发商批条子,让他们以很低的价格收购葡萄、偷税漏税,还和果品公司朋友合伙,将坏了的葡萄成箱成箱地卖给国家。看园子的铁头叔觉得账目不对,找人问了问,被王三江报复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年轻的老得发现了王三江的秘密,王又联合乡政府的文书诬告老得好逸恶劳、对抗领导,对他进行经济制裁,逼得老得也不得不离开。老得最终在不断观察与“思索”中琢磨出了人们惧怕王三江的那个“原理”:大家过去穷怕了,所以对王三江的小恩小惠也感恩戴德,但其实是受了愚弄和欺骗。
《秋天的愤怒》中,和王三江一样利用手中的权力钻改革空子的形象是村支书肖万昌,在胶东西北部的小平原上,肖万昌是个颇有根基的人物,他在村子里当了三十多年的干部,十几年前他在村里一手遮天,巧取豪夺私设公堂,很多无辜的村民被他整得死去活来。一晃十年过去,政策转变了,但肖万昌依旧是村头,他利用自己的权利和女婿联合种植烟田,实际上却利用自己的权利与狡诈成为了女儿和女婿的奴役者。经过一系列危险的挣扎和斗争,李芒终于迈出了勇敢的一步,痛下决心与肖万昌决裂,联合受害烟农检举肖万昌。小说通过一个令人“愤怒”的故事揭示了改革进程中农村出现的一种新的危机:改革开放了,但权利仍旧掌握在一些愚昧、狡猾甚至早已蜕化变质却又似乎总有道理的人手里,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阻挠农民的解放,毁坏农民的幸福,权利的嬗变让农民成为了新的被奴役者,而这些中饱私囊的基层干部则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桎梏。
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是一个需要细致与耐心工作,地往下一分,漏洞就多,干部钻空子为自己捞一把的机会就多。因此,基层干部的道德品质好坏便成为了改革朝正确方向发展的保障与关键。《老人仓》中就刻画了一批以权谋私、道德沦丧的基层干部形象,令人触目惊心:李家大队党支书李俊堂人很好,但是不管事,一天到晚搞自己包的几亩果园;红星大队支书田仲亭被村民称为“红星的红太阳”,明目张胆地将自家猪圈盖在大门外妨碍交通,更有手下“五虎大将”让群众敢怒不敢言;沟子公社党委书记汪得伍违规多盖私房,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有图形式、赶速度的浮夸倾向......这些基层干部结党私营,在农村编织出一张官官相护又严密庞大的“关系网”,动辄铁哥们、把兄弟,在虚情伪善的面孔之下掩盖自己的种种罪行。可见,在农村改革之初,基层权利的嬗变与异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不得不关注的重要问题,经济的转型需要政治权利保障实施,而政治权利更需要道德信念来防止越界漫溢,一旦党的干部变成了群众眼里的“土皇帝”“红太阳”,改革也势必会陷入违背初衷、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山东是孔孟的故乡,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山东文学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浸染是不言而喻的,在这块承载着厚重道义感的土地上,山东作家们承袭了最朴质务实的踏实、严谨、稳重、善良的因子,对道德传统与理想有着天然的亲近与敏锐,谦逊又不失胆魄。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在山东作家内心掀起的最大波澜不是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行动与雷厉风行的改革新人,而是深入到内心深处并让人战栗不已的一桩桩道德困境与心灵冲突,读之让人唏嘘感叹。诚然,以道德视角来切入分析山东改革小说并不能概括这一时期山东改革文学的全部实绩,然而山东作家们这种不吝笔墨的歌颂传统美德,不避矛头的批判道德沦丧的价值取向无疑让山东改革小说呈现出改革文学视野中一番新颖而有价值的全新风貌——对道德理想的关注与坚守,这是山东文学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也将继续在山东作家的手中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