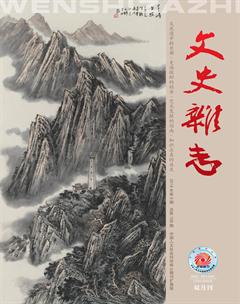明代西南上层社会的生活状态
胡开全
摘 要:幸存的五部“明蜀王文集”,是研究以蜀府为中心的明代西南上层社会面貌的珍贵文献资料,那里面展现了历代蜀王自觉的责任担当,高贵的生活情趣,积极的地方建设,严格的家人约束以及中国文化传统中高贵、担当、自由且内敛的贵族精神。蜀府的生活方式和情趣,对成都和西南地方社会和民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蜀府刊刻书籍、提倡文教、培建公祠,参与音乐欣赏和创作等,代表了明代西南地区上层社会对地方文化和风气的引领,在塑造成都城市精神的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闪亮的一部分。
关键词:明代蜀府;王府生活;贵族精神;文化引领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扼守长江上游,是中华大一统帝国存续的基石。明蜀藩一系,是明代高贵人文情怀的代表。明蜀府是朱元璋分封的24个藩府中,一直延续到明末的11个藩府之一。蜀府是唯一长期独占一省,并始终享有“忠孝贤良”“宗藩首善”等美名的明代宗藩。由于明末战乱导致成都的文献被毁,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常难得的贵族群体正面形象一直没能真正树立起来。关于研究蜀藩的成果,目前比较详尽的主要有陈世松研究员的《明代蜀藩宗室考》(《西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马士训的《明代蜀藩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宋立杰的《明代蜀王角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等。这些研究从已知的《明实录》、明代文献、明代考古发现,以及《明史》介入,初步勾勒出蜀藩的一些基本面貌,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如受《明史》影响,上述学人普遍将恭王任蜀王的时间压缩成一年,实际第十二任蜀恭王在神宗、光宗、熹宗三帝的实录里都有活动记载,[1]直至崇祯四年(1631年)朝廷遣行人龚廷献往蜀府主行丧礼。[2]至于蜀王朱至澍任蜀王的时间,则要推迟到崇祯五年。而关于蜀藩十世十三王中出现三位“友”字辈和两位“申”字辈,前述学者将其引申到蜀府内存在阴诡的权力争夺方面,这也与《皇明祖训》中关于继承的原则不符。[3]还有简单地将蜀藩描述成奢靡者、剥削者、寄生虫等,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有欠妥之处。
笔者借助五位蜀王的著作,即四部海外的孤本和国内仅存的一部,共五部“明蜀王文集”,结合明朝制度和《明实录》中具体的时间点,配合散落民间的碑文资料,计划作系列研究,[4]力图用蜀府为例来重塑中国藩王的形象。落脚西南地区,上层社会的代表性群体有黔国公沐英在云南建立的西平侯府(俗称沐王府)、播州的杨氏家族、环列的土司、长期在本地执政官宦、蜀府下属的郡王如德阳王府和汶川王府等,然后就是以新都杨家“一门七进士”为代表的世家。在这个层次的人群中,蜀府层级最高,在彼此间往来中,其他都要以朝觐的姿态前来。在整个明朝时期,蜀府的美誉度是西南上层社会的佼佼者,主要体现在其自觉的责任担当、高贵的生活情趣、积极的地方建设、严格的家人约束等方面。
一、蜀藩主动的担当和执政的策略
对于藩王这类贵族,人们印象中大多是循规蹈矩、衣着光鲜、白白胖胖、没有能力或实权的人。西方人也把明藩王们纳入贵族世界观的体系之中,而且印象都是一个模式。有一位葡萄牙人伯来拉(Galeote Pereira,活跃于约1545—1565年间)在广西桂林见过靖江王并受到了相当的礼遇。据他描述,这些皇亲国戚在城中的社会地位非常显赫:“他们尽情吃喝,多半养得肥肥胖胖,随便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我们也看得出他是皇亲。他们彬彬有礼,养尊处优,我们在该城的时候,发现从他们手里接受的尊敬和款待,超过别处”[5]。其实,在这种表象的背后,真正贤能的藩王通常受封即立志有所作为,并经过一系列的历练,包括严格的皇室教育和出外游历增长见识。蜀藩在这方面的行为及其留下的资料,为全国树立了典范。
第一任蜀王朱椿(1371—1423)在受封后、就藩前的历练期间,于18岁时写下一首《中都留别》[6]很能代表其志向,其中“昔闻河间献,亦有东平苍。唐宋称宗室,上下相颉颃。顾我才谫薄,志存先哲王”诸句,以历史上著名的河间、东平两位贤能藩王为榜样。对此,旁观者能深切感受到朱椿“忠孝为藩奉君父”[7]的决心。朱椿就藩后,还多次撰文警示自己和教育后人要时时牢记以河间、东平为表率。后世蜀王也很好地继承了这点,时时在诗作中重复这一志向,如第七任蜀王朱申凿(1459—1493)诗作《为善堂》[8]中有“东平为善非常乐,善足应知降百祥”句。蜀府的这种姿态以及实际行动被朝廷上下反复赞扬,如第一代蜀王朱椿被明成祖朱棣赞为“惟贤弟抱明达之资,敦忠孝之义,处事循理,秉心有诚,稽古博文,好学不倦,东平河间无以过也”[9];第八任蜀王朱宾瀚(1480—1508)被明孝宗朱祐樘赞为“河间礼乐文风盛,江夏忠勤世业昌。异代岂能专美事,吾宗亦自有贤王”[10];第九任蜀王朱让栩(1500—1548)被杨升庵(1448—1559)赞为“视河间可雁行,而于江夏有过无不及者”[11],也被后来的蜀府长史赞为“仰惟我成园……感兴操觚泉,达东平之颂”[12]等。这说明在朝廷上下看来,蜀府立场坚定,对皇帝、对朝廷是忠心的。尤其是朱椿,在明朝初年经历了自己岳父蓝玉谋反案,朱棣“靖难”之役,之后又是“谷王反复”,在众多兄弟被削藩的情况下始终屹立不倒,当是其绝对的忠心、严格的自律使然。而忠心与自律,不用说是蜀府在明代复杂皇权政治中之所以一直存在的最重要的保证。
除了忠心与自律外,有作为,为帝国大一统作出实际贡献,也很重要。四川在明代的版图上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明代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的《名藩择形胜》里有:“明封秦晋诸王,皆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置相傅以下官属,与京师亚冕服,则九旒九章车旗服饰,仅下天子一等。天子之臣,贵重至太师丞相公侯,不得与讲分礼,伏而拜谒。《续文献通考》曰:高巍上言,太祖既定中国,体三代之良法,择形胜之重地,建封诸子……四川虽西南一隅,山川阻深,故以蜀府王之”。明代彭韶在《山川形胜述》有更具体的描述:“蜀之地,南抚蛮獠,西抗吐蕃,上络东井,岷嶓镇其域,汶江出其徼,以褒斜为前门,灵关为后户,峨眉为城郭,南中为苑囿。缘以剑阁,阻以石门,而越负秦,地大且要,诚天府之国也。”[13]另一点对蜀府的生存也很重要,就是四川距离京城遥远,特别是朱棣迁都北京后,是所有藩府里离京城最远的,消息往来的时限最长。事关藩王去世的大事,消息傳到京城大约需要约70天,往返就是5个月。如《孝宗实录》有两则关于蜀王朱申凿薨的内容,就是一例。《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之七十八说:“蜀王申凿薨,王定王第三子,母次妃王氏。天顺三年生,成化七年封通江王,八年进封蜀王。至是薨,年三十五。讣闻,辍朝三日,赐祭葬如制,谥曰惠。”[14]其时间标为弘治六年七月癸巳,即1493年8月12日。《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之八十,又出现内容完全相同的一条,但时间却变成了弘治六年九月甲辰,即1493年10月22日。这应该理解为第一条是朱申凿死亡的时间,由后世编修实录时添加上的,而后一条则为孝宗皇帝听到消息并作出处理方案的日子。而普通人员和消息往返需要11个月。明朝礼部规定“钦依限期,山东德府等府,山西晋府等府,俱限六个月,代府限六个月半,河南周府等府俱限六个月半,陕西秦府等府俱限七个月,肃府庆府限八个月,江西益府等府俱限八个月,湖广楚府等府俱限八个月,广西靖江王府限十个月,四川蜀府限十一月”[15]。

有鉴于此,蜀府必然主动承担众多的责任,并相机择处,宣扬朝廷威仪,使西南民众虽然距京城千里却感受皇恩咫尺。如守土上,明朝初年蜀府还有兵权时,在宣宗时期,遇到松潘军情,要求蜀府参与配合,由于军情变化,有时不得不断然决策。当时蜀王按照朝廷指令,委派指挥领兵4000出征松潘,并向朝廷汇报。但刚过一个多月,“蜀王友堉奏,前后调发官军校尉七千余人助讨松潘叛寇。”[16]即由前线战报分析出兵力不够的问题,又增调3000人。于是“上嘉其能,尽藩职,恭朝命,赐书奖励之”[17]。蜀府并未以此为骄,反而于四年后,根据朝廷政策,“蜀王友堉奏成都三护卫,请以中右二护卫归朝廷,留左护卫官军供役。上嘉其能省约,从之”[18],即主动交出大部分兵权,用实际行动向朝廷显示忠心。不过,兵权的交出也是蜀府在明末时虽然富有却无力回天的原因之一。
蜀府最大的贡献是其独特的“以文教化一方”[19]策略,带来《明史》所载“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20]的局面,成为践行明太祖“治天下之道,必建藩屏”理论的典范。朱椿在延揽名士,鼓励文教方面成绩卓著。他在对宗教的关注和对宗室成员的安置上,最能体现其执政策略。从四川明代佛教碑文[21]可以看出,蜀府除重视传统的峨眉山、成都、大足寺廟外,重点关注的南面马湖地区、西南面雅安、天全一带、西面茂州至松潘一带的寺庙,为稳固边疆贡献良多。从军事角度看,四川作为当时的边疆地区,主要受到西北、西、南三个方向的威胁;而南面有四川行都司带领六个卫所,防守相对稳固。蜀府多次用兵,因之主要在松茂一带。[22]它仿效“天子守国门”的策略,将宗室主要布置在都江堰一带。[23]从实践看,这一策略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五任蜀王朱友垓(1420—1463)受到皇帝降旨表彰,特写下《迎诏》诗,里面对实现民族团结有这样的描述:“日星璀璨华夷见,雨露沾濡草木妍。万古岷峨为保障,亲藩共享太平年。”[24]
蜀府在经济上也力所能及地为蜀中作了一些贡献。首先是利用职权帮助蜀中百姓争取免税的机会,如只进贡蜀锦和川扇。对朝廷要求的专项“茶马交易”,蜀府一方面积极督促地方,一方面府内设立办茶的专门机构“蜀府正字”[25];每年向朝廷进马也成为常例,为国家贡献很大。小项非常多,包括资助修建寺庙、名人祠堂,都江堰岁修,给博士生拨款,给名士赐田等。明代在蜀中形成一个传统,凡是涉及修公祠、修庙,修桥等公益事业,牵头人都会想到向蜀府求助。从留下的文献和碑文看,蜀府或捐钱捐物,或赐田等,参与很多,让蜀中民众真切感受皇恩咫尺。下面简单举几个例子。
明初文人方孝孺就很赞赏朱椿的善举,他曾写道:“大明御四海,贤王受封至蜀,以圣贤之学,施宽厚之政。推先生之心以惠斯民,贫无食者赐之以粥,陷于夷者赎之以布。岁所活以万计,欢声远于遐迩”[26]。朱椿有时还主动施恩,“尝视成都郡学,分禄米以给教授,俸月一石,遂为令”[27]。他对成都平原重大水利工程都江堰更是长期关注,投入颇多。明人陈鉴《铁牛记》记载,在都江堰建铁牛时,“蜀王闻而贤之,命所司助铁万斤,银百两”[28]。正德年间的一次都江堰整治工程,“治之日,蜀府差长史李钧赍币帛羊酒,劳诸从事者。民环而观之者,亿万欢声,震山谷间。其父老皆合掌曰:此吾子孙百世利也……蜀府每年亦助青竹数万竿,委官督织竹笼,装石资筑”[29]。
二、王府高贵的生活方式
对于王宫内苑,由于可深入观察的机会不多,自古有很多揣测,西方人同样如此。葡萄牙人博克舍写道:“他的宫室有墙围绕,墙不高而呈四方形,四周不比果阿的墙差。外面涂成红色,每面各有一门,每道门上有一座门楼,用木料精制。四道门的主门前,对着大街的,再大的老爷都不可骑马或乘轿通过。这位贵人住的宫室建在这个方阵的中央,肯定值得一观,尽管我们没进去看。听说门楼和屋顶上了绿釉,方阵内遍植野树,如橡树、栗树、丝柏、梨树、杉树及这类我们缺少的其他树木,因此形成所能看到的清绿和新鲜的树林。其中有鹿、羚羊、公牛、母牛及别的兽类,供那位贵人游乐,因为如我所说,他从不外出”[30]。从五部“明蜀王文集”来看,蜀府的真实情况是高贵而有条理的。
作为蜀府的主人,在享受荣华富贵之余,仍然守土有责,勤政为本。王宫里有专门的“勤政堂”,第七任蜀王朱申凿有诗云:“多士皆知学,三农尽力田。明年应考绩,补内看乔迁。”诗歌表达了蜀王自己及臣属的职责。而朱申凿所写《思政堂》则让我们看到了蜀王执政的理念和工作状态:
思政堂[32]
勤政孜孜有所思,东方向曙早朝时。
奸邪误国当除却,贤俊匡时可荐之。
海内只期兴教化,民间须得乐雍熙。
唐虞稷契商伊尹,一念惟公岂有私。
蜀府如其他藩府一样,被规定不干政,不干军,不从事四业。其所执之政,并不太显性地让外人所知。但其仪式感十足的早朝制度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这是规定的皇家范式,同时还要接受地方官和镇守太监的监督,是朝廷在制度设计上对藩府的制衡。早朝大致处理一些府内的人、财、物,以及固定礼仪、王庄经营等事;然后就是在初一、十五接受地方官来朝觐。早朝的情况在朱友垓和朱让栩的诗作中都有描写。
要实现“忠孝为藩”,除了严格的皇室教育和藩王自己及子弟认真读书外,出外历练也很重要。第一代蜀王朱椿在皇宫学习由宋濂亲自编写的教材,然后又被派到凤阳,即在“中都阅武”多年,其间还发生了将西堂开辟出来,请李叔荆、苏伯衡等著名学者来商榷文史的佳话。等到他在四川就藩后,继续礼聘以方孝孺为代表的顶级文人前来服务,并带世子等进京[33]和巡视全川。之后的蜀王也纷纷效仿,长期与蜀籍名人如首辅杨廷和、万安,状元杨升庵、才女黄峨等保持联系,阅读并模仿他们的作品;然后利用尽可能出现的机会出外历练,以增加执政能力。朱友垓《定园睿制集》中对外出沿途的描述,在诗歌方面有《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陕州河亭陪韦大夫眺别》《巴南舟中》《宿关西客舍寄严许二山人》《江南旅情》《泊舟盱眙》《题江陵临沙驿楼》等,对细节的描述有《渔村》《访僧居》《茶人》等。朱申(1448—1471)《怀园睿制集》里亦有《京城》《旅馆》《商旅》《田家》《卜者》《医者》《樵人》诸诗,观察越来越细,体察民情也越来越准。

朱申凿的《惠园睿制集》里有《西蜀宦游》《宦途游览》《题永城驿》《长安秋夕》《春日长安即事》《洛阳早春》《江南旅情》等诗。它们有时还将这种出外历练描述得比较艰苦,其中比较典型者如:
赴京途中遇雪[34]
冲寒马一鞭,万里去朝天。
玉屑将埋路,琼花正满川。
群鹅浮远水,孤鹰落平田。
杳杳村墟外,微茫有暮烟。
到宣宗时期,朝廷开始阻止藩王进京。蜀王不能随意离开土地,世子等即便出门,也不能得到“面圣”的尊宠。再到后来,地方官进一步限制蜀府的行动自由,“旧例各王府亲王郡王以下,凡欲出城祭墓送葬之类,俱先期奏请得旨乃行。蜀府自献王以来,每遇亲丧,亲王郡王俱自行送葬,不经奏请。至是,四川守臣奏之,蜀王亦自以本府相承故事为解。命今后各王出城,仍照例先期以闻”[35]。这便导致后世蜀王行动不便,即葡萄牙人印象中的“从不外出”。后世蜀王难有更多的阅历,除经营内苑外,对王庄也疏于巡视。这也直接导致第九任蜀王朱让栩只能沉迷于宫苑之中,其《长春竞辰稿》以描写内苑景物而移情宫词散曲为主。其散曲作品不见南曲香艳缠绵的影响,与蜀中人士杨廷和、杨慎、黄峨等有一致的清丽之风与雅趣思力,显示出正德、嘉靖年间散曲创作南北分野之际的不同流脉,對当地音乐鉴赏和创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另外刘大谟、杨慎纂修的《四川总志》亦记载朱让栩“尝著有《适庵》诸集,多为缙绅博诵”[36]。
虽然行动不自由,但蜀府中人的吃穿用度仍然高人一等。荔枝是蜀府的特产,非常珍贵和稀少,经常作为进贡的礼物。下臣能得到赏赐,对其本人和家人都是很兴奋的事。朱椿有“梁园丹荔初颁赐,夺得归家遗细君”[37]之句。朱申有“颗颗含琼液,枝枝缀火珠……奇果真堪爱,轻红锦作肤”诗。[38]后者“贡珍来上国,劳使走长途”[39]之句,则显示这些荔枝主要来自川南一带,朱椿曾将其作为贡品送到南京。
另外吃新米和喝新茶也被他们记录下来,如朱申的“秋熟喜登场,晨炊玉粒香。流匙何软滑,乐岁试新尝”[40],朱友垓的“天产灵芽秀,惟钟谷雨姿。龙团和露采,雀舌候春期。山远步尤健,林深路更危。幽斋自烹啜,清味有谁知。”[41]
成都的炎炎夏日,外面酷暑难耐,但住在王府里面却是很惬意的——因为有凉庭、有冰镇西瓜等解暑的水果、有凉爽的住所。朱申笔下的王府既在凉庭里“日午寻凉向水隅,脱巾露发总无拘。不须白昼挥纨扇,喜有清水出玉壶。攸而兴来游竹径,坦然倦后卧纱厨。浮瓜沉李随时用,梦入华胥足自娱”[42],又可利用高大建筑在避暑时发挥巨大的作用,即“热极似炉中,来乘殿阁风。清凉生细葛,如在水晶宫”[43]。
外界很难知道这些细节,文人们只能通过蜀府的刻书和撰文以及推广文化和教育的实践,来推想蜀王们的藏书和读书情况。关于蜀藩刻书,“初蜀献王好文学,招致天下名刻书傭集成都,……故蜀多巧匠”[44]。这显然大大推动了四川刻书业的发展,故蜀藩刻书就走在了宗藩刻书的前列。据《中国古籍版本学》的统计,刻书超过10种以上的藩府有:“弋阳府56种,蜀藩38种,楚藩26种,周藩23种,宁藩22种,赵藩20种,辽藩18种,庆藩13种,益藩12种,沈藩11种……”[45],蜀府在数量上也名列前茅。刻书的基础是藏书,清人彭遵泗称:“藏书之富,敝乡之成都,莫比蜀府。成王喜读书,宫中为石楼数十间,藏书数亿万卷,日抄写者数百人”[46]。而且大多数蜀王也实实在在地爱读书,“潜心孔学应无倦,适间虞琴肯放闲。须信尊贤忘势利,行看礼乐继河间。”[47]蜀王们从中找到了乐趣:“简编用志须研究,坟典开心可卷舒。”[48]这些行为使蜀府在文人群体中树立起情趣高贵的群体形象。
三、蜀府积极参与锦城社会生活
蜀王府建筑宏伟,设计之初就带有“壮丽以示威仪”的意图,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成都600多年的文化中心。这里虽然不是成都的行政中心,但蜀府以模范作为,使其成为西南地区代表朝廷的演礼中心。其一举一动,在当地百姓看来都是睿旨纶音,深深地影响着成都乃至周边民族地区。具体方式包括鼓励名士风范,提携名医,修庙、修名人祠堂,创建市民公园,捐建义冢和桥梁,提倡以散曲为代表的音乐等,积极参与锦城的社会生活,并以自己的品味影响着成都。
成都自宋末以来,经济萎靡、文化凋敝,明初开始恢复,这与历代蜀王的关注与贡献密切相关。我们从几代蜀王所写“成都十景”[49]就能看出。蜀王除从外省延揽名士外,对当地的文化人也大力提携和表彰,热情为社会树立一些楷模。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蜀王命人写诗来赞美,如“王福,成都人,读书尚义。伪夏时,元御史丁帮翁流寓于蜀,福馆之,事以父礼。既卒,厚殡葬之不吝。蜀王闻其事,更名曰义,命儒臣诗以美之。”[50]对另一些人,蜀王则直接赐予田产改善生活,如“杨敏,字学可,新都人,师杜圭,博经史,避兵云南,还蜀,明玉珍迫之,不仕。洪武赐钞归隐。蜀献王给田八十亩,赠云:流水画桥题柱客,清风精舍读书人。”[51]
对医术高明者,蜀王积极向朝廷推荐,使之更好地造福于人。如“叶拱北,字朝贵,彭县人,幼习儒业,有大志,因母病,究心医理,遂精焉。天性孝友,博学能文,尤工诗,嘉靖乙酉(1525年),蜀成王深慕其名,卑礼聘之,试辄奇中,赐宅成都。疏荐于朝,应礼部试,居第一,授以良医正。回蜀,曾制《存养省察论》陈于王,王嘉纳焉。每岁制方药施贫乏者,其门如市。”[52]
对于成都西门著名的杜甫草堂,历代蜀王倾注心血最多。朱椿亲自到现场调查,访问当地人员。他有诗道:“卜居草堂近,梵刹有遗基……缅怀杜陵老,千载同襟期。”[53]修杜甫草堂时,方孝孺在蜀并撰文记载,即后人回忆的“蜀献王之始封也,见祠隘且就圮,曰:‘是足以妥灵而处祀乎?遂拓而新之”[54]。之后多位蜀王又有维修,到张时彻巡抚四川时,又向时任蜀王朱让栩禀报要搞大型的修缮工程。蜀府应允,“遂辟廊庑,起甍栋,引流为池,易甃以石,规模壮丽,增于故昔盖十之六七,费白金三千有奇”[55]。杜甫草堂是成都著名景点,来参观游玩的人众多,因之对蜀府的评价甚高:“是举也,见今王绳武之孝焉,尚贤之诚焉,风后之烈焉,非恭俭乐善,其孰能之?”[56]而蜀王本人对修缮工程也很满意:“遥指西郊旧草堂,少陵遗迹未荒凉……游人仰止祠前水,一曲沧浪引兴长。”[57]
之后,张时彻又请蜀王出力为诸葛亮建专祠,结果蜀府也同意了,“辟浣溪之隙地而祠焉”[58]。于是立碑,“盖以昭蜀王尚德之美”[59]。
蜀王在成都东门新建的祠堂,即净居寺的宋濂祠,经过几代蜀王的经营,也成为成都的著名景点。王樵《使蜀记》有记载,杨升庵受邀编撰《全蜀艺文志》,就是在净居寺花了28天完成的。对于这个祠堂,王士桢是这样记载的:“过桥至净居寺,气象疏豁。入山门为明王殿,次弥勒佛,次大雄殿,皆有画壁。最后藏经阁。西出为文殊殿,即宋(濂)、方(孝孺)二公祠,有宋文宪公(濂)像。殿后文宪墓,高如连阜,其上修竹万竿,扶疏栉比,无一枝横斜附丽。”[60]
蜀府还修了一些惠及面广的工程,如位于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园。成都老人口碑相传:“王宫之东另建园囿,内有古梨树数十棵,均二三百年古木,每年三月成都士女游玩其间”[61]。城外面的小工程很多,如新都由蜀府郡王修的德阳王桥,“旧名大小毗桥,水势极险,往来病涉,王命官督建,巡抚李公大书其碑曰德阳王桥。”[62]又如供穷人使用的坟地,即“义冢地,府城四郊,蜀府置”[63]。
蜀府喜欢与民同乐,但不声张、不扰民,如诗:
元宵[64]
银汉月华明,游人队队行。
笙歌归禁苑,灯火下蓬瀛。
笑语喧花市,星球璨锦城。
良宵堪玩赏,归去马蹄轻。
这种“归去马蹄轻”般悄无声息地参与,导致蜀府的存在感不强。然此处无声胜有声。蜀府在公众场合的低调,彰显出自由、平和而内敛的贵族气质,在潜移默化中自然提升了成都的城市品位,当是“忠孝为藩”的体现。
四、蜀府对家人进行严格管束
蜀府的蜀王不仅自己以身作责,主动作为,同时还严格约束家人,包括各郡王及其子孙、姻亲,以及属臣。蜀王的处置有时是非常严格的,如一些郡王犯错,就被剥夺继承资格,甚至迁出四川。[65]这些人后来糟糕的境遇对其他宗室的警示教育作用巨大。另外,偶尔发生的臣属在地方欺凌跋扈之事,因为不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或不可调节的矛盾,蜀府也都妥善处理,既平了民愤,又维持了蜀府的尊严。嘉靖年间刚入职行人的王樵称“蜀藩贤于富,宗人少犯法,亲王尤厚礼士大夫”[66],就代表了京城对蜀藩的整体印象和评价。能达到这种效果,缘于蜀府以理学为宗,教育到位。这方面第一任蜀王朱椿作出了典范,他甚至在生病时仍然在回忆从宋濂处所受的教诲:“却忆潜溪老,清宵魂梦驰。”[67]这使得蜀府在成都公众面前呈现出一个比较贤良的形象。蜀府内,郡王、“将军”的先进事迹自然也很多。其中一位奉国将军的事迹尤为显著。
《天启成都府志》载:“朱让栋,号几山,汶川奉国将军。生而慈和正静,能笃爱父母,顺承三兄,常捐赀济内外婚丧,以居产让贫族。方伯余公建桥塔,助米百石。中年丧淑人唐氏,遂不娶。居常延名师教二子诸孙,家庭礼让,宛然儒风。其冢子中尉承燸,博雅敦伦,绰堪宗范,先栋卒,人多惜之。栋年八十,蜀端王暨本郡王褒礼稠渥交,旌其闾焉。栋善事不一,此撮其槩。”[68]这则记录中的奉国将军,属于汶川郡王府,系蜀府第五等爵位,按规定“岁支禄米六百石,俱米钞中半兼支”[69],却能动不动就助米百石,而且还“善事不一”,确实令人敬佩。
而蜀王每年出城谒陵,更是蜀府“孝道”文化的集中展示。各個蜀王对于谒陵还有自己特殊的感想,有些被记录了下来,如朱友垓《谒和园》[70]中有“寝园树木笼葱茂,朝殿丹青焕烂鲜。恩德不忘怀厚土,劬劳难报感苍天”句,表达要不忘恩德,勤劳执政。朱申凿《余谒东景山》的“兄王厚土千年固,内翰雄才百世豪”[71],则有感谢兄长之意。朱让栩《东郊谒奠先考寝园有感而作》云:“朝罢匆匆应转首,彷徨东顾不胜哀”[72],表达出拳拳孝意。
蒯氏是与蜀府关系密切的显贵家庭,第一代蒯克随献王来蜀,第二代蒯缙任西城兵马指挥司指挥,其女为定王妃;后世袭职武德将军(正五品)、武略将军(从六品)等职。蜀府遂与蒯氏成为姻亲。某年,当后者完成国家任务,受到朝廷表彰时,蜀王特作《题蒯氏八咏》组诗,对其既褒奖又告诫,总体不离忠诚、行义、周贫、抚孤、修桥、耕读等。蜀王乃借机重申蜀府对外提倡的生活方式,兹录其中一首,以飨读者:
摅忠报国[73]
平生义气许谁同,志在操修竭寸忠。
勉力拳拳期报答,小心翼翼贵谦恭。
数竿劲竹凌霜翠,一点方葵向日红。
为国勤劳无懈怠,致身常近五云东。
这虽然是蜀府为蒯氏所写,但可以想象,由于各种传播途径,对其他姻亲和本地士绅会有引领作用。
结 语
蜀府一系虽然以忠贞报国,以仁义名世,但在明末乱世却毕竟不能够挽救明朝的危亡,合族也被张献忠屠杀,王府和陵园被破坏殆尽。其时,末代蜀王至澍投井,大致效仿崇祯帝之死。至于宗室成员在都江堰附近被杀,则跟明初的“天子守国门,死社稷”的政策有关。之后如张象华《哀蜀藩》所写“天社星隳古社坛,杜鹃声尽石苔瘢。井花清冷无人汲,留得丹心万古寒”,对蜀府消失扼腕叹息的文人不在少数。在明代的社会环境下,延续200多年的蜀府一系,能够展现自觉的责任担当、高贵的生活情趣、积极的地方建设、严格的家人约束等贵族精神,代表了那时贵族阶层的很多优良品质,虽地处西南一隅,却为全国作出了表率。蜀府这种有实绩、有文献、有文集、有陵墓、有民间口碑支撑的贤王群体,随着今后的系列研究成果(如《蜀府文教化一方》《杨升庵与明蜀王》《献王家范详论》等)的陆续推出,藩王的形象将被重塑,而中国传统贵族精神将会重现光芒。这也是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从传统中撷取的一份文化自信。
注释:
[1]见《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九、卷五百六十六,《明光宗实录》卷七,《明熹宗实录》卷六、卷十八、卷三十、卷三十七、卷七十九等。
[2]《崇祯长编》卷五十二,崇祯四年十一月戊子,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第3032页。
[3]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按照明朝制定的宗法系统,即:第一顺位:父死子继,有立嫡立嫡,无嫡立长;第二顺位:无后,兄终弟及,嫡弟优先,庶出其次;第三顺位:叔伯侄,先嫡后庶。有些郡王的继承资格是事先被蜀王剥夺的,后面的研究计划《献王家范详论》将作解释。
[4]笔者自费从日本公文书馆找到《献园睿制集》《定园睿制集》《怀园睿制集》《惠园睿制集》,并取得扫描件,配合国内的《长春竞辰稿》,目前已经完成基础性研究三篇:《明蜀王文集考——兼论从日本新发现的四部与国内仅存的一部》(《文史杂志》2017年第3期);《少城一曲浣花溪——明蜀王文集中明代成都的初步印象》(《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壮丽以示威仪——明蜀王府建筑群的文化内涵》(先被《天府文化研究院》第一卷收录,再发表在《文史杂志》2018年第2期)
[5][30]博克舍(CharlesBoxer),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vira,Fr.Gaspar da Cruz,0.P.[and]Fr.Martin de Rada,O.E.S.A(1550—1575)London (1953),pp.40—41.41—42.转引自(英)柯律格著、黄晓鹃译《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5页,第27页。
[6](明)朱椿:《献园睿制集》卷十三,成化二年刻本,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书号“汉16870”。
[7](明)释宗泐:《全室外集》卷四《蜀王江汉朝宗图》,台北:明文书局1981年版,第30页。《明实录》上另有“书‘忠孝惟藩以自警”的记载。
[8][31][32][34][48][71][73](明)朱申凿:《惠园睿制集》卷六、卷二、卷七《勤政堂》、卷十二《思政堂》、卷四《涌泉书舍》、卷七、卷六,弘治十四年刻本,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书号“汉16874”。
[9]《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第680页。
[10][11](明)杨慎:《长春竞辰稿》序,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五辑第1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23页。
[12](明)游淄:《长春竞辰稿》后序,第625页。
[13][27][36](明)刘大漠、杨慎等纂修(嘉靖)《四川总志》卷四十八、卷一、卷一,书目文献出版社,第698页,第20页,第20页。
[14][35]《明孝宗实录》卷七十八、八十,卷一百三十,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第1497、1524页,第2298页。
[15](明)《礼部志稿》卷七十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2页。
[16][17][18]《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卷三十、卷八十,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第790页,第790页,第1858页。
[19]蜀府“文教化一方”的内涵和具体措施非常丰富,笔者规划有专文论述。
[20]《二十五史》卷十二《明史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版,第705页。
[21]见龙显昭主编《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巴蜀书社2004年版。
[22](明)朱申凿:《惠园睿制集》卷六《西岷保障》有“将军挂印镇西岷,攻击羌酋靖虏尘”句。
[23]云间顾山贞撰《客滇述》有“蜀府宗支多在灌县,乃发兵围之,不论宗室细民皆杀之”,载叶梦珠辑《续编绥寇纪略》卷一,第5页。《鹿樵纪闻》卷中有“知蜀府宗支多在灌县,围而屠之;蜀世子亦被害”。
[24][41][47][64][70](明)朱友垓:《定园睿制集》卷四、卷三《茶人》、卷四《书斋闲咏》、卷二、卷四,成化五年刻本,藏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书号“汉16869”。
[25]目前在崇州、大邑、资州都发现有关“蜀府正字”的碑文,具体是承奉正办贡茶等,详细内容后面有专文论述。
[26](明)方孝孺:《成都杜先生草堂碑》,《遜志斋集》卷二十二,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716页。
[28](明)虞怀忠、郭棐等纂修(万历)《四川总志》卷二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00—23,齐鲁书社。
[29](清)黄廷桂监修《四川通志》卷十三上《水利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3]据《明实录》,朱椿是进京朝觐次数最多的蜀王。
[37](明)朱椿:《献园睿制集》卷十五《赐和典宝新荔枝并诗二首》。
[38][39][40][42][43](明)朱申:《怀园睿制集》卷二《荔枝》,卷二《荔枝》,卷七《稻》,卷三《凉亭避暑》,卷七《避暑》。
[44](清)罗廷权等修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十六,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第33页。
[45]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版,第273页。
[46](清)彭遵洒:《蜀故》卷十八《蜀府藏书》,清乾隆刻补修本,第52页。
[49]详见拙著《少城一曲浣花溪——明蜀王文集中明代成都的初步印象》(《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50][51][52][62][63][68](明)赵世雍撰《天启成都府志》,卷二十四《孝义列传》、卷二十五《隐逸列传》、卷二十四《孝义列传》、卷三、卷三、卷二十四《孝义列传》,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页,第339页,第331页,第66页,第57页,第328页。
[53](明)朱椿:《献园睿制集》卷十三《赐草堂谦巽中长老》。
[54][55][56](明)张时彻:《重修杜工部祠堂记》,杜应芳:《补续全蜀艺文志》卷二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678册,影印明万历刻本,第290页。
[57](明)朱让栩:《长春竞辰稿》卷八《成都十景》之《草堂晚眺》。
[58][59](明)张时彻:《新建诸葛忠武侯祠碑》,杜应芳:《补续全蜀艺文志》卷二十九,第290页。
[60](清)王士桢:《秦蜀驿程记》,转引自吴世先主编《成都城区街名通览》,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
[61](清)吴伟业撰,李学颖点校《绥寇纪略》“献忠屠蜀”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5]蜀府第一代郡王华阳王就被迁出四川,这一支后来有很多不良记录,但与蜀府已经关系不大,后面的研究计划《献王家范详论》将作详细解释。
[66](明)王樵:《使蜀记》,《方麓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2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67](明)朱椿:《献园睿制集》卷十四《卧病述怀》。
[69]《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666—668页。
[72](明)朱让栩:《长春竞辰稿》卷十一。
作者单位: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