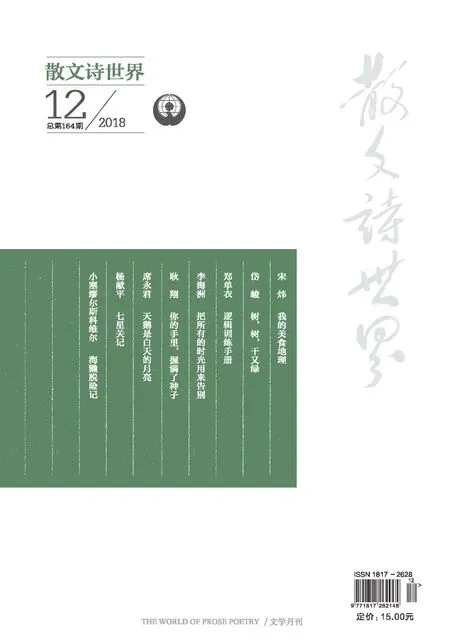出生地
吉海珍
我总梦见那个地方,那里有时候一片荒芜,墙垣,黄草,枯树。而更多的时候,我梦见的是草木葳蕤。梦见大山,草木,花朵的连绵不绝,经常感觉流水声就在枕边,那是熟悉却触摸不到,陌生却又流淌着温暖的地方。总无法分辨是生活在梦里,还是生活在生活里,这时我才发现那是我过去和现在内心思绪的对立体现。
该如何界定这种对立,又该如何甄别梦里的归属地。为此,我站在山顶一一排查从山坳中升腾的炊烟,我熟悉松木燃烧的颜色,那一团淡青色的烟一升上来我就能准确定位我呱呱坠地的院子,也曾站在岩石上聆听虫儿翻动土块的声音,那声音极其细微,那是我的秘密,从未与人分享,可梦里炊烟一直未曾升起,除了我的心跳和呼吸,没有任何的虫鸣,它们兴许在我的梦里做着它们的梦。
炊烟是根带子,拴住了所有内心有乡愁的人,我喜欢阿妈捧在手里细碎的红花,钟情于金灿灿的麦地,我经常残忍地用一把镰刀割断它们与大地的联系,之后变成喂养人们的馒头、面条和饼 。还有像银梯子一样的六月的田,水汪汪的,像孩童的眼睛,那样的清澈我曾经拥有,现在一路往回,寻找这些已经丢失了的珍贵。直到那夜,月光漫过窗台。
月光从山的那头过来,有些疲倦,我不知道这些落在窗前的月光,照见了多少人的醒与梦,经过房屋,森林,河流,石头,城市,乡村,原野。光,躺着,光溜溜的,爬满窗台,我有些慌张,以至于好长一段时间,都把月光搁在窗外,让自己黑黑地安睡。
更多时间,月光照着我的床,床头到床尾,夜复一夜,枕头上的花朵都照开了。当满世界的风到处乱抓时,我可以安静地躺着,躺在软绵绵的月光上,而那时光也均匀地盖着我的梦。
那夜,月光漫过来的时候也带来了西边的鸟鸣,一只猫头鹰停在路边的榕树上,叫声渗人。在我的村庄,猫头鹰的叫声预示着死亡。是的,那一次我亲眼看见猫头鹰就停在屋檐上,发出哀鸣,那晚月光皎洁,如果声音有颜色,或者形状,一定能够看得清它何时经过我,以及之后的路程。一声接一声的鸟鸣把舅舅叫走了,仿佛那是外曾祖父母的呼唤,舅舅就这么丢下了外公外婆跟着那叫声走了,以至于多少年来我都无法原谅一只鸟,从那时起,这个我既恐惧又无法摆脱的声音便混入了我的血液,日益膨胀。
鸟还在叫,我开始蜷缩,声音越来越大,叫声越来越近,仿佛就在窗外,栖息在月光的枝丫上,空气里全是声音和声音背后的恐惧,充满屋子,它们从耳朵进去,一口一口啄食着我的肉体。它们住进我的内心,膨胀成无形的怪兽,充满每个毛孔,把体内的水分一一挤出后,让寒毛清醒地立着。关门,关窗,拉帘子的时候,右手抖落的月光躺在黑暗的墙角,瑟瑟发抖。
许多夜晚我和妹妹搬来小凳子,坐在洒满月光的院子里,等着父亲打猎归来,但每次等父亲回到家时,只有母亲一人在那用玻璃酒瓶制成的煤油灯下醒着,第二天父亲总会讲起打猎的过程,时间长了,妹妹和我都知道,父亲大部分的打猎时间都在砖房附近,那里种植着一大片黄豆,那是父亲和母亲一锄一锄挖出来的,又在地边建盖了一间小屋,土墙,干瓦,一张简易的床和一个三角,父母在地里劳作的时候,我在三角下烧火,烧水煮饭炒菜,妹妹坐在床板上用手抠着土墙上的泥。
一块地,一群动物,一家四口。地里种过麦子、玉米、黄豆,我没有追上过野兔,但却亲眼见过父亲和小黄追麂子的情景。那时候,就在月光下,父亲每夜都能带回惊喜,兔子居多,长大后知道我走过的所有山路都留有父亲的脚印,我始终循着父亲的脚印从大山走到了城市,那些一串串看不见的脚印成了我最初对父亲的敬仰。
漫过窗台的月光像那一串串的脚印,漫过土墙,漫出了我的回忆录。那夜,月亮垂直照着我的时候,我正跪在爷爷的棺椁前,父母,叔婶,弟弟妹妹们一排排跪着,拜着,像是地田高低的麦子随着风弯腰和起身,麦子,黄豆,玉米,豌豆。兔子,麂子,野鸡,一茬茬庄稼,一拨拨动物,父亲学会了守护粮食的本领。正当播种麦子的季节,他扔下了耕作了一辈子的家走了,没等到收获。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给爷爷跪着。如果爷爷能活过来,我宁愿一直这样跪着。
如果真能跪活,父亲一定最想跪活奶奶,我不能想象一个九岁的孩子是怎样面对死亡的,失去母亲的痛一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从不敢在父亲面前提起奶奶,也从未听父亲说起过奶奶,那是父亲内心最深的痛,哪怕只言片语都能诱发还未愈合的伤口。在心灵和身体的双重煎熬下,父亲学会了生存,比如要守住一块地的粮食,就必须学会夜晚的潜伏,与动物们周旋,种植与狩猎变得同样重要,粮食保住了,生命才能延续,更何况是一家四口的命。
母亲同样关注活着,不仅我们,还多了一群牛羊猪鸡,喂饱了所有的嘴,母亲的一天还没结束。许多个夜晚,月亮升了一大截,母亲才回来,不同的方向,去地里的时候从后门回来,去田里的话从大门进来,脊背上永远少不了东西,草,玉米秆,稻草,麦秆,蚕豆,豌豆,加上月光,压得母亲直不起背。把一捆捆月光歇在圈楼上,让牲口一把把吃下,这是母亲常在月光里做的事。而那时的我,唯一的事就是等,等待一团黑影远远地向着我走来,我才安心地收回伸长的脖子和垫着的脚。月光重复地被我垫在脚下,一年年,我的内心变得澄明,安静。
我热爱土地,母亲总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上面,挖起的土块让坡地更加起伏,母亲抡起又放下的锄头把阳光一点点敲碎,混在泥土里,以至于我坐下时那滚烫让我立刻站了起来,也有一部分的月光,还在表面,如果继续地捶打,那么坡地应该会发光,像萤火虫一样忽明忽暗。
我看着月光,月光照着我,照着城市与乡村,照着喧嚣和宁静,照着生活的苦难与艰辛,照着内心的喜悦与悲伤。月光,照着所有人的夜,照着所有人不同的活着和死去。
可,无论活着或者死亡都离不开这片土地,这是从泥土,空气,河流注入到血脉,骨髓里分割不开的联系,这就是我的出生地。
祖辈开辟的荒原,一茬茬玉米,水稻,小麦随季节轮流上场,一代代带着虎性的族人在一个个茅屋,木屋,瓦屋下出生,死亡,粮食更替,生命延续。延续着祖辈的血液,延续着民族的符号,民族的自豪。
出生地孕育了我的生命,长出了我的思想,从这里我触到了母亲宽大粗糙的手掌,那是与锄头、镰刀、斧头交替摩擦的印记,就是这样一双手托起了我的生命,把我送出了布满红土的故乡,让我的双手远离她长久握着的农具,让我可以用一支笔记录生活,不用日晒雨淋地担心一粒粮食。在出生地,我怀念那片土地,怀念母亲及族人,喂饱馋虫的外婆味道,还有爷爷手里握着的那柄长刀。
当爷爷手握长刀,把这种带着彝族族性温度的舞蹈带到漾濞江,带到雪山河的时候,爷爷舞出了族人的精气神,舞出了村庄原始的野性,这也注定了我的出生地再也不仅是落噶河一带,爷爷打开了一个更大的地域,让我的出生地变得更加辽阔,让我的脚步能够抵达更远的未来。
用一幅画铺展辽阔的出生地,江,河,城,居所就这样安下来了,一幅画就沿河延伸。
想起画的时候,我先想到了村庄里绣花的族人,一针一线一层一层绣开梅花、桃花、梨花、木棉花,绣出蝴蝶飞舞,秀出喜鹊叫梅,秀出龙腾虎跃。就借用此法,福国寺,云龙桥,老街,茶马古道旧色的历史印记为底色,这是静态和永恒的水墨画,在时光变迁中越发让人铭记。
画布是平铺的,但我依然可以看到上面高耸着的大山,苍山,白竹山,万宝山,还有更小的山脉撑出出生地的立体感。石门关,一线天,像两副马鞍把苍山流水从鞍子底部流出,江水,河流,溪流,大大小小,布满了画卷,在山间缓缓穿行,那些水花是乳白色的。眼前望不尽的大山是不同人定位出生地的坐标,就像我更小的出生地,在白竹山脉,文笔山脚,这样说来,就能准备找到我呱呱坠地的那片土地。这也是生长在滇西大地的我们走不出的包围圈,在无数这样的包围圈里,养育出了有着博大胸襟,热情勤劳的彝族,白族,栗粟族等众多民族。
在更广意义上的出生地,除了我的族人,还有白族、傈僳族和更多的民族居住着,他们同样拥有自己固定的出生地,之后大家一起分享着延伸了的出生地,我们的居住地不同,风俗、语言、服饰各异,但唯一没有差别的便是对出生地的眷恋与热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心的赤诚,他们在获取的同时敬奉着神,山神、树神、灶神、门神、地神、牛神,他们拥有人类最原始的淳朴和信仰,他们同样对漾濞江、雪山河的滋养充满着感恩。
我热爱我的民族,热爱绣满花朵的彝族服饰,热爱只有族人听得懂的语言,房前的梨花,桃花,木瓜花,屋后的石榴花,梧桐花,槐花,地里的豌豆花,蚕豆花,核桃花,还有落噶河边的攀枝花,芦苇,这些让我拥有了对美表象的认知,而真正的美却是从族人的勤劳、善良里读懂的。
美,源自于出生地。我说的是大山的隐私。我要把这些秘密都搬到出生地的画作上,让它们在山巅绽放,在阳光里娇艳,在流水里沉睡。是的,我说的就是苍山西坡那片花海。每年三月,这里的春天都会活得很招摇,仿佛日子只过这一次,但来年又重复着招摇。我说招摇,并不带贬义,相反,是对那火热的一种敬仰,像火把节里一支支火把,风吹不灭,雨浇不熄,把苍山照得通红,也绘出出生地的热情,如载歌载舞的彝族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