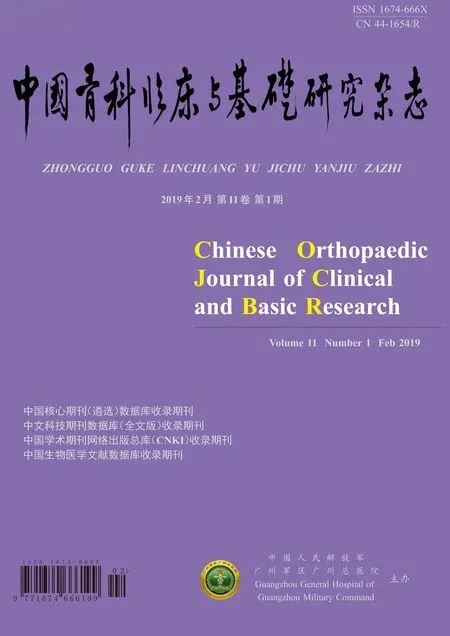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并发症研究进展
陈计稳,郑小飞,郑博元,王华军
肩袖撕裂是肩部最常见疾患之一,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体育、健身等运动事业的发展,肩袖撕裂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于上世纪90年代初问世,由于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等优点,目前已逐步取代开放手术,成为治疗肩袖损伤的金标准[1-2]。然而,随着对该手术技术总结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其术后并发症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影响手术效果、患者满意度及生活质量,严重者甚至导致肩部功能的丧失[3-4]。本文对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并发症及其防治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围手术期治疗方案的制定及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提供参考。
1 术后再次撕裂
肩袖再次撕裂是肩袖修补术最重要的并发症之一。以往数据显示再撕裂发生率超过11.4%[5],尤其是巨大肩袖撕裂,发生率甚至高达94%[6]。术后肩袖的完整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患者年龄、术前撕裂大小、肌肉萎缩、脂肪浸润、糖尿病、吸烟以及过激过早的康复方案等[7-8]。
1.1 年龄
基础研究方面,Plate等[9]的生物力学实验表明,高龄大鼠肩袖修补术后8周肌腱最大负荷明显小于幼龄大鼠;病理切片提示高龄大鼠腱骨结合部位成纤维细胞排列紊乱,腱骨界面胶原纤维组织形成较少,且与原腱骨组织结构差异较大,腱骨愈合稳定性显著降低。临床研究方面,Cho等[10]对87例全层肩袖撕裂关节镜下缝合桥修补术后患者进行平均25个月的随访研究,将患者分为≤50岁、50~60岁、≥60岁3个年龄组,MRI结果显示肩袖愈合率随年龄上升而逐渐下降,分别为81.8%、78.4%和39.3%;60岁以上患者术后再撕裂率显著增加。Diebold等[11]对1 600例肩关节镜下肩袖修复患者进行随访,结果显示术后肩袖再撕裂率随年龄增长呈线性升高,其中50岁以下5%,50~59岁10%,60~69岁15%,70~79岁25%,80岁以上高达34%;而肌腱愈合率则随年龄升高呈降低趋势,考虑与肩袖质量和血供随年龄增大而下降有关。
1.2 撕裂大小
一项217例肩袖撕裂患者的多中心研究显示,肩袖修补术后12个月总愈合率为122/217(56%),进一步分析发现愈合率随撕裂面积增大而下降,其中小撕裂及中等撕裂愈合率相差不大,分别为66%和68%,而大撕裂愈合率下降至47%,巨大撕裂仅有27%的愈合率[12]。有学者分析一组25例75岁以上的肩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病例(平均随访时间36.3个月),36%的患者出现肩袖再撕裂,中小撕裂、大撕裂和巨大撕裂的再撕裂率分别为13%、60%和80%,术前肩袖撕裂的大小与再撕裂率成正比[13]。Gulotta等[14]对193例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患者进行长达5年的前瞻性随访研究,结果也证实术后肩袖再撕裂的发生与术前撕裂的大小关系密切,术前撕裂越大,则术后再撕裂几率也越大。
1.3 生活习惯及代谢因素
患者个人生活习惯也与术后再撕裂的发生密切相关。Neyton等[15]对行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的105例小至中等冈上肌撕裂患者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非吸烟组肩袖愈合率为93%,而吸烟组愈合率为78%。吸烟严重降低了肩袖的愈合能力并影响手术效果,这可能与尼古丁等有害物质加重肩袖损伤处炎症反应,进而延缓肩袖愈合有关。
代谢因素如糖尿病也会对肩袖愈合产生影响。Bedi等[16]的生物力学检测结果提示,糖尿病组大鼠腱骨界面的纤维软骨明显减少,胶原纤维排列紊乱,局部糖基化终产物沉积增加,肌腱组织脆性加剧,腱骨结合部的力学性能遭到破坏,导致糖尿病组大鼠肩袖重建后力学性能显著低于正常肩袖修补组。一项对335例肩袖损伤关节镜下修复术后患者进行的回顾性比较研究(平均随访时间>2年)表明,非糖尿病组再撕裂率明显低于糖尿病组(14.4%vs35.9%)[17];Rechardt等[18]对6 237名芬兰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发现1型和2型糖尿病均与男性肩痛和肩袖肌腱炎增加有关;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证明糖尿病是肩袖修复后愈合失败和活动范围受限的危险因素[19]。
1.4 其他因素
脂肪浸润、肩袖回缩程度、术前症状持续时间等也是影响术后肩袖再撕裂的因素。脂肪浸润是老年患者肌腱退变的常见病理表现,Godenèche等[20]对182名肩袖修复术患者进行10年随访,MRI结果表明冈上肌脂肪浸润Goutallier 0级、1级、2级、3级的再撕裂率分别为10%、22%、31%、100%,提示肩袖脂肪浸润是肩袖修补术后再撕裂的高危因素。肩袖回缩增加了肩袖修复后的张力,导致足迹覆盖不良,回缩越严重,则表示肌腱质量越差。Kim等[21]对180例中、大撕裂肩袖修补术病例进行2年随访,结果显示,再撕裂组患者术前肩袖回缩程度明显大于愈合组。亦有学者研究发现,与术前症状持续时间<24个月患者相比,>24个月的患者术后6个月再撕裂率显著增加(20%vs13%)[22],可能是由于症状持续时间较长、病程迁延往往会加重病情,脂肪浸润和肌腱回缩程度更加严重,肩袖质量大大下降,肩袖损伤复杂化,增加了手术难度,最终导致再撕裂率的升高。
有鉴于此,对于符合手术适应证的患者应积极治疗,切勿贻误病情;临床上应针对上述危险因素,结合患者术前情况和撕裂程度决定修复策略,然后根据术中所见制定个体化的术后康复方案,尽可能减少再撕裂的发生。
2 术后关节僵硬
肩关节僵硬是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发生率约为2.6%~32.7%[4,23]。诸多因素可导致术后肩关节僵硬,包括术前诊断为钙化性肌腱炎、粘连性滑囊炎,或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采取盂唇损伤修补术、冈上肌关节侧部分撕裂修补术等术式也是导致肩关节僵硬的因素[24]。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术后制动时间过长以及未按康复方案要求进行锻炼[25]。Huberty等[23]将术后肩关节僵硬的诊断标准定义为患者对术后肩部活动范围不满意,结果发现489例患者镜下肩袖修补手术后肩关节僵硬24例,行镜下肩关节松解术后关节活动范围均达到满意程度。随后Randelli等[4]总结2 890例患者中414例出现并发症,其中74例为术后关节僵硬,发生率为2.6%。
关节僵硬常合并肩袖再撕裂。Chung等[25]研究发现,肩关节术后出现僵硬的患者肩袖再撕裂率高达89.5%(17/19),明显高于未发生僵硬的患者,原因可能是此类患者依从性往往较差,不能按计划进行科学的康复锻炼,出现关节僵硬后为弥补之前欠缺的锻炼而加大运动负荷,反而造成肩袖再撕裂。
肩关节僵硬对手术效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仅为轻度粘连,可嘱患者积极采取康复锻炼,疼痛耐受差的患者可在臂丛麻醉下行手法松解;而对于严重僵硬的病例,往往需再次手术。早期积极锻炼是预防术后肩关节僵硬的主要措施,但对于巨大肩袖撕裂或肌腱质量差的患者,过早过度的锻炼可能会导致肩袖再次撕裂。因此,肩袖修复术后应根据患者损伤程度和手术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适时适度,循序渐进。
3 术后感染
据报道,肩袖修补术后感染发生率约为0.85%~1.0%[26-27]。感染一旦发生,常引起骨髓炎、脓肿形成、盂肱关节炎、软组织覆盖不足等严重后果,不仅增加患者的痛苦,而且加重其经济负担,严重者甚至需要再次手术。术后感染的临床表现多样,可有红、肿、热、痛、关节僵硬、渗出等,病情严重者可出现疲劳、败血症等全身症状。
3.1 影响因素
肩关节镜术后感染的发生与手术方式、患者体质、手术时间等因素密切相关[26,28]。Vopat等[26]研究术式对感染率的影响,发现由1名医师主刀的1 824例肩袖修补手术中,14例发生早期感染,需要手术灌洗和清创,其中全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手术3例、余11例为开放手术,开放手术感染率明显高于全关节镜下手术;该研究还发现患者性别和体质量指数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2004年至2014年10年间在同一科室行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的3 29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总感染率为8.5/1 000;分析指出,男性、年龄超过60岁、手术时间>90 min是感染的预测因素;围手术期应用抗生素预防是术后感染的独立缓解因素,可将感染率从28%降至1.54%[27]。
3.2 预防和处理
肩关节镜手术感染的主要预防措施包括:①术前严格检查白细胞计数、血沉、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仔细观察手术区域或其他部位是否有潜在或明确的感染灶,若有确切感染灶存在,应积极控制感染后再行手术;对可能发生感染的病例,术前预防性使用抗生素。②术中严格无菌操作,手术时间超过3 h者于术中追加一次抗生素[29]。③术后切口加强换药并密切观察;如意识到有深处感染可能,应积极外科清创灌洗并针对性使用抗生素;一旦疑有感染,需对患者进行包括临床症状和体征、实验室检查在内的彻底检查。急性病例很少需要细菌培养和影像学检查;在亚急性或慢性病例中,彩超和MRI检查对检测肩关节周围脓肿形成或鉴别并发症很有价值。治疗感染的方法包括关节镜下或开放灌洗和清创、静脉应用抗生素等。
4 缝线锚钉相关并发症
锚钉缝线是肩袖修补术中最常用的材料[30]。其相关并发症主要有缝线磨损断裂以及缝线对肌腱切割导致的肌腱断裂。最容易发生磨损断裂的部位在钉孔、骨缘及线结处。Meyer等[31]研究发现,金属锚钉钉孔边缘非常锐利,锚钉正常植入时其钉孔处最易发生缝线磨损与断裂;如果锚钉植入过深,缝线与骨面可能发生切割磨损,造成缝线断裂,导致手术失败。
缝线对肌腱也有切割作用。Cummins和Murrell[32]对22例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后再次撕裂的患者进行翻修手术,术中发现缝线-肌腱界面是肩袖再撕裂最常见的部位,缝线对肌腱的切割作用往往是肩袖肌腱再次断裂的原因。因此有研究通过增加固定点(缝线与锚钉)的数量来改善缝线-肌腱界面的张力,尽可能避免缝线对肌腱的切割[33]。
肩袖修复失败的另一个常见原因是锚钉松动脱落,主要是锚钉植入位置欠佳或骨质疏松所致。Roth等[33]的尸体标本生物力学研究提示,骨皮质厚度是锚钉疲劳寿命及最大抗拉强度的决定性因素,锚钉最大拔出力随局部骨皮质变薄而大大降低。Kirchhof等[34]对36具尸体标本进行高分辨率定量CT扫描,结果表明,肱骨大结节后内侧骨质量最高,是锚钉固定的良好位置。Strauss等[35]的研究表明,45°植入锚钉固定局部产生的剪切力更大,易于失效,与传统deadman角(锚钉与骨面夹角≤45°)相比较,锚钉呈90°植入大结节及于肱骨头关节面连接处固定,效果更佳。
锚钉缝线术后亦可产生异物反应,尤其是可吸收材料,术后异物反应常见。肩袖翻修术中经常发现锚钉缝线周围包绕过度增生的疤痕组织或炎性组织,无菌性脓肿很可能是最终结局[36]。异物反应症状明显者需取出异物,甚至需要翻修手术。Goto等[37]报道1例肩袖修补术后金属缝线锚钉致全身性皮肤过敏反应的患者,对症治疗无效,二次手术取出锚钉后,过敏症状迅速缓解。尽管锚钉缝线导致的异物反应极少出现,但仍需提醒关节外科医师注意。
5 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和肺栓塞
肩关节镜手术后DVT少见,Alyea等[38]对914例肩关节镜手术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术后DVT发生率为0.66%。Schick等[39]一项对15 033例患者进行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发现,VTE发生率为0.15%。延长手术时间可能导致灌注液使用量增加,更易引起局部软组织肿胀,而术后肿胀的手臂常需制动,进一步增加手臂的组织压力,阻碍静脉流动,引发血栓形成[40]。为研究肩关节镜相关DVT的危险因素,有学者在意大利进行9个中心、1 366例患者参与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结果证实性别、年龄、手术时间>60 min、体质量指数>30 kg/m2是DVT的危险因素,抗凝药物的使用对DVT并无预防作用[41]。不止抗凝药物,阿司匹林的使用对于肩关节镜手术患者,也不能使本就很低的DVT、PE发生率进一步降低,机械预防和早期动员已然足够[39]。研究表明,肺栓塞的发生与创伤/骨折、手术、脑卒中、恶性肿瘤及急性心肌梗死等密切相关[42]。鉴于肺栓塞对患者生命的严重危害,肩袖修补术患者术后也应密切观察,给予足够重视。
导管直接溶栓技术可通过导管令溶栓药物直接到达血栓部位,疗效良好,安全性高,是目前治疗急性DVT和肺栓塞的重要手段[43-44]。而作为新型溶栓药物,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NK突变体(TNK-t PA)和重组人尿激酶原溶栓效率高、特异性好[45-46],可用于对这两种并发症的溶栓治疗。
6 其他并发症
肩关节镜下肩袖修补的术中并发症还包括关节软骨及关节盂唇损伤、肩关节周围血管神经损伤、器械断裂等,术后并发症有肩关节肿胀、脂肪液化、三角肌纤维化、术后出血及关节内血肿、反射性交感神经营养不良(reflex sympathetic dystrophy,RSD)等[47-51]。
术中并发症多因手术操作不够严谨、局部解剖变异、器械质量问题所致。术后关节肿胀与手术时间过长、术中过多灌注液外渗导致局部组织水肿有关;脂肪液化的可能原因是肥胖导致局部脂肪过多,过度使用离子刀后脂肪损伤变性,手术区域局部血运受损引起脂肪组织无菌性坏死等;三角肌纤维化主要指以三角肌纤维化渗出为主的肌纤维炎,可能与术中三角肌损伤有关;术后出血及关节内血肿主要是操作粗暴、术中止血不彻底造成[50]。加深对镜下肩袖修补术及其并发症的认识,熟悉患者体位和解剖变异,合理选择手术入路和手术器械,熟练操作技术,不断积累和总结手术经验,有望大幅度降低这些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RSD属罕见并发症,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常继发于外伤、手术及某些血管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受累肢体出现明显肿痛伴活动受限、多汗、颜色和温度改变以及感觉过敏等。目前仅在Brislin等[51]的一项对263例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的研究中报道过1例。其早期诊断十分重要,一旦确诊应尽早处理,及时给予非甾体抗炎药、皮质激素、理疗等对症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