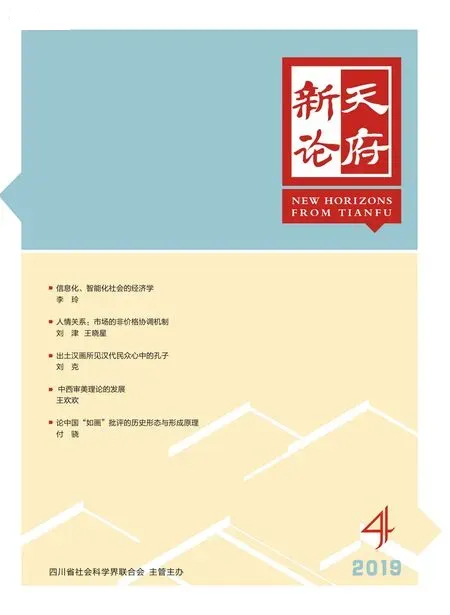调适性创新:“漫威电影宇宙”的文本策略初探
张隽隽
2008年横空出世的《钢铁侠Ⅰ》,标志着“漫威电影宇宙”(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的正式开启。截止到2019年3月《惊奇队长》收官,十多年来的21部电影已将超过170亿美元票房收入囊中。而即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Ⅳ:终局之战》的预售票房已经创下了多项纪录,可以想象又应是全球范围的“票房炸弹”。
如此辉煌的成绩,让制作了这些影片的漫威影业(marvel studios)在原创稀缺、增长乏力的好莱坞格外亮眼;IMDb、烂番茄和豆瓣等网站上不错的评分,也让因剧情俗套、人物空洞而饱受诟病的超级英雄电影重新成为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同时,一个电影圈的“外行”居然能够票房和口碑双赢,也让业内人士感到惊讶。作为老牌漫画出版公司的漫威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经声名远扬,但很长时间里并不具备制作电影的能力,只能将旗下蜘蛛侠、X战警等人气较高的角色授权给索尼、二十世纪福克斯等,获得与票房收益不相称的授权费。而且在出版行业江河日下的大环境下,漫威早已不可避免地显露出颓像,游走于破产边缘。因此,当它以多个重要角色为抵押,从银行贷得制片资金的时候,舆论无不将此举视为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然而, 《钢铁侠Ⅰ》的可观收益让漫威不仅保住了对众多角色的控制权,而且一飞冲天,在之后的十多年里“爆款”频出,成为最赚钱的电影公司之一。它打造“电影宇宙”的做法也引得其他公司纷纷跟风,各自打造不同的“宇宙”系统。[注]各类娱乐媒体中提到的“宇宙”包括华纳影业的DC扩展宇宙(DC extended universe)、环球影业的黑暗宇宙(dark universe)、传奇影业的怪兽电影宇宙(monster movie universe)等。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尝试都未能像漫威宇宙一样年年高产且部部火爆。让人不禁好奇,漫威究竟是如何做到一枝独秀的?
当然,自从2009年被迪斯尼收购之后,漫威电影从制作、宣传发行到上映,再到周边衍生品开发,都有这个庞大娱乐帝国的鼎力支持,这是其他公司不可企及的优势。但除此之外,影片本身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十多年里,漫威电影的核心创意人员多有变更,但一些鲜明的特质一直延续,成为漫威电影的重要卖点,并在原先并没有受众基础的中国市场上俘获了大量粉丝。本文将从正反面人物的刻画、跨文本的情节构造这两个角度,对这些影片文本进行深入读解,同时思考——在这样一个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文化环境中,这些特质折射出了怎样的文化症候,对于中国国内盛行一时的“IP”开发,又提供了怎样的反思和启示?
当然,在进入研究之前,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明确界定。以漫威漫画角色为主角的影视作品很早就有,但只有漫威影业制作或主导制作的影片才被归入“漫威电影宇宙”(以下简称“漫威宇宙”)。按照官方的说辞,这个“宇宙”名为“Earth-199999”。简单来说,漫威为旗下的8000多个角色设定了多个彼此相似却基本上互不相通的平行宇宙,[注]中文媒体多称漫威旗下有5000多个漫画角色,但根据漫威官网,这个数字达到了8000多。参见漫威官网中的公司信息,https://www.marvel.com/corporate/about/。漫画故事多基于“Earth 616”,电影则发生在另一个“宇宙”当中。这样的设定“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人物的身世、技能或性格在电影和漫画中有所不同;也将漫威影业和其他公司获得漫威形象授权之后拍摄的电影隔离开来。以这个设定为界限,索尼哥伦比亚的《蜘蛛侠》《毒液》,二十世纪福克斯的《神奇四侠》《死侍》等都不属于“漫威宇宙”,[注]蜘蛛侠被授权给索尼公司之后,漫威是无权在电影中使用蜘蛛侠的形象的。后来索尼、漫威、迪斯尼达成协议,漫威可以在与索尼合作的前提下拍摄有关蜘蛛侠的电影。因此,索尼哥伦比亚的《蜘蛛侠》系列、《超凡蜘蛛侠》系列和动画片《蜘蛛侠:平行宇宙》等都和漫威宇宙无关。另有网友预测,随着二十世纪福克斯被迪斯尼收购,神奇四侠、X战警等漫画人物为主角的电影未来有可能进入漫威宇宙。但尚未发生的事情无法成为本文的考察对象。也就不在考察范围内。
此外,“漫威宇宙”本身则是一个庞杂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体系。按照官方说辞,这个宇宙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化,从2019年起进入第四阶段。鉴于到目前为止的21部电影有着较为突出的共同特点,本文不打算采用创作人员的分期,依然将这些电影视为在风格策略上有着一致追求的整体进行分析。
一、英雄、非英雄和反英雄:超级英雄的形象新变
美国影视动漫中的超级英雄,大部分都出自DC和漫威两家公司。1938年,首次刊登超人故事的DC漫画杂志一经推出便迅速被抢购一空,跟风之作纷至沓来,大小漫画公司也接连成立。经过激烈竞争,DC和漫威两大巨头基本垄断行业的局面稳定下来;拥有远高于常人的身体能力、在现代都市中惩恶扬善、保护全人类福祉的超级英雄,则成为两家公司漫画杂志的常客。积淀为一代又一代美国青少年的集体记忆之后,超级英雄们的故事又频繁被改编成电影、小说、电视剧、动画片、广播剧、舞台剧等,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由于相互抄袭和模仿[注]根据美国记者肖恩·豪的传记式通俗读物《漫威宇宙:未讲述的故事》(苏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超人大热之后,漫威(当时叫“及时漫画”[timely comics])的老板马丁·古德曼指使手下的画师照搬这一创意;1960年代,他又在风闻DC推出正义联盟之后,迅速炮制出了“神奇四侠”这样的超级英雄群体。此外,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漫画界通行的规则是,漫画形象属于公司而不属于个人。而两家公司又常常互挖人才,因此,漫画师们常常在跳槽之后,利用一套新的设定对原先的创意改头换面,造成了版权分属两家公司的人物十分相似的现象。,超级英雄们往往彼此雷同。如美国队长和超人都是强壮的白人男性,他们穿着以红蓝为主色调的服装,上面带有五角星和条纹这些来自美国国旗的元素;而钢铁侠和蝙蝠侠则都是富可敌国的企业主,凭借整个公司的资金和技术,打造出普通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武器装备,从而拥有近乎超自然的身体能力。无差别复制和大规模生产是大众文化工业常见的弊病,但类同的形象能够跨媒介流传且长盛不衰却不能仅仅视为利益驱动的结果。深入挖掘可发现,这些形象并不是空洞浅薄的流行符号,而是契合了普遍性的社会心理。
从各个角度来说,这些超级英雄与上古神话和史诗中的英雄都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有着过人的才能、坚强的意志、非凡的毅力、进取的品格和追求正义的决心,借此完成了伟大的业绩,成为整个民族景仰的对象和仿效的榜样。由此,超级英雄的故事也就成了当代美国的世俗神话。美国队长在二战期间痛揍希特勒,超人在冷战阴云下挫败核武器阴谋,都是“象征性表述形式”;而他们大获全胜,不仅从想象的层面为潜在的社会冲突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而且也为社会树立了某种“行为特许状”。当普遍的恐惧和焦虑得到有效的抚慰,这些携带特定意识形态内涵的超级英雄也就成了“社会制度合法化的证明”。[注]劳里·杭柯:《神话界定问题》,选自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细看之下,漫威和DC的超级英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DC尽力展示超级英雄们超拔于人类的品质和能力,漫威却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英雄不那么完美。而出现在电影宇宙中的超级英雄们,就更加缺少英雄气概了。蜘蛛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漫画中,彼得·帕克是一位平凡的高中生,被一只经过基因改造的蜘蛛叮咬之后拥有了飞檐走壁的能力。他不时为困窘的经济状况发愁,但又牢记叔父的教导,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挫败了章鱼博士、蜥蜴教授等破坏力极强的超级反派。如果这样的角色称得上是平民英雄的话,则漫威电影中的蜘蛛侠似乎还未跨入“英雄”行列。在《蜘蛛侠Ⅰ:返校季》(2017)中[注]spiderman: homecoming有两种中文译名:“蜘蛛侠:英雄归来”和“蜘蛛侠:返校季”。本文认为,“英雄归来”不知所指,“返校季”则更为贴切。“返校季”是美国高中每年迎接校友返校的日子,学校会举办舞会、游行或体育比赛,在校学生积极参与并同台竞争。故事正是发生在返校季前后,因此有同学故意挤兑和嘲笑彼得·帕克,以展示自己的幽默感、提升人气;当暗恋对象丽兹答应做他返校季舞会舞伴的时候,彼得十分开心,因为这意味着丽兹愿意成为他的女朋友。可以说,“返校季”作为背景与故事情节较好地融合在一起,本文以此译名为准。,出于对他的保护,钢铁侠托尼·斯塔克在送给他先进战衣的同时,表示更希望他做一个“友好的社区蜘蛛侠”(friendly neigborhood spiderman),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身边人解决小问题,而不是过早涉足消灭反派这种“成年人”的事务中。同龄人的嘲笑,钢铁侠对他不是冷漠忽视就是粗暴训斥,连坏人都对他轻慢有加,让蜘蛛侠十分渴望通过制止坏人的犯罪行为来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拥有加入复仇者联盟的资质和能力。渴望赢得成年人的肯定并摆脱他们的监护,在同龄人当中因为“酷”而受到仰慕,这些青少年特有的心理需求成为“漫威宇宙”中蜘蛛侠行为的主要驱动力。这样的蜘蛛侠不再无所不能,也谈不上无私无畏,其能力也只能用来打击那些打家劫舍的“小”坏人(而不是毁灭星球的“大”反派),而其证明自己的愿望,看上去和其能力并不相称。
在其他漫威电影中,不那么像英雄的超级英雄也比比皆是。如《蚁人》(Ⅰ,2015;Ⅱ,2018)中的司各特·朗刚刚出狱,他需要找到一份足以养活自己的工作、重新面对前妻和女儿,还要在化身蚁人的时候千方百计地欺骗FBI官员,让他们相信自己依然遵纪守法地待在家里。《银河护卫队》(Ⅰ,2014;Ⅱ,2018)中的“星爵”彼得·奎尔自幼被居无定所的“掠夺者”收养,最亲密的朋友是些不见容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他没有体面的出身且安于“废柴”(loser)的地位,从事小偷小摸的灰色勾当。为此,他被悬赏通缉,还曾锒铛入狱。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与完美无缺的“英雄”相对应的,是非英雄(non-heroes)和反英雄(anti-heroes)。这两种形象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前者以《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为典型,受困于琐碎生活的蝇营狗苟而不得超脱,代表着对日常悲剧的幽微洞察;后者则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为典型,不惜践踏文明社会的通行准则以追求自我意志的实现,代表着对异化体制的决绝反叛。[注]赖干坚:《反英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角色》,《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1期。赖文认为,非英雄和反英雄有着很大的重合之处,包括缺乏传统的英雄品格、自我处于不稳定的分裂状态、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并充当受难者和牺牲品三个方面,而有些研究者并没有对非英雄和反英雄做出区分。本文认为,鉴于两者之间忍辱负重和亦正亦邪的气质有着很大的区别,应该对两者稍作区分。这样也有利于本文辨别漫威的21部电影中十几位超级英雄性格和形象的多样性。如果将受限于心理发展水平而不能自由行动的蜘蛛侠和受限于法律准则而不得不忍气吞声的蚁人类比为“非英雄”,那么颇有“垮掉的一代”风范的星爵和他的伙伴们就毫无疑问算得上是“反英雄”了。
当然,这样简单的类比忽视了文学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别——当前者致力于探索心灵荒原的时候,后者却在建构可大规模贩卖的美妙梦境;当前者以反思性、批判性的内涵启迪人心的时候,后者却以虚假的幻景让人沉醉于片时的愉悦。但如果说文学作品反映出20世纪后半叶以来有关宗教和理性的崇高信念相继幻灭的思潮转向,大众文化作品也并非对此无动于衷。因此,文学艺术会从大众文化中获得灵感和素材,大众文化则对文学艺术的深刻思辨做通俗化处理。正是在这样的交融之中,“漫威宇宙”中的超级英雄们不再是超脱于肉体凡胎的钢铁之躯,而不得不面对人类个体固有的局限;保持正直善良的品质和兼济天下的理想,又有了更多价值中立和道德暧昧的特征。由此,“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们突破了单一化、扁平化的特质,在不增加观众理解困难的基础上,拥有了更为复杂的内涵。
二、创伤、心魔和救赎:反派带来的复调空间
很多超级英雄漫画和电影会为主角打造一个和他/她能力相当,却一心为非作歹的超级反派。如果说超级英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肉身符号,超级反派则是恰好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上。两者之间斗智斗勇是电影主要的看点,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价值观念的仪式化呈现。然而,当“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们带上了非英雄和反英雄的色彩,作为敌人的超级反派们也不再纯粹邪恶。他们依然会滥杀无辜、发动战争,或做出其他有违人类社会普遍准则的事情,但同时也会表现出人性未泯、令人同情的一面,与超级英雄们发生更多的、深层次的互动关系。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两者之间难以切割的身份关系上。如雷神托尔的弟弟洛基、卡魔拉的妹妹星云,都生活在长兄长姐的阴影之下,被父亲否定乃至虐待,因此对家人怀有既爱且憎的复杂情感,并渴望证明自己才是更优秀的那个。当这一渴望强烈到无法遏制的时候,他们会为此大开杀戒——洛基在《雷神Ⅰ》(2011)中将冰霜巨人引入奥丁的神殿,在《复仇者联盟Ⅰ》(2012)中又带领齐塔瑞军队进攻地球;星云则帮助罗南毁灭整个星球(《银河护卫队Ⅰ》)。但这种种恶行,更像是一场发泄多年不平之气的自我疗愈,因此和超级英雄们的激烈斗争也成了一桩家庭事务。而和家人之间的心结解开之后,他们又会在亲情驱使之下,成为兄弟姐妹的坚定支持者。
有些时候,两者的善恶属性也不再那么分明。如《蜘蛛侠Ⅰ:返校季》中的反派——“秃鹫”图姆斯,就有些被“逼上梁山”的味道。他原本打算合法开发齐塔瑞军队留下的残骸,却因政府和斯塔克公司成立的灾害控制部门的强行介入而丧失机会,沦落到近乎破产的地步。申诉无门之下他恼羞成怒,索性铤而走险,盗窃残骸并将之改制成武器,卖给各色犯罪分子。如果说钢铁侠的军工企业与政府合谋而获得了巨额利润;他却只能通过手工作坊和黑市交易,攫取资本家吞噬未尽的残羹冷炙。虽然他和钢铁侠未发生正面冲突,但正是后者的利益扩张,客观上导致他从守法公民变成了食腐秃鹫一般的不法之徒(而他自制的盔甲也恰好模仿了秃鹫)。电影的最后,蜘蛛侠打断了他愤世嫉俗的控诉并将其绳之以法,但这样一个被庞大的官商联合体碾压和损害的小人物及其所凸显的某种“阶级冲突”,显然让持有朴素是非观念的高中生蜘蛛侠有点茫然。
还有一些电影中甚至并没有惯常意义上的反派。如《美国队长Ⅲ:内战》(2016)的主要冲突发生在几位超级英雄们之间。由于无法就是否应该接受联合国监管、是否应该为血亲复仇等问题达成统一意见,每派的意见又在情感和认知方面各有不可辩驳的合理之处,几位超级英雄最终只能依靠武力阻止对方认为是正义的行动。虽然确有人在不断制造事端,促使超级英雄们之间分歧暴露、矛盾升级,但这位无名之辈的挑衅只能算得上是一个诱因。个人自律还是外在约束机制、血债血还还是法律制裁这些政治的和伦理的基本问题,及其所包含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才是超级英雄们大打出手的根本原因。影片的最后,双方偃旗息鼓并相互表达了谅解,却都没有明确改变立场,这些敏感问题也就依然处于悬置状态,留下了开放的讨论空间。
总体来说,漫威电影中反派们的经历得到更充分的展示,性格得到更深入的刻画。他们或是携带着家庭和社会造成的难以消除的心理创伤,或是由于其成长环境和个人记忆而感受到迷茫和困惑,更多是植根于社会和个人内在的矛盾和混乱,而不再是超级英雄及其所捍卫的社会价值的外在的敌人,因此颇类似于佛教所说的“心魔”。这样,他们对超级英雄们或整个社会体制的控诉就显得有理有据、掷地有声,不仅能被观众理解,还能够博得一定的同情和共鸣。而自诩“好人”的超级英雄们则有可能在反派们的诘问下哑口无言、问心有愧,只能凭身体力量战而胜之。由此,电影有了更加丰富的意义空间。《复仇者联盟Ⅰ》等对于洛基这些反派来说,就成了揭示家庭创伤并达至和解的心灵之旅;《蜘蛛侠Ⅰ:返校季》则通过和钢铁侠的无声对比放大了“秃鹫”的可怜可悲之处,以他带有反抗性的犯罪活动,揭示了触目惊心的阶级分化,由此对钢铁侠行侠仗义的观念构成了反讽。在这样容许不同理念相互对话的复调空间里,虽然慷慨无私的超级英雄依然能够战胜自私自利的超级反派,但这样的胜利对两者来说都意味着救赎——不完美的超级英雄或者获得了心灵的成长,或者弥补了过去的错误,或者通过利他行为化解了内心的焦虑和愧疚。而反派们则被及时制止,没有滑向不可挽救的罪恶深渊;同时,也被超级英雄们的高尚精神和朴素信仰所感化,走出了以恶行报复自己所受伤害的怪圈,收获了心灵上的平静。
三、颠覆、拼贴和戏仿:幽默中的文本碎片
既然超级英雄和他们的敌人都不再单纯是正义和邪恶的象征,在情感和观念方面都有着共融互通的可能性,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就不再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漫威宇宙的情调也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部分电影以轻松戏谑见长,以至于很多观众看完后大呼“好玩到让人疯狂”(insanely fun and entertaining)、“全程都在笑”。[注]评论截取自IMDb、豆瓣中被点“有用”最多的短评。而这样的效果,是依靠颠覆、拼贴和戏仿等方式完成的。
首先是对人物某种“人设”毫不留情的颠覆。如《复仇者联盟Ⅰ》中,听到班纳指责洛基不可理喻,索尔愤怒地反驳道:“注意你的言辞!洛基虽然失去了理智,但他来自阿斯加德,是我的兄弟!”黑寡妇提醒他洛基杀人如麻的事实,索尔马上眨眨眼睛,放低语气辩解说:“他是收养的。”身为神灵,索尔说话的措辞和句式一贯带有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的庄严特点。但他上一秒还在义正词严地维护家族荣誉,下一秒就放下身段明哲保身,这种油滑有余、高贵不足的态度转变,与他的身份产生了严重的反差,令人不禁莞尔。
其次是不相干元素的拼贴。如《银河护卫队》(Ⅰ&Ⅱ)大量使用了19世纪60、80年代欧美乐坛的流行金曲。对于熟悉这一时期流行文化的观众来说,这些歌曲包含特定的情感和回忆,却和电影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当音乐响起,节奏韵律与人物动作、镜头运动形成和谐对应的关系,情绪氛围却和此时的故事情节形成了近似于后现代主义绘画中常见的“拼贴”关系。正如拼贴艺术“借助于两种异质之物的组合来同时改变双方的意义”[注]李方明:《拼贴:一种断裂的美学》,《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配乐和情节的错位也造成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效果——热烈深情的歌曲带上了轻佻滑稽的意味;打斗的场面也如同即兴的舞蹈一般机智谐趣。
最后则是对一些熟悉符号的戏仿。如《钢铁侠Ⅲ》(2013)中,头梳发髻、身着长袍的“满大人”总是用冷酷阴狠的口气宣称对恐怖袭击负责,甚至直接对着镜头开枪杀人。但实际上,他不过是个深陷毒瘾且手无缚鸡之力的失业演员,贪图报酬优厚才出演了这样一个纯属虚构的角色。钢铁侠稍一逼问,他就迅速招认自己对幕后真凶的阴谋其实一无所知,“杀人”也不过是镜头特技而已。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视为对文学和电影中的经典角色傅满洲以及漫威漫画中的“满大人”的戏仿。无论是“邪恶但却温文尔雅,不动声色,控制着一些无恶不作的地下组织,具有超人的能力,丧心病狂地要征服世界,消灭白人”的傅满洲[注]周宁:《“义和团”与“傅满洲博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黄祸”恐慌》,《书屋》2003年第4期。,还是漫画中精通古老秘术的“满大人”[注]关于漫威漫画中关于“满大人”的设定,可参看粉丝撰写的相关词条:https://marvel.fandom.com/wiki/Mandarin_(Earth-616).,都集中了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他者”的恐怖想象;然而,电影中的“满大人”却是徒有其表的空洞符号——他没有任何东方背景,完全由白人扮演和操控;也没有能力策划任何阴谋,只能在银幕上虚张声势。原型及其“不成功”戏仿的对比,更容易让人因他的猥琐、胆怯和无能而发笑。
通过颠覆、拼贴和戏仿的方式制造的幽默效果,是漫威电影卖座的原因之一。毕竟,对于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多数观众来说,一部轻松愉悦的影片是最具有吸引力的选项。有研究者担心,大量的戏仿与拼贴在带来创作自由的同时,“容易演变为无序与混乱”;在肯定世俗人性的同时,“游戏人生的态度也有可能使人类基本的价值准则被消解”[注]汪献平:《当代喜剧电影中的“戏仿”:表征与意义》,《当代电影》2008年第10期。,导致价值的虚无。不难发现,漫威电影中的笑料的确瓦解了之前超级英雄电影的庄严基调,同时也解构了其背后的某种宏大话语。仍以“满大人”为例,如果说傅满洲和漫威漫画中的“满大人”都以其东方面孔和机关法术,具象化了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隐约可见的“黄祸”迷思;电影中的“满大人”作为一个跳梁小丑式的角色,则使得所谓的“黄祸”及其背后的种族主义思想如同痴人说梦一般虚妄。[注]当然,考虑到《钢铁侠Ⅲ》曾经争取以“合拍片”方式登陆中国内地市场,并出现了所谓的“中国特供”版本,引入一个具有东方色彩的角色并尽量化解其中的种族主义因素,显然有讨好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观众的嫌疑。从“合拍”到买断的具体过程可参见新京报网转载《新京报》报道《从合拍到特供:〈钢铁侠3〉变形记》:http://www.bjnews.com.cn/ent/2013/04/26/260717.html;时光网《〈钢铁侠3〉中国变形记——揭开特供版三大疑云》:http://news.mtime.com/2013/05/08/1511398.html。而《奇异博士》(2016)中,刚到圣所的奇异博士以为魔法师莫度递来的纸条上写的是咒语,莫度却带着好笑的神情看着他说: “这是wifi密码,我们又不是野蛮人。”这句情理之中、预料之外的台词,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此前绚丽的特效场面对魔法的神奇之处的渲染;司空见惯的平实之物突然出现,也打破了幻想世界的封闭自足。当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放弃对科学的信仰投身魔法的时候,一位道行高深的魔法师却在享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利,这样具有颠覆的效果甚至可以说解构了叙事电影的某种“本质”属性。
但漫威电影以幽默消解宏大话语的同时,也通过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方式重申了某些价值。如《复仇者联盟Ⅰ》中,美国队长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过时,和他同行的神盾局特工科尔森郑重回答:“考虑到现在的局势,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人们需要一点过时的东西。”二战士兵出身的美国队长象征着正义、真理、荣誉和爱国,在价值多元、民族国家的神圣性遭到解构的今天,已经显得有点过时。何况,在这部电影中,他将要去面对的并非一个国家,而是整个地球(以及整个宇宙)的危机,狭隘的爱国情怀毫无必要。但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粉丝”科尔森,却再次肯定了这种“过时”精神的当下意义。科尔森的回答看上去仅仅是对个人的童年记忆的浪漫怀旧,因此几乎毫无说教意味,而且巧妙回避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星际主义”)之间的鸿沟,将一个愿为国家利益牺牲自我的士兵转化为一个愿为全人类生死迎难而上的超级英雄。在自我解嘲和抒发个人情愫的过程中,一些“古老”的价值再次得到肯定,观众也在轻松的嬉笑中感受到了崇高情怀不可解构的感召力。
四、网状叙事和“彩蛋”:开放中整合的“漫威宇宙”
有共同特征的同时,“漫威宇宙”的21部电影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从世界观的设定来说,钢铁侠、美国队长等的超能力都和前沿技术有关,关于他们的电影应属“科幻”;奇异博士掌握的是魔法,以他为主角的电影应属“魔幻”。从风格来说,《雷神Ⅰ》《雷神Ⅱ:黑暗世界》(2013)从布景、台词到故事情节,都有浓郁的史诗气质,《雷神Ⅲ:诸神黄昏》(2017)中过多的笑料则扭转了这种气质。从类型的角度来说,《美国队长Ⅰ》(2011)较多使用了战争片的类型元素,《美国队长Ⅱ:冬日战士》(2014)则更接近于谍战片。另外,同一个角色在不同电影中的性格也可能不一致。例如,原本更喜欢靠武力解决问题的雷神在《雷神Ⅲ:诸神黄昏》中却经常絮絮叨叨;而原本玩世不恭的钢铁侠在《美国队长Ⅲ:内战》中却时常神色凝重。之所以如此,和漫威影业的人事变动、导演的更换、方向的调整等有着直接关系。但其制片者却从一开始就宣布,所有漫威影业制作的电影都属于“漫威电影宇宙”,并采取种种策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就是文本间的网状叙事。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漫威电影中主要角色的表演者一直没有更换,如钢铁侠一直由小罗伯特·唐尼扮演,美国队长一直由克里斯·埃文斯扮演。[注]只有绿巨人浩克是一个例外。2008年的《无敌浩克》由爱德华·诺顿主演,之后则换成了马克·鲁弗洛。因此,有的媒体并不将《无敌浩克》列入“漫威电影宇宙”,但在漫威官方的纪录片中包括了这部电影,本文依据官方说法。参见漫威制作的一档电视特别节目《漫威影业:宇宙集结》(Marvel Studios: Assembling a Universe,2014)。这些演员/明星各自的形象气质与角色融为一体,让超级英雄更加真实可感。而以这些超级英雄为载体,不同电影的故事经常发生关联。如美国队长的好友猎鹰出现在《蚁人Ⅰ》中,并与蚁人短暂交手。因此,在《美国队长Ⅲ:内战》中,蚁人成为美国队长阵营的一员,帮助他冲出钢铁侠等人的包围。由于这次拔刀相助的义气之举,蚁人在《蚁人Ⅱ:黄蜂女现身》中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每次行动都要躲开FBI探员的监视。出现在多部影片中的角色无须反复介绍,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融入故事中,承担相应的功能。而电影就可以不枝不蔓、张弛有度地讲故事,并将大量的时间留给精彩的打斗场面。因此,网状叙事提升了一部电影的容量,也提高了故事讲述的效率。当主要演员基本稳定、角色来回穿插、情节彼此关联、视觉效果也保持同样水准的时候,这些电影很容易被视为一个整体。
另外的策略则是“彩蛋”的设置。“彩蛋”是个含混的称呼,从宽泛的意义来说指的是出现在一部电影之中或结束之后,对故事并不产生影响,却指涉着其他影视、动漫作品的电影元素。如《银河护卫队》(Ⅰ&Ⅱ)中太空狗、霍华鸭这些一闪而过的漫威漫画角色就是“彩蛋”;[注]参见时光网新闻《〈银河护卫队〉彩蛋全解析:扩展漫威宇宙 杂糅美国文化》,http://news.mtime.com/2014/10/14/1532692.html#/feature/。《蜘蛛侠Ⅰ:返校季》中蜘蛛侠好友奈德手中的《星球大战》的“死星”模型是“彩蛋”;洛基是“被收养的”这句台词同样也可以成为“彩蛋”,因为索尔说过这句话之后,后来的电影又多次巧妙化用了它。而正片结束之后的“彩蛋”则多是没头没尾的片段,暗示着尚未上映的电影的走向。如《钢铁侠Ⅰ》片尾的“彩蛋”中,神盾局长尼克·弗瑞突如其来地出现在钢铁侠家中并对他说:“斯塔克先生,这个世界上不只你一个超级英雄,跟你一样的人还有很多。我想跟你谈谈复仇者联盟的事。”为四年后的《复仇者联盟Ⅰ》早早做好了铺垫。
借助漫威漫画80年的积累以及美国流行文化产业的海量产品,一部漫威电影中埋藏的“彩蛋”有时能达上百之多。“彩蛋”扩展了故事世界的广度,也激发了观众的“认知癖”。这样,观看电影某种程度上等于参与了一场智力游戏——电影制作者调动种种资源制成“谜面”,观看者挖空心思地寻找“谜底”。只有对美国流行文化(尤其是漫威和迪斯尼的动漫影视)熟稔于心的观众,才有可能通过仔细观察每一帧画面,辨识出最多的“彩蛋”,在游戏中体会到成就感。因此,热心影迷往往会多次观看这些电影,寻找“彩蛋”并对尚未上映的电影进行想象和推测。而他们据此发布的文字帖和短视频往往会被对这些电影怀有好奇心和好感的观众搜寻、点击和浏览。通过阅读和观看这些网络图文,原本一知半解的观众能够识别出那些与别的文本相互呼应或别有用意的“彩蛋”,也会在观影的时候发出会心一笑。
换句话说,密集的“彩蛋”是所有漫威电影共有的一种鲜明特色。它们有效地区分了粉丝和非粉丝——看见“彩蛋”并为之一笑是粉丝独享的权利,而非粉丝则除了表面化的视觉效果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也让文本更具有开放性和对话性,让痴迷的观影者最大限度地参加进来。当少数影迷主动投入大量注意力去寻找“彩蛋”并体会到智力上的快感之后,他们对电影的喜爱程度也会有所增加。而一般观众借助他们提供的信息了解电影的细节之后,获得了更多的观影乐趣,也会与整个“漫威宇宙”形成独特的情感纽带。
借用传播学术语来说,“彩蛋”使那些细致、深入的观影者成为“意见领袖”,让他们自发进行“二级传播”[注]按照发明了此术语的学者札拉斯菲尔德的看法,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由于其灵活性和非正式性,“意见领袖”的作用甚至要大于大众媒体。,以非正式的、非灌输的方式勾画出漫威宇宙的图谱,并将其扩散到更广泛的人群中。[注]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在这个过程中,“格式塔”的心理机制发挥了作用,观看者通过不连贯的“彩蛋”,自发寻找或建立文本之间的关联,忽略电影内部及电影之间的裂隙,将这21部电影(及未来将上映的若干电影)认知为一个整体。而按照文化学者亨利·詹金斯等的说法,在“参与式文化”的运作逻辑下,漫威影业和它的忠实观众形成了合谋的关系,建立起既内向自足又借助流行文化符号无限延伸的漫威电影宇宙体系。
五、结论:“漫威宇宙”的调适性创新
漫威所建构的电影宇宙,从正反面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计与整合等几个方面,给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观看体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漫威电影毫无瑕疵。多部漫威电影情节生硬、人物单薄,因此饱受诟病。如《雷神Ⅲ:诸神黄昏》中,索尔和洛基刚刚找到失踪的父亲,奥丁便毫无预兆地告诉他们,他们从未谋面的姐姐海拉即将到来。话音刚落,奥丁便化作金光飘然而逝,而海拉则从一团虚空中走了出来,命令兄弟俩向她臣服。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得知家族秘密的震惊之情,慈父死去的悲伤之情,强大敌人出现的恐惧之情,每一种情感都应该给人物带来强烈的冲击并造成戏剧化的情节转折。然而,当它们同时出现并混杂在一起,却只能让片中人物和场外观众都无法细细体会,使情节显得突兀,缺少事实和情绪的铺垫。海拉作为奥丁的长女,曾和奥丁并肩作战,后因野心膨胀而被奥丁囚禁,并将其从家族谱系中彻底抹除。这样的坎坷身世理应造就一个立体的、有深度的反派,然而海拉却一味杀戮,没有对她的父亲、兄弟、故乡和臣民表现出一丝眷恋和善意;正如后者也未能对她表现出一丝悔过和同情一样。之所以如此,原因或许在于制作者注重的不是叙事,而是笑料的制作。据透露,由于担心原本100分钟长度的正片不具有足够的娱乐效果,制作者特意添加笑料,并“耗费巨大精力对笑料不断调试,力求让所有的笑点、包袱都在最佳时间出场”[注]参见人民网转载广州日报消息:http://ent.people.com.cn/n1/2017/1103/c1012-29624457.html; 及外媒相关报道:https://www.cbr.com/thor-ragnarok-early-cuts/。。笑料挤占叙事时间,当然会干扰故事的流畅自然和人物的心理发展。而观众在被一个又一个包袱逗笑之后,也很难有思考和回味的余地。
尽管有这样的缺陷,但从其可观的票房收入和众多的仿效者来看,漫威打造电影宇宙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不仅灵活而有效地将旗下的超级英雄推上银幕,而且能够让这些超级英雄相互借重,共同扩大影响力。不仅利用了漫威影业自身及其母公司迪斯尼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而且将消费者纳入了生产环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漫威此举改变了超级英雄电影的形态乃至整个电影产业的格局。
漫威之前的大部分超级英雄电影很少在多部影片之间建立联系,而更倾向于以强度不断提高的视觉快感为交换价值,提供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品。但漫威电影却以网状叙事和埋设“彩蛋”的方式鼓励反复多次地、细致入微地观看,由此获得更多的票房和流媒体播放量——在互联网时代注意力经济的逻辑下,后者同样蕴含巨大经济价值。而且,漫威还鼓励多个子公司和不同部门密切配合,靠全球上映的电影大片获得声势之后,再通过电视剧、动漫、网络短片、游戏等覆盖所有类型媒体[注]据不完全统计,漫威出品的电视剧包括《神盾局特工》《离家童盟》,动画片包括动画版《复仇者联盟》《少年雷神》等。但由于经营策略的调整,漫威影业和漫威娱乐、漫威动画的关系走向独立,互动减少。只有短片是电影原班人马制作,包括《47号物品》《特工卡特》《神盾顾问》《寻找雷神锤子路上发生的趣事》《王者万岁》《雷神小队》《银河护卫队:地狱》等,长度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主要是对电影中一闪而过的情节进行补充和扩展,风格偏于幽默。,进一步展现这个“宇宙”的方方面面,不断维持和加强大众对“漫威宇宙”的兴趣和记忆。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漫威的这些举措,“通过好莱坞电影重构了制片文化。……生产符合外界需求的电影文本和创意层级,此外,它还给融合时代的电影制片文化带来了具有可行性的意义”[注]德瑞克·约翰逊:《电影的命运:产业融合中的漫威制片厂和交易故事》,《世界电影》2005年第3期。。
但如果完全把这些改进视为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也未免对美国文化产业的历史过于无知。从电影语言的角度,漫威电影的种种技巧算不上新鲜,因为“引用、自反、集成各种风格的拟古之作……所有这些被认为是全新创意的东西,在大制片厂的传统中早就有一席之地了”[注]大卫·波德维尔《好莱坞的叙事之道:现代电影中的故事与风格》,谢冰冰译,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第15页,第25页。。而从制片策略的角度来说,正如亨利·詹金斯所分析,20年前的《黑客帝国》就已经做出了表率,以电影、网络漫画、游戏等媒介创造了宏大的世界体系,在不同的文本中丰富和充实这个世界体系,并鼓励“那些最忠诚的消费者寻找分布在多样化媒体中的信息资料,审视能够深入了解这一故事世界的每一种文本”[注]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6页。。因此,漫威的创新是有限度的,也是调适性的——它在经典好莱坞零度剪辑、线性叙事、时空统一的惯例基础上,借助最前沿的数字技术,广泛融合各类文化资源,迎合当代观众的期待和口味,“通过想象力丰富的方法使经典方法恢复了生机”[注]大卫·波德维尔《好莱坞的叙事之道:现代电影中的故事与风格》,谢冰冰译,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第15页,第25页。;在流媒体兴起和粉丝空前强大的条件下,将视效大片这样的文化“速食品”转化成粉丝百玩不厌的有趣游戏,但又将创意的方向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经历了“野蛮生长”之后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电影产业来说,漫威影业从几近破产到如日中天的传奇,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但几年来模仿其策略所谓开发“IP”的尝试,却几乎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背后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如电影产业政策环境不同等。但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产业,本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发展途径。与其奢求一种可以生搬硬套的模式,不如在制作电影的时候,寻找到崇高与俚俗、解构与坚守、封闭与开放、大众与粉丝之间的平衡与转化之道,讲述一个清晰、圆满又具有一定异质性和延伸性的故事。或许在解决了文本创意方面的短板之后,国产电影依然能够成为吸引最大多数观众的大众文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