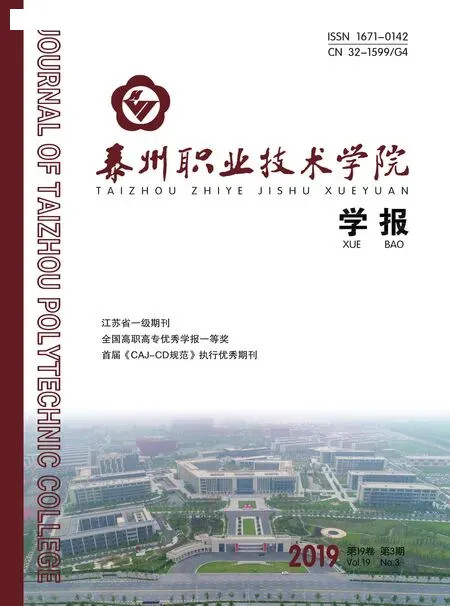强化“江苏文脉”视阈下“海陵文化”的深入研究
——以明清“海陵地区”家族文化与戏曲文化为分析对象
钱 成
(泰州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近年来学术界一致认为,“家学传统”“世家文脉”除反映特定宗族和家庭的艺文成就外,一定程度上甚至体现了一时一地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脉络,值得后世为之探讨、阐释和总结。2018 年12月3日在江苏无锡召开的“首届江南文脉论坛”上,南京大学徐雁平和苏州大学罗时进等多位学者均认为,“江南文人的家风,是江南文脉自身品格最直接的体现。”针对“江南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更明确提出:“这一工程固然可以江南为主,但又不必仅限于江南,如泰州学派、明代书院文化等都可以纳入整理与研究的范畴。”[1]“泰州学派”诞生、成长的文化土壤,是自汉唐以来形成的“海陵文化圈”。从地域文化特征上看,明清时期的“海陵地区”,尽管曾长期隶属于扬州,但却是一个独立于维扬文化圈外的文化区域。因此,明清时期这一文化地域自立于维扬文化和州府级行政概念之外,凭借着自身的文化凝聚力和扩张力,自成疆域。
明清时期,江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达到空前的繁荣状态,涌现出大批文化名人及文化世家,“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是明清以来江南文化体系中的代表形态。对于地处长江北岸,位于苏州与扬州之中的“海陵地区”而言,明初“洪武赶散”带来的苏湖移民、明中后期持续到近代的徽州和宁镇移民,成为本地区世家望族的主体。这些家族借助于本地区的水运和盐税之利,通过科举和教育等途径,成长为在诗文、书画、戏曲等诸多领域成果蔚然的艺文家族。与家族文化一样,“海陵地区”的戏曲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突出代表,有着极为悠久的文化底蕴,与其他文化形态一起,造就了“海陵地区”文渊悠久、文脉深广的独特气质,成为隶属于江苏文化版图的“海陵文化”另一代表性特征。
1 有助于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史研究的深入
历史上,“海陵地区”以泰州为中心,文化则与扬州、盐城、南通部分区域重合,其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区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在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但即便如此,研究苏中地区文化史的,大都只关注扬州文化研究,缺乏对古海陵地域文化的深入研究。
近二十年来,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新学术生长点。相对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政治体制而言,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存在的基础,并不在于象征最高统治地位的朝廷或拥有特权的宗教,而是借助宗族和血缘关系建立的封建宗法制度,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数千年来,在封建宗法制度统治体系下,广大宗族和家庭“耕读传家”的文化理想,不断延续“风雅祖述,前薪后火,息息相继”的文化信念,使得中华文明特别是文学艺术,拥有了绵绵瓜瓞的深厚根基与衍生机制,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
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清代皖学代表人物戴震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家学传统”“世家文脉”。文化的背景是社会的形态,家族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础和特征之一。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世家多为政治型集团不同,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较高的世家大族,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外,在社会文化领域,尤其是诗文、戏曲、书画等方面的积累和传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甚至是无法替代的角色,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特色之一。因此,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
由于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共生关系,因此,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并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在对明清苏中地域文化、文学的研究方面(除传统的诗文、经学研究外),进一步拓宽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学术界加深对“海陵地区”,特别是今泰州地区明清时期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成就的认知。同时,力争为“江苏文脉”工程和江苏地域文化史、戏曲史、家族史等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
2 有助于江苏地区文化家族研究的拓展
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宗族文化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由于家族是由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家族既是个体活动的中心,也是个体全部的依靠。近年来,家族研究已成为文史研究的热门课题。延至明清时期,江苏地区更是集中涌现出大批文化望族、文学世家,并成为江南(含今江苏、浙江、上海在内)地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特质之一。因明清时期本地区整体经济、文化的相对繁荣,当时江南已经形成了发达的城市群,城市商业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百姓视野相对开阔,无论科举考试还是治学,都可事半功倍。此外,诸如书画金石、诗词歌赋、戏曲弹唱等,也均成为江南地区世家文人的“基本技能”。
同时,以江苏为代表的江南文化之内涵,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载体,那便是以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李渔的《闲情偶记》等为代表的精致生活。其中,书画、戏曲、园林可谓此类富含文化内涵之精致生活的典型[2]。
以水绘园为例,作为海陵文化世家——如皋冒氏家族别业,传至“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著名戏曲家冒辟疆之手时,逐渐臻于完善,遂成为明末清初海内名园。他在园中构筑妙隐香林、壹默斋、枕烟亭、寒碧堂等十余处佳境,和董小宛等寄情山水,演剧抒怀。寄居此处的阳羡陈氏子弟、著名词人陈维崧曾在《水绘园记》中云:“绘者,会也,南北东西皆水绘其中,林峦葩卉坱圠掩映,若绘画然。”[3]明亡后,心灰意冷的冒襄将水绘园改名为水绘庵,在此隐居,教习家伶,借曲自娱,海内名士纷纷前来唱和,有“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无不以如皋为归”[4]之说。
但长期以来,研究江苏地区文化家族者,均把研究地域重心集中于环太湖地区的苏南苏锡常和宁镇扬地区,研究对象的时间选取多为明代,而对一江之隔的“海陵地区”,则大多予以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自明初以来直至民国时期,苏南、浙东、皖南和宁镇地区出现了前后四次,时间长达四百余年的世家大族北迁至苏中“海陵地区”的移民潮,其中涌现出了众多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等类型的望族。这些文化家族普遍具有旺盛的文化创造力,艺文成果丰硕。所以,自宋元时期开始,本地区就出现了一些冠之“海陵”为名的地域性文化、文学总集。如宋泰州如皋人周准辑录其父周麟之诗文为《海陵集》二十三卷;清泰州邹熊辑《海陵诗汇》二十三卷,《补遗》一卷,泰州博物馆藏清同治抄本。清泰州夏荃辑录唐以来,特别是明清两代“海陵地区”文人著述为《海陵诗征》《海陵文征》。
针对因海陵地区区域变革,至明初“海陵”已不再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情况,夏荃在《海陵文征·凡例》中云:“海陵之名,始于汉孝景之世,迄于明初,其名最古。历代建制沿革不一,近邑如盐城、泰兴、兴化、如皋,旧皆隶属于海陵。其隶之最久者,莫若皋。皋之隶,始于刘宋,至国朝雍正三年,乃分属于通。然皋究系泰属邑。仆此辑,在泰言泰,凡皋人之文,不敢阙入,其仍名《海陵文征》者,溯得名之始,从其朔也。”从夏荃之言可以明显看出,“海陵”作为固定的文化地理概念,是明清本地区文人的共识。
在明清江浙地区文化家族林立的社会时代背景下,“海陵地区”家族也势必会受社会时代氛围的影响,最终产生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家族文化的繁荣昌盛。
除诗学繁荣,“历三十余代不绝”外,还在围棋领域享誉全国,甚至出现了“一代棋圣”黄龙士这样的“大国手”。泰州靖江朱氏明清时期分别出现多个戏曲家班,其家族成员朱得之的“庄学”“列子学”成就被誉为“有明第一”;泰州俞氏除戏曲文化传承外,俞楷还在伊斯兰教文献汉文译著上“影响巨大”。
长期以来,对清苏中地区戏曲史研究集中在扬州戏曲史,而对明清“海陵地区”戏曲史,特别是文化世家与戏曲关系论述较少。因此,通过对当前“海陵地区”戏曲文化和家族文化研究成果的梳理与总结、拓展与延伸,可以探索诠释“海陵文化圈”以及苏中地区地域文化形态和精神的新途径,初步建构起一种以文化家族戏曲文化为中心的戏曲史、文化史研究新模式,创造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3 有助于戏曲史视阈下家族戏剧史专题的研究
明末以后,在“海陵地区”,众多因科举、盐业和商贸等兴起的望族,借助深厚的文化修养、显赫的身份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与独特的兴趣爱好,确立了文化家族在戏曲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同时,明清时期此地作为戏曲活动要津,在戏曲创作、家班表演、理论批评以及刊刻评点方面均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应受到学界关注。
基于此,立足于海陵文化圈内优秀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收集整理,在宏观论述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基础上,重点选取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形式多样、影响深远的戏曲文化活动开展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彰显戏曲等优秀传统文化高度的“文化自信”与独特的“艺术传承”,有助于进一步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以清代泰州城内的“九大家族”为例。清中前期的“宫陈俞缪”家族均拥有家庭戏班,家族成员分别在戏曲创作、戏曲表演、戏曲评论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清中后期的“支管卢王沈”等家族均有不同形态的戏曲活动。
支氏家族后裔,曾在泰州城内首先创办了以演唱昆曲为主的中山曲社。管氏家族管涛,字云度,号韲臼。《民国续泰州志》云:“廪贡生,候选训导,署六合县教谕。少负异才,有诗名。好集唐宋句,如无缝天衣,所交多知名士。著《锄金园诗集》。”[5]其人曾与宫氏家族宫国苞、俞氏家族俞国鉴一起入扬州删改词曲馆,参与“删改古今传奇、杂剧”。卢氏家族除相传曾建有家乐外(无确考),还出现了专业的戏曲演员。其家族成员卢文勤,为晚清梅兰芳之伯父梅雨田嫡传弟子,后成为京剧大师谭鑫培、梅兰芳的专用琴师。沈氏家族沈默、沈成垣父子,则为清“海陵本”《桃花扇》刊刻评阅者[6]。另清代泰州城内可称望族的储氏(明文学家、吏部尚书储巏后裔)、高氏(高岱瞻家族)及城外姜堰的黄氏(黄云家族)等,戏曲文化特征也十分明显。
另外,戏曲剧目的整理挖掘及著录,是戏曲研究的基础工作。笔者受诸方家治曲史方法的启发,在阅读明清“海陵地区”家族文人相关文献时,也有所发现。如历来剧簿均无徐信《遗臭碑政绩传奇》、李宸《香囊记》等的著录。再如对《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的研究,历来只知其为清末泰州人,但其家世、生平等均无所知。再如梅兰芳、程砚秋藏曲中,多部来自于清人高岱瞻所藏校。笔者发现泰州高氏三代藏曲,后世却湮没无闻。
所以,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串场河以南的古海陵地域为空间对象,以该地域文化圈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重点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的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既能从地域文化、家族文化的角度探求明末以来“海陵地区”戏曲繁荣的原因,又可以多途径、多层次分析、评价文化家族对本地区戏曲艺术发展的重要意义。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世家与戏曲关系的研究,重点分析该地区诸多戏曲文化世家的成因、特征与作用,证实明末清初随着戏曲中心的不断北移,苏中地域已成为继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后第二个全国性戏曲艺文家族的聚集地。同时,将明清“海陵地区”戏曲文化与区域外苏州、南京、府城扬州等地区剧坛的比较,正视海陵地域内区域戏曲的“先天不足”,探究“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艺术互为依存,协同发展现象后的原因。
借助对明清“海陵地区”家族文化与戏曲艺术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具体案例分析,探究本地区文化家族文人群的谱曲写剧、观剧赋诗、评剧校点、藏曲刊刻、家班组织(场下指导,台上示范,演员培养)、舞台表演、理论总结、因剧交游、以戏为业等戏曲活动在进行考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诸多被忽视的、不能确证的问题,如部分戏曲家的生平家世与交游,部分从未见著录的剧作,相关未见记载的文人家班,部分戏曲演员的家世生平,相关曲家藏校刊刻的戏曲文献等予以考证定论,有助于推动江苏地域文化史和明清戏曲史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
4 结语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借助于对“海陵文化”的深入挖掘、总结和研究,有助于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乃至江苏文脉等领域研究的深入,也能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文化忽略泰州地区之短板,适应了当下“江苏文脉工程”研究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实现江苏省委所提出的“努力通过系统整理研究江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深入探究蕴含其中的特殊精神基因、深沉精神追求、独特精神标识,深入阐发其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为传承发展中华文脉写好江苏答卷,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贡献江苏力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