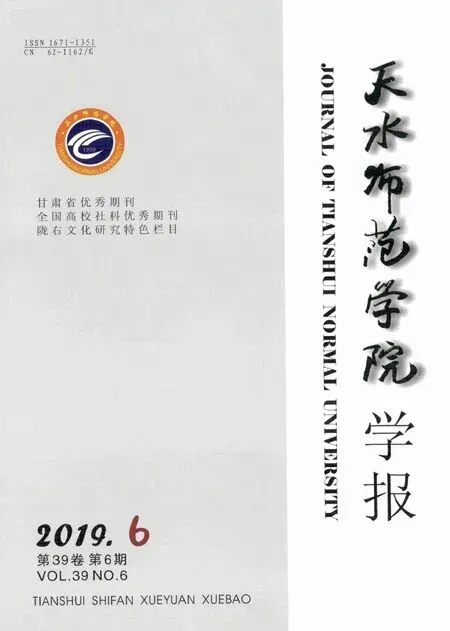唐诗中体现的校雠工作
黎文丽
(咸阳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陕西 咸阳 712000)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是记录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唐代已出现了雕版印刷术,早期主要刻印佛经、历书、杂书等民间用书,因此手工抄写仍然是图书生产的主要方式。书籍在复制和传播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错和讹误,故而对其内容的核对和校雠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校雠是书籍整理编订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勘定版本、校对文字、辨别真伪、考订谬误等,这和当今的编辑、校对工作类似。唐代设置有校书郎、正字等职官从事典籍文献的校雠工作。
一、唐诗中体现的校雠工作地点
唐诗中有很多含有“校书”“雠校”“校理”的诗歌标题和内容,体现了当时的书籍管理、校雠情况。如韩愈《送郑十校理得洛字》:“才子富文华,校雠天禄阁。”李洞《和曹监春晴见寄》:“兰台架列排书目,顾渚香浮瀹茗花。”刘禹锡《送分司陈郎中只召直史馆重修三圣实录》:“常时载笔窥金匮,暇日登楼到石渠。”徐铉《奉和子龙大监与舍弟赠答之什》:“石渠东观两优贤。”这些诗中的天禄阁、兰台、石渠、东观都代指校雠工作地点。汉代建立了多个中央藏书机构,如兰台、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东观、鸿都宫、仁寿阁等。这些机构中设置了相应的职官,负责对文献进行整理、校勘、编目。其中尤以兰台令史、东观校书郎较为著名。唐诗中沿用汉代的称呼以指代唐代的藏书、校雠机构,读来令人熟悉亲切。
兰台,是汉代宫内藏书之处,设置有兰台令史,多以饱学之士雠校其中,如扬雄校书于天禄阁,马融校书于东观。兰台典藏十分丰富,也是史官修史之处。唐高宗龙朔二年(662)曾改秘书省为兰台,705年又恢复为秘书省。秘书省是唐代文化事务管理机构,掌经籍图书,兼修国史。
秘书省是图书管理机构,也是政府藏书、校雠的场所,因此唐诗中的芸阁、芸台、芸省、秘省也是秘书省之别名。如孟浩然《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永怀芸阁友,寂寞滞扬云”是写给在秘书省任校书郎的诗人王昌龄的。许浑《寄袁校书》也有:“劳歌极西望,芸省有知音。”贾岛《送裴校书》写有:“拜官从秘省,署职在藩维。”
蓬山、蓬阁,指藏书之地,也是秘书省之别称。如武元衡《酬谈校书长安秋夜对月寄诸故旧》:“蓬山高价传新韵,槐市芳年挹盛名。”李频《江上送从兄群玉校书东游》:“逍遥蓬阁吏,才子复诗流。”蓬莱被誉为神山,传说仙府秘籍多藏于此。蓬莱池,亦曰太液池,是唐长安大明宫内一处以人工湖为中心的宫苑风景区,位于蓬莱殿之北、龙首原北坡平地的低洼处,池中有用石头垒成的蓬莱山。此蓬莱与传说中的蓬莱仙山遥相呼应,是以仙山比喻秘书省清要的地位。卢照邻《双槿树赋》写有:“日昨于著作局见诸著作,竞写《双槿树赋》。蓬莱山上,即对神仙;芸香阁前,仍观秘宝。”[1]743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省,设有校书郎、正字,因此以蓬莱代指藏书之地,在此可以饱览群书,以满足读书人的渴求。
唐诗中的芸阁吏、芸阁郎、芸香客代指校书郎、正字等官员。许浑《送韩校书》:“迹高芸阁吏,名散雪楼翁。”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青袍芸阁郎,谈笑挹侯王。”周朴《喜贺拔先辈衡阳除正字》:“名自石渠书典籍,香从芸阁著衣衫。”这些诗歌都对其所从事的职业表达了赞赏之情。
校书郎、正字的工作地点大都在长安、洛阳京都的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等藏书库,这里秘藏了大量珍贵典籍和文献,工作之余可以遍览群书以增加学养,也方便向名士大儒请教学问。许多著名诗人都曾任校书郎,并从此升迁转任其他职务,如杨炯、张说、张九龄、钱起、李端、卢纶、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杜牧、丁公著、李绅、李翱、段成式、韦庄等。曾任过正字的诗人有王绩、陈子昂、李嘉祐、章孝标、徐夤、王希羽、曹松等。
二、唐诗中体现的校雠工作内容
为了提高政府藏书的质量,鉴定版本、编订校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校书郎、正字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校雠典籍、订正讹误、整理图书、外出搜访图书等。
唐代的帝王重视图书编校活动。大型图书的修纂编订工作,朝廷会组织当时的通学大儒和学者总领编校事务,校书郎、正字从事具体的整理、校雠工作。如武元衡《送许著作分司东都》有“署分刊竹简,书蠹护芸香”,诗中的竹简指的就是书籍。许棠《送刘校书游东鲁》有“内阁劳雠校,东邦忽纵游”,即指其职务内容是校雠书籍。唐代集贤院编校的书籍被称为御本,是给皇帝阅览的。集贤院,又名集贤殿书院,是皇宫中的图书典藏机构,由唐玄宗设立,兼有修撰、侍读的功能。常衮《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写有:“缥囊披锦绣,翠轴卷琼琚。墨润冰文茧,香销蠹字鱼。”描述了当时集贤院校书和藏书情况:锦绣织就书套,翠轴装饰书页,茧纸写成墨书,芸香防护文字。司空曙《奉和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香卷青编内,铅分绿字中。缀签从太史,锵佩揖群公”,描写集贤院的工作情况,“青编”指书籍,“缀签”指给书籍分类标注,说明编校工作规范齐整、井井有条。
搜访图书、广求善本是图书编校整理的基础。唐太宗时期,图书搜访活动一直绵延不断。唐玄宗在对皇宫内所存典籍进行整理校订的同时,开元六年就开始全国性的图书搜访活动。储光羲《送沈校书吴中搜书》中有“秦阁多遗典,吴台访阙文”,描写了外出搜访图书的情况。此外,政府也会根据需要任命专门的图书使外出广搜图书,以补充和丰富官方的图书收藏。如卢纶《送耿拾遗湋充括图书使往江淮》诗中有:“传令收遗籍,诸儒喜饯君。孔家唯有地,禹穴但生云。”司空曙也写有《送李嘉祐正字括图书兼往扬州觐省》,可知李嘉祐曾奉命前往扬州等地区搜集图书。
唐代政府藏书有大量的副本以备不时之需,并实行完善的图书排架制度。“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曰正本、副本、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写给之。”[2]政府编校的书籍校雠精良,通常选用较好的益州麻纸,笔墨皆为上乘材料,书写字体讲究,装帧典雅大方。王建《宫词一百首》中有:“集贤殿里图书满,点勘头边御印同。真迹进来依数字,别收锁在玉函中。”[3]3440诗中说明集贤殿里的书籍按一定顺序编排,并有不同的收纳存放方法。至开元十九年(731),集贤院藏四库书总计八万九千卷。“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4]从这些记载可知,当时的书籍大都是卷轴式装订,书袋上系有标签和说明。集贤院所藏经史子集各部图书外观设计很有特色,书库排架井然有序,书籍分门别类放置,同时以不同颜色的牙轴、缥带、牙签分别标注,使图书摆放清楚明了,查找方便。这种收藏管理方法也影响和应用到民间私人收藏。唐代名臣柳公绰喜藏书,家有藏书万余卷。而且每藏一书必有三副本:上者版本纸墨精良为镇库典藏本,次者为平常阅览之本,下者为家中少儿子弟学习之本。其子柳仲郢曾为校书郎,继承并发展了柳家藏书。晚唐时期的徐修矩拥有图书数万卷,颇受皮日休与陆龟蒙的推崇。皮日休《二游诗·徐诗》写道:“轴闲翠钿剥,签古红牙折。帙解带芸香,卷开和桂屑。”陆龟蒙和诗《奉和袭美二游诗·徐诗》有:“插架几万轴,森森若戈鋋。风吹签牌声,满室铿锵然。”诗中不仅描写藏书数量之多,而且卷轴林立、签牌整齐,有风拂过便芸香满室,丁零声响成一片。这说明唐代私人藏书不仅丰富,而且大多还非常重视版本和装帧。
三、唐诗中体现的校雠生活
唐代诗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也用诗歌记述自己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经历。白居易任校书郎期间所写的《惜玉蕊花有怀集贤王校书起》:“集贤雠校无闲日,落尽瑶花君不知。”形象地描写了在集贤殿工作的景象,庭院中落满了瑶花,而忙碌工作的人们竟然毫无知觉,一任美丽的花朵随风摇落。
唐诗中也常用一些典故来比喻校雠工作。
科斗,是古代篆字手写体的俗称,因以笔蘸墨书写起笔处粗、收笔处细,状如蝌蚪而得名。科斗后来即指古文经籍。如:“架中科斗万余卷,一字千回重照见。”(刘言史《放萤怨》)“科斗皆成字,无令错古文。”(岑参《送王伯伦应制授正字归》)说明校书郎、正字的日常工作是校雠书籍,减少文字讹误。
铅椠,指石墨笔和木简。汉代扬雄任过校书,他曾携带铅椠四处走访采集资料,后以怀铅提椠指随身携带文具以备随时记录或写作。唐诗中多用怀铅、铅椠作为阅书校雠的典故。如:“芸阁怀铅暇,姑峰带雪晴。”(元稹《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芸香能护字,铅椠善呈书。”(杨巨源《酬令狐员外直夜书怀见寄》)“错简记铅椠,阅书移玉镇。”(皎然《奉和颜使君真卿修〈韵海〉毕会诸文士东堂重校》)
铅黄,比喻校雠书籍。如:“晓随鹓鹭排金锁,静对铅黄校玉书。”(李远《赠弘文杜校书》)“鱼鲁非难识,铅黄自懒持。”(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
古人常用铅粉和雌黄点校书籍,故有此说。
讨鱼鲁,也是校雠工作的别称。唐代名相李德裕曾经做过秘书省校书郎,王起当时也在集贤院校书,两人经常往来唱和。李德裕写了一首诗中有:“青编尽以汲冢来,科斗皆从鲁室至。”[3]5388王起在和诗中也写道:“忆昨谬官在乌府,喜君对门讨鱼鲁。”他们二人的诗歌描写了校书生活既辛苦,又充满了生活情趣。古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后来人们就以此形容书籍传抄中的文字讹误。手工抄书难免有错漏之处,于是“讨鱼鲁”也便成了纠错查漏的代名词,也给枯燥乏味的校雠工作增加些生趣。
唐德宗时期的秘书少监、集贤学士陈京长期在集贤院编校整理书籍。柳宗元所写的《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云:“在集贤,奏秘书官六员隶殿内,而刊校益理。”[1]5980经历安史之乱后,唐代官修总目《群书四部录》及图书亡散大半,且篇籍错乱,陈京按照《群书四部录》的轮廓重新编辑艺文新志,撰成《贞元御府群书新录》。此外,还有史馆修撰蒋乂。蒋乂幼年时曾寄居外祖父家,其外祖父是著名史学家、藏书家吴兢,蒋乂得到了他的不少藏书。其父蒋明,亦为集贤殿学士。蒋乂聪明灵悟,年未弱冠即博通群书,而史才尤长。其父任集贤学士时,请求携蒋乂入院帮助整理被战乱破坏的典籍。宰相张镒见而奇之,乃署为集贤小职。编次逾年,得二万余卷。后来蒋乂长期在朝廷任职,任史官达二十年。蒋乂也成为唐代著名的藏书家,累积图书一万五千卷。
唐代宫廷内藏有大量珍贵典籍和文献资料,使很多文士都希望在秘书省任职以便阅览藏书,如李邕、韦述、段成式等人即是如此。开元五年(717)十二月,马怀素见图书散落无序,上书提请召集宿学巨儒就校谬缺。唐玄宗拜马怀素为秘书监,负责秘书省图书校勘编次工作。韦述等二十六人参与详校图书,并因此得观秘阁藏书。韦述在工作之余悄悄抄写自己喜欢的书籍内容,再偷偷藏在衣服里带出秘书省。这些从宫廷传抄的文献资料经过整理校雠,就可以充实私人家藏书库。开元二十八(740)年五月,萧颖士以《赠韦司业书》向韦述提出请求:“尝愿得秘书省一官,登蓬莱,阅典籍,冀三四年内,绝笔之秋,使孟浪之谈,一朝见信。宁不知立身有百行、立命非一途,岂必系心翰墨,为将来不朽之事也?”[1]1449最晚在天宝元年之前,萧颖士果为秘书省正字,并负责外出搜书。
四、唐诗中的校雠意象
诗人们在创作中常常将一些和校书有关的意象写入诗歌,使唐诗的内容更为丰富,表达的内涵更为深广。
芸香。唐代宫廷内藏书众多,为了避免书籍被虫蚀,往往采用芸香来保护典籍,因此校书地点又称为芸台、芸阁、芸署。如:“马疑金马门前马,香认芸香阁上香。”(周朴《赠李裕先辈》)“正字芸香阁,幽人竹素园。”(孟浩然《寄赵正字》)芸香,是一种草本植物和名贵药材,有特殊的香气,书籍中放芸香草可防止虫咬啮噬,因此它也成为典籍藏所的代名词。中国古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宁波天一阁,就采用芸香作为防虫蛀的措施,使大量珍贵历史典籍得以保存完好。芸香草的香味也被称为“书香”。
青编。唐诗中有:“青编为我忽降书,暮雨虹霓一千尺。”(陈陶《杂歌谣辞》)“青编书白雀,黄纸降苍龙。”(令狐楚《南宫夜直宿见李给事封题其所下制敕知奏直…以诗寄》)青编,即青丝简编,借指史籍,此处比喻宫廷内藏书久远而珍秘。
落星石。白居易《韦七自太子宾客再除秘书监,以长句贺而饯之》:“落星石上苍苔古,画鹤厅前白露寒。”对秘书省的一些景象进行了描述。当时人们把秘书省内落星石、贺知章草书、薛稷画鹤、郎余令画凤并称为“四绝”。因此,这四绝便经常出现在诗中,落星石、贺草等意象也常指代秘书省。
邺架。邺架即指丰富的藏书。唐代学者李泌家中藏书三万余卷,经部用红色牙签,史部用绿色牙签,子部用青色牙签,集部用白色牙签。所有藏书均加盖了“邺侯图书刻章”印章。因李泌曾被封为邺县侯,所以后世多把藏书称为“邺架”或“邺侯架”。李泌精心收藏书籍得到很多人赞赏,著名文学家韩愈仰慕他藏书之富,曾作《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可见藏书的繁富与精美。
缥红。缥红指青、白、淡红色,也有说是纸名,写入诗中比喻纸张质地良好,色彩鲜亮。李峤《纸》“云飞锦绮落,花发缥红披。舒卷随幽显,廉方合轨仪”,用诗句形容纸张如鲜艳华美的丝织品一样光滑亮丽,而且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唐代采用的造纸原料有麻、藤、楮、桑皮、竹、麦秆、稻草等。由于原料和制法不同,造出了名目繁多的纸张,如安徽宣州府出产的宣纸很有名,即使存放很久仍可保持白如玉的光彩。唐代宫廷用纸更为讲究,如《艺文类聚》卷五八引《诸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赤纸、缥红纸、麻纸、敕纸、法纸各一百。”唐玄宗曾赐给李白的“金花笺”,是一种描绘有金花的书笺。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也有:“水精编帙绿钿轴,云母捣纸黄金书。”上官昭容即上官婉儿。贞元十四年(798),崔仁亮于东都购买《研神记》一卷,书缝处留有上官昭容的名字。吕温闻听此事感叹而有此作。诗中描写用水晶编成的书套来装书,用云母捣成纸而书写,以此形容上官婉儿藏书所用纸张的名贵,以及藏书装帧的华美。
五、结 语
唐代政府重视图书整理、校雠,在编目、装订、上架、借阅等图书分类管理上制定了明确的制度,并为后代图书管理工作所继承。对于校雠书籍的工作成效,也会按照一定标准对官员的业绩进行考核,以决定其升降赏罚。唐代政府在书籍缮写抄录后,还设有三级校对、四次详阅以及监督等程序。即便是现当代,书籍原稿也要经专家审定,又经过编辑们认真细致地编辑、校对,达到“齐清定”的要求,才会以完美的形态展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