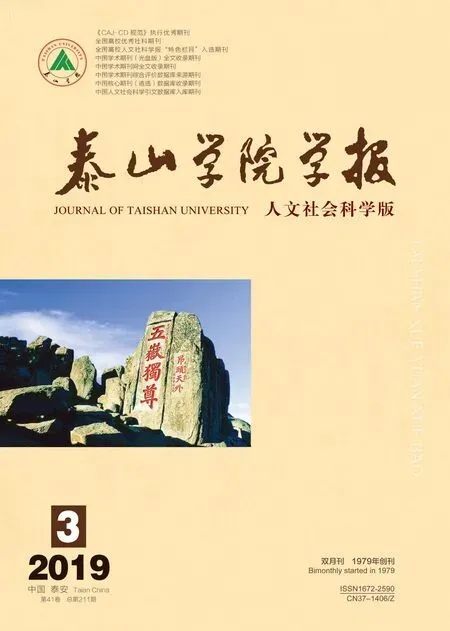大汶口遗址与大汶口文化再认识
——基于当代世界考古学视野
赵兴彬
(泰山学院 历史学院 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山东 泰安 271021)
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基本范式的中国传统考古学,跟世界先进考古学相比,具有很多局限和缺陷,这在整体上主要表现为观念的陈腐、理论的匮乏和方法的落后。如果摆脱中国传统考古学的羁绊,用世界先进考古学的视野和理念,重新审视、思考大汶口遗址与大汶口文化的若干具体问题,诸如大汶口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大汶口遗址重要遗物(稻谷、S纹骨雕象牙梳型器、骨牙雕筒、陶鬶)的文化解读、社会性质、族属等等,可以得出许多新认识、新启示。笔者根据个人的有关研究体会,结合多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最新成果,在此做一些细微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历史考古学与考古学文化
要重新认识大汶口遗址与大汶口文化的诸多问题,应首先对中国传统考古学跟世界先进考古学之间的差距有一个清醒判断,亦即充分认识中国传统考古学的局限和缺陷,不虚美、不隐恶,对其观念的陈腐、理论的匮乏和方法的落后给以充分评析。
众所周知,作为一门正式学科,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表征的考古学,最早于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埃及和西亚两河流域南部的大规模田野发掘而正式诞生,其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尤其是“三期论”)成为该学科的两大法宝。迄今为止,世界发达国家考古学在不断反思和争鸣中几经演变,每次演变都在思想观念、学术兴趣焦点、理论方法诸多方面有质的飞跃。对此,陈淳在其《考古学研究入门》一书中认为,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是西方“进化考古学”阶段(1867~1925),主要关注文化遗存的“何时”,并用“时期”、“阶段”等概念范畴,单线径直解释文化的演变规律。1925~1960年是“文化历史考古学”阶段,其兴趣点是文化遗存的主人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主要使用“类型”和“考古学文化”概念工具,运用描述方法概括器物类型,用“传播论”解释变异,并将考古学文化等同于民族群体。1960~1980年为“新考古学”(又称过程考古学)阶段,关注遗存“何以如此”,使用“动力”、“系统”、“人地关系”等新概念工具,运用假设和演绎方法,注重从环境考古和文化适应观念去解释文化遗存。20世纪80~90年代为“后过程考古学”阶段,流派纷呈、理论多元,主要使用“思想意识”、“信仰”、“个人”、“性别”等概念工具,反对把文化看作是某种系统的整合。21世纪初始至今为“个体考古学”阶段,注重遗存的个体、个性在文化形成和演变中的具体作用,反对追求普遍性和决定论。[1]
中国考古学由西方传入,以1921年安特生主持发掘仰韶村遗址为肇始,其后李济、梁思永等人把西方文化历史考古学家柴尔德的理论方法引入了国内。张忠培曾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归结为六个阶段,每一阶段都用“揭示考古学所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的理论或其实践中的一些重大科学事件”作标志,即: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1931年梁思永揭示后岗三叠层;1948年苏秉琦发表《瓦鬲的研究》[2];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1975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讲演;1985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3]在这里,张氏刻意隐去了李济的重大贡献。
中国考古学的成就固然需要肯定,但由于民族传统、社会历史背景、知识、学术及社会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4],致使中国传统考古学在观念、理论和方法上跟世界先进考古学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暴露出很多局限和缺陷,不能漠视。
首先是观念陈腐。15年前,笔者曾用“世故”和“保守”[5]两词指摘历史学,现在看来,这两个词同样适用于考古学。“世故”主要表现为考古研究的“泛政治化”和对发掘材料的强烈垄断欲、占有欲。前者无需赘言;后者则是考古学界内部的顽疾。许多重大发掘材料,在考古界正式发表报告之前,往往被严密封锁、秘不示人,决不让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染指。但由于能力所限,单靠考古工作者自身往往难以完成室内研究,结果导致发掘报告迟迟不能公布。譬如,1959年对大汶口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直到1974年才发表《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而1974年和1978年进行第二、三次发掘,更是晚至1997年才出版《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这种画地为牢、以邻为壑的行为,严重阻碍了考古学前进的步伐。如果考古界之外的学者偶尔掌握发掘材料,也被禁止发表成果。譬如张宪文回忆他学生时代的一件事,说他当时参加了南京博物院主持的北阴阳营遗址发掘,用发掘材料写成毕业论文,被《考古学报》相中,准备刊用,结果遭到南京博物院的阻止而未能遂愿[6]。
观念“保守”则表现在对国外考古界新事物的强烈抵触。张光直在《哭童恩正先生》一文中提到过这样一件事:20世纪80年代初,他与来哈佛大学访学的四川大学童恩正结识,二人计划通过申请美国国家基金会的经费,开展一项中美合作考古项目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是先在四川大学设立5个中国当时还没有的实验室,第一年由美方提供所有仪器和化学药品;另一部分是合作开展“关于民族植物学与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课题,中方由童恩正参加主持。结果此计划遭到夏鼐断然阻止,其反对的理由是:外国人的考古技术发达,中国人很难赶上,如果在中国境内一起搞考古,中国人的成绩一定不如外人;外国人不可信。夏鼐还说:只要我在考古所任上一日,外国人就别想碰中国的古物。对此,张光直评价说:“这种心态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心态。”[7]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考古学内部也曾有整体反思活动,苏秉琦同门弟子俞伟超和张忠培态度截然对立[8],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考古学界新旧两种势力的激烈交锋。俞伟超发表《考古学新理解论纲》[9]后,张忠培发表了一系列批驳文章,尤其是《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10]。俞伟超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新考古学理念,以开阔的胸怀批评“传统考古学”;张忠培则以旧有观念抨击俞伟超。其间,考古界老一代学人普遍拥护张忠培,年轻一代则热情支持俞伟超。
其次是理论匮乏。主要是宏观层次的哲学理论和中观层次的学科自身理论的匮乏,而那些只适用于具体领域、具体问题的微观理论,如苏秉琦“区系类型说”等在中国考古界并不鲜见。在宏观理论方面,考古学界实际接受的是摩尔根模式和郭沫若唯物史观社会史体系。前者问题重重,后者则是教条化、简单化、机械化的典型。它们被用于指导考古实践,导致考古研究削足适履、牵强附会,或出现理论与考古实践之间“两张皮”的现象。一些重视挖掘实践的学者,由此误认为运用宏观理论就是走从前“以论代史”的老路。殊不知,所谓“论从史出”和“以论代史”,在认识论上本来就不是对立命题。按照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认识论原理,一切科学认识的获得,莫不是“假说—演绎”模式运用的结果,都通过“P(Problem)-TT(Tentative Theory)-EE(Elimination Error)-P(New Problem)”否证验证方法实现。这就是说,一切科学认识的开始都是建立在某一“理论”前提下,这与认识的根本来源问题不是同一个概念。[11]另一方面,由于极度缺乏中间层次的考古学自身理论,也就无法实现宏观哲学理论的合理衔接与转化。正如俞伟超所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新出现的那些考古学理论,实际上有许多是为达到探明历史文化进步规律这个最高目标而建立的中间环节性质的理论……我国的考古学界,过去可能是习惯于直接使用哲学的历史唯物论概念来解释考古学的现象,而忽略了中间理论的建设。”[12]而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和进步的核心指标正是中间层次的学科自身理论状况,中国考古学界最匮乏的恰是这一层次的理论[13],这使考古学界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时(如:对权威的否定,理论的批判性、实践性,解释的多样性,过去与现在信息的断裂,考古学对大众的重要意义等),显得茫然无所适从。理论缺乏多元化,窒息了中国考古学界的质疑精神。
再次是方法落后。这不是指技术性的操作方法,而是指精神图式性的方法论。应当说,对于技术性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考古学界对西方考古学新方法的介绍,一大批青年学者已经主动吸收和试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绝对年代测定法(14C法、钾氩法、古地磁法、铀系法、热释光法、光释光法、裂变径迹法、电子自旋共振法、氨基酸外消旋法等)、浮选法、动植物分析法、植硅体分析法、食谱分析法、古病理分析法、分子生物学方法以及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的具体方法等等。但是这些技术性方法的引进,仍然无法摆脱基本方法论束缚,在整体上“我们还是使用40年代以前的方法,就是类型学和地层学”[14],并坚定地把它视为考古学的两把尺子[15]。但类型学的分类和类比方式,具有盲目性和或然性,只适合常态和渐变,不适合特殊情形和突变[16]。考古地层学中的文化层堆积厚度与其形成时间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17],更不能把某一文化堆积与某一族群的活动做简单对应。
正是由于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全面滞后,导致中国传统考古学在整体上只相当于世界考古学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发展水平,它对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目标和任务的理解和定位,实际就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认知高度。中国考古学界所标榜的“中国学派”[18],实质就是夏鼐对考古学的定义:“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19]认为考古学是以古代人类的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突出工作手段,以证史、补史为目的,隶属于历史学。现行中国学科管理分类中,考古学也是被列为历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在实际研究中,中国传统考古研究者的惯用手法,首先是运用器物类型学的分型分式方法,把遗存之中具有相同特征的器物归并为一类,即“一批反复共生的遗存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和房屋式样”,并努力找出其中的典型器物作为该类遗存的代表;然后再用柴尔德“考古学文化”概念,把这些被概括为具有共同特征的遗存,按最早发现地的最小地名来命名为某种考古学文化,诸如“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等。他们认为,这些相同类型的遗存因具有共性,则必然年代相近、民族群体相同,文化传承也具有同一性,故而可以据此做出史前史的编年,解释民族群体的演化和迁徙。如果在这一“反复共生的遗存”中出现了“异类”,考古学家通常都用外来文化的传播作用予以解释。为了把眼花瞭乱的中国史前各种遗存之间建立起某种时空联系,便普遍运用了苏秉琦的“区系类型”[20]学说。
然而,“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这种考古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经常流于机械化、简单化,有一定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也正是西方“新考古学”猛烈予以批判并奋力做出改变的原因。目前,西方考古学界已经不再把考古学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从人类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等多学科角度看待考古学。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文化人类学影响下,欧美考古学者开始反思编年式“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方法论。他们不满于“文化——历史考古学”那种只见器物不见人,也就是简单类比器物和凭感觉经验排比年代、描述文化遗存的做法,试图更具体、更科学地了解某种文化发展的原因动力机制,包括特定文化的内部演化机理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变迁动力,也就是注重追寻某种文化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因而被称为“过程考古学”。它在理论和方法上深受文化生态学影响,强调考古学要走出单调的器物类型分析,注重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不把器物分类等同于文化分类;文化分类也未必一定等同于族群身份的差异;某种文化中心和分布范围经常发生变动,上下叠压的文化未必具有继承关系,而有继承关系的文化在同一地区内也可能发生变异;重视概括文化演变的规律,提出了文化演变的“假设——验证”解释模式,如史前文化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演进模式;强调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开展系统论研究。这些新思想、新认知,对于中国“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凤凰涅槃都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大汶口遗址与大汶口文化,提供了新视觉和评价参照。
二、大汶口遗址与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遗址与大汶口文化皆为中国“文化——历史考古学”范畴内命题。在前述中国考古学的局限和缺陷制约下,对这两个命题的认识也就存在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澄清。
其一,大汶口文化能否与地域文化挂钩?我们知道,在“文化——历史考古学”那里,“考古学文化”中的“文化”有其特定含义,即“专门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的特征的一群遗存”[21]。这显然主要指物质文化,尽管也有不少研究者试图透过物质文化去窥探精神文化,却因传统考古学所限而经常显得力不从心。在日常生活中,“文化”概念的使用极为混乱,但在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却是分层次的,一般认为“文化”概念可分为三个层次:即浅表器物层(包括物质、技术载体)、中间制度层(规范文本、风习)、深部心理层(观念、意识及其形态)。后两者主要属于精神文化,“是指在特定社会群体(主要是民族)中反复出现,通过各种符号和形象所获得并予以传播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22],这是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众多学科最看重的成份,尤其是群体心理中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更是文化最深层的本质和内核。由此可知,通常所言各种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泰山文化、海岱文化等等之中的“文化”,其重点和核心内涵,仍然指精神文化。如此一来,一种特别看重物质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就跟特别强调精神文化的“地域文化”之间产生了抵牾。这就是说,在落后的“文化——历史考古学”那里,把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大汶口文化跟“地域文化”相提并论,就显得枘凿不入。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须跳出“文化——历史考古学”的窠臼,用前述西方新考古学的理念、理论和方法重新审查既有的考古遗存,像美国考古学那样,把考古学更多地与文化人类学相联系,由注重考古遗存的器物表层研究转入揭示其内涵的精神文化分析和阐释。只有把“文化——历史考古学”升华为“是一门时间跨度很大,空间范围很广,求之细则无穷细,推之广则无穷广,因而在本质上是开放的,没有最终结论的,不断丰富其细节,也不断调整其框架的大学问”[23],再来说“大汶口遗址是泰山文化的肇始”、“大汶口文化是齐鲁文化的滥觞”,才能名副其实。
其二,大汶口文化并非严格的命名,具有考古学家的“主体间性”。按照“文化——历史考古学”原则,某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应当按照这类共同遗存的最先发现地的最小地名来命名,倘若真要如此,“大汶口文化”本该被命名为“花厅文化”,因为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同类遗址最先于1952年在江苏省新沂县花厅村发现。由于江苏考古界的最先发现者对花厅遗址的文化性质存在争论,甚至误入了争议更大的“青莲岗文化”,结果失去了被命名的最佳时机。随着同类遗存的不断发现和学界深入的研究,直到1977年在夏鼐的推动下,才最终以“大汶口遗址”所在地而被正式命名为“大汶口文化”。[24]另一方面,“大汶口遗址”也不是最先发现于大汶口镇,更不是以最小地名来命名的。今天的“大汶口遗址”概念是跨行政区域的,它实际包含了两部分:一是1959年第一次发掘的大汶河南岸宁阳县堡头遗址,约30万平方米,主要为133座墓葬;二是大汶河北岸岱岳区大汶口镇所在地遗址,约52万平方米,分别于1974年、1978年和2012年进行了第二、三、四次发掘。“大汶口遗址”之所以不用“堡头遗址”来命名,无非是看重了大汶口百年古镇的盛大名气而已。这一事实说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类型归纳和命名惯例,并非客观真理和金科玉律,它在认识论上反而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所揭示的认识规律。也就是说,“文化——历史考古学”对文化遗存的解读,其真理性程度实际并不取决于遗存本身,而是取决于认识主体(考古学家)的“主体间性”,它指不同认识主体对某一观点或假说殊途同归的共识。这一概念被当今西方哲学界广泛用来作为判断人文学科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因为人文学科的认识具有强烈的主体选择性和价值取向性,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认识客观性;认识是否与对象相吻合,取决于这种认识是否在现实世界中具有有效(或意义)性。[25]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破碎凌乱的考古遗存,就是认知符码,“而符码的主体间性将使我们遗忘它们的存在和功能。如果你、我和任何其他人运用同样的符码来表现世界,这些符码就不再会像这样能感知到,而是相反,被当作了世界本身的一部分而被体验。”[26]
当然,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角度看,用“大汶口遗址”这一符码来表现“大汶口文化”时,“大汶口遗址”自然就成为“大汶口文化”的代表性遗存,从而得出这样的感知:首先,大汶口遗址82.5万平方米的总面积以及前后四次发掘所揭露的8200平方米面积,都在同类遗址中首屈一指;其次,大汶口遗址是具有清晰来源和去向的前后延续的文化发展序列,上承北辛文化、下继龙山文化,并且大汶口文化本身的早、中、晚三期文化遗存,也是前后相继、共处一地;再次,大汶口遗址所反映的生产发展水平最快;又次,大汶口遗址的社会组织结构在同类遗址中发展水平最高。由此,大汶口遗址所在区域成为大汶口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带,用“大汶口”来命名这类文化遗存,似乎比机械地套用“最先发现的小地名”更加合理。[27]
其三,大汶口遗址内重要遗物的重新解读。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环境考古学的持续开展和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影响,新考古学已经把人类文化看作是复杂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更加关注人类文化的生成、发展和演变跟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挑战、应战),反对机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人类文化对环境的主动适应和调节的强大能动作用。多学科研究证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大汶河流域正处于地球“全新世气候最佳适宜期”,其地质、地貌、水文颇具地域优势,众多考古遗存都昭示了亚热带生物特征,因而古汶河流域具备现今江南气派。[28]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大汶口文化区的粮食作物适合种稻,所以在兖州王因遗址,从孢粉样品中检测出了水稻的花粉[29]。沂河上游的山东莒县分布着凌阳河、大朱村、小朱村等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期的众多遗存。近年环境考古工作者通过动植物遗存浮选、孢粉组合、植硅体和人骨同位素与微量元素分析,发现其食物结构以粟为主,稻、麦次之,间食陆地动物肉、杂粮、榛子、胡桃、板栗、锥栗等[30]。由于大汶口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时没有收集植物大遗存(种子、木炭等),更没有浮选孢粉、植物硅酸体等微体植物化石,所以没有发现稻谷遗迹,但这不等于没有种植稻谷。因此对于大汶口文化区的粮食作物来说,应是河谷洼地植稻、坡地种粟,稻、粟因地而异,尤以稻谷种植为主,这可能是大汶口文化区与仰韶文化区的明显差异之一。
文化人类学强调,解读考古遗物的文化含义时,需要考古工作者在综合多学科知识的前提下,努力跳出解读者自己时代的文化背景,从遗物本身所处的时代特点去理解遗物的功能。比如同样是一把石斧,它是宰杀动物的工具还是杀人武器、伐木器、收割工具,抑或是权柄的仪仗,就不能因为解读者的经验体会而妄言之。在大汶口遗址的M10中,出土过一件精美的象牙刻符骨“梳”,因其外形颇似后世的竖式梳子,故而被发现者用“梳”给予了命名,并且因为象牙的尊贵而进一步认为墓葬的主人具有极高的社会等级。显然,这种认识是错误地受到了发掘者自己文化背景的浸染。其实,在那个古生态环境下,大象在大汶口文化区比比皆是,经常与人为伍,随处可见,象牙未必像后世所感知的那样珍贵。况且在那个以“栉风浴雨”为通俗的时代,也根本不需要如此精致的梳头专用器,尤其是其上的神秘刻符更是提示我们,它不可能是一件梳头实用器,因而笔者建议把它改名为“S纹骨雕象牙梳型器”。至于其真实的功能,目前学界已有了这样的认识:它是带有最早太极图的卜卦工具,与太极八卦六十四卦、阴阳五行十月历、河图洛书、二十八宿、一年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甚至十九年七闰密切相关,是天文、历法、易学、易数基本知识的体现[31]。
同样,在大汶口遗址的M26等15座墓葬之中,共出土26件骨牙雕筒,对于其功用,学界认识不一,“或认为是斧钺、旌旗的尾端装饰;或认为是人体装饰品;或认为是财富的象征;或认为是宗法祭器,由巫师把持,与沟通天地鬼神的信仰有关”[32]。而笔者极为赞赏这样一种新认识:从分子遗传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域关系诸角度分析,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有相同渊源,均属东部地区同一文化大类,因此大汶口文化骨牙雕筒应是良渚文化玉琮的前身,其衍生功能繁多,但原初功能相同,主要用于殓罩男性生殖器,以期求祖根不腐、瓜瓞绵延,这昭示了史前生殖崇拜的一种常态。[33]
至于大汶口文化中的另一代表性器物——陶鬶,学界一致确认该器物模拟了鸟的形象,但它具体模拟的是哪一种鸟,则很少有人论及。常见的说法是“三足乌”或鹰、鸮之类[34]。然而,笔者通过对大汶口文化时期汶河古生态和嬴姓部落图腾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认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鬶,其模拟的具体鸟类就是小鸊鷉,俗称“须嬴”,陶鬶的大小比例、体态、形态、神态,俨然小鸊鷉。而小鸊鷉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东部沿海河沼、湖泊中的水鸟,形似野鸭,它是东夷嬴姓部落群的原始图腾。[35]
其四,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20世纪70年代,根据大汶口墓葬所显示的贫富分化、男尊女卑现象,学术界曾掀起过一场关于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讨论。讨论得出的主要结论:一是大汶口文化处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过渡阶段,二是大汶口文化已处于奴隶社会。然而,探讨社会性质必先以复杂的宏观历史哲学为理论前提,上述结论都是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理论依据的,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源于摩尔根《古代社会》所构建的史前人类社会模式。但摩尔根模式明显具有时代局限性,不断遭到中外学术界指摘。譬如,事实上,原始时代母系、父系的继嗣方式,并非摩尔根所认为的那样一定是前后相继的直线关系,更多的是习惯维系;母系、父系也不等于母权制、父权制;氏族社会并非一定先有母系、后有父系。[36]另外,郭沫若把大汶口墓葬中随葬猪头骨的多寡视为贫富分化的一个依据,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随葬较多的猪头骨,有可能是部落平民出于对墓主的尊重或某种希望的寄托,是完全出于习俗或宗教信仰的需要,有可能墓主生前并不占有大量财产,比如神职人员等。这就像后世一些贫困之人死后,生者也往往扎纸马、纸牛、纸车、纸轿,剪大量纸钱、纸衣等予以随葬。反之,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墓主也未必厚葬,如汉文帝的霸陵等。因此,如果不综合分析墓葬的构成,单纯凭借随葬猪头骨的多寡,不能得出贫富差距、阶级分化的结论。
三、关于大汶口人的族属问题
大汶口先民的族属(来源)是大汶口文化形成的内在动因。文化既然是人的创造,那么相同部族(或种族)的族属,必然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和继承性。大汶口人到底属于哪一族属,或者说大汶口人最早是从哪里来的?这在学术界仍有不同认识。从前,体质人类学曾提出大汶口人是蒙古人种的波里尼西亚类型[37],或者是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38];传统考古学则多认为是东夷人中的太昊、少昊氏①相关研究参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东岳论丛》1983年第2期;《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地区》第64-65页;《文物春秋》2003年第6期、2004年第1期等。。然而,当代国内外分子遗传学的突破性进展,不但给出了新证据,而且从独立的视角为前辈学者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人的“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说”或者“江汉、河洛、海岱三民族说”,提供了强力支持。
根据分子遗传学描绘的“人类迁移图”[39],人类Y染色体遗传标记M168,是现代人类祖先10万年前在非洲的共同遗传突变位标;约5万年前他们迁出非洲,穿越曼德海峡向北迁移,当到达阿拉伯半岛时,M168突变为M89。此时,其中一支,左转踏上M45位标,在西伯利亚沿M242位标一直向前直达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最终至南美洲突变为M3;另一支,右转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突变为M9,约3万年前到达印度兴都库什山北部时再突变为M175。而M175的一部分族群,约在2万年前开始从两个入口即云南和珠江流域,沿3条线路进入中国。从云南入口到达中国的M175人群又分两支:一支直接东进,约在1.5万年前到达中国西南地区,遗传位标突变为M7,成为苗瑶语族的祖先;另一支沿云贵高原东侧向北前进,遗传位标突变为M122,成为汉藏语族的共同祖先,他们约在1.5万年前到达黄河中上游地区。在这里,汉藏语族再发生分离,一支最晚在3千年前到达喜马拉雅山脉的东北面定居,遗传位标突变为M134,最后分化出藏、羌、彝、景颇、土家族等;另一支向东迁移,约在8千年前到达渭河流域,遗传位标突变为M117,他们成为华夏族的祖先,后来不断向黄河、长江流域扩散,最后融合为汉族。
在第二个入口(即珠江流域),他们是从东南亚半岛绕道而来的M175人群,约在1.5万年前到达长江下游,遗传位标突变为M119,他们成为侗台语族的祖先,其中的一支沿东海岸急速北进。稍晚,北亚人群遗传位标M242的一支,也进入中国北部,统称为阿尔泰部落,其中,突厥群游牧在河套、黄土高原,蒙古群在河北平原,通古斯群在环渤海和朝鲜半岛,他们东进、南下,与南亚人群逐渐融合。
早年迁徙的人群,其黄、白、黑、棕之肤色差异,并不像今天这样分明,一个族群往往包含多种肤色人种。王国维曾考证大夏为白种吐火罗人,山东长岛县北庄遗址的骨骼,也含有白种人基因。多种族、多族群的流动性,远比文明时代的编户部族要自由得多。国内学者通过中国28个民族群体“微卫星”的遗传位点分析,认为中国北方群体的“基因池”来自东亚人群和中亚的阿尔泰人;而东亚人群则含有东南亚人群、阿尔泰人和欧洲人群的基因;这些民族群体间存在过实质性的基因交流[40]。
据此推知,最先进入大汶口文化中心区的先民,应是M119的侗台语族;随之M7的苗瑶语族,沿江汉流域东达,开始与侗台语族整合;再接着,华夏语族沿黄河东来;最晚到达这里的族群,应是以通古斯族为主体的少量北亚人群。因此大汶口文化区是一个早期先民多部族交汇、融合的大熔炉。在这个熔炉里,侗台语族的越人大约生活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此时的“夷”即是“越”,“从语言看,夷与越也可能有相当近关系”[41]。苗瑶语族大约生活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此时的“夷”即“苗蛮”,其中的一支曾回撤到了太湖地区,创造了良渚文化。关于“夷”与苗蛮的关系,前辈学者王献唐[42]、徐旭生[43]等多有精辟论述,今人也有新论[44]。越、苗瑶、通古斯和华夏族的混合体,大约生活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他们融合以后创造了龙山文化,但仍主要风行越和苗蛮习俗。在华夏族挤压下,部分越、苗蛮人逐步向南回撤,而另一部分通古斯人则进入了朝鲜和日本。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证据看,大汶口文化的拔牙习俗,从东北方向的日本、朝鲜,经泰山南部向南,到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广东增城金兰寺遗址、台湾高山族、云南的僚族和濮人等,一路留下了东部先民早期迁徙时期的痕迹[45]。可见,大汶口人的主体成分应是侗台语族人,他们一开始从华南珠江迁移,经长江下游至海岱地区,繁衍出嬴姓少昊部落群和风姓太昊部落群,再由此向其他地区扩散。[46]
少昊系部族主要分布于泰山以南的汶泗流域一带,其中心在今曲阜,即“少皥之虚”,西周春秋时的少昊后裔,在泰山之北者尚有爽鸠氏、季荝、逢伯陵、薄姑氏,在泰山之南者尚有徐、奄(偃)、莒、郯、嬴等古国。太昊系主要分布于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其中心在今河南淮阳,即《左传·昭公十七年》所云“太皥之虚”在陈。他们很可能是因战争或洪水之故,由苏北和鲁东南地区南部迁徙而来。其后裔,在江淮之间者,夏商时有风夷、风方;在山东境内者,直到春秋时期尚有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古国。从太昊、少昊系部族有共同的鸟崇拜和程度接近的文化遗存看,太昊和少昊应不是前后相继的传承关系,而是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共存关系。[47]
以上这些观点或看法尽管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论证,却给我们开辟了认识大汶口文化的新思路、新天地,这对中国传统考古学的升级换代或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