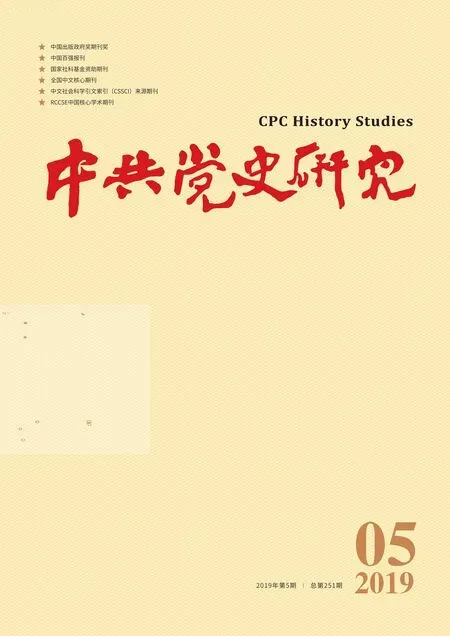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学”模式的创立
李 洁
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随后制定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两个科学规划,即《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科学技术规划纲要》)和《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科学技术规划纲要》一直是国内学界研究的重点,而对《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或是在相关回忆录中简单提及,或是在相关研究中简要涉及。如在《从容忆往:95岁抒怀》一书中,刘导生简要回忆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制定过程[注]参见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88—191页。。薛倩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发展历程与历史贡献》一文中,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为视角,间接提及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注]参见薛倩:《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发展历程与历史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5期。。储著武在《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历史考察》一文中,对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制定过程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并提及了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源头[注]参见储著武:《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从中央宣传部指导作用的视角出发,围绕中宣部科学处[注]有关科学处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其领导自然科学方面的相关工作,比如郑丹的博士论文《在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宣部科学处(1951—1966)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8年)、张藜、赵涛的《科学处与新中国早期的科学领导工作(1951—1956年)》(《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第4期)等。至于科学处与哲学社会科学关系的专门研究还没有,相关的均为回忆性、访谈类文章,散见于各相关回忆录或访谈类文章中,比如龚育之所著《龚育之自述》《在漩涡的边缘》、于光远所著《我的故事》等。的职能作用,通过进一步梳理第一个《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分析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学”模式的确立及意义。
一、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决策
“1956年这一年以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载入党的史册,同时又以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载入党的史册。”[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39页。当时,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潮流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发展以巨大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共中央将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日益重视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周恩来在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时明确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并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183、182页。。因此,中共中央在面临国内外新形势和新任务时,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是中共中央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依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作出的明智决定,它确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目标、基本政策和发展方向。但中共中央最初在筹划制定科学规划时重点考虑了自然科学方面,并没有过多考虑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这从苏联专家柯夫达的建议书以及中国科学院呈报国务院的报告中可见一斑。
1955年1月,苏联专家、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为帮助中国更好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在借鉴苏联制定科学规划经验的基础上,草拟了《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草案)》。在该《办法》中,柯夫达提出,中国有些自然科学部门和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很薄弱。自然科学部门方面,有物理学和化学的许多学科、地质学的全部学科、采矿学、动力学、天文学、土壤学、肥料化学、水文学、土壤改良以及水利工程学。社会科学部门方面,法律学、经济学、艺术、文学和民俗学的发展都很薄弱。[注]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55页。他认为应加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部门的发展力度,并提出设立新的科研机构和组织,加强中科院、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研究所在工作中的合作,合理使用干部等措施。当然,从柯夫达对自然科学部门和社会科学部门的描述和分析来看,他更明显地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对于自然科学的强调与重视,在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4月呈报国务院的《关于贯彻院长顾问柯夫达建议向国务院的报告》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这份报告只是简单提及了社会科学,即关于成立新的研究机构及研究机构的合理地理分布问题上,考虑将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及考古研究所合并以及其他机构或部门工作向内地转移,今后陕西西安将以农业、生物、土壤及考古等学科为主。[注]中国科学院联络局:《中国科学院关于贯彻院长顾问柯夫达的〈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草案呈报国务院的文函》(1955年4月),转引自张柏春等著:《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84页。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4月起草的《关于规划和组织全国科学事业准备工作的决议》中,仅有一句话提及社会科学的两个学科,即“在计划中应特别规定……经济学和法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的措施”[注]《关于规划和组织全国科学事业准备工作的决议》(1955年4月),转引自张柏春等著:《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第486页。。
中共中央最初制定科学规划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自然科学,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加强国防建设等多项艰巨任务有直接关系。在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国家必然会把精力和资源更多地投入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但是,从战略层面来看,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不容低估。正因如此,中宣部科学处提出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建议。“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还组织一批专家,编制了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86页。中宣部的这个指导作用,大体上是以科学处为组织依托完成的。
科学处从其工作职能角度提出的这个建议,坚持了“党领导科学工作”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宣部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指导和管理全国的宣传文教工作[注]中宣部现在主要管社会科学方面,而“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宣部是负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部分的。,而科学技术被当作文化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也划归中宣部管辖,在其内部规定各处职能的文件中就有一条“党对科学工作的管理”。当时有一种观念,中国科学院应该有一个党的机构来管理,中宣部正是这样的机构。[注]李真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1954年中宣部机构调整后,单独设置了科学处,明确科学处负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因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以科学处相应地也负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注]《龚育之自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并逐渐成为管理、联系哲学社会科学和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职能部门。1955年6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注]在钱三强率中科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后,中科院党组于1953年5月提出了建立学部的构想。1955年6月1日,中科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内的四个学部正式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建立的基础是中科院之前已成立的六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语言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第一所、历史研究第二所、历史研究第三所。,它是领导中科院哲学和社会科学各研究所工作的机构,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起着组织和指导作用,并向中科院负责[注]潘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41页。。为了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1957年7月2日,中科院党组向中宣部报告说,院党组经研究建议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注]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潘梓年任分党组书记,刘导生任副书记,成员为裴丽生、尹达、刘大年、何其芳。参见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3页。,向中宣部负责。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思想方面的问题也由中宣部直接领导。中宣部批复同意后,中科院党组通知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即日开始工作。[注]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第83页。自此,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一直由中宣部负责分管,科学处肩负具体管理这方面工作的职能。因此,科学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推动新中国第一个《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使哲学社会科学由此走上“规划科学”模式的道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本来只准备制定自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科学处处长于光远认为应该有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他在一次会议上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自然科学方面,另外还应该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建议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注]参见于光远:《我的故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0页;孙小礼:《长功夫、大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于光远与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9期。周恩来听了之后立即表示赞成这个意见[注]刘导生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是周恩来总理同意正式作出决定的,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参见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第188页。,并且要于光远“负责去组织这方面的工作”[注]于光远:《我的故事》,第20页。。
1955年底,在中宣部领导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正式开始。为了完成规划的制定工作,中宣部还专门成立了由周扬、胡绳、于光远、潘梓年等人组成的“研究制定发展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计划九人小组”(以下简称“九人小组”)[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编:《人民共和国是一切胜利之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离退休干部征文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由科学处负责相关的具体事宜。“九人小组”于1955年12月27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充分考虑各学科和相关问题的基础上,会议决定另设11个小组并由各小组分别提出各学科的发展计划、研究人才的培养等[注]转引自储著武:《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1956年2月3日,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开始着手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拟订工作。”[注]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374页。因为中宣部部一级领导并不直接负责这项工作,因此,具体工作主要是由科学处主持负责[注]李真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6期。。3月12日,周恩来听取了关于“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长期规划工作的汇报”[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56页。。3月14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注]1956年2月17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范长江就科学规划委员会名单和领导核心问题向周恩来提交请示报告。2月20日,周恩来对报告进行了修改。2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和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名单。其中,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由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文教办公室钱俊瑞、范长江、周扬、钱学森、钱三强等34人组成。至于领导核心,由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由张劲夫任秘书长,于光远、张稼夫、范长江等12人任副秘书长。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28—129页。,在负责自然科学规划工作的同时也负责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工作。与此同时,通过对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的领导,科学处依然随时关心与指导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例如,在刘大年被任命为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主任之后,科学处负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副处长林涧青就常找他商谈并作出一些指示。此外,中宣部召开有关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会议,刘大年也常去参加。[注]黄仁国编著:《刘大年年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9、130、134、139、140页。
1956年6月,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在将各学科的远景规划草案进行汇总的基础上,完成了《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的制定。6月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哲学、经济学、法学、国际问题、历史学等15个学科的750多名科学家参加会议,讨论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及如何在科学研究中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注]《七百多位科学家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热烈讨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光明日报》1956年6月12日;《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379页。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制定,采取了上下结合的办法。一方面,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请各学科的著名学者分析本学科的现状、国外发展态势,并提出其未来12年的发展重点;另一方面,由有关的研究所和高等学校的系科走群众路线,讨论相关学科未来12年发展的远景规划,并提出未来发展的目标。规划草案完成之后,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向700多位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及22个省、市的广大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征集意见[注]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148页。。收到反馈意见后,哲学社会科学部于同年9月13日召开第八次学部常委会议,对规划草案进行了讨论[注]《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383页。。
1957年5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48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社会科学方面行政上科委管,思想工作还由中宣部抓。”[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1页。此后,科委逐渐加强了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注]据于光远回忆,自1958年后,国家科委就不像国务院科委那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管,而是只管自然科学。聂荣臻之所以不管社会科学并不代表他不重视社会科学,相反他还是很重视社会科学的。只是一同社会科学打交道,国家科委就会更深地卷入政治运动中。参见于光远:《我的故事》,第58页。。同年6月13日至15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1957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计划、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哲学社会科学的统筹安排等问题。13日上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发言中就如何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问题发表了意见[注]《逐步解决科学界当前反映出来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开幕 聂荣臻主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他指出:“《规划》(草案)曾经发给全国许多地方广泛征集意见,并根据意见进行了修改。目前《规划》(草案)已经部分地付诸实施。这个规划是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家的集体创作。当然,由于我们对制定规划还缺乏经验,加上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规划》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缺点。但因为有了这个《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有了大致方向。”[注]周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7年第45期。13日下午,“哲学社会科学小组举行小组会,讨论如何实现远景规划下半年应该着手进行的工作,包括成立学科专业小组,成立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问题”[注]《逐步解决科学界当前反映出来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开幕 聂荣臻主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15日,科委主任聂荣臻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进一步安排,科学规划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委员将专门开会讨论,委员会并将组织专门的办公机构来处理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注]《科学将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 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结束》,《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委员讨论后,原则上通过了《规划》草案[注]《努力实现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光明日报》1957年6月23日。。同年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办公机构并开始工作[注]《争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重大发展(草稿)》(1958年3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中宣部科学处发挥了重要作用。195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分批赴莫斯科,主要是征求苏联科学家对中国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意见[注]《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458页。。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代表之一[注]刘导生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实现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十分重要。为此,1957年秋冬之际,他和学部委员、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作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专门赴苏联进行访问。参见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第190页。,于光远此行的任务有三个,其中之一就是征询苏联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意见。苏联科学院的经济学、哲学、法学学部和文学、历史学学部为他们组织了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提意见的会议。最后一次会议,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还针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提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注]于光远出国访问笔记(1957年11月)。
1958年2月,根据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起草一年多来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在征集各方面的意见后,由部分原执笔人和有关专家在规划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修改,并且征求了在京科委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委员们的意见。[注]《争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重大发展(草稿)》(1958年3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同年3月,经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原则通过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正式通过,标志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学”模式的正式确立。同年7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
二、“规划科学”模式的初步体现:《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
“规划科学”模式的特点有三个,一是体现执政党的意志,二是由国家资助、主导开展,三是科研项目规模巨大。从一定意义上说,“规划科学”与社会主义思想和体制有某种必然联系,苏联就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规划科学结合得比较成功的榜样。[注]从一定意义上说,“规划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内在逻辑体现。1918年4月列宁草拟了《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建议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委托俄国科学院成立一系列专家委员会,尽快制定俄国工业和经济发展计划。1920年12月,列宁倡导并组织200多位专家制定了被称为“第二党纲”的《俄罗斯全国电气化计划》。1925年俄罗斯科学院改称苏联科学院,并将1918年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也并入苏联科学院。其后苏联科学院又制定了1933年至1937年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文化科学的五年发展计划。参见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繁重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重建任务以及严峻的国际局势,中国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采用了“规划科学”的模式,并且在实践中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
从制度因素来说,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规划科学”所要求的统一与协调有着紧密的契合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制定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把《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并提,并敦促要“组织全国科学研究的力量,有步骤地实现这两个规划所提出的任务”[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26页。。于光远在中共八大上以《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为题作了大会发言。他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半年的努力,我国科学家和各有关方面合作,初步拟定了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规定了十二年内必须完成的科学任务和必须着重发展的科学部门,规定了为了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许多省市也加强了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最近‘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对于鼓励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充分地发挥创造性,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的说来,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已经具备极其良好的条件。”[注]于光远:《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
所以,《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是依据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当时研究力量的具体情况以及国家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形势而制定的,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需求,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学”模式的重要特征。为此,《规划纲要》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任务是:“运用正确方法,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整理我国的科学文化遗产,吸取世界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有力地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这个总任务,初步明确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定位。
(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与“规划科学”体现执政党意志的政治特征。《规划纲要》强调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学科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和编写的重要著作、重要工作、研究干部的培养、研究机构的加强和设立以及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规划纲要》首先列出的内容是各学科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和编写的重要著作。在这部分内容里,包括哲学[注]在《规划纲要》列出的第一个学科——哲学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里,第四个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关于这一方面,科学处在于光远的带领下单独制定了一个十二年规划。、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国际关系、考古学、教育学、少数民族研究、新闻学、文学、语言学、档案学、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16个学科,并详细列举了这16个学科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和重要著作。当然,《规划纲要》不可能包括这16个学科的所有问题,如与各学科相关的在实际生活中提出的新的重大问题是必须研究的,但这些问题是无法列入《规划纲要》的。列入《规划纲要》的问题,仅表示研究工作的大致范围和方向。此外,还有一些学科,没有列入这个《规划纲要》。
以哲学研究为例,按照《规划纲要》提出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总任务,摆在重要问题首位的是“研究中共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而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中,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放在突出位置,并把“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作为认识论第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由此出发,《规划纲要》要求 “1959年以前写出可供高等学校、中级党校、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理论学习教学或参考用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1963年以前写出可供高等学校哲学专业和党校哲学教研室用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这样的强调,无疑是把哲学对形成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引领作用突显出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地位更加明确,“规划科学”体现执政党意志的政治特征也彰显无遗。
为了保证上述各项任务的完成,《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还采取了“规划科学”模式中目标管理和分头实施的方式:为了保证12年内必须完成写作的一部分重要著作(包括教科书在内)具备更高的科学水平,要求同一问题的著作,在可能条件下,应由更多的人来分头写出若干本,而不是只由少数人来写出一本;为了便于系统地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情报,要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世界各国现代和古典的重要学术著作,整理中国历代重要的学术著作以及有计划地进行社会调查;要有计划地培养专业的研究人才,发挥业余工作者的力量,并组织和充分发挥各地哲学社会科学的力量;有步骤地设置与各学科相关的新的研究机构,并充实和改进已有的机构;必须要树立良好的学风,使理论和实际正确地联系起来,鼓励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探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使规划进一步具体化,保证其能顺利实施,要求各学科在此规划以外,还要分别制定自己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并按照年度提出由科学规划委员会掌握的重点项目。[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规定在12年内需要完成的若干重点工作与“规划科学”模式突出重点、注重人才培养的政策导向。在12年内需要完成的重要工作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各国共产党文献的翻译和出版、教科书的编写、中国历代重要著作的整理和出版、世界各国重要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工作、社会调查、地方志的编纂、百科全书的编纂、学术刊物的改进和创办以及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的情报机构等。做好这些工作,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这些重点工作没有人才的依托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紧紧抓住人才培养这个关键,并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困难。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力量还很薄弱,必须发展和加强。根据1956年的不完全统计,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共有相当于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以上水平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约3000人;相当于讲师或助理研究员以上水平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约6000人;相当于助教和研究实习员以上水平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约12200人。再加上党校、军事学校和在职干部理论教员11900人,共计33100人。[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这个数量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数量[注]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明确提到: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约为10万,高级知识分子加上一般知识分子共有384万。对比下来可见,社会科学方面知识分子的数量还是相当少的。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4页。,也根本不能满足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且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不仅在数量方面没有相当的保证,在质量方面也有待提高。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在社会科学方面是51人,但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却只有几个人[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4页。。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强调,除了有计划地培养专业的研究人才外,还应特别注意发挥业余工作者的力量。要在12年内,将社会科学方面研究人员的总数增长到现有数量的2倍左右,即约增长至66000人。[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尽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曲折,但当时国家集中力量解决人才培养这个关键问题的战略方向是正确的。
为了更好地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培养研究型人才,必须要有与各学科相应的研究机构。但当时的研究机构还很不健全,已有机构的研究力量也很薄弱。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取“规划科学”通力协调、上下结合的方式,即自上而下地不断充实和改进已有的研究机构,并有计划、有步骤地设置新的研究机构和各种全国性的、地方性的专门学会等。《规划纲要》还强调由于研究机构的增多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应不断加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建设和力量。[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国际合作的领域与“规划科学”模式在国家主导下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方式和途径的确立。当时的国际合作主要是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合作,《规划纲要》还具体列举了一些可以采用的国际合作形式,比如相互提供哲学社会科学情报、互派学者讲学、互派留学生、互派专家提供某种咨询、互换各研究机构的研究计划、联合进行某些专题的集体研究等。此外,《规划纲要》还建议应注意促进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学术文化交流,可以邀请各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来国内参观、访问、讲学、出席某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等。[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这是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开放性的关键所在。
上述三个方面,基本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领域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发展方向、相关科研院所的增设和研究人员的培养以及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学”模式的初步体现,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发展的长远来看,其积极作用及历史影响是值得充分肯定和深入研究的。
三、 “规划科学”模式的正式确立:《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主要意义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上下齐心合力制定出来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全力推动规划的实施,期望其能真正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以“保证我国许多重要的科学和技术方面在今后十二年内能够接近世界上先进水平”[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225页。。可是,《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刚刚制定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及此后各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使得其实施的进度、力度和影响力大打折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由此大受影响。[注]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第190—191页。但必须指出的是,《规划纲要》的实施虽然受到了政治时势的影响,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并对此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自此走上了由国家主导的“规划科学”模式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更好、更有针对性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关键问题。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制定实施,无疑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解答。“规划科学”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体现执政党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哲学研究注重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升辩证唯物主义在高等学校和党校干部教育中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通过统一编写教科书的方式向全国高等学校和党校、干部学校强力推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引领。与此同时,在“规划科学”模式下,国家势必会集中一切相关的人力、物力等优势资源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从而在组织性方面对其学科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也是《规划纲要》产生的最重要的意义,其成果均是在“规划科学”模式下才得以产生。
二是在实践层面上,为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搭建了桥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虽然没有包括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也不可能涵盖所列学科需要研究的所有问题,但其中列出的16个学科所需研究的重要问题和所需编写的重要著作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国家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制定的。在《规划纲要》的指导下,各学科的政治目标更为明确,也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郭沫若说:“有了规划,我们便能提纲挈领地全面进行工作……不至于在暗中摸索……这样,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就能按部就班地更迅速地开展起来了。”[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95页。比如,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实施过程中,在这个形势下,“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和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国家计划和客观经济规律的关系”就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首要问题,而“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及个体经济的关系”也必然被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经济学这个研究目标的确立,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实际进程所决定的。通过《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这个桥梁,哲学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规划科学”模式由国家主导、体现执政党意志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三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向前发展,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对《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中规定的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等16门学科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和编写的重要著作,各学科都按要求努力研究,逐渐实施了其中的规划。如到1957年5月,哲学方面:开展了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接受中国哲学遗产问题等重要问题的讨论;经济学方面:开展了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等重要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开始了系统的资料收集工作,配合有关业务部门,进行了系统的关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的调查研究;历史学方面: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近代农业史资料、手工业史资料均已相继编写完成;等等。1957年5月,潘梓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各个研究所已经开始根据这个规划草案来制定自己的年度计划,高等教育部门也组织了57种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其他各部门和各地方的研究工作也正在逐步开展。”[注]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7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印,1998年,第140页。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向前推进的实践中,“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确立及发展是值得研究的一个案例。“自然辩证法”在国外被称作“科学哲学”,属于科学方法和认识论的范畴。在《规划纲要》中把它纳入进来,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相融合的重要桥梁。《规划纲要》要求“对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作哲学的分析”,“依据现代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新成就,研究自然界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1958年 10月,在于光远、艾思奇、陆平等人倡议下,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举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班,来自全国高校、党校的70多位教师参加了培训。于光远、杨献珍、艾思奇以及钱学森等人授课。1962年,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招收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各招四名研究生,由于光远、龚育之担任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孙小礼具体主持工作。在此期间,上海、广州、黑龙江等地相继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北京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在1957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冲击影响下,“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注]范岱年:《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四是充实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培养了相关方面的专门人才。《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明确规定要有步骤地设置新的研究机构,并充实和改进已有的机构。《规划纲要》实施后,哲学社会科学各相关部门按照要求,积极扩充新的研究机构,并对已有的研究机构进行调整。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例,到1957年5月,已由原先的6个研究所和1个研究所的筹备处,发展到了10个研究所。新增加的研究所包括文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所。[注]《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148—149页。至于人才培养方面,《规划纲要》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同实际需要是不相称的。要求在12年内,研究人员的总数由33100人增长到66000人左右。[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规划纲要》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措施,如改进和健全培养研究人员的方法和制度、要在各种实际岗位上来培养、逐步做好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工作,以及从实际岗位中抽调一些政治上坚定、学术上有一定基础和培养前途的干部等。在《规划纲要》的具体指导下,全国各地逐渐培养了一批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人才,这为以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初步奠定了人才基础。
总而言之,虽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它依然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实际影响。它使哲学社会科学开始走上了由国家主导的“规划科学”模式之路,并由此实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整合,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等等,这些都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四、结 语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学”模式的确立,缘起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制定。这个纲要是在“党领导科学工作”的中国政党治理模式下,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建议、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决策下制定的,是在革命与建设相交织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和实施的,它映衬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治路线发展的曲折历史,也昭示了未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及发展方向。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大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周恩来把科学技术规划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起作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并在中共八大上进行了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制定凸显了中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理性思考,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的重要性,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始阶段就作出把科技和哲学社会科学共同推进的决策。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是在“党领导科学工作”的重要政治条件下产生的,它的历史使命在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台后,把党的领导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于光远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总结中国的遗传学“在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之间长期存在着的争论”的经验教训时说:“这一争论只有靠生物学家自己来解决……让科学研究成就来做最后结论。党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还是不多的,我们应该在工作中积累和总结这种经验。”[注]于光远:《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 。因此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中,推动某些研究领域较好地处理了学术批判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比如,《规划纲要》在着手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要求研究“外国哲学史和现代各国哲学思想”,研究“西方哲学史,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和十七、十八世纪英、法等国及十九世纪俄国的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在重点研究中国国民经济史的同时,还要研究“外国国民经济史”[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在“国家与法的历史研究中”,“世界各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和世界各国政治法律思想史重要问题的研究”(以东方和近代为重点)也列入其中。这些方面的内容,为改革开放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最初的“规划科学”模式样本依据。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制定和实施是与中共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相一致的。但1957年以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冲击了中共八大路线的贯彻执行,也影响了《规划纲要》实施的后续政治生态环境。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深受影响,当年规划目标不仅未能实现,而且严重萎缩。有学者甚至认为:“由于1957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背景,社会科学研究受到极大的干扰,规划基本上没有实施。”[注]周秋光、黄仁国:《刘大年传》,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15页。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政治运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形成阻力和干扰的严重后果是明显的。比如,“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哲学社会科学部实际有13个研究所和2个相当于研究所的研究室,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总计约2200人”。“与苏联、美国、日本差距很大。苏联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仅仅历史、哲学、经济、语文、法律五门学科的研究人员就有159000人,光研究中国的就有10000多人。美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有250000人,日本有129000人,朝鲜社会科学院也有6000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3页、“正文”第5页。这方面的教训深刻,也告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改变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动摇不得的关键所在。如果发生丝毫动摇,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以及工作方式,都将发生改变,造成严重后果。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向‘左’的方向偏转,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462页。。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开启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规划科学”之路的步伐。1979年7月,在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注]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与中国科学院等同,相当于部委一级的单位,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第1页。的组织下,中国完成了《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第27页。。自此以后,为不断贯彻落实党的最新会议精神和满足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要求,中国又相继制定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1986—1990)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八五”(1991—1995年)国家重点课题规划》《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1996—2000年)规划要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2001—2005年)规划要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等。而且,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了更好地推动本地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也制定了本地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比如,《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九五”规划(草案)》《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纲要》等。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制定迈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规划科学”模式的第一步,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奠基意义,其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