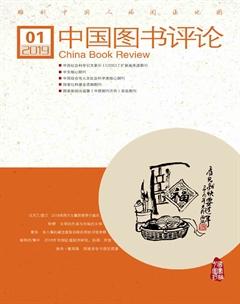2018年海外民族志述略:全球流动背景下的海外民族志研究
陈盈莹 赵萱
“海外民族志”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背景下所提出的概念。高丙中教授认为,海外民族志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出路。他将中国社会科学区分为“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前者指我们如何看待中国自身,后者指我们如何看待世界,指出只有这两种学术取向结合在一起,知识才可能“有进有出”,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王铭铭教授将中国人类学分为三种类别:“处在中国的人类学”(AnthropologyinChina)、“研究中国或关于中国的人类学”(AnthropologyofChina)、“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人类学”(Chinesespeakinganthropology),亦有同样的意味[1]。他认为,海外民族志是Anthropologyin China和Chinesespeakinganthropology的结合。海外民族志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对象的变更,因为即使是从事 AnthropologyofChina的学者,也可以有独特的洞见。
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科学刚开始发展不久,便有一批学者开展海外调查,如吴泽霖、李安宅、田汝康等人[2]。5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中断,海外民族志研究陷入了停滞状态。得益于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重新兴起。2013年,海外民族志研究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机遇,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議下,更多学者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进行田野调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做出了贡献。2018年,在“一带一路”建设走进第五年之际,中国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与非洲各国达成新的合作共识。与此同时,海外民族志研究在区域研究、跨境民族、全球流动等研究领域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包括成立相关的学术机构、举办国内与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和出版相关研究成果等。本文将从这几个方面梳理2018年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发展的基本情况,并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提出一些建设性的观点。如有遗漏或不当之处,还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行动:学术机构的成立与学术会议的召开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全国各大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了从事海外研究的学术机构,尝试通过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建立智库、学术交流等方式,一方面为国家提供智谋与人才,另一方面借此机会推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2018年,京沪两地均有高校成立区域研究院。4月12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有近100位国内外学者出席。院长钱乘旦指出,国别与区域研究是中国了解与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工具,北大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形成具有北大优势和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同年9月28日,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该研究院获得了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被视为上海支持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决定。未来,该研究院将继续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以“立足本土,放眼全球”为理念,打造一流的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平台。
2018年,学术界还开展了一系列相关主题的学术会议,参会者多为具有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边疆学或国际关系学等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这些会议突出了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互相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推动了跨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2018年4月12日,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揭牌仪式结束后,北京大学围绕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一主题,举办了包括“天下论坛”和“博雅工作坊”两个板块的学术活动。“天下论坛”由三位学者进行主旨发言,指出学科发展应重视理论基础的培养和历史资料的搜集,形成跨学科合作的局面。在经济学院举行的“博雅工作坊”则分为四个工作间,第一工作间以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科建设与培养这两个问题为主;第二工作间讨论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尤其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第三工作间讨论中东问题,关注中东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以及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第四工作间则以欧洲问题为中心,探讨欧洲当前的挑战和未来的走向。
在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前4个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就已经主办过相关主题的学术会议。2018年5月19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行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案例”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见证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校党委书记姜锋在开幕式上宣布,上外将启动田野调查专项基金,专门资助从事海外调查的学者。会上,16位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学术报告人分别就“政治学跨国田野调查”“国际发展合作田野调查”“海外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国海外利益田野调查”等四个主题分享他们的田野经历及其成果,促进了学者、商业人士和媒体人士之间的海外经验交流[3]。
2018年6月,学术界举办了两场涉及“全球流动”这一主题的学术会议。6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在云南昆明召开,此次论坛由西南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联合主办,共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本届西南论坛以“全球化与中国西南”为主题,会议的主旨发言讨论了全球化时代下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应用,另就西南民族研究的既有成果与发展前景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会议的分组研讨会则设12个议题,涵盖西南民族、跨境民族、边疆治理、跨国流动等研究问题。在跨境民族方面,学者重在讨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的跨境民族,以及中国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与现状;在跨国流动方面,学者们关注的是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物、人、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并反思全球流动对中国社会环境和学术研究路径的影响。
2018年6月23日至24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全球相遇:跨过流动视角下的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有来自19个国家的近百名学者参加,共设12个议题,以讨论跨国与跨境流动的现象、理论与方法为中心。参会者的发言报告涵盖了不同国家语境和研究视角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和在华外国人研究,其中前者的研究对象包括了东南亚、非洲、拉美地区和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华人群体。此次会议使国内外学者在“全球流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学术共识,为未来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8年11月3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了博雅工作坊第十四工作间的研讨会,题为“亚洲的人与社会:人类学的实地田野考察”。8位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者就亲身完成的长期田野调查进行海外民族志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对话,涉及马来西亚、菲律宾、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印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8年11月16日至18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和中国世界民族学年会在同一时间举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8年年会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主办,由陕西师范大学承办,年会分为多个专题会议,其中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会边疆学专业委员会和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共同申办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议,就海外民族志、人类学民族学的区域研究和东南亚研究这三个议题展开讨论。2018年中国世界民族学年会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国世界民族学会联办,会议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行,以“全球化背景下多民族国家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学术研讨会”为题,围绕多民族国家治理、国际移民与难民、“一带一路”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展开讨论。
二、成果:研究课题的立项与学术论著的发表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共通过4506项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通过3128项规划基金、青年基金和自筹经费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则有174项课题通过評审。笔者在社会学、民族学和交叉学科门类中筛选出涉及海外(境外)民族志研究理论与方法的项目与课题,这些项目或课题大多涉及两个主题:第一,跨境民族与跨境流动,尤以中缅和中越边境的研究为多;第二,中国台湾的族群认同与政治,包括对台湾的原住民和云南移民群体的研究等。此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和海外华人研究仍然占据一定比重。
根据海外民族志的基本定义,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需要具备三个主要要素:一是到海外(境外)去,二是进行规范的田野调查,三是形成符合学术要求的研究报告。基于这三个要点,对2018年11月1日以前中国知网所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文章进行筛选与整理,按照研究主题将其分为三种类型进行介绍:跨境流动、海外华人和区域研究。
2018年有许多学者关注西南边境(尤其是中缅、中越边境)的人口流动。例如段颖对边境地区缅甸华人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华人的跨境贸易、跨境而居和参与中国地方事务这三种行为,揭示了缅甸华人公民身份的灵活性:既是缅甸公民,又是海外华人[4]。由于长期生活在缅甸,这些华人对缅甸有着较强的国家认同;与此同时,华人的身份又使他们得以享受中国相关政策的优待,在动荡时期暂时逃离缅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缅甸华人在跨境活动中不断定位自己的公民身份和族群身份,这种跨境流动的现象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族群和国家认同问题的新视角。冯罛炜、汪洋对云南瑞丽居民的跨国赶街习惯进行分析[5]。在滇缅边境一带的传统集市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生活在瑞丽的边民却更习惯去缅甸的集市,甚至不惜花费更多的交通与时间成本。作者认为,这种跨境消费应被解释为一种“惯习”,延续了过去尚未划定明确边界时的赶街习惯。换言之,跨境消费成为边民保存历史记忆、怀念传统文化以及逃离现实焦虑的方式。这个观点对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基层市场未必凝聚一定范围内的村庄形成乡村共同体,也未必是国家与地方的中间纽带。瑞丽居民的跨境消费指出了基层市场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空间的可能性,指向了消费行为背后的文化意涵。
海外华人研究是研究成果最丰富、最多元化的一个领域,包括了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问题。伍庆祥的文章指出了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内部差异[6]。他选取缅甸的勐稳人作为研究对象,将其与缅甸果敢族以及华人进行比较。这三个群体都属于广义上的“华人”,但却有着不一致的身份认同。果敢族位于中缅边境,在中缅划定边界后才属于缅甸,因此这个民族拥有比较特殊的政治身份,有强烈的地区认同和较弱的国家认同;华人则散居在缅甸的各个城市,他们因为靠近主流民族而表现出较弱的地区认同和较强的国家认同;勐稳人由于生活比较封闭,鲜少与果敢族和华人接触,因此表现出较强的国家认同和模糊的民族认同。作者引入“空间属性”的概念对这种差异进行解释,认为身份认同与居住空间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即使同为海外华人,但由于彼此的居住空间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黎相宜的文章以美国四邑华人社团为例,探讨了海外华人社团内部冲突的成因[7]。她认为汉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存在缺陷,这种观点往往将海外华人社团解释为传统社会和组织的延伸,将社团的内部冲突与其对祖籍国的政治态度挂钩,从而忽视了所在国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影响。美国华人社团内部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新老移民的冲突,这与美国《排华法案》废除后新移民的加入有关;其次,这些社团的运作体系受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影响,社团内部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人对权力的争夺,是一种非政治性的日常冲突。而社团与祖籍国的联系仅仅是社团建构自身合法地位的手段之一,归根到底仍是日常权力冲突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海外华人组织的分析必须结合区域社会结构和所在地文化系统。
在海外华人的宗教信仰方面,有马潇骁、麻国庆二人对泰国清迈华人精英的“报”这一宗教实践的研究[8]。他们探讨了华人精英参与慈善活动的原因及其结果,即“报”的实践是如何产生和运作的。华人精英出于对神灵的感恩和对社团的责任,往往会对神缘社团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本,这是华人精英对神灵的“报”;华人精英向神灵献祭的物品会以神灵之名捐出,惠及社会其他人士,这又形成华人精英对社会的“报”。在这个过程中,华人精英一方面通过仪式展演获得神灵对自身地位的肯定,从而使前期投入的社会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另一方面又通过施惠获得社会对自身地位的肯定,从而使象征资本又转化为新的社会资本。由此,神灵、施惠者(华人精英)和受惠者形成一个“报”的循环系统,华人精英借此实现了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在文化习俗方面,有李牧以纽芬兰华人的春节庆祝活动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移民的族群记忆与所在地的地方性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9]。纽芬兰华人的春节庆祝活动经历了从私人化到公共化的发展历程,这个过程一方面表现了纽芬兰主流社会对华人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表现了华人积极向主流社会推介族群文化的渴望。纽芬兰华人将族群记忆与地方知识相调和的努力,使华人的春节文化展演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又是为了积极融入主流社会。这种新的族裔文化的形成,展现了文化超越民族与国家的可能性。
在区域研究领域,有针对泰国、墨西哥、以色列等国家社会问题的探讨。龚浩群研究的是当下泰国城市中产阶级的修行实践[10]。她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框架,提出了“灵性政治”(spiritualpolitics)的概念,将宗教实践与宏观的政治社会转型相联系,认为新自由主义对个体的关注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反映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上。泰国城市中产阶级的修行实践是一种注重个体内心解脱的宗教活动,提倡用当下的解脱代替来世的功德,以消除个体之苦作为消除社会之苦的前提。这种宗教实践表现了“信仰层面的能动性和政治层面的无力感如何在人们的灵性体验中相互交织”[10]。修行是一种突出个人主体性的行为,然而将个人价值置于社会问题之上,会使自我救赎成为人们回避现实冲突的出路,从而削弱了社会变革的动员能力。
张青仁通过研究墨西哥如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讨了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非遗保护何以被视为重建全球秩序的努力,以及社群的自觉参与对于非遗保护的重要性[11]。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非遗保护计划是在两个社会条件下兴起的:一是拉美国家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二是殖民历史和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明对拉美文明的挤压。后者使墨西哥学界对非遗保护的认知具有强烈的反霸权主义色彩。在墨西哥,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学者要求重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族群象征的价值与意义,他们以民族志方法进入社群,与社群成员一同识别、记录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激发社群成员自觉参与遗产的保护行动。作者认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动机和理念,虽然不一定能够改变既有的全球秩序,但它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对社群参与的重视却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赵萱的文章基于自身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区的田野调查,尝试突破地缘政治的单一叙事,用日常视角来看待巴以冲突。以往的研究通常视领土和宗教为巴以冲突的焦点,赵萱则以耶路撒冷基督教的实践为切入点,通过三个案例展现了超越领土和宗教界限的耶路撒冷图景,认为宗教是冲突焦点的同时,也创造了冲突以外的社会空间和秩序[12]。其另一篇文章从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个案出发,讲述了这一群体如何被悬置在“例外状态”(state ofexception)之中[13]。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地缘政治和生命政治的互动关系,观察到国家主权、社会规训和人口治理这三者的结合如何构成新的生命政治治理术,以及个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换言之,巴以冲突在当地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复杂性,提醒学者应当跳出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对日常实践予以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三、趋势:全球流动视野下的海外研究
在《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趋势》中,周大鸣和龚霓指出,海外研究是当下中国发展的需求,是“他者”和“自我”互观互动的需要,也是学科恢复发展的必经阶段[14]。但是,海外研究不能局限在“到海外做研究”这么简单的认识上。在两位作者看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海外研究必须具备流动的视角,观察全球范围内人口和事物的流动。因此,对于在华外国人的研究也必须被包括在海外研究中。另外,海外研究还需要有更远大的抱负,即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从中国的文化和认知体系出发,用中国学者的眼光来讲述“海外”,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从2018年海外民族志研究的进展来看,区域研究和全球流动显然是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区域研究自不必多言,海外民族志的第一要点就是走出国门,加上“一带一路”的倡议逐步向外推进,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区域和国别的研究中。至于全球流动,如李明欢所言,全球流动不是单向或双向的流动,而是环形的流动[15]。这意味着,研究全球流动是无法规避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包括中国。然而若如周大鸣和龚霓所言,将在华外国人的研究包括在海外民族志研究内,是否已经违背了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第一要义,即田野地点的变更?观察上述有关全球流动的研究,尤其是在跨境流动方面,我们会发现将田野截然二分为“海外”和“本土”更为困难。例如对中缅边境人口流动的研究,研究地点是属于海外,还是国内?更何况,边境研究一直都在打破所谓的族群和国家边界,而海外民族志对“走出国门”的要求却正是建立在对国家边界的认识基础上的。
事实上,全球流动的现象对“海外”这一概念的冲击,或者正好指向了海外民族志发展的最终方向。即当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使在海外做田野调查不再稀奇时,人类学家便不再以在海外或在本土做研究来区分彼此,而是形成一个内部多元而又一致对外的學术共同体。换句话说,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目标是学术话语体系和学术共同体的进步,最终破除“海外民族志”这一概念本身。在当下,海外民族志研究因肩负着这样的使命而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将“到海外去”视为工具而非目的,以问题意识为优先,以理论突破为抱负。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兼具一种互惠人类学的视野,坚持以互惠观念中的回馈精神和他者关怀为学术伦理的基本[16]。
注释
[1]王铭铭.所谓“海外民族志”[J].西北民族研究,2011(2).
[2]王建民.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史[J].西北民族研究,2013(3).
[3]根据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网站:http://www.sirpa. shisu.edu.cn/a6/f8/c227a108280/page.htm.
[4]段颖.跨国流动、商贸往来与灵活公民身份———边境地区缅甸华人生存策略与认同建构之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18(1).
[5]冯罛炜,汪洋.作为传统的异域集市———以瑞丽弄贺村民跨国赶街习惯为中心的讨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6]伍庆祥.空间属性与缅甸勐稳人的身份认同建构[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2).
[7]黎相宜.从区域社会结构与在地文化系统视角看海外华人社团内部冲突———以美国为例[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2).
[8]马潇骁,麻国庆.以神灵之名———泰国清迈华人精英“报”的道德实践和资本转化[J].开放时代,2018(3).
[9]李牧.族群记忆与地方性知识的交互与融合———纽芬兰华人春节庆祝的历史、文化表演与仪式过程[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3).
[10]龚浩群.灵性政治:新自由语境下泰国城市中产阶层的修行实践[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11]张青仁.社会动员、民族志方法及全球社会的重建———墨西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J].民族文学研究,2018(3).
[12]赵萱.“圣地”秩序与世界想象———基于耶路撒冷橄榄山基督教社群的人类学反思[J].世界宗教文化,2018(3).
[13]赵萱.隔离墙、土地与房屋:地缘政治与生命政治的交互———一项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志研究[J].开放时代,2018(5).
[14]周大鸣,龚霓.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趋势[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15]根据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明欢教授在“全球相遇:跨国流动视角下的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整理。
[16]赵旭东.海外民族志的文化自觉[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9-7.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责任编辑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