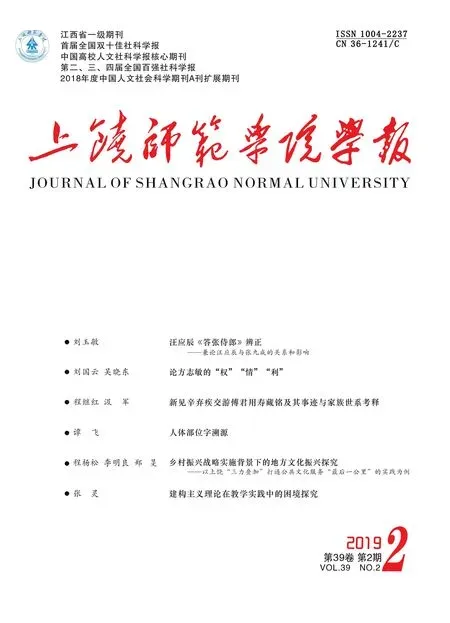读吴长庚《六经图碑本研究》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经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为“六经”,“六经”被称为中华元典,由孔子所删修整理。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建言后,儒家经学一直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然而“六经”文简义富,历代儒者虽然“皓首穷经”,致力于经典的诠释,仍很难说得到了“六经”的本意。尤其是经典中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概念,这些概念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复杂、交叉的立体层次关系,如果只是用语言表达会有一种治丝益棼的感觉。为此,宋人杨甲发明了《六经图》,试图用图表的形式来理清经典中各概念之间的关系。可惜时至今日,杨甲的《六经图》很少有人关注,并且也难以看懂。值得庆幸的是,吴长庚的《六经图碑本研究》为我们弥补了这个学术空白和遗憾。
我与长庚相识较早,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首届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我们便见了面。随后社科院历史所与上饶师专合作创办《朱子学刊》,我们就有了更多的接触。后来长庚带领几位老师参与了《儒藏》春秋类文献的整理,在北大儒藏中心多次召开的会议上都有机会见面交谈。我所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也邀请长庚参编撰稿。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告诉我,正在对《六经图》开展研究。今年年初,他又告诉我,书已经出版,并邮寄到岳麓书院,希望我读后谈谈对该书的看法。但该书部头甚巨,洋洋七十万字,通读固为不易,只能在浏览之余,谈一点个人感想。
宋人解经,锐意创新,而以易学为尤著。宋代周易象数学中有一项创造,就是发明了许多易图(旧称“图书”)。易图的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用以推演天地造化的基本原理,一是用以说明《周易》六十四卦之间的复杂关系。前者是要以易图或易数形式建构一种宇宙图式,后者是要进一步揭示隐藏于六十四卦之间的易数与卦变等等的规律。综合地看,《六经图》作者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在《周易图》解析中,作者对《周易》经传的有关概念、历代易学家发明总结的义理规律、易学与天地事物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较清晰的阐释。正如吴著在后记中指出:以图解经无疑为经学解释提供了方便,但宋人的图已经不是简单的事物形态的再现,而是用以表现抽象的哲学概念,这多集中于《周易图》中。但作者并没有周旋于这些繁琐的哲学概念之中,而只是就图及图所涉及的经典问题给出思考答案,或历述古今各派观点,启发读者思考领悟。如《三变大成图》和《四易之易图》的解析,引用历代典籍,详加比较分析,使读者对图意有清晰的理解。书中,关于《先天图》和《中天图》的解析也颇有特色。
随着科举制度的推动,宋代的经学教育开始全面展开。为适应这种需要,以图解《易》的方法也很快推广于整个经学教育之中,一方面,宋儒以解经的方式建构其思想理论体系,图学能简单明了地说明其经典概念、范畴之间的层次、从属关系。如《周礼》述大宰掌治、司徒掌教、宗伯掌礼、司马掌政、司寇掌刑、司空掌事等问题,文字都很繁冗,而列为图,则一目了然,线索清楚。另一方面,在《周礼》《仪礼》中,都有许多古代名物制度的知识,如各种冠冕、礼服、礼器、祭器、乐器,或如天子大射、五等礼文、治朝燕朝、燕射宾射等制度,《考工记》中车马各部件的名称等,若无图示,则很难明白。所以,以图解经的方式虽然是儒家经学的一个支流,但对于儒家经典诠释的发展却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注意到,“六经”之书,各有其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社会功用,因而在诠释中能把握住点与面、轻与重、难和易的关系。所谓面,是指在各图普遍性的诠释中,立足经典原著,理顺历代经学家的理论发明,动态地阐述理论发展变化的历史。所谓点是指重点,即“六经”流传后世最重要的理论内容。《六经图》之中,最难的是理论体系的揭示。但图只是个体的存在,图与图之间或有体系,并不都构成横向联系。所以在面上,各图的诠释都单独成篇,相对独立。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注意到各经的主体内容,并作出相应的重点揭示。如《周易图》的易有太极、河图洛书、释象释爻、十三卦取象之类;《尚书图》的山川地理、帝王世次、天文历法之类;《诗经图》的风雅比兴之类;《周礼图》的官制、政制和礼制,井田之法之类;《礼记图》中对礼制的分析判断,如礼以义起、非古之礼、非礼之礼的判断;而在《春秋图》中,则注重对春秋笔法义例的揭示。杨甲《春秋图》中,从四个方面总结归纳了“春秋总例”的不同方面,共有四图,而作者对此都引用了原典的例子,并一一作出诠释分析。
将经图刻诸于碑,一在确定定本,防止纷争;二在期以传之久远。作者之所以选择宋元碑本,是在详考《六经图》流传演变的基础上而作出的有眼光的选择。自《六经图》问世后,学者多以己意改动,至明清以后,已改得面目全非。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历代修改并非全无意义,但杨甲原创的价值,自非后世改本所能取代。尤其是原碑今已无存,重刻仅剩残段的条件下,上饶的碑本就显得更为重要。今吴长庚教授依据所发现的元代所刻六经图碑的完整拓片,进行整理、研究、出版,无疑将大大有助于经学思想研究的推展。尤其是其中12幅大的碑版,为《四库全书》所未存,其文献学的意义十分重大。
这里,我要稍微谈一下《六经图碑本研究》课题的难度。《汉书·艺文志》论及治经之难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在古代,儒者能通一经就很难,过去有“老学究”一词,“老学究”的原意就是“学究一经”。治一经其难如此,因而像郑玄、朱熹等极少数能遍注群经的大儒,被推尊为“大贤”“功臣”。《六经图碑本研究》虽然不属于遍注群经,但若作者对“六经”及各家注疏不熟悉,那也绝对做不好这一课题。吴长庚教授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独立完成了这个课题,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现在许多高校开设了儒家经典研习课程,我相信这部书对于读懂儒家经书会起到一种“按图索骥”的功效。倘如此,则吴长庚教授功莫大焉!
我曾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300万字,部头不可谓小。但挂一漏万之处,所在多有。特别是于宋代杨甲《六经图》这部重要成果全未曾措意,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幸作为当时课题组成员的吴长庚教授后来弥补了这个缺憾。这使我想起唐代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义疏》(又称《五经正义》),而于《仪礼注》《周礼注》《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皆未作义疏,其后由贾公彦补作了《仪礼注疏》和《周礼注疏》,由杨士勋补作了《春秋穀梁传注疏》,由徐彦补作了《春秋公羊传注疏》。其中贾公彦和杨士勋皆曾是孔颖达《五经义疏》编纂团队的成员。所以,当吴长庚《六经图碑本研究》出版并赠书于我时,我十分高兴,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遂书此数语以表庆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