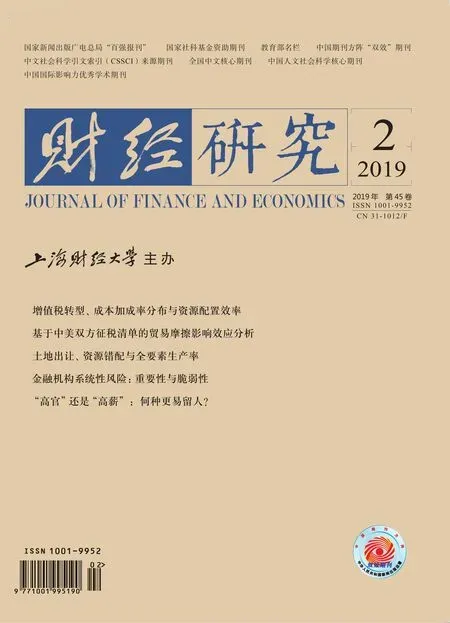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
张皓辰,秦雪征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一、导 言
古语云:“至要莫如教子。”父母的家庭教育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后者也一直是劳动经济学关注的重要话题。不少文献从人力资本跨代传递的角度入手,考虑父母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对子女发展情况(如健康、教育、收入等)的影响(Goode等,2014;Qin等,2016)。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支出及其对孩子人力资本塑造的作用,在经济学中也有相关研究(Mauldin等,2011;Chi和Qian,2016)。除了考察家庭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经济学文献对家庭内部人力资本的产生和积累机制也有关注,比如考察父母对孩子教育投入的时间与精力、父母关于养育孩子的价值观等因素对孩子发展的影响(Zick等,2001;Gniewosz和Noack,2011)。然而,在家庭内部的人力资本生产机制中,有一个因素在经济学中较少被关注,这就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对于父母的教养方式及其对孩子发展的重要作用,心理学和教育学文献有着广泛的研究(徐慧等,2008;Smetana,2017),但这方面的经济学文献尚少。本文旨在填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即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考察教养方式对子女发展的影响。
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发展心理学中的重要话题。最初由Baurmind(1971)提出了这一概念,将教养方式按照其总体特征划分为权威型(authoritative style),专制型(authoritarian style)和溺爱型(permissive style)三种类型,后来Maccoby和Martin(1983)在此基础上,用相互正交的两个维度对教养方式的定义进行了扩展,即“要求”(demandingness)和“反应性”(responsiveness),进而通过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在原有三种类型基础上界定了第四种教养方式类型,即忽视型(rejecting-neglecting style)。其中,要求(demandingness)代表父母是否对孩子的行为建立适当的标准,并且坚持要求孩子去达到这些标准,可以体现为设立常规的任务要求,设立优秀的标准,对孩子日常活动(如睡眠、看电视时间等)的规定和限制;而反应性(responsiveness)则表示父母对孩子接受和爱的程度及对孩子需求的敏感程度,可以体现为鼓励孩子独立的活动,鼓励孩子的语言表达,提出要求时伴随理由和解释以及父母的利益不占统治地位等方面。根据这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我们可以将教养方式划分成四种类型: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以及忽视型。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是高要求与高反应性相结合,父母对孩子的行为有明确的限定,但是在限定范围内又给孩子自主选择的权利,对孩子的接受和鼓励程度较高;专制型的教养方式是高要求与低反应性的结合,父母希望孩子对自己的要求言听计从,无条件强制执行,通过严厉管教来保障要求的实施,缺少对孩子的鼓励和关爱;放纵型或溺爱型的教养方式是低要求与高反应性并存,父母对孩子行为的约束和控制较少,给孩子很大的自主权,同时给予孩子较高的关照和温暖;而忽视型的教养方式则既缺乏对孩子的严格要求和限制,也很少给予孩子必要的鼓励和支持。教养方式类型的划分方法如图1所示。(Lamborn等,1991;Steinberg等,1994)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关注教养方式对孩子发展的影响机制,其中也包括个别的经济学文献。比如在孩子的学业发展方面,Blondal和Adalbjarnardottir(2009)的研究发现,权威型的教养方式下,父母提高参与度有助于降低孩子的辍学率;Feinstein和Symons(1999)通过实证研究说明,父母教养行为是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影响孩子表现的渠道,父母参与程度与孩子的学业成绩正相关;Lizzeri和Siniscalchi(2008)则通过建立经济学理论模型来刻画父母监督下的孩子学习过程,并在父母保护孩子和让孩子试错的权衡中解出最优的教养方法。此外,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是衡量其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在心理健康方面,Dooley和Stewart(2007)基于美国全国青少年追踪调查(NLSCY)数据发现,当加入了父母教养方式变量之后,家庭收入对孩子的情绪-行为表现并没有显著影响,而教养方式则对孩子的表现有显著作用。

图1 父母教养方式四种类型划分的图示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将教养方式与其他影响孩子成长的因素联合起来考察,比如父母的教育水平和家庭的收入水平等。一些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行为是家庭背景影响孩子发展的中介桥梁,不利的经济条件、父母较低的教育水平,可能通过作用于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而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McLeod和Shanahan,1993;Gonzales等,2011)。当然,父母的教养方式也受到孩子行为表现的影响,这一点在心理学文献中得到了较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Kerr等,2012;Moilanen 等,2015)。同时,一些经济学研究,如 Burton 等(2002)用博弈论模型演绎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并对这种双向因果关系进行了验证。
本文试图考察的结果变量是青少年的人力资本。根据现有文献,青少年时期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阶段(Heckman和Kautz,2014)。Heckman和Mosso(2014)搭建了一个家庭内人力资本形成的分析框架。其中,人力资本主要可分为认知能力(cognitive skills)和非认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两个方面(Xiang和Yeaple,2018)。认知能力主要从受教育(schooling)方面的指标表现出来,对于上学期间的青少年来说,文献中多用孩子的学习成绩作为对认知能力的反映(Heckman,1995;Cunha和Heckman,2010)。对于非认知能力,其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如自我控制、信任、社交和情绪等(Heckman 和Rubinstein,2001)。由于抑郁程度反映的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影响了社会情绪(socio-emotional)表现,本文使用国际通行的CES-D抑郁量表来度量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将其作为非认知能力一个方面的代理变量。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用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考察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子女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两方面发展水平的影响。我们用两种方法对教养方式进行衡量,一个是父母在要求和反应性这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值,另一个是在两个维度基础上划分出的四种教养方式类型。我们发现,父母在要求和反应性上的分值越高,其子女的学业成绩越好,尤其是要求维度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则只与父母的反应性得分呈正相关关系,而父母在要求维度的分值增加容易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负向的影响。根据我们的分析,教养方式可能是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我们还分性别和城乡对各分样本进行了回归,发现教养方式的作用在不同性别之间以及城乡之间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
二、数据介绍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构造。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2年和2014年的数据。这项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依次开展了三轮全国范围的入户调查,覆盖中国25个省份,每次调查的样本大约包括15 000个住户,每个样本住户中的各个家庭成员都会成为受访对象进入样本。调查分别在社区层面、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进行,个人层面的问卷又分为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问卷问题涵盖社会经济、人口和健康等多个领域。
关于本文所关注的教养方式,CFPS少儿问卷的少儿自答部分(仅由10到15岁的少儿作答)中有考察父母参与度的教养方式量表,在父母代答部分中也有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问题(Parker等,1979;喻文姗等,2017)。我们将这些问题与心理学文献中关于教养方式的界定方法相结合,从要求(demandingness)和反应性(responsiveness)两个维度,根据心理学主流文献给出的界定,对教养方式的两个维度进行细分,构造能划分教养类型的教养方式量表。
量表中关于“要求”和“反应性”各有5个问题,6个问题出自父母代答部分,4个出自少儿自答部分。①关于问卷问题的具体形式,家长代答部分的例如“您经常要求这个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吗?”“当看电视与孩子学习冲突时,您会经常放弃看您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以免影响其学习吗?”,少儿自答的部分例如“请根据过去12个月的情况,选择你家长对待你的方式:……当你做得不对时,家长会问清楚原因,并与你讨论该怎样做”。“要求”的5个问题反映父母对孩子日常行为规范的标准是否够高,要求和控制是否严格,包括父母对孩子下学期考试平均成绩的期望,以及父母要求孩子完成作业、检查家庭作业、阻止或终止孩子看电视和限制孩子看的电视节目类型的频率。我们将5个问题进行计分处理,以便后续量化。关于下学期平均成绩(满分100分)这个问题,我们根据样本分布特征,将小于70分记为0,往后每10分为一档,100分单独为一档,其值记为1到4。②在3 209个观测值中,期望为100分的就有848个,占到总体的26.4%,因此将此单独作为一档;期望在70分以下的只有73个观测值,因此不再细分。涉及频率的四个问题,由低到高共有5个选项,我们将其赋值为0到4,其中0=从不,1=很少(每月1次),2=有时(每周1次),3=经常(每周2到4次),4=很经常(每周5到7次)。将5个问题所得答案的分值加总,得到反映父母对孩子要求程度的连续变量demandingness,取值范围为0到20。关于“反应性”的问题也有5个,反映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接受程度,对孩子需求的反应程度,具体包括家长做以下几件事的频率: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放弃自己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孩子犯错时问清楚原因并讨论怎样做、鼓励孩子独立思考问题、要求孩子做事时说明原因、喜欢和孩子说话交谈。同样地,频率答案设置均为5个选项,从低到高赋值为0到4,即0=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很经常。将5个问题所得答案的分值加总,得到反应性的得分值responsiveness,取值范围同样为0到20。
我们参考Kristjana和Sigrun(2009)给出的划分方法,根据demandingness和responsiveness这两个分值,得到反映样本父母所属的教养方式的类型(虚拟变量)。具体来说,首先依据2010年,2012年和2014年每年的CFPS截面数据计算出样本父母在demandingness和responsiveness这两个变量上的中位数,然后将得分值小于或等于该中位数的样本划分为低类型,将得分值高于该中位数的样本划分为高类型,最后结合“要求”和“反应性”两个维度的类型给出该父母的教养方式类型(虚拟变量)。由此,高要求和高反应性的父母被划分为权威型(authoritative),高要求和低反应性的划分为专制型(authoritarian),低要求和高反应性为溺爱型(permissive),低要求和低反应性为忽视型(neglecting)。在以教养方式类型为自变量的回归中,我们将专制型教养方式作为基准组,在回归中加入表示另外三种类型的虚拟变量。
关于主要因变量,即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状况,CFPS问卷中也有相关的问题予以衡量。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根据三年问卷中共有的原则,使用父母对孩子的数学成绩和语文成绩的评价这两道问题进行衡量。其中,评价的等级有四个,由低到高赋值为0到3(0=差,1=中,2=良,3=优),再将数学成绩和语文成绩的等级对应的数值相加,得到一个从0到6的离散变量academic,数值越高表示孩子的学习成绩越好。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我们使用CFPS少儿自答问卷中CES-D量表来衡量。CES-D是心理学中广泛使用的抑郁量表,其问题设计贴近日常生活,形象具体,容易得到高质量的回答,能较好地反映受访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具体地,在2010年和2014年的少儿问卷中,各有6个问题考察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都是关于孩子在过去一个月内感到某种负面情绪的频率,①例如“最近1个月,你感到情绪沮丧、郁闷、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振奋的频率”,“最近1个月,你感到坐卧不安、难以保持平静的频率”。每个题设置5个选项,我们将频率由高到低赋值为0到4,其中0=几乎每天,1=每周两三次,2=每月两三次,3=每月一次,4=从不。将6个题的分值加总,得到反映孩子心理健康的指标cesd,是一个从0到24的虚拟变量,取值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在2012年的少儿问卷中,CES-D问卷的呈现形式有所不同,共有20个问题,问孩子在过去一周内某种感受或行为出现的频率,其中4个问题针对积极情绪,16个问题针对消极情绪。每个题设置4个选项,赋值为0到4,对于消极情绪的部分,赋值为0=大多数时候有(5−7天),1=经常有(3−4 天),2=有些时候(1−2 天),3=几乎没有(不到一天);对于积极情绪的部分,赋值方式相反,0=几乎没有(不到一天),1=有些时候(1−2天),2=经常有(3−4天),3=大多数时候有(5−7天)。将20个题的得分加总,得到一个从0到60的连续变量cesd_2012,数值越高代表孩子的心理健康程度越好。为了便于对三年数据中的CES-D指标进行统一,我们在每年的截面数据中取CES-D的百分位数值cesd_pctile。一个样本对应的CES-D百分位数值就是具有这个数值和小于这个数值的样本数量占当年截面数据中总样本数量②这里的当年截面数据内总样本数量指的是经过我们样本选取之后的样本数量,而非整个调查数据库中的样本总数,后面将详细介绍样本选取的过程。的百分比,这个数越大表明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比同年样本中的其他个体相对更好。
我们将样本限制在10到15岁的青少年,因为只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做少儿自答问卷,而教养方式和心理健康情况的度量都离不开少儿自答问卷中的信息。另外,由于所用数据横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三年,10到15岁的样本流失比较严重,为了保证样本尽量大,将这三年的数据合并使用,形成混合截面数据。同时,将在关键变量如教养方式指标、学习成绩、CES-D指标等有信息缺失的样本去掉,最终得到3 209个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该样本覆盖全国26个省份。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首先,按照上文所属的划分方法,我们得到四种教养方式类型在各年份截面数据中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四种教养方式在各年份数据中的分布结构大致均衡,权威型和忽视型的占比各在30%左右,而专制型和溺爱型的占比在20%上下。

表1 四种教养方式类型在各年份截面数据中的分布情况
除了上文提到的核心变量(教养方式,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之外,我们还控制了反映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的变量,以及性别、年龄、城乡和区域等基本的控制变量。其中,我们用家庭年收入考察家庭的经济条件,这个家庭年收入的计算经过CFPS项目组调整,在三年的截面数据之间是可比的(具体的调整办法见许琪和张春泥(2017)),将此收入取对数,作为反映家庭经济条件的指标。关于父母的教育程度,我们采用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来度量。这样,就有了ln_income,fatheredu,motheredu这三个反映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的变量。此外,在后面的回归中还用到了如下控制变量:孩子的性别male(男性为1,女性为0)、孩子的年龄child_age、父母双方的年龄father_age、mother_age、家里的孩子个数n_child,以及表示城乡的虚拟变量urban(在城市为1,在乡村为0)、表示区域的虚拟变量east(中国东部地区为1,其他地区为0)和west(中国西部地区为1,其他地区为 0)。
考察四种教养方式下因变量的特征,我们发现权威型教养方式下孩子的平均学习成绩评价值为3.88,心理健康指标的平均百分位数值为42.29,均高于另外三种教养方式。而溺爱型教养方式下孩子两方面表现的均值分别为3.64和41.12,高于专制型和忽视型。此外,就学习成绩而言,忽视型教养方式下平均的学习成绩最差,值为3.01;而就心理健康而言,也是忽视型教养方式产生的结果最差,平均的CES-D百分位数值只有37.48。
此外,我们考察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相关的变量与教养方式可能的相关性。就收入而言,忽视型样本组的平均收入水平稍低,收入的对数值为9.92;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中,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受教育程度略高于另外三种,分别为平均10.81年和10.01年,而忽视型教养方式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则在四种类型中最低,平均为9.92年和8.17年。
三、回归方法
(一)基准回归模型。
1. 以学习成绩作为因变量。在学习成绩作为因变量时,我们使用如下的OLS模型作为基准回归的模型:

其中,academic表示孩子的真实学习成绩。PS表示父母的教养方式,分别用“要求-反应性”两个维度的连续变量以及“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忽视型”四种类型的虚拟变量表示。SES代表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家庭年收入的对数和父母的受教育年限等变量。X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城乡、区域信息以及年份虚拟变量。
同时,考虑到学习成绩变量academic是一个从0到6的离散排序变量,而OLS将排序视作基数来处理,可能导致估计的偏差,因此,我们还使用了排序响应回归这一非线性模型进行最大似然估计(MLE),将其作为对OLS结果的稳健性检验。①具体地,在Ordered Probit模型中,我们构造一个连续的潜变量academic*,令其为各个自变量的线性函数,并根据其取值在不同区间的概率得出实际因变量academic取不同数值的概率,从而进行极大似然估计。
2. 以心理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对于心理健康指标,我们使用的是CES-D数值在当年截面数据中的百分位数,这是一个连续的变量,其取值在0到100之间。我们在基准回归中也使用OLS模型进行估计:

其中,PS为教养方式变量,SES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X为其他控制变量,这些变量的定义方式与上述相应回归模型相同。此外,考虑到会有一部分样本个体的取值都为100,对应的是在问卷回答中心理健康状况最好的样本,也就是数据的分布会在区间的上限100处有一个集聚。对于这样的数据特征,我们也依据文献惯例,使用Tobit模型估计作为对OLS结果的稳健性检验。②具体地,在Tobit模型中,我们分别针对cesd_pctile=100和cesd_pctile < 100两种情形写出样本观测点的概率密度函数(为各个自变量的函数),从而构造样本似然函数并进行极大似然估计。
(二)工具变量回归。以上模型均假定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外生的,但实际上相应的回归可能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这种内生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一些不可观测的变量(家风、基因遗传、能力等)可能同时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孩子的表现;二是孩子的发展水平和行为表现也会促使父母对教养方式进行调整,从而导致反向因果问题,而这一点已经在心理学和经济学界得到广泛认同(Burton等,2002;Kerr等,2012;Moilanen 等,2015)。
为了解决上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受访者所在社区(或村落,以下统称社区)的教养方式特征作为工具变量(IV)。具体来讲,考虑到教养方式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地域性的特征,即同一地区的教育文化很可能表现出一定的共同性,同一社区或村落里不同家庭的教养方式也有其相似之处,因此个体父母的教养方式往往受到社区共同教养方式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其他家庭父母的教养方式一般不会直接影响本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③同时,我们也尝试了其他的模型设定方法,包括在工具变量中加入c_demandingness×c_reponsiveness这个交叉项或加入c_demandingness2和c_reponsiveness2这两个二次项形成过度识别的模型,其回归结果与我们展示在后文表5中恰好识别的回归结果类似。基于此过度识别模型,我们进行了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原假设为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检验得到的p值都大于0.1,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假定。这种教养方式在地域上的集聚性被心理学界的大量研究所证实,例如Dwairy等(2006)就用在阿拉伯的青少年调查数据说明教养方式特征在各个地域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Valentino等(2012)也从虐待儿童的视角研究了社区层面的特征与教养方式的关联。由此,我们在要求demandingness和反应性responsiveness两个维度上取社区层面平均值,得到反映社区教养方式特征的两个变量c_demandingness和c_responsiveness。其公式为:

其中,i和j表示个体,c表示社区,t表示年份,nct代表t年份的数据中c社区内的个体数量。即个体所居住的外在社区教养方式的要求程度,就是在当年截面数据中,个体所在社区内排除该个体之外的所有样本的要求程度的算术平均,反应性平均值的计算方法类似。为保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在社区层面计算平均时,我们将个体本身的情况排除在外。
由于前面的基准回归使用的都是OLS模型,使用工具变量时,为便于与基准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我们使用2SLS模型进行估计。在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中,①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在正文中用表格汇报一阶段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电邮:zhanghc@pku.edu.cn。对工具变量联合显著性检验的F值都大于10,表明此处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Stock和Yogo,2002)。
四、结果与讨论
(一)主要回归结果。
1. 教养方式对学习成绩的影响。首先关注将学习成绩作为因变量的基准回归,这部分结果呈现在表2列(1)至列(4)中。在前两列回归中,我们将demandingness和responsiveness两个连续变量作为核心自变量,表示父母教养方式要求和反应性的程度大小。在第(1)列,只加入demandingness和responsiveness两个变量和反映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的三个变量,发现要求程度和反应性程度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第(2)列,我们又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随着控制因素的增多,demandingness和responsiveness的系数绝对值有所减小,但依然保持高度的统计显著性,体现了结果的稳健性。在控制父母社会经济条件及其他控制变量后,demandingness每提高1分,孩子学习成绩academic的数值平均会上升0.039,父母的要求程度每提高1个标准差,孩子的学习成绩将提高约0.08个标准差;类似地,反应性程度每提高1个标准差,孩子的学习成绩提高约0.13个标准差。这说明,父母对孩子设置更高的要求,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怀,都对孩子学习成绩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表2 教养方式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在表2的最后两列中,我们汇报了使用前面所述的工具变量方法控制内生性之后的回归结果。这时,反应性程度responsiveness的作用不再显著,而要求程度demandingness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与我们在基准回归中得到的结果有所不同,即考虑教养方式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时,父母对孩子要求的严格程度是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
2. 教养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下,我们考察将孩子的心理健康指标(即孩子的CESD数值在当年截面数据中的百分位)作为因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呈现在表3中。
在表3的列(1)、列(2)中我们加入demandingness和responsiveness两个变量来表示父母的教养方式,其他变量添加和模型设定方法与表2的前两列相同。我们发现,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而言,要求程度的作用不再显著,即设置更高的要求可能并不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而此时,反应性的系数则显著为正。其他条件不变时,反应性程度的值每提高1分,其对应的CES-D百分位数值上升大约0.37个百分点。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反应性的系数有所减小,但依然保持统计显著性。这表示,父母对孩子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反应有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而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与父母要求的严格程度无关。
与表2类似,在表3的(3)、(4)列中,我们将表示教养方式类型的虚拟变量authoritative,permissive和neglecting作为核心自变量加入回归,将专制型作为基准组。这时我们发现,就孩子的心理健康而言,权威型和溺爱型的教养方式都显著优于专制型的教养方式,而忽视型的教养方式则与专制型的教养方式无显著差异。从边际效应上看,与专制型的父母相比,在权威型和溺爱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的心理健康CES-D的百分位数值平均要高出超过3个百分点。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在表3列(1)至列(3)的结果分析中得到的结论,即反应性responsiveness这个维度是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父母给予孩子更多关照,对孩子的表现做出更积极的反应,能够有效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①此外,我们也在基准回归中对前面模型设定部分提到的非线性模型(Ordered Probit和Tobit模型)进行了尝试,所得的结果与我们用OLS得到的结果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上基本一致。由于篇幅所限,这部分结果不在正文中汇报,有兴趣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在表3的最后两列中,我们汇报了工具变量2SLS回归结果。一方面,responsiveness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另一方面,demandingness的系数显著为负,也就是说,家长对孩子要求越严格,可能越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发现专制型(高要求、低反应性)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其心理健康表现显著低于高反应性的权威型和溺爱型,也就是孩子的心理健康与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内生性后依然稳健。
(二)分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1. 根据性别划分子样本。考虑到男孩和女孩在面对的教养方式以及行为表现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我们以性别为依据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教养方式的作用机制在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异性。为便于比较,所使用的模型与基准回归中的设定相同。相应结果呈现在表4中。

表4 以性别为依据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在表4的列(1)至列(4)中,我们考察以学习成绩为因变量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其中,前两列以demandingness和responsiveness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第(3)、(4)列以教养方式类型的虚拟变量authoritative,permissive和neglecting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所有的回归中都加入了反映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的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第(1)列和第(3)列是男孩的样本,第(2)列和第(4)列是女孩的样本。第(1)列的结果显示,对于男孩来说,要求程度和反应程度都与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要使男孩学习成绩好,既需要较强的控制,也需要较多的关怀。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权威型、专制型和溺爱型三者没有显著差别,只有要求和反应性都低的忽视型导致的学习成绩显著低于另外三种。而对于女孩的样本,结论则不尽相同。要求和反应性两个维度之中,只有表示反应性的responsiveness显著为正,即女孩学习成绩的好坏和家长对孩子要求的严格程度关系不大,而主要与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和反应程度相关。在第(4)列的结果中,我们发现专制型和忽视型对于女孩的学习成绩的影响无显著差别,而权威型和溺爱型这两种高反应性的教养方式类型所对应学习成绩显著高于低反应性的两种类型。这与第(2)列的结果一致。
以心理健康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呈现在表4的后四列中。可以发现,不论男孩女孩,其心理健康都与教养方式的要求程度没有显著关系,而与反应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系数和显著性上来看,这一关系对于男孩更强,对于女孩则相对较弱,特别是在第(8)列的回归中,不同教养方式下的女孩在心理健康表现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别。而对于男孩,则遵循了基准回归结果中的模式,即更多的关心和反应有利于促进男孩的心理健康发展。
2. 根据城乡划分子样本。考虑到我国城乡家庭在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特征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城市和乡村地区教养方式及其影响也可能有所不同,我们根据CFPS划分城乡虚拟变量urban(1=城市,0=乡村)进行分样本回归。这部分回归结果呈现在表5中。

表5 以城乡为依据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在表5的列(1)至列(4)中,我们发现对于城市家庭而言,学习成绩与要求程度demandingness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与反应性程度responsiveness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第(3)列中,权威型和溺爱型的教养方式下,孩子的学习成绩显著优于专制型和忽视型。而在农村,要求和反应两个维度均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四种教养方式的比较中,权威型最优,忽视型最差,专制型和溺爱型居中。这样的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在教育质量上的差异:在城市,中小学的教学质量较高,学校对孩子的学习习惯和内容已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程度不再发挥显著作用,而父母对孩子的关照和反应则发挥着更强的作用;在农村情况则有所不同,孩子的学习成绩提高需要父母的关心和反应的同时,也需要父母提出较为严格的要求,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而就心理健康而言,后四列的结果也显示城乡存在较大差别。城市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相似,即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反应性程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而言,权威型和溺爱型优于另外两种教养方式类型。在乡村,我们发现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的影响。可能由于农村家长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重视普遍不够,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较少,对孩子的关照和反应相比于城市更少,故而没有通过教养方式的提升来促进孩子心理健康的发展。
从整个分样本回归的结果来看,教养方式对男孩的效果要强于女孩,在城市的作用效果要强于农村,这也反映出女孩群体及农村家庭等弱势群体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相关政策需要加强对其父母教育方式和观念的培养和重视,以缩小青少年的人力资本发展在性别和城乡上的不平等。
五、结 论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教养方式这一新的视角,探索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在家庭内部的形成机制。我们将心理学和教育学中研究较为广泛的教养方式这一因素纳入青少年人力资本形成的研究框架,探索教养方式在“要求”和“反应性”这两个维度上的差异,据此区分出的不同教养方式类型,并将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这两个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作为因变量,考察教养方式对其产生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三年的混合截面数据,我们的研究得到了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和反应性程度都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能带来最好的学习成绩,溺爱型和专制型次之,忽视型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最为不利。同时,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有显著影响,反应性程度与孩子的心理健康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要求的严格程度可能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权威型和溺爱型下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专制型和忽视型。这说明,父母一方面要加强对孩子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孩子的关爱和反应。在中国“望子成龙”、从严治家的文化背景下,我国父母往往更加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从而在教养方式的选择上可能对子女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分性别和城乡的子样本回归结果展示出一系列能反映中国国情、具有特殊意义的结论。教养方式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影响在不同性别群体和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该影响在男孩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要求和反应性这两个维度的指标都对男孩群体有显著作用;对于女孩而言,则只有反应性对其学习和心理健康发挥显著作用。从城乡差异来看,农村家庭的孩子其学业成绩受到父母要求和反应性的共同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城市青少年样本的学业成绩则只受到父母反应性的影响。在心理健康的发展方面,只有城市家庭的子女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显著影响。经过前文的分析,这些差别可能与城乡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教育发达程度有关。
据此,我们建议:在学校教育之外,要更加重视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加强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宣传和培养,在整个社会传播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建设积极和睦的家风,通过家庭教育的改善,支持青少年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质量的提高;要加强家校共建,促进家庭和学校之间的信息沟通,使父母了解孩子的情况,从而科学地设置要求,适度地给予反应;要从家庭教育层面努力改善我国教育的城乡不平等现象,加强对留守儿童以及农村地区青少年的关注和培育,提高乡村地区教育教学质量,同时更多关注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提高农村地区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关注,使得父母的教养方式和质量能随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而有所改善,进而缩小城乡教育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