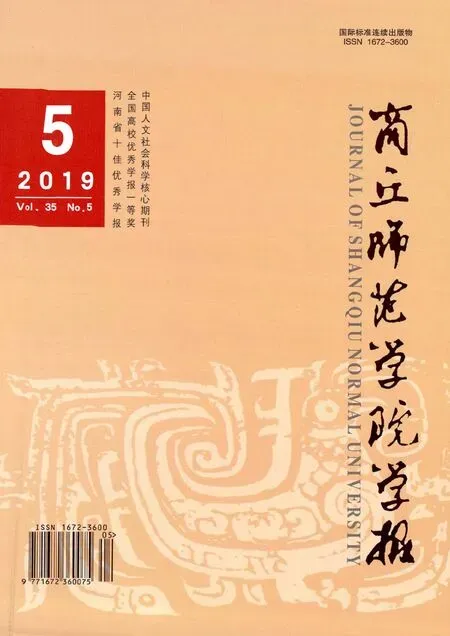论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
崔 雅 琼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200042)
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是法国人设立的,是用于审理法租界内以华人为被告的案件的类司法机构。与法租界会审公廨相似的还有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只不过学术界关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已有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反观对与公共租界处于同样重要地位的法租界会审公廨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缺少细致、完整的学术成果。
关于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的成立时间,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一些可查的文献资料上记载了法公廨第一次开庭审判案件的时间是1869年4月13日[1]417。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法公廨成立的时间在该日期之前,且早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成立①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是英、美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设立的审理发生在公共租界范围内华人为被告的案件的具有司法性质的机构,它成立于1869年4月20日。。法公廨又称法公堂,与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不同的是,法公廨是法国人于法租界内私自设立的,并未经过中国官府的同意。因此,法公廨严格来说是不应被承认的,相应的其所作出的判决也没有法律效力②对于这一点,法方则引用其与中国订立的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辩称,依照此条款的规定,列国对中国取得的权利,法国也当然享有,并将其作为法公廨设立的依据,以及反驳法公廨无法律地位,判决无效的理由。然而,法国人仅适用最惠国条款中有利于自己的规定,对于列国对中国所负的义务,则不予接受。参见[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页。。然而,中国当政者过于软弱,默认了法公廨的设立,同时还派遣中方人员参与法公廨的审判。法公廨成立之初,仅由法国总领事达伯理与上海道台③上海道台,又有“上海道”或者“沪道”的叫法,它的正式称谓是“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从正式称谓中可看到它的职能范围包括苏州、松江、太仓地区,因此仅从管辖区域来看,也可看出沪道处于高于上海县、松江府,低于江苏省的行政级别。管理上述地区的行政事务及军队。由于松江港口位置越来越重要,自1730年起,苏松太兵备道的府衙由苏州迁往上海,自此被称为沪道,并一直沿用下来。杜文澜达成协议,约定法公廨的审判组成,由道台派委员一人,与法国副领事组成。中方委员为主审官,法副领事为陪审官,在法领署内共同审理华洋诉讼案件,每周开庭三次[1]418。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法公廨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最晚于1869年4月已成立,且法公廨还早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成立,并不是巧合,而是有其原因的。这是因为公共租界一直有联合行政的意图,而法租界因小刀会起义引起的战乱,为了自保曾与公共租界组成过统一的市政组织[注]1854年7月5日,英、法、美三国领事共同签署了新地皮章程,章程在“租地人会议”中通过,并正式成立了统一的市政机构——工部局。1862年4月29日,法租界公董局成立,标志着对工部局的正式脱离。法租界公董局是上海法租界内的最高行政组织和领导机构。在成立之初,曾仿照英租界内工部局的模式,实行“自治”,但是不久便被法国官方推翻,最终形成了领事具有行政决定权,是公董局最高领导的格局。。但是这些只是法租界的权宜之计,法国公使以及驻沪法领事更倾向于保持法租界的独立性。因此,在退出联合市政组织之后,法国人不可能再以任何形式参与公共租界。同样当英、美领事于1868年同中方代表签订解决租界内和租界外纠纷的办法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时,法方并无代表在上面签字[注]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于1868年12月28日共同议定《上海洋泾浜会审章程》,1869年1月《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颁布,法国驻沪总领事最后以《章程》第5条“中国人犯逃往租界中不须县票、洋拘捕,直接由委员选差径提”的规定,和第10条中“如果原告是诬告,则无论华洋,由委员依照章程处罚诬告之人”的规定,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以及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的内容相违背,以及与上海法租界内华官逮捕华人人犯,需经法领同意的司法惯例不同为由,拒绝接受章程的约束,虽然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要维护法租界司法的独立,不被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左右。。为了保证法租界行政、司法的绝对独立,法国人在公共租界设立会审公廨之前,已早一步设立自己的会审公廨。
由于法公廨成立过于仓促,并没有制定会审流程之类的文件。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公廨受理案件的范围都是遵循《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中的规定。这一点在1905年11月9日法国总领事的一篇机密性报告中也得到证实,报告中称:“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缺乏任何一般性的章程和任何中法两国间的协定。……章程的缺乏使法租界会审公廨只得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之后尘。”[2]23
一、法公廨会审办法
法公廨制定的自己的会审办法,同法公廨成立的时间一样,由于资料的缺乏,无法得知其制定的具体日期。目前最早记载法租界会审公廨的会审办法是在1914年5月9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报纸记载了法租界会审公廨的管辖范围、设立依据、诉讼办法、拘留、上诉等内容[3]。
(一)法公廨的审判组成与管辖
法公廨中的任何案件均由中法双方各派一位审判人员共同审理。法方审判人员通常为法领事署内的翻译官,中方审判人员为地方官委派的代表(清季由沪道委任,民国成立后,由江苏都督委任)。在审判的座次上,中方审判员居上,坐在法方审判员的左侧,这样的法庭组成及位次一直维持至法公廨解散。法公廨的管辖范围起初规定为“凡华洋诉讼,以及华人之间的民刑诉讼,均由中国委员会同法国领事审讯”[4]。但是这一规定过于泛泛,1902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因案件的管辖问题,发生了两公廨的权限之争。之后经领事团商议,制定了《上海租界权限章程》。依据章程的规定,法公廨的管辖范围确定为:民事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均为华人,且被告居住在法租界内的;或者原告为法国国籍,被告为华人,无论居住在何处,均归法公廨管辖。刑事案件的管辖以行为地为准,如果原被两造均居住于华界,而在法租界内犯罪的,由法公廨管辖;如果是居住在租界,但是犯罪行为发生在华界,除了原告为法国国籍外,由中国官府管辖[5]51-52。
(二)案件的起诉、适用的法律及执行
民事案件中,原告需在法领署检察处购买正副状纸各一张,并交予检察处核收,检察处法方收缴诉讼费后,开立收据给原告,并负责派发开庭日期的传票。普通的民事案件,一般于具状后两至四星期开审,如果是原告希望快速传讯的案件,则需要再缴纳15元的排前堂期费,即可提前审理;刑事案件中,大部分案件的原告先报告给巡捕房,由法捕房起诉,如果原告为华人、被告为法国人,则向法领事署起诉[6]2,5,7。
对于法公廨中适用的法律,规定为如果被告为中国人,则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办理[7]292。然而在实践中,法国人曾一度以中国无《民法》为由,适用法国民法的规定审理案件。比如,1905年,法会审公廨审理的伪造罪,以及伪造货币罪即是援用的法国法律[8]。显然,适用法国法律审理民事案件已被当作公廨中的司法惯例,因为中方在颁布了新民法草案之后,法国人仍旧依照法国民法审理公廨中的民事案件。对于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与民事案件法律适用情况基本相同。对此,我国法学家伍廷芳在针对会审公廨的奏折中称:“如果华人被控犯罪,理应由华官依照个别情形及以往的判例,加以量刑。但是现在外国领事只以本人的见解,而不考虑中国法律及判例,去判决诉讼案件。这种本质不正常的判决日愈增加。因此使租界的华籍商人和居民根本不知受何种法律所统治。”[2]26可见,由于租界司法被外人掌控,即使有中外双方制定的章程、规则,也是一纸空文,如何履行全由外人决定。
在公廨中,案件的执行颇具现代法制的色彩。民事案件主要是金钱给付为主。值得一提的是,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为了保障审理的正常进行,亦采用了中国传统司法中对证人的规定,即对民事被告人和证人均适用拘留措施,拘留之所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总捕房。如果被告可以缴纳保证金或者提供保证人,则不必拘留于捕房。刑事案件中未结案的,分别拘押于各捕房。已结案的,男犯于卢家湾捕房收押,女犯则于捕房女所收押。公廨内执行的刑罚种类分为两个阶段:在1906年之前,公廨内的主刑仍沿袭清朝时期的刑罚,主要有笞杖、枷号、监禁和罚款;1906年以后,停止笞杖之刑,但是枷号仍然沿用。直至1914年,经驻沪法领事同意,将枷号和同跪审一并废除[1]420。
审判环节中,还有法公廨关于聘请律师的规定。法公廨中的律师首先要得到法租界行政当局的承认,并且要精通法语,方可承办案件。以致长期以来,法公廨中的律师只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担任[6]6。法公廨中,还对民、刑案件聘请律师的标准作了限制性的规定,即民事案件标的额需要在1000两以上,才可以延请律师,刑事案件不得延请律师。[3]与公共租界中任何案件都可以聘请律师的规定不同。
(三)法公廨中的上诉
法公廨在清朝时期仅简单的规定以沪道为上诉机关,即遇有不服公廨判决的案件,则由道台会同法总领事审讯,然而并没有具体的上诉办法。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原会审公廨中的中方谳员[注]谳员又称“会审员”,或者“华洋同知”,简单的理解就是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他们是司法领域中较为特殊的称谓,因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的成立而出现,因会审公廨的撤销而消失。因此,这一称谓存在时间是从1869年到1927年,近六十年。逃走,法公廨完全落入了法国人的手中。由法国领事重新任命会审官,并将会审公廨归入公董局管辖范围,将廨内的收支均纳入公董局的预算范围,由公董局负责支付廨员的薪俸和经费等[9]142。这一时期,法租界内仅有会审公廨,并无相应的上诉机关,甚至到民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于是公廨内的案件无法上诉。对于这种情况,中方委员与法领事商议,并达成如果有上诉的案件,则将公廨的判决停止执行,等上诉机关成立,再继续审理的共识[10]420。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出现因案件当事人不服案件的判决,需要上诉而停止判决执行的情况。尤其是刑事案件中,即使是被判处死刑,也仅是交由法领事核准,即执行[10]149。在此需要补充的是,法公廨刑事案件审理权限在最初适用《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中规定的,华人犯重罪者交由华界官府审办。1905年,领事团又通过《续增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将公廨的审判权限扩大至5年[10]139。之后,外人又以上海地方官府“不能按照定章办理,以致稽押甚多,窒碍尤深”为借口[11]38,擅自将审判权限扩大至所有刑罚,包括可以判决死刑。会审公廨无论是判决死刑,还是额度较大的民事判决,均为一审终审。“公廨居然成为最高级之法庭矣……除北京大理院以外,他种法庭,殆无其匹。”[12]9如此审判规定,除了再一次证实法公廨已完全由法国人掌控之外,也反映了司法的荒诞。
这种无上诉审级的情形一直持续至1921年年初,之后法领事以布告的形式规定了类似上诉的条件、期限等。之所以说是类似上诉,是因为严格来说这些内容不属于上诉审级的条件。首先是因为没有设立高于法公廨的上诉机关,在上诉的章程中,仍是由原会审公廨承办上诉案件,只不过由非原审法官组成审判庭。其次,并不是以不服案件判决,作为民、刑案件上诉的原因,而是要符合以下条件:1.越出公堂定章范围,在判决前或者判决时未经原被告同意认可的;2.判决内宣布未请求的事项,或有越出申请事项之外的,甚至有遗漏紧要关键的内容,以及对于同一要点,两造均不服的;3.判决中有抵触、错误,或理由不充分的;4.判决时已承认的证据,在判决后发现是伪造的;5.判决后发现有新证据的;6.判决中对事实或法律有误认的,才能向会审公廨提出复讯。刑事案件中,除了盗犯、杀人犯外,对其他刑事案件的判决不服者,均可请求上诉[6]15-16。其三,是否开庭受理,要经承审官于会商室查核理由后决定,如果核准,则将开庭日期照常通知原被告。上诉期为判决后的14天之内。综合上述理由,与一般意义上的上诉并不相同,反而更接近现代法制中对已生效的判决的复核和再审的规定。此外,上诉规定中虽然将案件交由原审法官之外的审判人员受理,但是仍是由公廨负责,并没有真正的超出原审范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上诉审中因法官之间互相包庇而导致案件的不公正审判。
尽管在上诉章程中进一步规定,上诉之后,中法法官意见不一致时,则通过外交办法解决。这种看似高于原审级的处理方式,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种方式明显缺乏可行性,即使真的有交由外交处理的案件,容易出现造成案件久拖不决的情况;二是这种方式是无视我国法权,凌驾于我国法权之上的行为,因为无论是从属地原则还是属人原则上,都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法公廨中虽然作出了如何进入二审或者类似上诉的规定,但是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二、会审公廨更像是法国人的另一个领事法庭
会审公廨虽有会审办法,但是在会审过程中,却很少依照中法双方的约定办理案件。案件的审判处处以法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些问题的解决多是依照领事法庭的规定处理,法租界会审公廨更像是法国在上海的另一个领事法庭,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会审过程中法律的适用问题。对于租界内的民商案件,法租界以中国无相关成文法为由而适用法国法律,刑事案件则适用我国颁布的《暂行新刑律》。而在实践中,案件的审理多以法国法律为主,即使是在我国民商法已经公布之后,法公廨仍依照原有的办法审理案件[8]。
第二,法公廨中逮捕权归法国人支配。会审公廨设立之初,提传罪犯由公董局下的巡捕房和中方的会捕局共同执行,当时的会捕局是由镇压太平天国之乱时的会防局发展而来,会捕局中共有绿勇10余人,供中方谳员支派。但是到了1896年,沪道裁撤了会捕局,致使法公廨中中方谳员无吏役可派,逮捕和提传犯人的权力全部落入法租界巡捕房的手中[9]45。
第三,法领事享有案件的最终决定权。在遇有中法双方审判官有争议的案件,依照法国人的意见处理。无论是华洋混合案件,还是纯粹的华人案件,法领掌握案件的最终决定权。造成如此格局的主要原因是中方审判人员无捕役可派,“捕房西人一依西文之判决单执行,曰释则释,曰拘则拘,若华文判单与西文判单绝对不同,则检察员询问原审判官有无错误。如果原审官却与副领意见不同,则副领不签字,而判决文亦终无效矣”[12]8。例如,1902年6月,在法租界的牢房里关押一名因过失致人死亡的中国罪犯,依照当时的规定,本应送往中方的官府审讯,但是时任驻沪总领事拉达认为将他送往华界审判,害怕受到严重惩罚,所以因为怜悯决定不把他移送至知县处[2]25。领事对法租界内案件的裁判权力早已超出了会审办法的规定。
第四,只能聘请通达法语的律师。法公廨更像是法国的领事法庭还体现在延请律师的规定上。法廨中律师资格的取得无需执照,法官有自由指定律师出庭的权力,在法公廨的诉讼过程中,聘请的律师必须通达法语,否则不能代理诉讼,即使是纯粹的华人之间的案件也要遵守其规定。因此很长时间以来,法廨内的律师除了法国和意大利人充当外,没有出现其他国家的公民。在中国的土地上,以掌握外文为供职的必要条件,这种严重侵犯国家主权的规定,足以证明法国人已将上海法租界当作自己的殖民地。
综合以上四点,法租界会审公廨虽名为会审,实则早已是法国人的一言堂。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人在法廨内诉讼,尤其是与外人之间的诉讼,其利益很难得到保障。
法租界司法权俨然已掌握在法国人手中,法国人在上海法租界中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犯程度是所有租界之最。形成这样的情形与晚清政府的懦弱、国力的衰败以及动荡的社会局势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法国人在中国奉行的政治策略有关。这一点在前文的论述中,以及一些法国官方往来的信函中都可以体现出来,法国人十分重视法租界的独立性,无论在行政管理方面,还是司法方面,都采取很多的措施以防止与其毗邻的公共租界以及华界的干预。这是因为一方面上海的经济因其作为通商口岸以及地理位置的优越等因素而得到快速的发展,外人更重视其在上海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是因战乱而导致华洋杂居格局的形成,使外人开始重视对租界政权的掌控,在经济、行政都被外人掌控时,他们不可能无视司法权力,因此外人对租界司法主权的完全侵占是这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法租界会审公廨之两重性
辛亥革命前后,法租界会审公廨已由一个中法会审法庭,转变成一个十足的法国法庭。法国人曾以中国法律不够完备、民刑不分、刑罚苛酷、狱吏腐败为由,阻止中国官府插手租界事务。但是通过对法人在租界司法的研究,他们也并没有做到依法讯断、公正审判。比如,法公廨中担任审判官的法国人多为领事署里的翻译官,这些人大部分缺少法律知识,断案全凭自己的喜好进行。并且法公廨中对延请律师是严格限制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是完全由这些不懂法的人在审理案件,特别是在遇到涉及法国人的案件,很难保障法国审判人员不向着法国人当事人一方倾斜,中国人的利益在此种情况下处于无任何保障的状态。
尽管如此,会审公廨的存在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是我国传统司法向现代法治过渡的重要媒介[13]4。国人在这个外人管控的区域内,最先接触先进的司法制度,并在潜移默化中具有了现代法律意识,为在传统法制为主的社会关系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具有现代法制特征的诉讼程序。法公廨内专设检察处,负责收受状词等事。如在民事案件中收取诉讼费之后,开立收据,并安排案件审判的日期。检察处内有承发吏6人,由华人探员充任,负责传达人证、发封房产、调查证据、照验保单等差事。刑事案件分为公诉和自诉案件,公诉案件由法捕房向公廨提起诉讼,自诉案件中原告向检察处递交诉状起诉。很明显,检察处的分配职能与传统中的受理案件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体现了现代法制中案件起诉、受理、分配的特征。此外,审判过程中取消了传统法制中跪审的模式,法庭布置上也出现了具有现代法制特点的被告席和原告席、律师席、法捕房录事,以及华人和西人旁听席,是一个近似现代庭审的法庭模式。
第二,注重对物证、非言词证据的利用和收集。公廨审判中,已经开始重视将人证以外的其他证据作为判决的依据。例如,1922年6月,法公廨受理了一起法租界自来水公司诉大发公司的案件。案件审理过程中,大发公司多次依据两方签订的合同中的条文,来证明自己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并且由法捕房作证(捕房派人监督被告数日,也未发现有违约情形)等证据,对抗原告[14]。在申请上诉的规定中,也有要求将相关的证据交由审判官查验等语。
第三,废除刑讯,慎用肉刑。中国传统法制中,刑讯是必要且合法的审判方式,刑讯的工具有竹板、荆条、夹棍、拶指等。清朝时期延用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此外,清律中还规定了阉割、刺面、刺臂等刑。审案的官吏还经常超出法律规定的讯拷范围,使用法外的酷刑对当事人、证人等进行严刑逼供。历代也不乏酷吏滥用刑讯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实例。对此,外人持反对的态度,同时一直将刑讯作为他们干预中国司法的借口。公廨成立初期,除了审理“发落枷杖以下罪名”以外,还有打手心、打板子、罚金等惩罚种类。1906年,清廷针对租界会审公廨审理刑事案件中适用的刑罚制定《议奏奏审公堂刑章改订》,规定在适用笞杖刑罚时,可以并处罚金,规定了最高可杖100、罚钱15两的刑罚等级[15]175。由于法国已废除肉刑,所以公廨中对于这类刑罚,选择慎用和少用。只有当被告人使用凶器伤人,或者殴伤老、妇、幼时,才会选择适用笞杖之刑来惩处,对于大部分案件,则适用罚金或者关押等方式代替[10]146。之后,会审公廨中对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和证人的讯问不再伴随刑具、刑罚,甚至在刑事案件中也很少使用刑讯的方式。传统法制中的跪审、佩戴枷号听审也被取消。虽然此种裁判方式不符合当时中国法律的规定,但是更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了法制的先进性。
第四,律师制度的引入。中国传统法制中,将律师称为讼师,民间以及官方都十分鄙夷讼师这一职业群体,并且将他们称为“讼棍”,案件审理中如果出现讼师被视为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注]比如1892年,上海县官府还张贴“禁止匪棍包打官司”的告示,可见即使当时的上海已经作为通商口岸近50年,但是传统的思想观念,仍然在国民心中占据主要位置。参见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2页。。当然,讼师和律师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中国的讼师主要代人写诉状、并不以出庭为必要条件。讼师还不具备法律知识,而是多由涉案者的亲属担任。官司结束后,就不再以讼师的身份出现。而这些特征,与我们所说的律师有很大的不同。1869年的会审公廨中,虽然对担任律师的条件作了限制,甚至被法国人操控的公廨中,仅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充当律师,但是应该肯定的是,律师的出现,正在逐步地改变传统审判程序,为现代法制的传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除了更接近现代法制之外,法公廨中关于移交政治犯的规定,也为一些革命人士提供了保护。法公廨成立之初,对于租界内政治犯是从不移交华界官府的。1914年,法租界为了实现扩界,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关于移提界内政治犯的条约,但仍不可随意抓捕、移交,仍要符合一些前提条件。首先,对于“租界内的人民,中国官府不得无故的指为内乱犯;其次,对于内乱犯的审理仍须领事会审,倘证据不足,仍立时取消”[9]141。1916年,袁世凯去世,党禁解除,法租界的政治环境更为宽松。只要不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政府的活动,法租界行政当局多是以放任的态度对待,不对其进行过多的干涉。比如,1921年至1922年期间,居住法租界的陈独秀曾经两次因为进行过激的言论宣传活动,被法巡捕房拘捕,最终以关押22天、罚款100元和关押5天、罚款400元了事。之后,仍继续在法租界从事革命活动[16][17]。再如,法租界巡捕房还曾在孙中山先生的居所提供巡捕站岗,保障他的生命安全[18]334。
法租界会审公廨是法国人侵占我国租界司法权的产物,公廨虽有会审之名,但是法权实际掌握在法国人手中,更近似于法国人的殖民地。但是不可否认,法公廨作为西方制度在中国适用的“实践基地”,通过审判和法律的使用,使法租界内的华人居民逐渐了解,并培养出了具有现代法制特征的法律意识和司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