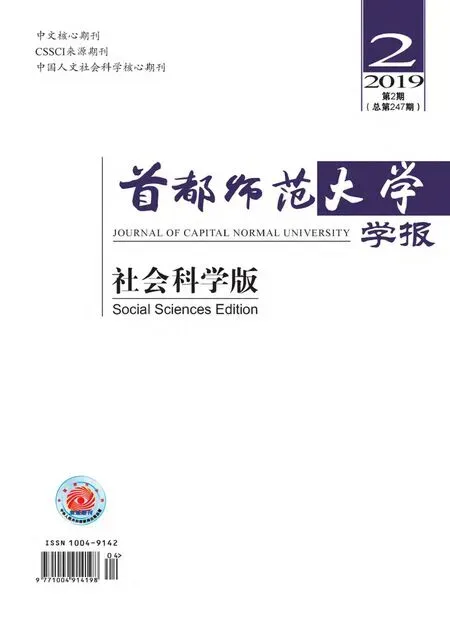高尔基研究中的若干关键问题
汪介之
刘文飞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研究工作已全面启动,这套著作将系统表达我国一代俄国文学研究者关于绵延一千余年的俄国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成就与特色的认识,其中当然包含关于高尔基及其创作的理解与阐释。目前国内学界高尔基研究的基本状况是:有的论者仍然坚持1950年代中期之前对高尔基的旧有评价,维护着一个被“神化”、也被歪曲了高尔基形象;另一些论者事实上认为高尔基“早已过时”,甚至对他进行全盘否定;还有的论者则感到无所适从,于是放弃研读、拒绝谈论高尔基。在这一背景下,对高尔基其人其作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便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中关于高尔基的评价,将在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的阐述中呈现出创新特色。
一、高尔基的创作高峰究竟在哪里?
历来的外国文学史、俄国文学史教材都认定《母亲》是高尔基的代表作,列宁也曾说过《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小说是高尔基全部创作的高峰。作家本人曾在《母亲》法译本序言中称自己的这部作品写得匆忙,有缺点。如果说,“代表作”指的是最能代表作家的思想深度和美学追求的作品,那么,《母亲》就很难说是他的代表作了。国内外读者接受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全面阅读高尔基的作品就不难发现,他最成功的作品是写于“民族文化心理研究时期”(1908—1924)的“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体三部曲,以及《罗斯记游》《日记片断》《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等系列作品。这几组作品以开阔的艺术视野着力描写俄国生活中蛮荒阴暗的现实,提供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众生相,绘制出一幅幅令人目不暇接的民族风情画,不仅呈现出本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与民族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其中,《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三部曲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作品浓郁的生活气息,行云流水般优美自如的语调,纯熟洗练的描写艺术,常带抒情色彩和沉思性质的叙述文字,体现着作家忧患意识的沉郁风格,均给读者以极大的审美享受。三部曲自问世以来,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不仅至今仍是在我国印行量最大的高尔基作品,而且赢得了西方批评界几乎一致的好评。如法国《拉罗斯大百科全书》认为高尔基的几部自传体小说是“俄国文学的杰作之一”;意大利都灵版《俄国文学史》认为自传体三部曲和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等构成高尔基全部创作中“卓越的阶段”;瑞典学者托·柴特霍姆和英国学者彼科·昆内尔合编的《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则肯定自传三部曲是高尔基“最伟大的文学贡献”[注][美]托·柴特霍姆、彼科·昆内尔编著:《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李文俊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直到晚近,审美趣味高雅、目光甚微“苛刻”的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罗姆,也在《西方正典》中把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列入20世纪俄国文学“经典书目”。自传体三部曲无疑是高尔基创作中的一座高峰。
如果从思想的丰富、对俄罗斯民族灵魂的洞察之深入、对这个民族精神生活史的艺术概括的广度来看,高尔基的晚期巨著、四卷本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应当是他的总结性作品。关于这部长篇的深广意蕴和鲜明特色,笔者在《伏尔加河的呻吟》、新版20卷本《高尔基文集》总序、《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译本序中都有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复赘言。这里只引征国外评论者的一些评价意见,从中可以见出各国学界对这部作品的重视程度。如《美国百科全书》称这部长篇为“1917年革命前40年中俄国社会、政治和文学生活的缩影”;德国学者尤·吕勒在其《文学与革命》一书中,专辟一章《知识分子的安魂曲》论《萨姆金》,称它是“现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理解那个时代的俄国、特别是那个时代的一般人的钥匙”。日本《万有百科大辞典》则认为这是一部“空前规模的长篇叙事诗”,“堪称20世纪的精神史”,“作为思想小说,达到最高成就”。[注]参见高尔基著作编辑委员会:《英、美、法、德、意、日等国家大百科全书高尔基条译文》,翟厚隆、杨志棠、高慧勤等译,大连全国高尔基学术讨论会资料,1981年6月。
显而易见,各国评论者都没有否认高尔基作为一位作家的艺术成就,但都不认为长篇小说《母亲》是他创作的高峰,而是几乎一致地给予他的自传三部曲和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肯定性评价。
二、关于《不合时宜的思想》的评价
长期以来,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直被说成是作家“思想错误的产物”,相关的文学史著作和教材,或压根儿不提这本书,或把它作为高尔基思想“动摇”、犯了政治错误的例证。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1917年,从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巨变,把革命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注入高尔基的思索之中。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新生活报》上连续发表了80多篇随笔,其中有58篇使用了“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个统一标题。这些文章后来结成两本互为补充的文集:第一本名为《革命与文化:1917年论文集》,共收34篇文章,1918年在柏林出版;第二本名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札记》,收有48篇文章,同一年在彼得格勒出版。后来人们往往把这两本书合称为《不合时宜的思想》(1917—1918)。在苏联国内,这两本文集一直被严密封存,30卷本《高尔基文集》也未收入。直到1988年,《不合时宜的思想》才在苏联重见天日。十年后,《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译本在我国出版。
我国研究者大都是从1990年代初才开始注意这部著作的,但仍有一些评论者坚持认为,《不合时宜的思想》集中反映了高尔基的错误思想立场。但只要我们阅读这本书,就必然会得出与此完全相反的结论。书中,作家对于提高民族精神文化素质问题的忧心关注,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高度重视,对政治与文化之关系的卓越见解,对民族文化心理条件与民族命运之关系的深邃思考,等等,不仅显示出一种思想家的目力,而且至今对于我们仍然具有启迪意义。高尔基特别强调文化的道德价值,他写道:“文化的真正实质与意义,在于从生理上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野的事物,厌恶一切贬低人、使人痛苦的东西。……对于文化的真正感悟和理解,只有在对自身的和外在的一切残酷、粗野和卑鄙都同样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条件下才有可能。”[注]М.Горький, 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 мысли. Замет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и культур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cc.144-145.对于思想文化领域中矛盾的特殊性、规律性,高尔基有着深刻的洞察,认为“思想是不能用肉体上的强制手段战胜的”,言论的力量不是可以机械地被消灭的。若能让各种不同意见尽可能充分地发表出来,那么,在各种思想的公开交锋中,错误的思想终究会暴露其蹩脚之处,很快就会失去市场;相反,被人为地驱逐的思想,却常常会获得某种“高尚的色调,并引起同情”,“被封锁的言论常常具有特殊的说服力”。他还指出:“不理解或没有充分估计知识的力量,这是‘通往文明之路’上的一个最大障碍”;“哪里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注]М.Горький, 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 мысли. Замет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и культур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c.100, c.166, c. 145, c. 159.这些文字穿透浩瀚的历史风云,至今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华。《不合时宜的思想》不仅体现了高尔基这位正直知识分子的强烈社会使命感,而且已成为关于那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一部独特的编年史,一部关于革命与文化的忧思录。
1921年秋,高尔基离开俄国,先后在德国、捷克逗留,1924年迁往意大利索伦托。在国外,他曾创办《交谈》一刊,致力于“恢复俄国和西方知识界的联系”,并在国内文学界和境外文学界“两岸”之间搭桥。在柏林出版的高尔基的随笔《论俄国农民》(1922)以及那一时期他致列宁、罗曼·罗兰等人的一系列书信,也和《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样表现了作家忧国忧民的思想。
三、高尔基是否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一提到高尔基,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母亲》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这种判定不仅早已成为各种文学史教材中似乎无可非议的结论,而且也给出了人们认识高尔基的基本思维框架,成了一个不可变更的“符码”。然而,随着苏联解体以来各种文学档案的逐渐披露,这一几乎天经地义的传统结论已受到怀疑乃至否定。拂去岁月的风尘,越过当年极左思潮和话语所设置的屏障,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一“主义”的真正态度便清晰地呈现出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最初出现于1932年,它是进入30年代以后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要求文学一统化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提出和苏联作家协会的建立,是斯大林在文学领域推行极左政策的两大措施。这两件事都由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格隆斯基负责实施。1932年4—5月间,斯大林曾问格隆斯基:“如果我们把苏联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么您以为如何?”[注]Гронский М. и Овчаренко А. Переписка//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9, № 2, сс.147-148.格隆斯基随即无条件地表示赞同,5月20日便在莫斯科文学小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布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史实清楚地说明:首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斯大林本人。
1932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一次由苏联领导人和作家参加的座谈会上公开表明自己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次座谈会是斯大林利用高尔基在国内的时机,在莫斯科小尼基塔街高尔基寓所召开的。如果说,前述斯大林对格隆斯基所说的话具有为苏联文学创作方法定名的意义,那么他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要通过一大批作家向整个文学界传达他个人的意见,这显然比5月20日格隆斯基的宣布更具权威性。至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提法已取得不可动摇的地位。座谈会召开地点的选择,给人们造成了高尔基和这一提法密切相关的印象。
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注意:其一,10月26日的文学座谈会虽然是在高尔基寓所举行的,但在整个晚上他却始终没有谈过苏联作家应当运用什么创作方法的问题,更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其二,10月29日,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委员会秘书吉尔波丁做论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报告,高尔基恰恰在这一天离开苏联,重返意大利。
至1934年5月,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总结这场讨论时,已经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草案》的理论部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了“完整的表述”,后来被人们经常引用的、为人们所熟悉的那一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至此已完全成型。三个多月后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只是对其履行程序上的通过手续而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被正式载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于1934年8—9月间在莫斯科举行。高尔基是这次大会的主持人,并在此次大会上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是在这次大会上被正式确立为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的。这一切似乎为“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提供了某种证据。但是,透过这些只有形式意义的表象,却可看到一些更具实质性的内容。实际上,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以文学主管的身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阐释的,不是高尔基,而是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高尔基始终没有附和后者的意见。作为这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主持人,高尔基在大会上先后致开幕词(8月17日),做长篇报告(8月17日),发表讲话(8月22日),致闭幕词(9月1日),还在大会结束后随即召开的作协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但是,在所有这些发言中,他总共只有两次使用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而完全没有就这个概念、定义及其特点展开论述。这种情况绝非偶然。
假如高尔基果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创始人,假如他确实从1906年创作《母亲》起就创立了这一方法,那么,28年以后,当这一方法终于被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为整个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时,他本人却对此避而不谈,没有表现出任何“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取得成功”的喜悦,好像这是一种和自己的漫长创作生涯毫无关系的“创作方法”,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1935年2月19日,高尔基在给作协理事会书记谢尔巴科夫的信中,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提出怀疑。他写道:“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写过不少东西,但是还没有一致的和明确的意见,这说明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批评没有显示自身的存在。……我怀疑,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以完全必要的明确性显示自身之前,我们已经有权来谈论它的‘胜利’,并且是‘辉煌的胜利’。”[注]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т. 30.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6, с.381, с. 383.由此不难看出高尔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正态度,也有力地表明他既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发明者,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关于高尔基本人所遵循的创作方法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有从他的作品出发,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系统阅读高尔基的作品,就可发现他的早期创作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手法;他的中期创作,则显示出清醒、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体现了作家深刻的忧患意识;他的晚期创作,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积极追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新发展的潮流,博采众长而熔铸一新(《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统而观之,不难看出现实主义始终是高尔基艺术地把握生活的基本方法,但他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又分别借鉴了其他文学流派的艺术经验,为自己的思想探索不断寻求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在高尔基的作品中,很难找到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与《母亲》相近的作品。在完成《母亲》之后,高尔基还进行了30年的创作活动,写下大量作品,这些作品没有一部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显然,高尔基并不是一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
四、怎样看待1928年以后的高尔基?
高尔基评价中的要害问题,是如何看待他的晚节。苏联解体前后陆续出现的对高尔基形象的颠覆性言论,从那时起就不断地随着北风吹到我国来。对高尔基的否定性评价,主要集中于1928—1936年这8年时间内他的所作所为。有人指责他从意大利回国期间对残酷的现实一声不响,将保卫人民、文化和正义的大事置于一边,却忙于参观视察、会见权贵和出席各种庆典活动。也有人认为他参与了30年代个人崇拜的鼓噪,赞许当时那种分裂、敌对和仇恨的氛围。还有人说他好像有两个脑袋、两副面孔,这只曾经呼唤革命风暴的海燕,晚年竟在证明斯大林主义的正确性,甚至支持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杀。更有人断言他是“幸福的幻影”的制造者,而在幻影破灭时则保持沉默,甚至不惜对自己说谎。上述评价意见,一度使人真伪莫辨。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关于高尔基“晚节”的评说,更极大地改变了广大读者对晚期高尔基的原有印象,而丝毫没有注意到他如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十分成功地熏黑了历史的真相”。于是,所有那些与索尔仁尼琴的评价相左的意见,包括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俄国流亡作家霍达谢维奇、扎米亚京等人的看法,便较难进入人们的接受视野了。
国内有人在书中写道:1928年高尔基“从海外归来后就一头扎进了肉麻吹捧斯大林体制的队伍中”,成了“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斯大林制度的维护者”。[注]金雁:《倒转“红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笔者尊重的一位著名评论家也认为高尔基是“两截人”:前半截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后半截却支持斯大林的反人道行径,实际是一个“双头鹰”。
但历史事实却不是如此。1929年11月27日,也即高尔基结束第二次回国、返回意大利之后不久,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于国内正在发生的“大转折”的看法。高尔基反对“党内摩擦”,认为青年们会把党内矛盾“理解为两个派别为了权力而进行的斗争,甚至还理解为反对您的‘个人专制’的斗争”。[注]Л. А. Спиридонова, Вокруг смерти Горького. Документы, факты, версии. М. Горь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ыпуск 6. М.: ИМЛИ РА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следие, 2001, c. 292.由此不难看出,高尔基希望能够阻止斯大林排除异己、迫害“敌对分子”的一系列行动。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个人崇拜泛滥时期,高尔基为保护一大批受到不公正批判的作家挺身而出,与极左思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对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左琴科等诸多遭受批判的作家的高度赞扬,同样具有抵制极左路线的意义。
高尔基还坚决反对把苏联作家协会实际上变成扩大了的“拉普”,力求阻止原“拉普”的一批领导人进入并控制作家协会理事会,进而称霸整个文学界。1934年8月初,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高尔基直接写信给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能赞同由原“拉普”批评家、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书记尤金提出的作协理事会建议名单,同时推荐另外9名理事人选。但是高尔基的意见却未能改变由原“拉普”成员构成作协理事会主体的格局。对此,高尔基十分不满,又于代表大会闭幕当天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写信,公然发出激烈的抗议,盛怒之情溢于言表。直到1936年逝世前不久,他还写信给斯大林为横遭批判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辩护,对“批判形式主义”运动提出怀疑。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是:正是在30年代初,高尔基拒绝给斯大林写传记。1931年10月,斯大林通过国家出版局局长哈拉托夫向高尔基转达了自己的意愿,希望作家为他写一部传记。高尔基先是对此事采取了回避和推脱态度。年底,哈拉托夫又写信追问已回索伦托的高尔基,高尔基立即回信,列举自己近期要尽快完成的十来件事情,唯独避而不谈为斯大林写传。1932年,高尔基把给他寄来的有关斯大林的材料全部退回。如果高尔基真是“个人崇拜的奠基者”、“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那么为斯大林作传,不正是向领袖献忠心的最好机会吗?他怎么会放弃这个求之不得的为主人歌功颂德的“天赐”良机呢?
高尔基对待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态度,也表明他绝不是什么“斯大林制度的维护者”。例如,1933年9月9日,在看过卡冈诺维奇寄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高尔基写信给他说:“第57页上称托洛茨基为‘最可恶的孟什维克’。这很好,但是不是过早了?实际上不是过早,只是读者可能会提出问题:‘最可恶的’怎么就不仅进入了党内,而且还占据了党的领导岗位呢?……我担心,书中所提供的对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他某些人的评价,同样也会在读者那里产生类似于关涉托洛茨基的问题。姑且不论,依我看来,这些评价其实是对以上诸人永远关闭了党的大门。”[注]Л. А. Спиридонова, Вокруг смерти Горького. Документы, факты, версии. М. Горь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ыпуск 6. М.: ИМЛИ РА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следие, 2001,c. 293.
高尔基对“领袖至上主义”的抨击,更有力地证明他不仅不是“个人崇拜的奠基者”,而且正是它的坚决反对者。1933年,高尔基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领袖至上主义是一种心理病症,当自我中心主义扩展起来,它便像肉瘤一样毒化、腐蚀着意识。患领袖至上主义疾病时,个人因素膨胀,集体因素衰竭。领袖至上主义无疑是一种慢性病,它会逐渐加剧……为领袖至上主义所困者,都患有好大狂,而在它背后便是如同黑色阴影般的迫害狂……”[注]В. И. Баранов, Огонь и пепел костра. М. Горький: творческие искания и судьба, Горький: Волго-Вят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90, c.327.
透过这些言论,不难看出高尔基对于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及其后果的警觉和反对。如果高尔基真的支持斯大林的反人道行径,还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吗?
俄罗斯的高尔基研究专家、世界文学研究所高尔基文献保管、研究与出版部主任斯皮里东诺娃在她的《马·高尔基:与历史对话》(1994)一书中,曾根据大量的实证材料得出如下结论:晚年的高尔基“试图阻止斯大林恐怖,谴责强制性的集体化运动,为大写的人而斗争,其积极主动并不亚于在十月革命的如火如荼的年代。与索尔仁尼琴的断言相反,他不会歌颂1937年,不会为其辩护,也不会忍耐屈服。”作家的“人性的真诚和真正艺术家的内在嗅觉,不容许他成为斯大林时代的御前歌手”[注]Л. А.Спиридонова, М. Горький: диалог с историей,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Наследие, 1994. c. 300, c. 301.。这段话可视为对索尔仁尼琴观点的最好回应。
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也写道:“高尔基直到1936年才逝世;而只要他还健在,就会利用其巨大的个人权威和声望保护一些杰出的引人注目的作家免受过分的监管与迫害;他自觉地扮演着‘俄国人民的良心’的角色,延续了卢那察尔斯基(甚至是托洛茨基)的传统,保护着有前途的艺术家免遭官僚统治机构的毒手”,“高尔基的逝世使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唯一强有力的保护者,同时也失去了与早先相对比较自由的革命艺术传统的最后一丝联系”。[注][英]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苏维埃文化》,潘永强、刘北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这是对高尔基晚期活动和作用的公正评价!
高尔基并非完人,他在自己的晚年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无疑不是完美的。但高尔基的全部不足、迷误和缺陷,除了表明极权政治体制操控作家和文学的可怕力度和结果之外,还有他个人认识上难以避免的局限性的原因,但这些局限丝毫不带有趋炎附势、卖友求荣、见风使舵、助纣为虐的性质,丝毫无损于他的人格光辉。他个人的经历、修养、知识结构和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他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条件,决定了他在自己的晚年只能那样说、那样做,也使得他时时充满着思想矛盾与精神痛苦。这些矛盾与痛苦的根源在于:作为俄罗斯母亲的儿子,他要力图维护自己的祖国在世界上特别是在西方民主知识分子面前的形象,但是20年代末期以后的苏联现实却不断破坏着这一形象;他始终怀抱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集体理性”的社会主义理想,但是斯大林“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与方式却是直接同专制主义、践踏民主的行径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直寄希望于科学和文化的振兴与繁荣,但是反科学、反文化的因素却不断从外部强有力地牵制着科学与文化的发展。面对这一切,高尔基始终不渝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文化、保护知识分子;但是他既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个人崇拜的蔓延和极左路线的推行,更无力拯救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们;既不可能超越时代,也不可能超越人类的认识水平去解决那些不断困扰着他的矛盾和问题。这就造成了罗曼·罗兰1935年访问莫斯科期间所发现的他的内心痛苦。罗曼·罗兰对高尔基不仅抱有一种同情性理解,还做出了切合其思想实际的评价,所以他的观点已被我国学界许多研究者所接受。事实上,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和精神特点,对于过去一个世纪中追求人类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说,应当说具有某种典型性,这也就是高尔基至今仍然使包括中俄等国在内的几代忧国忧民的知识者感到亲切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