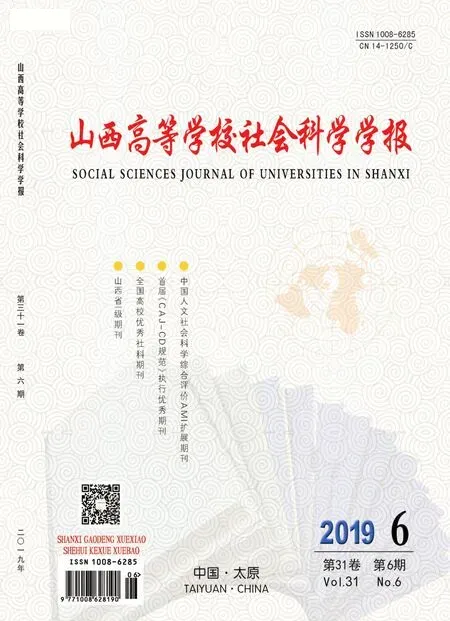政企之间的博弈如何展开?
——《困境下的多重博弈》品藻
黄振南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在企业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中,政企关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政企关系史的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新史料的开放,新方法的运用,新视角的拓展,都为政企关系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近日,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晓锴副教授以35.8万字的《困境下的多重博弈——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研究(1945—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展示世人。该书以抗战胜利以后5年间上海卷烟业为研究对象,以政企关系为切入点,别出心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读这部选题新颖、视角独特、资料丰富、逻辑严谨、论证清晰的著作,收获自然与众不同。
一、从博弈角度研究政企关系
政府之于企业,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称之为“看得见的手”,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所称市场是企业“看不见的手”双双构成著名的经济学理论。这两只手究竟哪一只更重要呢?战场上有“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之说,经济生活中则未必如此,在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的时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所起的作用尤不可忽视。
就像“看不见的手”无时无刻都在影响企业一样,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矛盾与冲突无时不在,合作与互动亦无处不有,向来是一个难以厘清的问题。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金瓯待拾、创伤待医的中国,这一关系更加纷乱繁复。选择这一时期上海卷烟行业与政府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无疑是个极具挑战的课题。作者不畏艰难,敢于挑战自我,令人敬佩。
博弈本指下棋、局戏,拓展开来,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生产活动中为了谋利而开展的竞争。博弈既有合作性的,也有非合作性的;既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既有零和博弈,也有非零和博弈,如此等等。对于博弈的结果(参与者的得失)来说,游戏规则十分重要。单从下棋的表象看,博弈是参与者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游戏,但在社会实践中却非如此,参与者之间除了互相拆台以外,相励相扶同样必不可少。卷烟业既然能给政府提供巨额税收,政府在掌控、强制卷烟业的同时,当然要为卷烟业的有序发展提供因势利导的服务,这样才能收缴更多的税额。沿着这一主旨,该书以上海卷烟业和政府为博弈参与者,将其放在抗战胜利后的重重困境之中,分析其多重博弈的种种表现,总结这种博弈的结果及其启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理顺纲目架构,是该书研究政企关系的具体做法。以书中第二章《卷烟税收中的政企博弈》为例,该章下分三节,在介绍抗战前后国家卷烟税收政策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卷烟企业、卷烟同业公会与政府三方的合作与矛盾,最后着重探讨政府对卷烟业的管制措施。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逻辑性很强的提纲,起到了提要钩玄的作用。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制定法律,利用强制手段,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分配方式。所以,马克思称“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1]。没有税收,政府就无法正常运转,更不能提供如文教科技等公共服务。但是,不能因此滥用政府强制力,也不应只管收税而对企业放任自流。那么,民国政府对上海卷烟业在收税之外还做了些什么事呢?该章第三节下所立三目:一是“进口卷烟管理”,二是“生产材料监管”,三是“卷烟缉私及商标管理”。这三目四项,提纲挈领,立收纲举目张之效。
既然政府在强制收税的同时监管企业,这就有了下文卷烟原料供应中的政企合作、卷烟工潮中的政企互动等内容。不同于一般论著的是,该书是通过论述政企矛盾、合作、互动来实现“政企关系”这个论题,既非通过政权兴衰过程的考察来旁及“政企关系”,亦非通过企业发展历程的叙述来揭示“政企关系”。这种写法,从历史的纵向和行业的横向展示政企、行业、劳资等博弈态势,是史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犹如清风拂面,读来别有一番韵味。
兹举一例。“年赏”(年终奖励)是业界的习惯做法,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业界,“年赏”各异,卷烟行业也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劳资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工潮此起彼伏。为调和劳资矛盾,同业公会和政府社会局出手干预,经多方协商,公布工人底薪标准,商讨“年赏”发放办法,共度危机。书中第四章用相当篇幅来论述卷烟业工潮与政企互动,并用列表方式举出有代表性的颐中烟草公司1946年3—12月间64起劳资纠纷的调解情况,一目了然,可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总览全书,政企关系作为一条主线,从税收中的政企博弈到原料供应中的政企合作,从行业工潮中的政企互动到国营与民营论争政企对弈,贯穿于全书的自始至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用《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重新建构》《上海卷烟业的行业自卫与诸方博弈》《特殊背景下卷烟业政企关系之审视》三节来回应“政企关系”这个主题,收束全部议题,结构严谨,綦组工整,切中窍要,引人注目。
二、选择上海的卷烟业研究政企博弈
卷烟业是个特殊行业,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高利行业,又是一个因危害民众健康而被广泛诟病的行业,正反两面的矛盾异常突出。就反面来说,1840年中英战争源于毒品鸦片(烟土)入华,鸿胪寺卿黄滋爵奏请对瘾君子“罪以死论”[2]、林则徐在广州严厉禁烟,妇孺皆知。鸦片由罂粟提炼而成,卷烟是烟草的加工品。烟草于明朝传入中国,晚于罂粟。初始,烟草是国人备受推崇的治病良药,但不久人们便发现它是鸩毒之物,有识之士发出了切莫吸烟的忠告。明末崇祯皇帝则绕个弯,因其祖上有“燕王”、京都为“燕京”(今北京),“吃烟”与“吃燕”同音,有吃掉燕王、攻破燕京之嫌,下令禁止吃烟,“犯者论死”[3]。满人取代明朝前后,制定律例,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后因国势衰微而不果。到了清末,卷烟这个舶来品又登陆华夏,继之设厂制造,中国逐步演变成全球生产卷烟之首。烟土与烟草虽有区别,但其有害于健康则同辙。相较于鸦片被严禁,历届政府对烟草的态度暧昧得多。民国时期,蒋介石以自己不抽烟的行动做榜样,还发起“新生活运动”来抵制卷烟。然而,残酷的现实打压着正义的行动,“看得见的手”无力还击,税收与健康之间的矛盾无法化解,致使烟草迄今尚在种植,卷烟业至今还在发展。
卷烟业非因存在而合理,但其存在于不合理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唯其如此,学界对卷烟业的研究并不少见,成果也比较多,除了论文、专著,还有志书、工具书,使许多领域望尘莫及。这些成果,大多以上海的卷烟业为研究对象,是有原因的。
上海扼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之咽喉,自185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广州之后,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在这里,艨艟浩浩荡荡,商舸川流不息,舶贾络绎不绝,白帆红帜,交相辉映;各色人等,纷至沓来,熙熙攘攘,蔚为壮观。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早期开埠的基础累叠,到20世纪前中期,上海成为中国工业的翘楚,未有望其右者。中国的卷烟业诞生于上海,研究卷烟业,怎能撇开上海?
正因为上海与中国近代卷烟业关系如此密切,政企关系在这里自然非同一般,各种博弈在这里当然交错纷呈,以税收纷争为例,即可见诸一斑。
蒋介石政府之所以禁烟不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它需要钱来打内战。抗战胜利以后,国共矛盾日显,导致了全面内战的爆发。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国民政府债台高筑,1947年财政赤字29万亿元,翌年攀升至435万亿元,这是多么可怕的升幅!如何填补窟窿?“看得见的手”唯有借助政权的力量搜刮。烟卷既非生活必需品,政府便以所谓“奢侈品”的名义,在“寓禁于征”思路指导下大肆提高税率,使之成为货物税中最高的税种,征收总额超过货物税的半数。上海卷烟行业要上缴多少税金呢?1946年为1734亿元,1947年便升至1.3万亿元。重税之下,烟厂纷纷倒闭。
到底要杀鸡取卵还是要培植税源?论争随之而起。为了生存,卷烟企业、行业公会与政府之间展开“博”无法避免“弈”,从该书第109—110页用表格归纳1946年4月至1947年12月间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向政府“反映情况”来看,这种博弈异常激烈。如1946年9月24日该公会就沪市卷烟业濒临破产向上海货物税局和行政院请愿,提出将调整税额周期由3个月改为6个月等要求;1947年1月4日,因工人怠工、罢工向上海货物税局提出延交税款的要求;1947年1月24日,因烟税调整影响成本而推举代表晋京请愿等,都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政府矛盾、摩擦的表现。
博弈不是单方的事,作为政府一方,对企业的诉求、请愿当然要回应,特别是在工人罢工、工厂倒闭的关键时刻,任其自为有违收税的初衷。所以,政府面对企业的诉求是无法回避的,尽管企业的要求大多达不到目的,或者不完全达到目的,但在一定范围内改善处境是有可能的。例如,1948年12月,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致函上海货物税局要求降税,该局局长时寿彰亲自赴京与财政部长、税务署长洽商,终于核减了税额(见该书第115页),尽管核减后烟厂纳税仍重,但毕竟它是博弈的结果。这样的事例,书中还有不少。
由此可见,以上海卷烟业作为研究政企博弈的对象,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具有典型意义,是正确的选择。
三、拔取抗战胜利后的5年研究政企博弈
选择上海卷烟业作为政企博弈研究的对象之后,为什么要将研究时段框定在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5年?作者在《绪论》中首先说明这5年 “是一个承先启后、去旧迎新的时代”。不错,这个为期不长、炮火连天的时段,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汪朝光先生称这5年“在后人眼中或许不过是惊鸿一瞥的瞬间,却以其历史演进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波及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影响到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从而在个体生活改变的同时,更在集体意义上改变了中国的走向,实可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演进的关键性年代”[4]。在和平年代回首那段不平凡的历史,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莎翁那句“Nothing is so common as the wish to be remarkable”(没有什么比希望不平凡而更平凡的了)的名言,或许能够说明作者的写作心态。
那么,人们是怎样看待1945—1949年这段峥嵘岁月的呢?作者引用法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玛丽-格莱尔·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夫人为其弟子王菊出版的博士论文《近代上海棉纺业的最后辉煌(1945—1949)》所写的序言中说的话:1945年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个学术界了解得不够深刻的时期,因为这段历史曾被普遍地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研究和思考,从而使历史本身受到了先验论的干扰。的确,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有偏颇,国内如此,国外亦然。在中国,单从国共双方对这段历史的称谓便可看出其政治倾向:国民党称之为“动员戡乱时期”,共产党则称之为“解放战争时期”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何谓“戡乱”?1947年7月4日举行的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蒋介石交议的《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即一目了然;共产党的称呼针锋相对,“解放”“革命”之名同样一点也不含糊。全面内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等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武装力量从1946年9月中旬起开始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产党控制的区域被称为“解放区”(抗战时期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根据地曾用此称),与国民党控制的“国统区”相对而立。1969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胡素珊(Suzanne Pepper)以这段历史作为博士论文,旨在回答“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取得政权的”[5]。所有这些,足以说明这段历史政治特点的鲜明。而意识形态的差别,研究者或先入为主,先下结论再去寻找史料来说明这个结论;或将这段历史视为雷区,唯恐避之不及。所以,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总体上是薄弱的。
上海既是史学研究的富矿区,也是史学研究重镇,人才济济,硕果累累,世所公认。但检视1945—1949年上海历史研究的成果便可发现,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相当薄弱,至于专门研究1945—1949年间上海卷烟行业历史的成果,竟是空白。都说学术贵在创新,创新包括许多方面,开启一个前人没有研究触及的科研领域,其创新自不待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选取抗战胜利后5年上海卷烟业的政企博弈作为研究对象,是既新颖又有挑战性的课题,其学术价值就不难判断了。
四、用丰富的史料研究政企博弈
政企关系错综复杂,选择一个特殊行业、一个较短时段、一个典型地区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个定位无疑是准确的,也是可行的。当然,基于这个题目的指向,需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展开,研究工作方能取得成效。而作为史学工作者,首先看重的就是史料的搜集了,诚如梁任公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6]该书史料之丰富,使“史之组织细胞”特别健壮、发达。
该书使用的史料,主要包括档案、民国时期的报刊和后人整理而成的史料汇编3大类。作者在书末开列的“参考文献”中,“史料汇编”共有37项,剔除其中的工具书、志书、专史等既非“史料”、亦非“史料汇编”者,与该书有直接关联的不多,称之为“参考”相当恰当。相反,“著作类”的“民国著作”项下,却有一些真正的“史料汇编”,如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秘书处1945年12月编印的《上海区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章则汇编》、昌明书屋1946年编印的《收复区特种法令汇编》等等,是作者分类不清之故,并不影响对这些史料的运用。
真正用来论述该书命题的史料,档案和民国时期的报刊最值得称道。报刊包括民国时期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还有行业性的《烟业日报》《烟草月刊》《英美烟公司月报》等,其出版地以上海、南京居多,还有天津、武汉、南昌、广州、沈阳等城,其内容涉及商业、金融、经济、银行、烟草、物流、进出口贸易、国货产销、农业、劳工、青年与妇女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如果说以上报刊读者还比较熟悉的话,那些不太常见的报刊被征引,则令人眼前一亮了。例如,关于上海卷烟业临时工使用的规定,书中引用《新闻报》1947年12月18日第4版刊登《劳资评断委员会第十五次大会报道》为证据(见该书第265页);在回顾晚清上海老晋隆洋行引进美国的“品海”“小美女”等卷烟品牌后迅速销遍全国的史料,征引自1934年1月出版的《国光》杂志第2卷第1期(见该书第25页);抗战胜利后中华烟草公司修改日本人“全禄”牌香烟商标被称为“香烟史上光荣的记录”,引自1946年3月23日出版的《快活林》杂志第8期(见该书第283页);如此等等。可见作者对史料的发掘,是相当用功的。
尤其感人的是,作者对档案史料的搜集,达到不遗余力的程度,其五赴上海的经历即可说明。在沪上,上海档案馆关于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工人福利会、上海市参议会、上海商会、上海市工业会、永泰和烟草公司、财政部上海货物税局、中华烟草公司的11种档案被作者翻了个遍,上海社会科学院关于英美烟公司抄档以及1930—1950年代初期经济类剪报资料、企业史和行业史资料也被作者逐项查阅。
我们知道,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将大量宝贵的文物、资料运到了台湾,这就是现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里那些珍贵档案的来历。作者利用赴台半个多月时间,复印了实业部、农林部、经济部的相关档案,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国华成烟草公司、中华烟草公司、颐中公司等上海烟草企业的资料,这是在大陆所无法看到的档案,弥足珍贵。
近水楼台先得月。作者在南京求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自然不会放过。而2010年该馆《民国时期烟草行业档案选编》的数字化,为利用这些档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批档案与卷烟有关的2000多个条目,涉及行政院、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国税署、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海关总署等20多个卷宗,实在是太丰富了。
该书以“有史料的地方,便是史学工作者的天堂”发凡,再往下看,是史料给了作者用武之地,像在太空遨游,像在天堂寻觅,是众多的史料给作者研究政企博弈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五、用生动的文字研究政企博弈
学术研究有自己的规律,其成果的呈现无法像文学作品那样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但拗口饶舌、佶屈难读往往是人们对学术著作(尤其是史学著作)的鞭挞。捧读该书,文句朴质,不加雕饰,通顺畅达,清新自然,完全没有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艰涩隐晦、诘屈聱牙的表达方式,大大增强了学术著作的可读性。
学术专著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字浅显并不意味着就能打动读者的心,善于分析,深入浅出是制胜法宝之一。该书第259页对工潮起因的剖判,有理有据,使人信服,便是例证。第41页巧妙地运用史料描述诸名人嗜烟如命的众生相,栩栩如生,令人忍俊不禁,欲罢不能,同样是书中的看点。
图文并茂是该书的又一个特色。在这本370多页的著作中,共有插图20幅(不包括多幅未命名者)、表格42个,使其版面多姿多彩。插图有自绘的,有翻拍的;有曲线图,有线段对比图;有组织系统图,有圆形比例图。表格不但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有比率表,有比较表;有数量统计表,有原因分析表;有仅一两行的表,有长达数页的表。这些图表,或浓缩大量的文字,或保持资料的原貌,简洁明了,直观性强,使密密麻麻的页面变得生动活泼,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收到良好的效果。如第49页翻拍《申报》关于中华烟草公司即将开工的报道,既再现了一代名报的新闻风格,又替代了书中的行文,可谓一举两得。第53页所载抗战前后卷烟制造程序与部门比较表,撷取3种文献史料的精华制成,高度概括,一目了然,既节约了大量的篇幅,又使阅读变得更加轻松,实在可圈可点。
不消说,这部著作从选题到写作无疑是成功的。当然,如果在此基础上对全书文字作进一步的加工润饰,使之更加优美,必将锦上添花。再则,书中这么多图表,若将它们列入目录中,检索就更方便了,这就是拜读之后的切身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