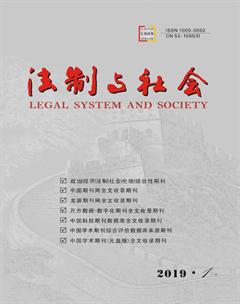体系性地解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
摘 要 无论在理论上亦或是实践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都是考察是否构成贪污的重点。事实上其对于不同的贪污行为有不同的含义。同时,在其他罪名中存在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罪状也与贪污罪中有所不同,本文试图从对差异的比较,体系性地解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
关键词 职务便利 行为模式 贪污罪 职务侵占罪
作者简介:张逸芊,江苏省启东中学。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1.222
一、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概述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贪污罪构成要件中的一个行为要素。 而仅仅是这一表述的确立就已经过多次的修改,并非自始至终均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且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具体分析运用向来存在争议。为此,首先必须结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历史沿革进程,明晰其立法意图和特征。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刑法史上的历史沿革
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部惩治贪污贿赂罪的刑罚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第二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此处的“假公济私”包含了“利用行为上的便利”的含义,但表述过于情绪化。而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得到改善,法律用词逐渐变得更加理性和专业。
1979年7月6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成立,在第155条中对贪污罪进行了如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从此,我国的刑法第一次明确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纳入到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之中,也象征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标准化的说法登上历史舞台。
此后,1988年1月21日,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单行刑法《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虽然扩大了贪污罪的主体范围,但依然维持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构成要件要素地位。
自此,直至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刑法进行了全面修订,贪污罪最终被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仍然坚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表述并至今延续。
综上所述,在我国刑事立法的过程中,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行为要素的表述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从建国初期仍较情绪化的“假公济私”演变为如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标准化的说法。这让我们看到我国法律术语的不断完善,亦昭示了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发展。
事实上,虽然表述不同,但从始至终贪污罪罪名中一直打击的是利用公家赋予的职权和优越条件,为自己利益服务、破坏了职务廉洁性的腐败行为。
(二)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特征
首先,此处的“职务”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至少是较长一段时间内职权的拥有者,而非完全的“临时工”。若行为人本不具有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职权,而只是受临时委托暂时经手,便不可称之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其次,“职务”必须为“现有职务”,利用的必须是本身已有的职权,若国家工作人员本身目前不具有此职务,例如行为人已处于退休状态或利用的是其下属的职务,便不可称之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除此之外,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特征的认定也不得不涉及到“职务上的便利”与“工作上的便利”这一法学界惯有的有争议的辩析。笔者认为,“工作上的便利”侧重于行为人利用对工作环境的熟悉,在工作中获取的人际关系以及对犯罪场所的控制能力等能影响犯罪的因素,而“职务上的便利”范围要狭小得多,其限定行为人本身具备主管、管理或经手公共财物的职权。
在明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特征后,其内涵也会相应地更易理解,其与其它罪名中相同表述的区别也同样会更加明了。
二、不同的贪污行为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內涵
事实上,在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中,“侵吞”、“骗取”、“窃取”亦是其重要的行为要素,而这些行为模式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着不同的内涵。定罪时,不能将不同的贪污行为混淆。而这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对不同行为模式的判断,笔者认为,区分这三种不同行为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与他所贪污的公共财物间的关系以及行为人与其利用的权限的关系。
(一)侵吞行为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所谓“侵吞”是指将本人基于公务而事先合法占有支配控制下的公共财物,非法地占为己有 。根据此含义可知,“侵吞”意味着在行为人非法将公共财物占为己有之前,他已经拥有了对此公共财物的控制支配权利。
正如某案例中,被告人周某利用其作为储蓄所柜员所具有的职务便利,向同案犯卞某提供该储蓄所储户,即受害人陈某的存款资料,并由卞某凭借该存款资料办理陈某的假身份证之后并办理挂失手续,冒领储户陈某的存款,之后两人私分。此案中周某利用职务便利,采用盗用银行储户资料,进行虚假挂失冒领。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贪污的行为。首先,在非法占有之前,周某原本就有对银行储户资料的控制权,也并不需要偷偷翻看,他对存款材料本就具有主管、控制、管理的权力,于是他利用这种便利条件置办假身份证条件冒领存款,构成贪污罪中的侵吞行为。
(二)窃取行为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所谓“窃取”,是指将本人管理使用的公共财物以秘密的手段转归自己控制的行为 ,即在行为人将公共财物占为己有之前,他对此公共财物拥有管理权,但仍未拥有控制支配的权力。在判断窃取时,很容易与侵吞混淆,对此,有一较简便的区分方法,所谓“侵吞”,侵占吞并,都是明目张胆的、直接的。而所谓“窃取”,既带上了“窃”字,其行为必定是私密地以非公开的方式完成。
另有案例,被告人郑某利用其作为银行复核员的职务之便,将受害人朱某存折中的10万元全部领出。此案中郑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存折中10万元全部领出,而这10万元原本并不属于他控制支配,他只是有经手权,只是这些钱款的管理人,利用经手钱款的便利条件将10万元秘密领出,因此在据为己有的过程中,他是私下地、非公开地,显然,他的行为构成了贪污罪中的窃取行为。
(三)骗取行为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所谓“骗取”,是指通过欺骗具有控制分配公共财物权限的领导,使其基于认识错误而作出将公共财物处分给行为人的决定的行为。 该行为与侵吞、窃取的区别就在于侵吞、窃取行为系利用职权公开或私密地侵占公共财产,而骗取却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虚构事实以达到目的。在这里笔者将以案例释义。某案中,被告人曹某作为某国有啤酒公司的供应科科长,负责审签交回公司啤酒空瓶开具的回收单,但其利用其职务便利,伙同采购商故意在回收单上涂改增大数量,骗取回收款749258.76元。该案中,曹某仅有审签回收单的职权,而根据该回收单下拨回收款的则另有其人,因此,其虚构事实的行为构成了贪污罪中的骗取行为。
总之,虽然同属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事实上差别很大,区分的关键便是上述所提到的不同差异。
三、与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比较
事实上,在进行这一部分撰写时,笔者原本考虑将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及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纳入讨论。但经过案例上的比较以及对立法意图的检索,笔者发现,我国的刑法体系对罪名的设定具有一致性,不同罪名中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定义差别并不大,因此,笔者最终只选择了职务侵占罪作为代表与贪污罪进行比较。
由于法律需要保证公平性,在各个不同罪名中需保证同一要素在规定中包括基本相同的行为模式,来尽量避免量刑的混乱和不公平情况的出现,并且职务侵占罪中的窃取、骗取与一般的盗窃有明显的不同,行为人对其对象原本是有一定管理权的,因此虽然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模式,但可以想见理应与贪污罪中一致,依然包括侵吞、窃取、骗取三种,它们并无实质区别 。
而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一定的区别却是毋庸置疑的,而其关键的区别在于职务的具体范围。
在对比正式开始之前笔者将通过两个案例来具体阐述。首先,第一个案例中,被告人张某是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保管公章并有权以该公章代表公司签订合同。某日,张某在未经股东决议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公章向银行借款数十万元,并携款潜逃。在此案中,张某非国家工作人员,且其利用了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享有的使用公章签合同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了公司财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而第二个案例则是某国有银行出纳利用其保管银行保险柜的职务便利,打开保险柜窃取30万元人民币并携款潜逃。在此案中,出纳系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取得钥匙伙同他人侵占公共财产,其行为便构成了贪污罪。
因此,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差别如下。首先,其具体范围因行为主体的不同产生了变动。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即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其他所有职工。而贪污罪的主体便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委托保管公共财产的人员。同时,职务所对应的职权也是不同的。贪污罪中利用的是行為人经手管理、主管他所持有的公共财物的便利条件,而职务侵占罪中利用的则是行为人经手管理、主管本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由此也可以看出犯罪对象“财物”是有所差异的,贪污罪中的对象只局限为公共财物,而职务侵占罪中的对象则包括行为人工作范围内经营的本单位财物。
四、结语
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不同的行为模式及罪名中有着细微的差别,而这些差别与犯罪的主体紧密相关,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中的犯罪主体是不同的。对此,笔者认为,之所以将国家工作人员与一般人员区别开,目的就是要强调国家工作人员的表率作用,其本质在于维护职务廉洁性,上行下效,作出良好表率。因此,我们要精准地区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不同行为及其他罪名中这一概念与贪污罪中的不同之处,但绝不应囿于此,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事前预防,而非事后判断。立法不是为了判定罪名,而是为了防范犯罪,而真正的对法律的完善也正是对犯罪的防范。
注释:
邹兵建.论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指导性案例11号为切入点的反思.政治与法律.2016(11).46-60.
陈洪兵.体系性诠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法治研究. 2015(4).59-71.
肖中华.也论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法学.2006(7).136-144.
刘流.论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法律适用.2001(6).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