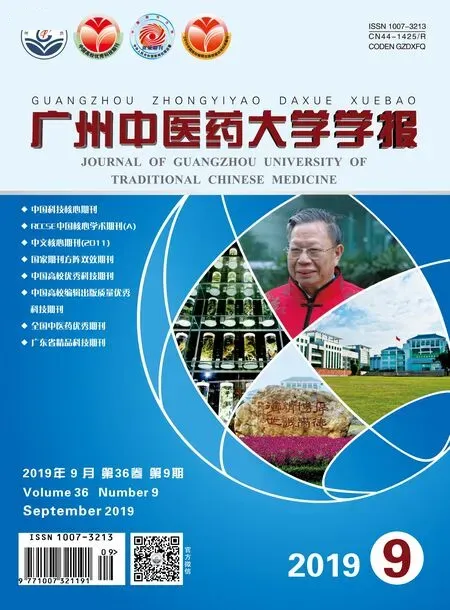黄绍刚辨治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经验
郑欢, 吴皓萌, 秦书敏, 黎颖婷, 陈君千(指导:黄绍刚)
(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广东广州 510006)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是肠易激综合征(IBS)的一种亚型,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功能性肠病,腹痛、腹泻为其主要症状,但未出现肠道结构改变等器质性病变的体征[1]。现代医学认为IBS发病机制复杂,肠道菌群失衡、感染后、肠道黏膜屏障免疫、遗传因素、内脏高敏感性、饮食异常或机体代谢异常等均可导致本病的发生或加重[2]。IBS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3,4],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5]。西医对IBS无特殊治疗方法,主要采用抗生素、益生菌、5-羟色胺受体拮抗剂等药物治疗。
中医古籍无IBS的病名记载,因其以腹痛、腹泻或腹胀等为主症,可将其归属“泄泻”、“便秘”或“腹痛”等范畴[6]。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现代中医专家对IBS的认识也逐步深入。
黄绍刚教授是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广东省中医院青年名中医,师从广东省名中医周福生教授,专注于IBS临床及实验研究多年,首次提出从“血三脏”理论辨治IBS[7],并认为基于“心胃相关”理论,采用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IBS,可明显缓解患者腹部疼痛、胀气、腹泻、排便不尽感等症状,减轻其发病程度和频率,使患者生活质量有较大的改善[8]。以下探讨黄绍刚教授辨治IBS-D的经验。
1 肝郁脾虚是IBS-D发病的关键
黄绍刚教授认为,肝郁与脾虚均是导致IBS发病的重要因素,且两者相互影响而为病,形成以肝郁脾虚为主的证候。
1.1泻责之脾脾主运化,升清气,浊气糟粕则直降小大肠而出。若脾虚运化失职,气机失调,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则致水谷精微不能正常输布,肠道气化不力,食物糟粕不能正常排出,故见腹满、泄泻等症。《古今医鉴·泄泻》曰:“夫泄泻者,注下之症也。盖大肠为传导之官,脾胃为水谷之海,或为饮食生冷之所伤,或为暑湿风寒之所感,脾胃停滞,以致阑门清浊不分,发注于下,而为泄泻也。”可见泄泻与脾虚相关。
1.2痛责之肝从肝的生理病理来看,肝血虚,血液充盈量减少,可导致腹部所属脏器失于濡养,不荣则痛。肝郁则气滞,气机不行,血运不畅,不通则痛。从经脉循行来看,足厥阴肝经循行于腹部两侧,衔接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绕阴器、抵小腹。若肝经气虚血少,或经气不畅则可致阴脉失充,经脉循行之处的腹部脏器出现失养而痛或滞涩而痛。
1.3肝郁脾虚是核心尽管腹痛责之于肝,泄泻责之于脾,但在IBS的发病过程中,肝脾两脏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脾在志为思,肝在志为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怒伤肝,思伤脾”之说,情志的改变易伤及肝脾两脏。《景岳全书》指出:“凡遇怒气便作泄泻者,必先怒时挟食致伤脾胃,但有所犯即随触而发,此肝脾二脏之病也,盖肝木克脾胃受伤而然。”在IBS的发病过程中,不论是先有肝郁,还是先有脾虚,二者总是先后发生,相互影响。肝郁克脾太过,可导致脾虚;素体脾胃虚弱,肝木又会反侮,最终形成肝脾失调共存的现象。所以,肝郁、脾虚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成致病之本,正如《医方考》所言:“泻责之脾,痛责之肝;肝责之实,脾责之虚,脾虚肝实,故令痛泻。”故黄绍刚教授认为IBS的病变主要在肝脾,肝郁脾虚在其病机演变过程中居核心地位。
2 心神失调是难治性IBS-D的根本因素
黄绍刚教授临证时发现难治性IBS-D患者多存在心神不宁的情况。究其原因,黄绍刚教授认为应归之于现代社会工作、生活以及学习压力大,再加上现代人饮食、睡眠等不规律,久之则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而持续的不良情绪又可致心神不宁。心神失于调摄,情绪烦躁不安,加重不寐、抑郁、焦虑等。《黄帝内经》曰:“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心为五脏六腑之首,正是由于心神不宁,导致肝脾功能不能正常发挥,肝疏泄功能失常,脾运化失司,情志不畅,气血亏虚,才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反复发作。若久病不愈,不仅损伤肝脾之气,更影响心神。心藏神,可以主宰人体的精神心理活动,心属火,脾属土,心脾为相互资生的母子关系。《素问·玉机真脏论》提出:“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久之形成恶性循环,疾病缠绵难愈。故元代医家张洁古云:“脾主湿,自病则泄泻多睡,体重昏倦。若肝乘脾为贼邪,心乘脾为虚邪,肺乘脾为实邪,肾乘脾为微邪。凡脾之得病,必先察其肝心二脏。盖肝是脾之鬼,心是脾之母,肝气盛则鬼邪有余,心气亏则生气不足,当用平肝气益心气。若诊其脉,肝心俱和,则脾家自病,察其虚实而治之”。故在临床上若单纯运用疏肝健脾的方药治疗时,效果甚微。
精神心理因素影响胃肠生理的具体病理机制复杂,尚未完全阐述清楚,但医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精神心理等因素主要影响脑——肠轴而导致IBS-D的发病[9]。持续的精神心理刺激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继而引起胃肠激素的异常分泌,最终出现胃肠动力减缓等一系列病理变化[10]。
3 从心肝脾三脏辨治IBS-D
黄绍刚教授提出“肝郁脾虚,心神失调”为IBS-D的病机,指出心肝脾三脏在IBS-D发病和治疗中的重要作用,这与周福生教授的“三位一体”的学术思想[11]相一致。因心肝脾三脏在生理上与血密切相关,因此称为“血三脏”。血三脏与功能性胃肠病关系密切[12]。黄绍刚教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从肝脾辨证体系的构建[13]到文献研究[8,14-16]及临床验证[7,17-20],均显示血三脏理论可作为辨治IBS-D的指导思想。
血三脏理论与现代医学之“脑肠互动紊乱”有共通之处。血三脏理论的提出不仅是中医理论自身创新的需求,更是中医整体观“心身同调”的体现。如情志失调及肝气郁滞与现代医学的应激相吻合[21]:应激可以引发脑肠互动的异常和相关脑肠肽分泌紊乱;肝气疏泄不畅,亦会影响心主神志的作用,肝木横逆乘脾犯胃,脾胃升降失调,又因脾在志为思,忧思多虑伤及脾胃,影响脾主运化的功能,脾失健运,进而产生腹部疼痛、腹泻等IBS-D症状。又如精神注意力过度集中及脑力活动过度等,都会使胃肠功能发生异常,继而导致IBS-D的发生。由此可知,心肝脾三脏共同参与了IBS-D的发生发展,契合现代医学提出的脑肠轴理论。
4 肠激灵治疗IBS-D疗效显著
根据IBS-D患者“肝郁脾虚、心神不宁”的病机特点,黄绍刚教授提出了“疏肝健脾、养心安神”的治疗大法,并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创制肠激灵方。肠激灵方由白芍、白术、陈皮、茯苓、酸枣仁、素馨花、延胡索等组成。方中痛泻要方的主要组成药物白芍、白术、陈皮意在疏肝健脾。白芍性凉,味苦而酸,性微寒,入肝、脾经,有补血养血、平抑肝阳、柔肝止痛之效。延胡索性温,味辛苦,入心、脾、肝、肺,具有行气止痛之功。素馨花性味甘平,归肝经,具有舒肝解郁之效,因其性平,故疏肝而不伤阴。三药合用,白芍柔肝缓急止痛,又能养益肝阴;延胡索行气活血止痛,其性温,白芍能制约其辛燥而不太过,素馨花与白芍相伍增强疏肝之效,相得益彰;白术性温味苦、甘,归脾、胃经,具有健脾益气之效。如《本草求真》言:“白术为脾脏补气第一要药也”。而炒白术能缓和燥性,借麸入中,能增强健脾作用。茯苓甘、淡,性平,归心、脾、肺经,能健脾渗湿,宁心安神。两药相伍,既能健脾以升清止泻,又能渗湿,使水湿有路可行而治腹泻,从不同的路径解决患者腹泻的症状。酸枣仁味甘酸,性平,酸甘化阴养血。“肝藏血,血舍魂”,养肝血则滋养心神。酸枣仁与茯苓相配,更助宁心安神;与延胡索相配,取酸辛之法,与“肝体阴而用阳”相适。酸枣仁之酸补肝阴,延胡索之辛助肝之用。本方有疏肝解郁止痛、健脾止泻、宁心安神之效。
5 验案举隅
患者张某,男,20岁,2016年5月20初诊。患者自述脐周隐痛不适,晨起眼睛干涩,大便中夹杂不消化食物,情绪紧张,胃纳可,咽干,眠差,舌淡红,苔白稍腻,脉弦。曾行电子肠镜检查但未见异常。西医诊断:肠易激综合征。中医诊断:腹痛(肝郁脾虚)。治以疏肝解郁,健脾行气止痛。处方用药:太子参15 g,北黄芪30 g,炒白术15 g,茯苓15 g,白芍20 g,蒸陈皮10 g,广木香10 g(后下),防风10 g,合欢皮15 g,广藿香15 g,炒薏苡仁20 g,六神曲15 g。共处方7剂,每日1剂,水煎,早晚分服。
2016年7月8日二诊。患者自诉服药后脐周隐痛稍有减轻,大便烂,情绪紧张,咽干,眠差,舌淡红,苔微黄稍腻,脉弦。治以调和肝脾。处方用药:黄连10 g,法半夏15 g,蒸枳实15 g,延胡索1 5 g,广藿香15 g,葛根2 0 g,熟党参15 g,防风10 g,云苓15 g,素馨花10 g,蒸陈皮10 g,炙甘草5 g。共处方5剂,每日1剂,水煎,早晚分服。
2016年8月8日三诊。患者自诉服药后症状减轻,脐周隐痛偶发,大便不烂,情绪紧张改善,睡眠良好,咽稍干,舌淡红,苔白稍腻,脉弦。治以疏肝健脾,温肾益气。方用:蒸枳壳15 g,广藿香15 g,熟党参15 g,防风10 g,云苓15 g,素馨花10 g,蒸陈皮10 g,炒白术15 g,北黄芪20 g,盐补骨脂15 g,肉豆蔻10 g。共处方7剂,每日1剂,水煎,早晚分服。
按:本病案患者初诊时情绪紧张,腹部隐痛,大便夹杂未消化食物,失眠,心神不宁,表现为明显的肝郁脾虚症状。肝主疏泄,主藏血;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心主神;不通则痛。故治以疏肝解郁、健脾行气止痛之法,另加合欢皮宁心安神,治疗眠差症状。二诊时,腹部隐痛稍有改善,大便夹杂未消化食物的症状消失,转变为大便烂,情绪仍紧张,睡眠仍差,咽干。因肝郁化热,表现为咽干;木郁乘脾,脾虚则大便烂。故在初诊的基础上,治以调和肝脾,并用素馨花代替合欢皮养血疏肝安神。三诊时,患者诸症好转,治病求本,故治以疏肝解郁及温肾益气之法以巩固疗效。
从本病案的诊治过程可知,肝郁脾虚、心神失调贯穿IBS-D患者病程始终,治疗时应补泻兼施,标本兼治,综合调理,方能取得满意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