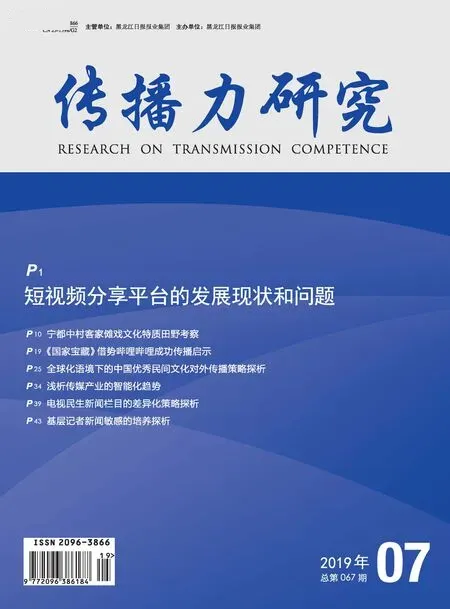融媒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社会效益评价的变革
孙菲 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随着移动互联科技的飞速发展,我国媒体格局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媒体逐渐走出最初转型期的阵痛及广告断崖式下跌的局面,形成了与新兴媒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媒时代新型主流媒体业态。作为国有文化企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型主流媒体,在引领文化产业有序发展与有效实现社会效益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只有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双效合一,才能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并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舆论环境中行稳致远。融媒时代,新媒体在实现主流媒体的社会效益上作用日益显著,这也为新型主流媒体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新要求,评价框架、维度、指标和权重等方面均将发生相应变革。
一、评价体系框架的多元重构
目前,我国主流媒体均已实现了与互联网、手机、社交平台、第三方信息发布平台等新兴媒介的聚合互动,从“报、网、微、端”的媒体融合1.0,不断壮大平台、渠道和规模,形成了多维立体的传播矩阵,“两微一端”的布局似乎刚刚完成,随即便迅速跨入“两微一端一抖”的全新格局。
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会所发布的《媒体抖音元年:2018 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超过1340 家中央、省级及地方级主流媒体入驻抖音APP,累计发布短视频超过15 万条,累计播放次数超过775.6 亿,累计获赞次数超过26.3 亿。(1)以新闻短视频为主流的报道模式,往往紧跟时事热点,做到正能量和暖新闻的即时性、随时性发布,无疑成为新型主流媒体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有效引导舆论、实现其社会效益的重要阵地。因此相应的,对于新闻主流媒体的评价体系框架也应从以往以报纸、广播、电视、网站,扩充至传统媒体、微博、微信、客户端、抖音、第三方信息发布平台等新型主流媒体集群中的各个成员及合作渠道平台。
二、评价维度的“四力”变革
长期以来,对于我国主流媒体的评价标准,经历了由建国后的“政治标准”单一维度过渡到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导向+量化”,再到新世纪后的“政治导向+绩效”双重维度的发展历程。然而,对于当下的融媒时代,此种评价标准难免过于简单、粗放,显然无法适应崭新的传播格局和复杂的国内外舆论环境。
融媒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社会效益的实现,离不开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与公信力四个要素,此四力的首次集中提出来自习近平总书记“2.19”重要讲话,并在其此后多次对媒体的讲话中得以强调。其中,所谓传播力,即主流媒体立足新闻业务水平,以其新闻作品对目标受众及社会形成影响的能力;而引导力,指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形成主流舆论,抑制负效应,并使引导内容内化为受众本体思想意识的能力;影响力为媒体通过各种样态的媒介作品,在社会产生反响、引发关注、形成共鸣,甚至产生动员的力量;公信力则指媒体以新闻报道为主体,获得受众及社会的普遍认可和赞誉的程度。四者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缺一不可,对于主流媒体社会效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在上述四方面均发挥过积极有效的作用,但在当前的传播格局中却呈现出势微的迹象。其中,衡量传统媒体传播力的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广告量等传统指标均出现明显下滑趋势,而此时,被传播赋权的各新媒体平台纷纷崛起,一跃成为受众获取信息、形成舆论的主要渠道,使得传统媒体以往近乎绝对的引导力与影响力也随之发生位移。另外,网络时代对于“即时传播”、“流量为王”理念的推崇,导致有的主流媒体把关不严,一味求快,在虚假信息和反转新闻方面频频中招,公信力也自然随之下滑。
对此,在国内外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冲突中抢占主流舆论场,在多渠道联动的报道模式变革中打造媒介精品,在算法技术普遍应用的背景下强化“把关人”角色,在层出不穷的反转新闻中及时澄清事实真相,新型主流媒体社会效益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只有实现上述四力的共兴共荣,方可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因此,作为融媒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生产力与生命力的重要支撑,对上述四力考核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言而喻,可将其作为主流媒体社会效益评价的四个维度,也就是评价体系中的四个一级指标。
三、评价指标的细化呈现
结合新型主流媒体社会效益的特征,以媒体分类为基础,上述四个一级指标可细化为二级指标11 个,三级指标32 个。其中,根据引导力包含舆论引导、创新能力、队伍建设等二级指标;传播力包括媒体覆盖率、内容生产与服务、受众规模;影响力包括认知建构、媒体关注和社会公益;公信力则包括媒介管理和受众反馈2项指标。
对照相应的二级指标,具体落实至操作层面的三级指标则更为丰富,其设置可结合不同主流媒体的实际情况和运营特点量身制定。例如,传播力中媒体覆盖率的评价,除包括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等传统指标之外,还应将粉丝量、下载量、公众号总量、收藏量等“两微一端一抖”和第三方平台的覆盖指标纳入体系;对于内容生产与服务的评价,则可具化为内容生产总数、原创内容总数、原创率、播放量、阅读量等三级指标。
而对于影响力中受众认知建构的二级指标,可细分为总点赞量、总评论量、总转发量、总分享量,同时运用媒体及内容检索、内容转载频次等指标衡量影响力中媒体关注度的二级指标,并可适当引入“人民网媒体影响力排行”、“百家号媒体影响力榜单”等由权威平台、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公布的排名指标。
四、指标权重的此消彼长
互联网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媒体格局的变化,不仅仅是新媒体的崛起及其与传统媒体的融合,新闻生产方式、媒体社会功能和运营管理机制等方面均发生了变革,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权重也必然随之相应改变。曾作为媒体评价重要指标的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的权重已向粉丝量、下载量、播放量等不断偏移,曾较难进行量化统计的受众反馈方面,也因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变得简便易行,在媒体评价体系中逐步扩大权重比例,这种此消彼长在下述其他方面也均有体现。
融媒时代,我国主流媒体战略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守本求变”,即在巩固主流舆论引导权的基础上,抢占互联网媒体舆论场,为国家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然而目前,主流媒体作为舆论策源地的主体地位正逐渐弱化,众多新闻事件往往发端于移动互联平台,经过裂变式传播迅速发酵为公共议题,其中一些甚至演变成现象级热议话题,并伴随事件要素与公共舆论的多次反转。对此,主流媒体议程设置能力亟需强化,对其评价也应涉及议程设置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效果,既要考察媒体议程设置报道是否及时,所设置框架是否符合公众认知角度,也要考察其能否成功转化为公共议程及其他媒体的议程,以及有否有效实现舆论引导功能。
同时,对于主流媒体内容创新的评价也应更为侧重。目前,以“流量为王”的信息发布平台所提供海量内容已经导致数字化生存的一代陷入深深的信息焦虑。而对于主流媒体而言,用户流量虽是当下重要的评价指标,但低级化、失序化的流量却是应该抵制的。新型主流媒体应构建自身“主流算法”,有效实现主流价值观、正能量与用户个性需求的匹配对接,以优质原创内容彰显属于主流媒体的“价值阅读”。
另外,对于主流媒体把关角色的评价同样亟需强化。海量信息充斥网络,主流媒体的把关人角色更为重要,尤其是对于虚假信息的过滤,对于网络流言和谣言的澄清,已经成为当前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的主要功能之一。对此,转发、传播虚假新闻等各种损害媒体公信力的行为均应纳入评价体系。主流媒体可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新闻数据库审查机制,从内容生产者的原始文件到编辑修改、主编审稿、用户评论皆可进行追溯,从而实现对信源把关、版权保护,对虚假新闻、标题党、谣言进行控制,并对严重的违规事件追责。一旦出现上述问题,将实行一票否决制,从而强化主流媒体的把关角色。
相应的,对于把关人角色缺位而引发媒体社会效益负效应的行为也应有所侧重。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网络信息传播时代,“流量为王”大行其道。众多传播主体在利益驱使下运用各种方式吸引受众关注,其中即包括“标题党”。这种传媒行业内“专业”的逐利现象的产生,源于那些罔顾新闻职业理念的内容生产者,运用自身谙熟的新闻价值理论,专门针对受众的选择性需求,以吸睛为目的“订制”标题。这些标题或故弄玄虚,表意模糊,刻意渲染后果,或断章取义,文不对题,制造情绪恐慌,充斥着各大信息发布平台,其中部分也来自于“主流制造”。这些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编辑业务中需绝对避免的问题,如今在网络空间司空见惯。用“标题党”吸引受众阅读,基于算法推荐扩大其传播范围,充斥网络空间,极易造成信息污染,干扰受众的信息选择,此类行为应在社会效益的评价体系给予权重方面的加强。
五、评价方法可操作性的强化
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兼具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倘若评价指标的可获得性较差,那么体系的重构则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将无法真正客观、准确地对主流媒体进行评价。运用大数据信息技术手段对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分析等相关处理,进而实施评估,同时适当引入具有行业权威的社会评价结果,将使评价方法更为便捷。
对于主流媒体社会效益评价体系的构建,应符合新闻传播规律,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契合,并实现对我国新闻行业发展的有效引导,助推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
注释:
(1)《2018 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发布》,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27日,http://www.cssn.cn/xwcbx/xwcbx_rdjj/201903/t20190327_48544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