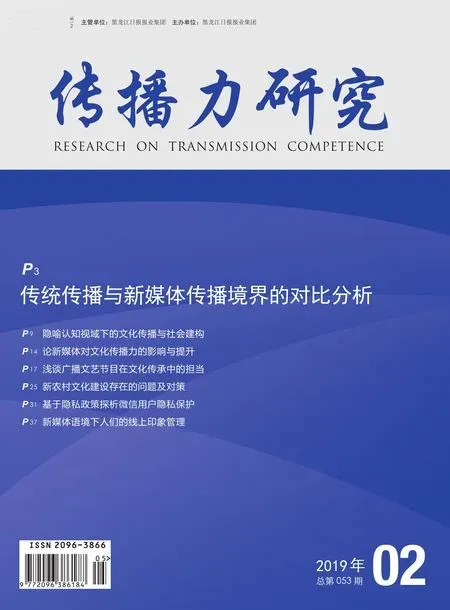中国电影的诗意复归
——以《八月》为例
宋敏 中国传媒大学
正如伊·皮洛所说,“艺术不一定都需要离奇曲折的情节,也不一定都要塑造超凡的‘英雄’。实际上电影真正的、独特的领域是平凡的事物,电影教会我们品味日常平俗事物的魅力。”①诗意潜藏在生活之中,“电影艺术可以借助散落在时光中的任何事实,可以运用生活中的一切。”②生活中不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之美的眼睛。导演张大磊借助摄影机眼睛,缅怀了一个十二岁少年眼中九十年代国有体制改革前,孤独而又无所事事的诗意夏天。在这个夏天之前,人们自然而然地生活着,随着夏天的结束,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境。
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但不等同于现实,诗意的生成需要导演精确的编码,导演张大磊在影片的画面造型、镜头形式、剪辑都做了精心的处理以营造诗意的生活。
影片在画面造型上选用了大量的景深镜头,主要人物往往活动在远景处,将前景空出,这样的人物调度拉开了剧中人物与观众的距离,形成了视觉观看上的远望和凝视。缓慢疏离的镜头语言中人物置于环境中,人物的比例变小,人物的动作不再明显,呈现更多的是画面中的氛围和情绪,给观众留下更多想象的余地。在拍摄姥姥家的场景时,多采用景深镜头,一家人相聚的画面处于远景处,前景留白,或是与远景处的人物隔着一扇玻璃窗,观众此时就会很容易带入到上下文产生的情绪氛围中。
在突破技术的限制后,黑白也是一种色彩,具有色彩的表意功能。黑白在电影的文法中代表着追忆,代表着一段旧时光,代表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如同一张封存已久的老照片。如《艺术家》中致敬的20世纪三十年代的黑白默片时代。《八月》以黑白展示小雷童年时光,也是导演“我”记忆中的旧时光。并且这段时光是理想破碎的前夜,是最后的梦幻时光,导演在影片的结尾处将录像带中的影像变为彩色,展示向生活妥协的父亲的形象,暗示了梦醒了,回到现实中。
影片在镜头形式上大量选用缓慢的、横向或纵向的摇移,镜头引导观看视线跟随人物缓缓移动,在运动中呈现出平静、舒缓的镜头语言,镜头仿佛带有情感地从被拍摄人物中一一拂过,观众跟随摄影机经历同样的感受。影片中摄影机总是跟着小主人公小雷行动,跟随他的行动和视线去观察周围,影片在客观视角和主观视角中切换,观众以全知的视角观看,也从小雷的视角去看。视角认同带来心理认同,使观众进一步体会小雷的心理感受。
影片在剪辑上不以保持连贯性和强化故事戏剧性为逻辑,打破了电影中镜头构成场景、场景构成段落、段落构成故事的语法规则,而是以一种看似随意实则精心设计的规则来剪辑,形成影片剪辑上的诗意。影片一开场出现的镜头依次为:楼房——商贩蹬着山轮车离开——躲在角落里惬意地观察四周的小花猫——商贩蹬着山轮车折返——楼房。五个镜头前后并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后一个镜头不是经典剪辑意义上对前一个镜头的承接,也不是蒙太奇中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单个镜头都是完整的,镜头间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又构成了一个诗意的回环。影片的剪辑方式是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审美心理的,在诗词文化浸染下的国人,可以理解“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同样可以理解通过意象堆叠而形成的影像时空。
成功的景物镜头的设置可以引发特定的回忆和诗意的联想,影片中单个的景物镜头散落在叙事流程中,导演带有主观性的景物选择同样能够唤起观众的共情。塔可夫斯基坚信“如果作者本人为他所选择的自然环境触动,如果这个环境唤起他的回忆,激发他的联想,哪怕这些感受再主观,也会让观众感到某种兴奋。很多片段正是充溢着作者这样的情绪,例如白桦林、医疗站的桦树枝叶掩体、最后一场梦境的自然背景和淹水的死寂树林。”③
国有体制改革带来的下岗潮是影片中的一个重要戏剧冲突,但是影片通过剪辑将戏剧冲突拆解,反而带来更加强烈的情感共鸣。小雷父亲所在的电影厂股份制改革,人到中年的父亲面对必须重新择业、离家的困境,“低下高贵的头颅”臣服于“韩胖子”去当厂工。这条线索第一次出现是通过电视新闻画面,第二次出现于外公与父亲的对话中,父亲与母亲几次关于找韩胖子的争吵延续了这条线索,然后接着就是父亲匆忙离去坐上离家的汽车。冲突被拆解到电影的不同的时间点中,甚至不足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力。父亲匆匆坐上离家的汽车,甚至没有机会和小雷告别,小雷不解地站在原地目送父亲离去,车上播放着《你在他乡还好吗》,汽车音响播放的音乐声转变为现场演唱的声音,导演利用相似的声音转场画面切到电影厂职工聚会的场景,电影厂的工人们齐聚一堂推杯换盏,每个人都很开心。墙壁上的条幅显示的文字示意这是运动会成功举办的庆祝会。在前文中父亲不经意的一句话曾透露出电影厂改制的消息是在运动会后宣布的,导演没有直接去拍电影场的工人们听到消息后的错愕和伤痛,也没有将这段影像放在电影的中部,而是在父亲的离家的回忆中展示了大家得知消息前最后的欢乐时光。导演通过含蓄的镜头语言暗示了这一条情节线,并且在剪辑上形成了一种先抑后扬、延宕、反差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比戏剧化地展现冲突具有更多重的感染力。
影片中“姥姥”和“大舅妈”和解的处理方式以及小雷思念父亲的表现方式,都体现了导演含蓄蕴藉的叙事方式。通过“姥爷”与“大舅”的交谈我们得知“姥姥”与“大舅妈”之间的隔阂,“大舅妈”第一次出场便是躲在厨房洗碗,直到大舅过来催促,“大舅妈”和“毛儿”才去到客厅。“太老”去世后一家人在院中拍合影,“姥姥”躲在房间里,“姥姥”因为“太老”的缺席而伤心,“大舅妈”回到屋内安慰“姥姥”,“妈,过去是我不对。”“妈,要不你哭吧,憋得难受。”从头至尾,影片没有过多地去赘述婆媳之间的矛盾,而是通过两个日常生活的片段去展示二人和解的过程。在合影一场戏中,“大舅”在按下相机快门时,喊女儿“毛儿”给自己空出位置,小雷听到后环视周围,意识到父亲的缺席,他伸出胳膊做出搂抱的动作,为父亲预留这一细节设置了位置,含蓄地传达出小雷对父亲的思念和一种纯真。
现实生活是残酷的,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影片中的父辈经历了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童年时期,在而立之年遭遇重大的体制改革被迫投入到市场经济的竞争浪潮中。在导演眼中现实是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保留着温暖,影片中回忆了那个时代,亲人、朋友、邻里、工友间互助、理解的关系。影片中的“韩胖子”是一个耀武扬威、缺乏修养的人,仿佛是影片中的一个负面形象。在“三哥”从监狱中出来回到家中时,父亲遗留的包裹中是父亲舍不得穿的剧组棉衣、舍不得吃的剧组夜宵,还有一封“韩胖子”捎回来的信,信中夹着钱,钱是“韩胖子”给“三哥”用来料理父亲的丧事的。“韩胖子”信中说到一些对“三哥”鼓励的话,并且安排“三哥”到剧组工作。这一场景在我看来是极其温情的一幕,体现出周遭对“三儿”的理解与关怀,大家并没有因为“三儿”入狱而对他产生偏见。记忆中的九十年代是充满坎坷与变故的,同样也是温暖的。
结论
《八月》由一段段生活日常组成,镜头与镜头间没有因果的承接关系,现实、梦境、空镜不加过渡地剪辑在一起。习惯于经典叙事的观众会认为影片不知所云,也无法提炼出影片的主旨。想要理解影片,就需要改变固有的观影思维,观众不需要执着于影片的叙事逻辑,而是静观生活的流程,任其在银幕上渐次展开,影片结束时每一个镜头的含义和影片想要表达的情绪、情感和意义便生成了。
注释:
① [匈]伊·皮洛.世俗神话—日常生活领域的亲电影性[J].世界电影,1987(1)P7.
②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张晓东译.雕刻时光[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8版,第65页.
③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张晓东译.雕刻时光[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8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