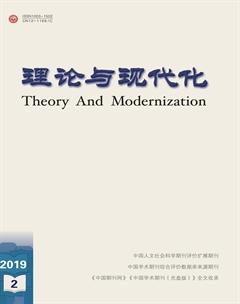池田大作生命尊严观及其对日中友好的思考
纪亚光 杨卫芳
摘 要:尊重他者的生命尊严立场是池田大作从不停歇地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的思想源泉。基于生命尊严立场,池田大作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人本主义解读,成为其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事业的坚实出发点;基于生命尊严立场,池田大作找到了从“国家”到“民间”继而通过文化、教育交流构筑日中民众彼此信赖的共同意识,为日中世代友好奠定坚实基础;同样基于生命尊严立场,池田大作在致力于生生不息的日中世代友好事业时,将日中青年交流放在首要的位置,努力通過多种多样的日中青年交流,培育日中青年间深厚的友情,以此将日中友好事业代代相传,使日中世代友好大业成为现实。
关键词: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日中友好
中图分类号:B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2-0067-07
众所周知,日中世代友好是池田大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池田大作面对重重阻力甚至生命危险,自20世纪60年代起,五十余年如一日大声疾呼、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从未有丝毫的动摇与停歇。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池田大作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而矢志于此呢?笔者认为,尊重他者的生命尊严立场是池田大作从不停歇地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的思想源泉。具体而言,以人为本的中国史观是池田大作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的思想底蕴,以民为本的友好交流观是池田大作生命尊严立场在和平友好事业中的具体表现,以青年为本构筑世代友好“金桥”是池田大作生命尊严立场在和平友好事业中的理想愿景。
一、以人为本的中国史观
以人为本的中国史观,是池田大作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的思想底蕴。
池田大作非常推崇中国的历史文化,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蕴含着智慧与和平思想。他说:“纵观中国历史,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尚文的国家……除了极其例外的时期,‘尚文的风气,一直是推动中国历史的巨大力量。” [1]池田大作进而认为,“对文明道德和理想的关注”,是中华民族得以控制“蛮性的冲动”和“破坏的本能”的主要力量,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2]。在池田大作看来,对人的尊重,是中国历史文化蕴含文明道德和理想的首要因素。他说:“我曾对中国产生这种自制力的背景加以探讨,发现这种看法、想法之中,人总是占据着中心位置。”[1]39-40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他多次呼吁人们注意中国3000年历史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他指出,中国的人本主义包含着自立、自律、自强的含义。他说:“‘自,虽然是‘自己、‘自身等词语的根干,却与在欧美有根深蒂固的‘个(individual)差异很大。‘个意味着作为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的孤立的个人,与之相对,‘自这一文字,决不限定于一个人,带有自在的深度和广度。” [1]100池田大作同时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所蕴含的对文明道德和理想的关注,还表现在中国是对异民族宽容开放的社会。他借用金庸的观点指出:“在唐代非汉族而成为宰相的最少有23人。不是计较出身,从中国来看只要有‘文明的话便可以”。进而他呼吁:“今后向着世界一体化的时代,应向有史以来以一个文明圈发展过来的中国,好好学习它的智慧。”[1]182
作为世界和平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家,池田大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推许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他在系统考察世界近代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认为:“从和平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时,应当注意的是,殖民主义可以说是近代国家之间战争的元凶,其背后事实上存在着缺少‘人这一基轴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说,正是那种把近代西欧当作唯一的标准,从而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文明和‘未开化两种类型的傲慢的思考方式,才产生了错误的选民意识,从背后支撑了殖民主义。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欧洲的近代文明虽然留下了很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但就其总的倾向来说,它并没有对人的野蛮的狂热起到自制作用和抑制作用,反而起到了掩饰这种野蛮的狂热的作用。”[2]131
正是从世界和平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出发,池田大作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现实价值。他同意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对中国的评价,认为只有具备不同文明的眼光才能发现中国文明优美的本质,这就是人或国家控制其自身本能和兽性的文明力量——亦即自制力或意志力。他指出:“如果不是不断地大量积蓄这种力量,那就不可能想象会有导致抑制乃至废除军备的和平的道路。”[2]130
基于构建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池田大作深刻认识、反省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不仅深刻指出日本近代对华侵略是恩将仇报,“永无彻底赎罪赔偿之日”;而且对二战后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行为,明确指出是“一个多么没有‘心的国家啊!”[3]在此基础上,池田大作特别指出:在与中国这样曾经被日本侵略过、尝到过辛酸的国家的人民接触的时候,就必须正确认识那段历史。他说:首先要从正确认识历史、从了解中国人民受到的痛苦和苦难开始。只有这样,作为日本人才能唤起反省的意识,自然地也就能说出谢罪的话了。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池田大作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人民的中国,“新中国一贯坚持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在内心里是以新的眼光在看待这一事实。因为在一切令人预感到正在酝酿着开辟历史的新的民众形象。”[2]72在不同场合,池田大作多次阐明了他的如上观点。池田大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观也极为推许,他认为:“在革命后的中国,在各个领域里都是把人民大众当作基本的出发点;已故的毛泽东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感到正是站在这一历史观的基础上,采取了可以称之为为民众服务的‘民众史观的结构。在这一点上,令人感到它和以‘帝王史观——这种史观把尧舜的神话时代当作最高典范——为主流的儒家的传统的历史观划了一条明确的界限。” [2]135-136在与金庸对话时,他就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原因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在建立新中国之前的漫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能取得民众的信赖是获得胜利的主因之一,就是用严以律己的纪律来校正党风。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以及有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人一种开创新的时代,充满爱民之心的感觉。我也是对此深受感动的一个。”[4]
总之,池田大作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蕴含着充满智慧与和平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人民的中国,中国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现实追求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样的中国观成为池田大作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坚实基础。
二、以民为本的友好交流观
池田大作的生命尊严思想,注重将人视为生命的存在,而不仅是社会的存在。从人作为生命的存在视角出发,池田大作多次强调人要从“小我”转变成“大我”,以世界为出发点,成为“世界的公民”,成为“国际人”。他指出:生命具有超越民族与国界性,只有将人视为生命的存在,才能抛开国界与民族,站在同样身为人类的立场同他人用心交流。
池田大作通过亲身实践与读书学习,以生命尊严思想为基础,反思近代以来的世界战争史,提出了应该以“人类主权”代替“国家主权”的独特的世界和平思想。他认为,近代战争的发生,几乎全部是由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益诉求与权力争夺造成的,人们“热爱自己生长的土地和社会,使其进一步发展,……这本身是一种美德,是作为一个人的至关重要问题。没有这样的热情和魄力,恐怕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社会发展”。但是,“对自己生存的社会的自然的爱,一旦被利用来卷入国家对国家的对立中,就会带上邪恶的色彩”[5]。
怎样去克服这样的国家主义逻辑,使人类主权逻辑提升到思想的制高点,怎样更好地去构筑一个防止战争的国际和平环境,成为池田大作的毕生研究课题[6]。他认为,在当今世界,对于一个国民和民族来说,即使是有利害关系的对立或观点的不同,也能通过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其基础就是被称为民主主义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池田大作主张:大家作为同样的人,应该从生命的尊严和生命的平等的立场出发,来采取变革,构筑这样的价值观是非常必要的[6]386。关于这一点,池田大作提出“地球民族主义”的概念。他说:“正是因为有意识形态的不同和肤色的不同,肯定就有利害关系的对立。但是,不论这一切是怎样的不同和对立,同样都是人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如果站在这个共同意识之外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开辟出真正的和平和安全保障的道路来。这就是我所说的‘地球民族主义。”[6]386
池田大作注意到,只有通过民间的交流,在民众中确立包括全人类在内的命运共同體意识,以此为目标,才是使世界从对立、对抗转变为和平、和谐的大前提。不仅如此,池田大作还找到了从“国家”到“民间”继而通过文化、教育交流更进一步推广到“人”“心”这样一种开展外交的方向。
池田大作希望通过构筑民间层面的交流,使普通人民大众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来推动和平。对此,他进行了如下阐述:“为了和平,政治家们之间的对话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同时要看到草根文化、教育交流在当今时代也是很好的安全保障。如果没有了人民大众的团结合作,想要取得和平是多么地不容易。对此,历史经常提示我们。”[7]进而,池田大作指出:我们可以期待通过人民大众之间强大的信赖渠道,来防止国家间发生可预见的不幸事态的[6]389。
从生命尊严的立场出发,池田大作在思考如何实现日中友好、世界和平这一问题时,特别注重深入开展民间文化与教育交流。他指出:“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信赖、互相贯彻信义、身为人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并以此为基础,一起面对未来。政治和经济虽然重要,但能在更深层的民众意志受到重视之下而进行交流,才能加深真正的相互理解。因此,我一直以来都重视文化交流和教育交流,就是希望藉文化来弹奏心灵的共鸣乐章,以教育来耕耘和平与友谊的心灵大地。”[8]
在谈到文化和文化交流的时候,池田大作作了如下说明:“文化的精髓原本无非是普遍的,充满蓬勃生气的人类生命。因此,人类欢乐的高调恰似在人们胸中拨动的琴弦奏出的共鸣音一样,文化作为人类的固有行为超越了所有的隔阂,净化着每个人的心灵。正是这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才是文化交流的出发点。”[6]389-390在此基础上,池田大作更进一步指出,所谓文化交流,其实表现的就是要缩短“心灵的距离”,以人与人之间的整合为出发点[9]。
池田大作基于同样的思考,也非常重视教育交流。他强调:“我坚信应该将世界的永久和平、民族与民族间的合作、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创造和谐的富有生气的社会作为‘教育的基础。教育就是使社会向新的高度飞跃、充满活力的甘洌的人类文化之泉。” [6]318这正是池田大作的信念。池田大作相信,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术人才,能够超越国家主义的束缚,也无意识形态束缚,有的只是对人类未来共同的责任和对真理不断追求的洞察力的挖掘。因此池田大作主张:“学问就是普遍的世界,可以超越国界,民族、语言来进行交流。教育应该担负起培养立足于全球视野的世界公民的职责。”[6]318池田大作就是力图通过“教育”的交流,来超越国家的局限,从而形成人类的共同意识。
池田大作深信,日中要永远和平友好,必须要有民众间的相互理解。他强调,中日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信赖、互相贯彻信义、身为人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并以此为基础,一起面对未来。政治和经济虽然重要,但能在更深层的民众意志受到重视之下而进行交流,才能加深真正的相互理解。”[8]他认为,民众间的友好交流是渐进式的,超越了时代,是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民间的文化和教育的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池田大作一直以来都重视日中文化交流和教育交流,就是“希望藉文化来弹奏心灵的共鸣乐章,以教育来耕耘和平与友谊的心灵大地。”[8]
三、以青年为本的世代友好观
生命生生不息地悦动是生命尊严的理想愿景。作为个体而言,生命的终止是不能避免的自然现象,但作为整体的生命而言,生生不息则是可以实现的目标。池田大作基于生命尊严的立场,将日中友好事业的生生不息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为此,他明确提出“金桥”这一形象的词汇来描述日中世代友好事业。1976年,在创价大学“金桥之碑”揭幕式上,池田大作说明了“金桥”的含义。他说:“这里‘金并不指的奢华的意思”,“金就是‘生,是指生活下去、充满光辉的生命之意,是所谓和平的意思”[10]。从生生不息的和平友好事业观出发,池田大作高度重视青年的价值与作用。他指出:“中国有句谚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百年的规模来思考的话,焦点放在肩负两国未来的青年身上,方能建构万代友好的基础。”[11]
为了使日中友好“金桥”更加坚固,将日中世代友好和世界永久和平薪火代代相传,池田大作高度重视日中青年交流,希望以此促进日中青年携手,“共同构筑起符合新时代的互惠关系与共和世界”[12]。
在池田大作的指导下,创价学会青年部承担着与中国青年交流的重任。创价学会青年部的交流对象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双方开始接触于1979年,1985年签订了十年交流协议书,开展了定期团组互访、共同培养语言研修生等交流与合作活动。由于成效显著,1994年、2004年双方分别再次签订十年交流协议书。进入21世纪,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出现无视日本侵华史的教科书事件,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热”的低谷。在这种背景下,池田大作多次派遣创价学会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借此教育日本青年正视日本侵华史,希望他们以史为鉴,更好地面向未来,推进日中关系走出低谷。2006年7月,创价学会青年代表团200名团员访问中国,先后访问了上海、北京、天津。这是创价学会青年部历史上派遣人数最多的访华团。在来访前,池田大作对代表团说:“日本青年要以诚实的心,明朗活泼地与中国青年进行交流,接过中日友好的接力棒,两国青年携手合作,一定可以巩固中日友好的‘金桥。”[13]此次访华期间,代表团广泛接触中国青年,先后访问了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并与学校的师生进行交流。在与北京大学学生举行的中日友好学生座谈会上,代表团成员表示,将秉承池田大作先生的精神,以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铭记历史,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加强与中国青年的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以青年之手开创中日友好的美好未来。
池田大作创办的创价大学也通过教育交流的途径担当起推进日中青年交流的重任。
早在1975年,池田大作就履行了与周恩来的约定,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首次派出的6名公费留学生迎进了创价大学。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相当富于勇气的决策。不仅如此,池田大作还担任了这些留学生的保证人。1979年,创价大学与北京大学签署交流协定,这在日本是第一次。至今为止,创价大学已与中国超过30所大学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先后接收了来自中国各高校的一百六十余名教师作为交换教员到创价大学进行交流,并且将六百余名学生派遣到中国各大学进行交流学习。2006年3月,为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创价大学在北京大学设立了办事处,并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了以教育交流为中心的友好交流活动。与此同时,创价大学设立“中日友好学术交流研究资助计划”,对中国的各大学及研究机构进行的“以加深中日两国的相互了解和推进两国友好关系为目的进行的研究,特别是为和平、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研究项目”给予资助并接待研究者赴该校访问,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与中国各高校开展学术研究的资助、交流机制,标志着创价大学与中国的教育交流进入到制度化的新阶段。
为培养创价大学学生对中文与中国文化的兴趣,增进他们对中国的理解,1974年10月,在池田大作的倡议下,创价大学中国研究会主办了第一次中文辩论大会。辩论大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泛,逐渐以日本三大中文辩论大会形式固定下来。登台的辩手以从日本全国选出的学生为主,還包括社会人士、家庭妇女、中小学生等,其水平逐年提高。从第20次大会开始,改名为“创立者杯”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加强日中友好的意思。在那些受奖的人员中,后来涌现出中文翻译、中文教师、日语教师、驻中国的商社职员等许多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杰出人才。此外,中国研究会还以学生为主体成立“创价大学学生访华团”,自1978年8月起定期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其中,第4次以“周樱”访华团为名,在北京受到了邓颖超的会见。创价大学各俱乐部之间也开展了一系列对华友好交流活动。20世纪90年代,丝绸之路研究会、考古学研究会、书法部、美术部、吉他部、日本舞蹈部、木偶剧部等,与中国的大学生和青年进行了深入交流。
创价大学不仅重视与中国各高校开展教育交流活动,而且特别注重营造日中友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创价大学中,伫立着闻名遐迩的“周樱”“周夫妇樱”,自1979年以来,每年樱花盛开的季节,都会举行由学生主办的“周樱观赏会”,至今已举行了30届,在日本和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校园中还随处可见体现日中友好的纪念碑。如《日中友好》纪念碑,是创价大学学生组织中国研究会为纪念《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和池田大作发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35周年,而于2003年树立;校园内最大的学生宿舍“泷山寮”门牌,由复旦大学前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题写;校园内最美丽的“文学之池”上的“文学之桥”,由敦煌研究所著名学者常书鸿题写等。
可以说,在池田大作的指导下,创价大学已成为日中友好交流的重镇。正如创价大学校长山本英夫教授所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也要坚守创办人池田大作先生‘中日友好是世界和平的关键这一信念,为了中国和日本友好的未来,全心致力于发展两国的交流活动。”
除了创价大学,创价教育系统中的小学、中学与中国的交流也频繁开展。如创价小学与邓颖超曾任教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定期进行交流,创价学园与上海的中学之间经常举行足球比赛,通过中国希望工程在云南省建立了希望小学等。
如上交流对于培养日中青少年和平友好的信念、增进彼此的友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调查,在创价大学、创价学园中,77%的学生对中国抱有好感,关于今后的日中关系问题,70%以上的人认为应该朝着好的方向努力。这与日本社会中存在着的隐瞒歪曲历史、否定侵略行为的思潮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这些友好交流活动,中国前驻日大使陈健作了下述评价:“池田先生曾经几度率领大规模代表团访问中国,在两国之间架筑一道友好的‘金桥,并且在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创价大学先于日本的任何一所大学,接受了新中国第一期留学生,在中日友好人才的培养上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发展事实切实地告诉我们,只有民间的教育、文化的交流才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才是原动力。现在,创价学会的各位正在教给我们进行重大交流的方法。”[14]
总之,生命尊严思想作为池田大作思想的核心,在池田大作思想与实践的各个方面都有具体的表现,其中包括池田大作日中世代友好思想与实践。正是基于生命尊严立场,池田大作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人本主义解读,成为其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事业的坚实出发点;基于生命尊严立场,池田大作找到了从“国家”到“民间”继而通过文化、教育交流超越国家的局限,形成日中民众彼此信赖的共同意识,进而实现日中世代友好;同样基于生命尊严立场,池田大作在致力于生生不息的日中世代友好事业时,将日中青年交流放在首要的位置,努力通过多种多样的日中青年交流,培育日中青年间深厚的友情,以此将日中友好事业代代相传,使日中世代友好大业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日〕池田大作.池田大作讲演·随笔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34-35.
[2]]〔日〕池田大作.池田大作集[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131.
[3]〔日〕池田大作.青春对话Ⅱ[M].东京:圣教新闻社,2000.243.
[4] 日中恢复邦交秘话——池田大作与日中友好[M].卞立强,编,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78.
[5]〔英〕A.J.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與池田大作对话录[M].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225-226.
[6] 创价学会指导集编辑委员会.创价学会指导集[M].东京:圣教新闻社,1976.482.
[7]〔日〕池田大作.向着希望的明天[M].东京:圣教新闻社,2000.477.
[8] 池田国际会长贺词[N].黎明圣报,2004-06-21.
[9] 创价学会学生和平委员会.向着新“人类主义”[M].东京:第三文明社,1991.115.
[10] 王永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60.
[11]〔日〕池田大作.寻求21世纪世界与日本的“和平世纪”之道(三)[N].圣教新闻,2001-12-30.
[12] 池田大作先生对《金桥》的贺词[J].金桥,2011,(1):4.
[13] 日本创价学会派最大规模青年代表团访华[N].中国青年报,2006-08-07.
[14]〔日〕SGI画报(国际创价学会画报)[J].1999,(10).